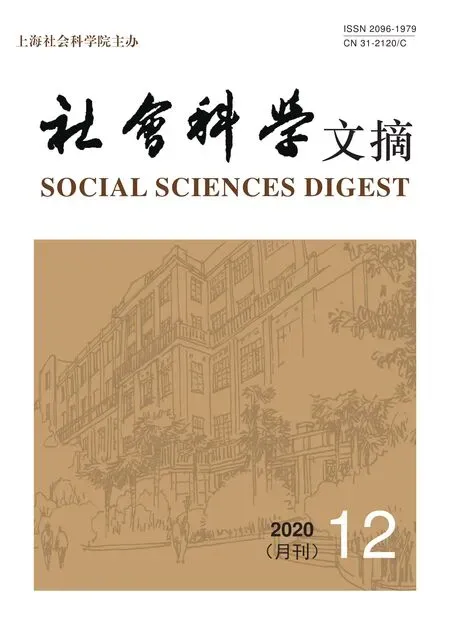康德如何看待恩典对克服“根本恶”的作用
——与韦政希博士商榷
文/舒远招
一般认为,作为强调理性和自由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在人重建原初向善禀赋(即克服根本恶)的问题上,强调的是人自己的力量和作为,而非外在神力的援助,仅当人自己作出全部努力,因而配得上神的协助之后,才可以希望恩典降临。康德在《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以下简称《宗教》)中虽未否定恩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将之虚化并置于次要地位。韦政希博士不同意这种理解,他在《康德宗教哲学中道德自律与恩典的一致性》一文中提出了四个观点:其一,不能将康德的恩典概念仅当作一个实践理性的悬设使之概念化,而要看到恩典对克服根本恶的实在作用;其二,道德自律只能促成改良,人心革命只能指靠恩典;其三,恩典与道德自律互为前提,恩典是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道德自律是恩典的实践论前提;其四,康德对宗教二律背反的解决体现了恩典与道德自律、启示宗教与理性宗教的一致性。这就提出了康德的恩典概念究竟是实是虚,恩典是否促成人心革命,恩典与道德自律是否互为前提,以及康德是否消除了恩典与道德自律的矛盾等问题。
康德的恩典概念究竟是实是虚?
由于康德首先强调人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努力改恶向善,然后才有资格配享神的可能的助力,人们通常会把恩典理解为人自己付出努力之后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假定。韦政希博士反对这种理解,认为这会把康德的恩典概念理解为一个“虚概念”,即一个没有实在效力的假定。他主张把它理解为一个“实概念”,即一种有助于克服根本恶的实在神力。
康德在假定超自然协助为必要的情况下,认为人必须“假设”这种援助,这表明他并不一概拒绝恩典,而是视之为一种必要的假设。但对康德而言,人要接受神的援助,必须事先做到使自己配得上接受它,即首先做到“自力更新”,然后才有资格接受恩典。人的“自力更新”是“实的”。人通过自身力量而实现心灵革命并重建原初向善禀赋,这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因为“应该”蕴含了“能够”。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为,才能被评判为在道德上是善的;倘如是外在神力使人心重新变得完善,那就不是人自己的功德,他也就不会是道德上的善人了。
对康德而言,哪怕他说“必须假设”神的援助,这种援助始终还是“虚的”。这不仅因为人只有付出自己的努力之后才能希望接受这种援助,而且因为这种援助对人而言是“无法探究的”,是一种“超自然的”神力。人完全无需知道这种援助存在于何处,而且难以避免的是,当它的发生方式在某个时刻得到启示时,其他人却在其他时刻对它形成了不同的概念,并且都自以为真诚。但无论如何,“知道上帝为他永福在做或做过什么,这不是根本的,因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相反,“为了配得上这种援助,每个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这是根本的,因而每个人都是必要的”。通过这一鲜明对比,康德把恩典置于次要地位,否定了它对于人的得救具有根本性意义。“自力更新”为主,神力援助为辅,是他在重建原初向善禀赋、克服根本恶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康德说,宗教学著作四个总附释(1.论恩典作用;2.论奇迹;3.论奥秘;4.论邀恩手段)都属于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补遗”;它们不在纯粹理性的界限内,但与之接壤。理性意识到了在满足其道德需要方面的无能,于是把自己扩展到据说能弥补那种缺陷的超越的理念,但并不就把它们当作扩展了的财产占为己有。理性并不否认这些理念之对象的可能性或现实性,但它不能把它们纳入自己思维和行动的准则。康德很谦逊地对待神恩所涉及的各种超验理念,他仅仅在“反思的信仰”名义下给予承认。他还指出,一旦我们把这些道德上的超验理念引入宗教,就会导致不幸的后果:1.被认为的内部经验(恩典作用)的结果是狂热;2.所谓外部经验(奇迹)的作用是迷信;3.在超自然事物(奥秘)方面的所谓知性顿悟,其结果是顿悟说,即术士们的幻觉;4.对超自然事物施加影响的大胆试验(邀恩手段)的结果则是魔术。这些做法都超越了纯粹理性的界限,而且属于“教条的”而非“反思的”信仰。
康德特别就恩典作用指出:如果理性坚守其界限,就不会将恩典作用纳入其准则,正如它不会将其他超自然事物纳入其准则一样。他还认为,在理论上说明这些恩典作用的根据何在,这是不可能的;而在实践上使用恩典理念,其前提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要使用恩典理念,就需要预设一个规则,告诉我们为了达到某种东西,就必须自己去作出某种善;而期待恩典作用却恰好意味着相反的东西,这就是说,道德上的善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另外一个存在者的行为。”所以,康德仅仅在“反思的信仰”中承认恩典作用是不可理解的东西,但反对把恩典作用纳入理性的准则,不论是为了其理论的还是实践的运用。
恩典与道德自律是否分别促成人心革命和改良?
在从“实”的方面理解康德的恩典概念时,韦政希博士把恩典的作用与人的心灵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在康德那里,道德自律仅仅促成人的逐渐改良,而心灵革命仅仅是恩典的作用。
康德确实既从量又从质,既从外在行动的合法性又从内心动机的道德性来谈改恶向善,因而区分了仅有外在行动合法性的逐渐改良和内心思维方式的彻底革命。人的行动往往只能做到合乎法则,而不能出自义务即出自对法则的敬重。此时,他可以成为“律法上的善人”,但还不是“道德上的善人”。要成为“道德上的善人”,就不能通过逐渐的改良,而是“必须通过人的意念中的一场革命”。但是,说一个旧人通过心灵改变成为一个新人是“革命”没有问题,说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改良”却是误解。韦政希博士把通过心灵革命而促成的由旧人到新人的转变过程说成是改良,这就抹杀了革命和改良的原则界限。
由于误将心灵革命之后的践履过程当成了改良,韦政希博士提出了“革命是改良的本体论前提”这一错误命题。康德并没有提出改良只能在革命之后进行,而是说没有革命仅有改良还不够,习俗的转变还有待发展到心灵的转变。如果认为康德把革命当作改良的本体论前提,而革命又取决于恩典,这就把恩典当作道德自律所促成的改良的本体论前提了,外在的神恩也就成了人的心灵转变即重建原初向善禀赋的先决条件,而人的道德自律反倒成了一个次要的附带后果。但是,这与康德的恩典概念完全相悖,违背了康德“自力更新”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把神恩不合理地纳入理性的准则。
恩典与道德自律能否互为前提?
韦政希博士在提出革命是改良的本体论前提时,还提出了恩典是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道德自律是恩典的实践论前提的观点。于是就有了两者的互为前提,以及在互为前提中的内在一致性。他把道德自律视为获得恩典的实践论前提,这一点问题不大,与康德强调人“自力更新”具有优先性的思想相一致。但把恩典说成是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这就过分夸大了恩典的作用。他是从人格性、人格性禀赋或上帝的精神造就了“属灵之人”等方面来立论的,但其观点难以成立。
首先,人格性不可能是作为道德自律之本体论前提的恩典。这是因为,在《宗教》中,人格性意味着堕落之人将心中始终存在的法则理念连同对法则的敬重重新纳入其准则,这恰好等同于原始向善禀赋即人格性禀赋的重建本身,当然不等于这一重建的本体论前提。
其次,人格性禀赋不可能是作为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的恩典。诚然,康德非常看重人格性禀赋在心灵完善中的作用,虽然人性败坏或颠倒,但他始终对心中的人格性禀赋怀有极大信心,不仅认为在它之上不能嫁接任何邪恶,而且认为我们必须假定它作为善的种子以其全部纯洁性保留下来。原初向善禀赋的重建,并非获得一种业已丧失了的向善动机,而仅仅是建立道德法则的纯粹性。因此,康德把它视为心灵中唯一值得惊赞的对象,认为这一惊赞是正当的,也鼓舞人心作出只有对自己义务的敬重才能要求它作出的牺牲。但人格性禀赋并不属于超自然的神力即恩典,而恰好属于人的本性或人自己的力量。即使我们承认人格性禀赋是上帝造人时赋予人的一种恩典,它也绝不是康德在此所说的协助人改恶向善的外在神力。
最后,“上帝的精神”造就的属灵之人,也不是作为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的恩典。韦政希博士认为上帝的精神造就了“属灵之人”,因而恩典构成了道德自律的本体论前提。如果脱离文本语境,在一般意义上泛论人的道德自律首先需要一个受造的属灵之人,这没有问题。但在人克服根本恶的问题上,却不能把这个受造的属灵之人当作协助人改恶向善的外在神力。受造的属灵之人,就像人格性禀赋一样,都属于“人”而非“神”的方面。
在克服根本恶的问题上,需要严格把恩典限定为神从外部助人改恶向善的超自然协助,而不能把人所具有的人格性禀赋,或者把具有此种禀赋的受造之人当作人“自力更新”的本体论前提,也不能泛论“道德自律”,而要严格地把它理解为人的“自力更新”。一旦我们遵守康德的恩典概念,就会发现他并没有把无法规定的恩典当作人“自力更新”的本体论前提。至于人格性本身,由于恰好意味着重建禀赋的目标的达成,需要人自己所为,更不可能是什么本体论前提。而“上帝的精神”的作用,虽表面上不同于人格性禀赋的作用,但两者殊途同归,都服从于道德宗教的真正目的,因而也不同于康德所批判的“邀恩的宗教”中的神秘恩典。
启示宗教中的恩典与理性宗教中的道德自律是否和谐一致?
康德在《宗教》第一篇“总附释”说:“实践上使用恩典理念,其前提就是自相矛盾的。”韦政希博士把这个矛盾说成是恩典与道德自律的矛盾,并认为康德在第三篇中关于宗教哲学的二律背反的解释,在理性宗教与启示宗教相统一的框架下解决了这一矛盾。在他看来,二律背反的正题代表启示宗教的恩典说,它把救赎或恩典当作上帝赐予人属灵生命的行为,反题代表理性宗教的道德自律,它把善良生活方式视为人的意志行为。
康德在第三篇论述“教会信仰逐渐过渡到纯粹宗教信仰的独自统治,即接近上帝之国”中提出,建立在作为经验的启示之上的历史性信仰只有局部有效性,而缺乏真正的教会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因此历史性信仰虽然能够成为一种教会信仰,但尚未是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纯粹宗教信仰。康德由此把真正的、唯一的教会所采纳的信仰,称为“造福于人的信仰”,这是纯粹的宗教信仰。而与之相对的,则是一种“侍奉神灵的宗教”,它信奉的是一种“奴役性的”和“有报酬的”信仰。康德接着说,造福于人的宗教包含人希望永福的两个条件:其一,是在属神的法官面前得到赎罪,这就是救赎(偿还罪孽、解脱);其二,进入一种新的、符合其义务的人生,这是对自己能够在一种今后奉行的善良生活方式中使上帝喜悦的信仰。如果我们认为一个条件可以必然地从另一个条件派生而来,则要么是对我们负有的罪孽抱有信仰而产生出善良生活方式,要么是对任何时候都要奉行的生活方式的真实而积极的意念,按照道德上的作用因的方式产生出对赦免的信仰。前者构成了正题,认为教会信仰优先于善良生活方式,首先相信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情(恩典),本质上是“因信称义”;后者构成了反题,认为善良生活方式优先于教会信仰,主张为了配享恩典而必须先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本质上是“因德称义”。
康德是在同一种造福于人的信仰内部,依据两个条件的不同结合方式来理解正题和反题的,而并未把正题反题分别当作奴役性信仰和造福于人的信仰的原则,因而并没有通过这一二律背反,来体现历史性宗教中的奴役性信仰与纯粹道德宗教中的造福于人的信仰的根本对立。康德这样做富有深意。他固然站在理性宗教的立场上赞同反题,认为我们只能凭借自己在遵循义务方面的努力而配享恩典,但认为如果我们把正题中的信仰理解为“合理的信仰”,则从它开始导出善良生活方式,就与从善良方式开始导致这种信仰殊途同归,没有实质区别。这要求我们把对“圣子”耶稣的信仰,与道德的理性理念相联系,并将之当作我们的行动准绳和动机。这里并无两个相反的原则,而仅有同一个实践理念,我们之所以由这种理念出发,要么是由于它把原型表现为存在于上帝之中并从上帝出发,要么是把原型表现为存在于我们心中,但在两种情况下它都把原型表现为我们生活方式的准绳。康德由此认为二律背反只是表面上的,它不过是把在不同关系中被看待的同一个实践理念,误解为两种不同的原则。
韦政希博士看到康德对二律背反的这一解释,由此认为康德消解了启示宗教的恩典与理性宗教的道德自律的矛盾,但他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这就是康德的解释是在同一种造福于人的宗教内部进行的,此时的宗教信仰,已经被康德作了理性化、道德化的诠释,不再是侍奉神灵的宗教中的奴役性信仰了。而这种侍奉神灵的宗教,在启示宗教的历史上客观存在,也是康德极力批判的对象。他的解读以偏概全,简单地把经过康德理性诠释的启示宗教等同于启示宗教,因而没有认识到同一种造福于人的信仰的两个观察角度的统一,并不意味着理性宗教中造福于人的信仰与历史上存在的侍奉圣灵的宗教中奴役性信仰的矛盾的解决。
事实上,康德在对二律背反作出上述解释之后还接着指出,如果有人把对一度出现于世的“神-人”现象的现实性的“历史信仰”,当作造福于人的信仰的条件,那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即经验性的原则和理性的原则。于是,无论从它们当中哪一项出发,都会出现“真正的准则之争”,而且任何理性都无法平息。也就是说,对耶稣的经验性-历史性的信仰,完全不同于对他的理性信仰或纯粹道德信仰。前者依然属于侍奉神灵的宗教,不属于真正的造福于人的信仰,它只是从信仰开始,但不会导出善良的生活方式。如果人们想仅仅凭借这种信仰就可以赎罪,从而把善良生活方式的决心推迟到罪孽洗清之后,就会导致心灵遭受奴役。
可见,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康德通过对基督信仰的特殊诠释消解宗教二律背反的矛盾,把对耶稣作为道德“原型”的信仰与善良生活方式统一了起来,但却并不能认为康德由此就消解了神秘恩典与道德自律的真正矛盾,也不意味着由此就消解了在实践中引入恩典概念所导致的矛盾。《宗教》第一篇所说的矛盾,并没有在第三篇中通过康德对宗教二律背反的解释而得到解决,康德在此仅仅是认为可以对启示宗教作出理性的诠释,由此将之同纯粹道德宗教相一致,而绝非认为任何启示宗教都是纯粹道德宗教,其恩典说都不需要加以抵制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