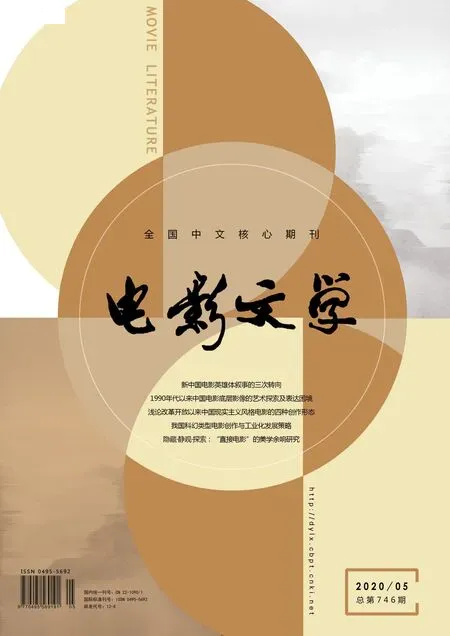论恐怖片的视听语言
潘小楼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艺建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4)
自1896年,乔治·梅里爱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恐怖短片《魔鬼庄园》,1910年,电影史上第一部怪物电影短片《科学怪人》问世,1920年,罗伯特·威恩执导了第一部恐怖长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恐怖片走过了百年历程。时至今日,恐怖片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电影,并拥有一套相对固定的视听语言系统。下面,我们将从七个方面来谈恐怖片视听语言的特性。
一、影 调
恐怖片的影调有着明显的倾向:暗调、冷调。这样的光色基调能够给予观众直观的视觉气氛,实现代入感。红色在这种光色中的表现最为突出。作为一种高能量色,红色具有两极性。作为血液的本色,它既能够象征爱情和激情,也能够象征血腥、暴力和死亡。需要指出的是,单色的冷暖倾向,要放置在具体的光色语境中看。在恐怖片的暗调、冷调中,红色倾向于阴冷。如吸血鬼题材电影《惊情四百年》,在压低色彩饱和度的基础上,对红色做了单色强调。红色是德古拉的标志色,也是吸血鬼世界的标志色。红色在冷调中,拥有让人不寒而栗的强大能量。
也有的恐怖片采用和暗调、冷调相反的影调:明调、暖调。但这种用法,大多是为了表意。如“黑暗童话”《鬼妈妈》,用光色将影片的空间一分为二:现实空间和“鬼妈妈”的空间。现实空间为轻度消色的冷调;“鬼妈妈”的空间则为高饱和色偏暖调。这种有悖常理的用色,也是为了表意:幻想世界是美丽的,但就像肥皂泡泡一样,总会破灭。影片最后,卡洛琳以决绝的方式告别幻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她重新接纳不完美的一家人,重新热爱不完美的世界,实现自我成长。
二、视 点
恐怖片为了让观众有强烈的代入感,在叙事上一般采用受限视角,即主观视角;对应这个叙事视角,其镜头视点为主观视点。观众跟随未知者,感受气氛的恐怖,探寻事件的真相。
除了未知者的主观视点,恐怖片还设置了偷窥视点。一般来说,影片可以通过机位的设置、景别的跳切、手持拍摄、光线变化、音效等,强调偷窥视点带来的惊悚感。在陈可辛导演的《三更》之“回家”中,阿伟父子走过寂寥的街道,进入小区大门前,几个过场戏镜头就已经对气氛做了充分铺垫。其中,有四个镜头运用了偷窥视点。第一个镜头:将机位设置在米店内,以米店场景为前景,全景景别,固定镜头,拍父子俩的横向移动。第二个镜头:机位设置在临街暗室内,以窗花为前景,跳近为中近景别,手持抖动拍摄,依然是父子俩的横向移动。第三个镜头:机位设置在暗室的门缝后,以孩子为背景,画面主体为锁,依然是手持抖动拍摄;景别随后跳近,变为特写。通过偷窥视点和孩子镜头互切,完成一个情绪小高潮。之后这个偷窥视点仍跟着他们,甚至在他们进入小区、走进大楼之后,依然在搬空的屋子里窥视他们。此时,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偷窥的主体,但从镜头设计、音效及被偷窥者自知或不自知的反应上,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三、镜头空间
镜像空间在恐怖片中常常会得到强化。镜面和类镜面反射现实,镜像里是虚拟的现实,可以说,镜像世界是最奇诡的镜头空间。
电影《安娜·贝尔2》中恶魔现身一场,珍妮丝走进安娜·贝尔的房间,房间放置多面镜子,它们分别反射着不同角度的空间,镜头着力捕捉的每一次反射,都让人惊惧不已。而恶魔现身的“关键帧”,就是在镜像空间里呈现的。在这个片段里,玻璃窗被当成类镜面。安娜·贝尔走向窗户,玻璃上映出她人畜无害的脸;接着珍妮丝走近,她的脸同样映在玻璃上。两者在镜像中同框。珍妮丝询问安娜·贝尔想要什么。影片用安娜·贝尔的静默延宕了观众在等待中的惊惧。她用手指敲击玻璃的节奏让人越来越不安。忽然,她转过身来(非传统手法的入画调度),已是恶魔的脸,就这样完成情绪小高潮。镜像在这里形成了画面分割,恶魔现身前后形成鲜明对比,观众在猝不及防中恐惧感更添一层。
在电影《招魂1》中,小男孩罗伊也是在镜像空间里现身的。罗琳和小女孩谈论关于罗伊的事。小女孩交给罗琳一个音乐盒,里面有一面画有螺旋的镜子,上发条后,镜子转动,由于视觉暂留,运动的螺旋形成一个小小的旋涡,像是一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罗伊正是在这面镜子里入画出画的。
四、单镜头设计
(一)低机位
低机位是恐怖片中常用的机位高度。 为什么要在恐怖片里使用低机位,究其心理机制,我们可以反观大俯视点的效果。大视野的俯瞰角度,常常被誉为“上帝视点”,因为这个机位高度,凡人非借助外力而不能及,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世人皆如蝼蚁;反之,低机位可视为“来自地狱的视点”。
恐怖片里的低机位常常配合仰角使用。最早把低机位的恐怖效果发挥到极致的,是电影《闪灵》。在酒店长长的走廊里,丹尼不管是骑着小三轮车,还是步行,机子跟拍他的时候,用的都是低机位仰角。一般来说,机位高度要和拍摄对象眼睛的高度持平,形成平视角度,容易让观众对其产生代入。诚然,丹尼是个孩子,拍他时,机位高度自然比拍成人时要低。但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机位高度,要低于丹尼眼睛的高度。同样的镜头设计也用在了迷宫的追逐戏里,迷宫通道的线条和场景与酒店走廊颇为相似,用这种角度拍摄,两边的墙壁对拍摄对象形成“夹击”,拍摄对象就如同困兽般无处可逃。
电影《闪灵》的低机位镜头设计对后世恐怖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电影《堕入地狱》中,女主角在屋子里遭遇恶魔,在她奔跑的时候,同样用了低机位仰角,配合倾斜角度,带上天花板的压制,会让观众产生压抑感。观众能在这类角度的镜头里,感受到来自地狱的深深恶意。
(二)倾斜角度
倾斜角度相对于水平角度而言,是一种非正常的角度。恐怖片在段落小高潮里,常会用到倾斜角度镜头来呈现人物或气氛的非正常状态。在电影《道林·格雷》中,亨利为道林举办告别聚会,但这只是一个幌子,他实际上是想趁着这个机会,拆穿道林阁楼画像的秘密。当道林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迎来了一个情绪上的小高潮。对应这个剧作需要,道林的近景在广角镜头下扭曲变形,而他追赶亨利的一组镜头综合运用了倾斜角度、入出画调度、快速剪辑、平行剪辑等,来凸显危急感。在电影《堕入地狱》中恶魔现身这一场戏里,停电片段就是用倾斜角度拍克里斯汀;与此同时,还综合了低机位仰角,带上天花板,呈现非正常的压抑状态。
五、调 度
入画出画作为运动性调度的一种,在恐怖片里常常用到。出其不意的入出画设计,尤其是入画,甚至成为整部片子的华彩段,成为观众的记忆点。
入出画调度,除了传统的手法,还有利用遮挡物、光影等手法。我们所说的“光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过多地强调“光”,恐怖气氛会减弱;过多强调“影”,恐怖气氛则会加强。利用光影进行入出画调度,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在电影《雨月物语》中,源十郎跟随若狭小姐和仆妇进入废园。先是用破门的影像和音效做了气氛铺垫。在废园长满藤蔓的残壁上,以荒草为前景,三人以“影”入画。之后,夜幕降临,在节奏奇诡的音乐中,导演通过源十郎这个未知者的视点,呈现了废园如何变为大名宅邸。影片利用侍女点燃走道灯前后的光影变化,以及走道的竖条挡板作为遮挡物,实现她们入出画的调度。而若狭小姐在官邸再次现身,亦是以“影”入画,她的脸在阴暗中渐渐浮现。大名宅邸的阴森气氛塑造就此完成。
相反,在电影结尾,当源十郎回到家,他死去的妻子现身时,观众为何不会恐惧?这是因为导演采用了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视听手段。源十郎在破屋里转,镜头跟着他横移,导演利用墙作为遮挡物,让他出画,妻子入画。虽然这个入画出其不意,但由于她处在大面积光区里,非但不会让观众感到害怕,反而,在源十郎的呼唤中,她的出现还会让人感到惊喜。镜头里强化的是“光”,不是“影”。此外,在妻子给源十郎盛吃的时,镜头用了小推运动,源十郎出画,落幅变成妻子的近景,这样的视点转化设计,会让观众对这个人物产生代入,站在这个角色的立场上去看整个事件,从而感受到此情此景她的哀伤。
六、声 音
恐怖片的声音,除了众所周知的音效,还有一种音效不得不提,那就是低频音。
低频音为什么会产生恐怖的效果?究其心理机制,我们可以反观高音的效果。教堂里视听设计的核心,就是要引导来者“向上”,产生崇高和圣洁之感。首先,在视觉上,哥特式教堂高处装着彩色镶花玻璃窗,当光线透进来,五彩斑斓的光线会率先引导人的视觉“向上”;其次,在听觉上,当赞美诗的高音部一起,自然而然也能在听觉上刺激来者“向上”。反之,处于低频区的声音,会在听觉上引导听者“向下”,产生和“圣洁”“崇高”相反的心理感受。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恐怖片的声音设计中,低频音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了。
在电影《道林·格雷》中,就在不同场次使用了低频音。第一场是在离开20多年后,道林·格雷重新现身伦敦的聚会。旧相识们都已狼狈老去,而他就像浸泡在福尔马林里一样,保有俊美的容颜。这场戏的视听设计,采用了低机位、入画调度、慢速率等手段;而在声音的设计上,则使用了低频音。这个无源声,其实就是在场的旧相识们的心理主观声,他们无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第二场是道林要带亨利的女儿艾米丽离开,亨利表面上为他们举办告别宴会,实际上则伺机探究阁楼画像的秘密。在亨利一句“或者你可以拿灵魂做交换”之后,道林有所察觉,恍惚之间,侍者夹着银盘在他眼前经过,他看到银盘上映出自己苍老的灵魂。银盘是高光面,在这里作为类镜面使用。在这一场戏的视听设计里,使用了短较、镜像、慢速率等手段;而在声音的设计上同样用到了低频音。这个声音,其实就是道林恍惚之间的心理主观声。以非正常的视听设计,呈现道林此时非正常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七、剪 辑
(一)停顿或静场
剪辑讲节奏。一般来说,高潮戏之前,都需要有一场节奏比较缓和的戏来缓冲,这是剧作的节奏。剪辑亦如是。剪辑的节奏,就是一部电影的呼吸。只呼不吸,或只吸不呼,都形成不了气息。在恐怖片的高潮片段之前,少不了停顿或静场,其实就是急和缓的调和。电影《堕入地狱》在恶魔现身这场戏里,克里斯汀查看院门,大风猛然刮起之前,有个短暂的静场;怪风过后,厨房的锅碗瓢盆山响之前,又是一个静场;当她拿到手电筒之后,恶魔以影入画之前,还是一个静场。静场就相当于解除观众的心理预警,让他们在毫无防备中接受刺激。每一次静场,都只会让观众对紧跟其后的刺激更敏感。
(二)景别的跳切
在恐怖片中,常用到景别跳切。电影《堕入地狱》在恶魔现身这场戏里,克里斯汀去查看院外被风吹动的铁门,从剧作上看,这个片段并没有出彩之处,之所以能引发观众心理上的恐惧,完全是因为它的剪辑。影片用了克里斯汀的五个景别跳切:中近、近景、近特、特写、大特写。不同的景别对观众心理的压迫程度不同。景别卡得越紧,对观众的心理压迫就越大。而由松到紧的镜头景别节奏很好地营造了危险层层逼近的效果。
总而言之,恐怖片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作为一种逐渐成熟的类型电影,它有着鲜明的视听美学特征。梳理其视听语言,有利于促进其视听技法的不断创新、丰富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