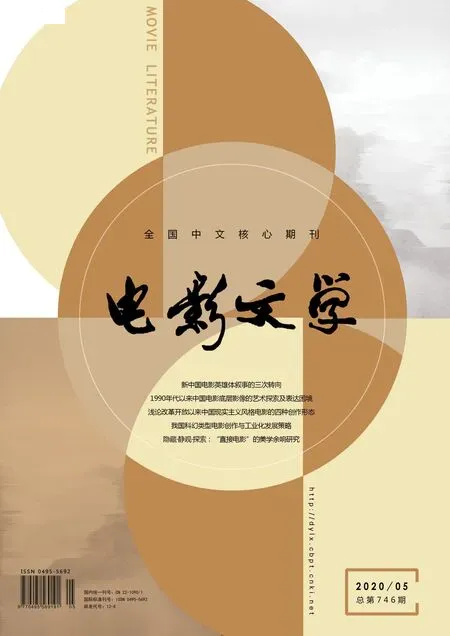21世纪哈萨克斯坦电影中的民族影像建构
汪 娟
(嘉兴学院 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作为中亚五国之一的哈萨克斯坦,近年来电影产业发展迅猛,成为推动亚洲电影崛起的重要力量。2000年—2017年哈萨克斯坦共拍摄电影254部,共有百余部电影通过各大国际电影节在国际上亮相,这些都标志着哈萨克斯坦电影的国际地位与艺术水平具有很大的提高。纵观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电影发展,20世纪90年代,哈萨克斯坦电影 “新浪潮”以国际化的路线达到宣传国家形象的目的,美国学者格雷戈里·H.沃勒指出:“新浪潮后的哈萨克斯坦将如何处理与表达其民族特性,这是一个人们拭目以待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观察肯定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古尔纳拉·阿比克耶娃认为21世纪的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形象已经树立和稳固。国家从总体上开始重新定位:一个有着坚定目标的国家——‘进入五十个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打开国门,以新的方式展现自我成为一种渴望。”通过近年来上映的哈萨克斯坦电影可以看出, 21世纪的电影定位以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述、重塑为主要目标,树立哈萨克民族英雄与胜利者的形象,哈萨克斯坦电影的这种定位也决定了其民族电影史诗风格的形成。电影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无论从宏观的国家层面还是电影文化本身而言,哈萨克斯坦电影中对本族历史与文化的表述都是值得研究和注意的对象。本文力图对21世纪哈萨克斯坦电影中民族形象的重建进行解读,对影像符号下的民族文化记忆呈现进行考察,探究哈萨克斯坦电影中重新确立的民族身份的多重话语。
一、历史重述中的民族形象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历史意味着民族存在的基础,追寻历史正是为了寻找真正的民族之根。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言:让世界真正承认你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历史。进入21世纪的哈萨克斯坦面临着如何迅速恢复本民族形象的重要问题,以影像的方式重新构建民族的历史,就是要落实民族形象问题,把本民族的文化记忆重新描绘和凸显出来。因此 ,对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而言,“在21世纪坐标下思考民族的历史是表达民族思想的第一步”。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悠久。“公元15世纪,哈萨克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哈萨克汗国。19世纪60年代哈萨克汗国被沙俄吞并。十月革命后,哈萨克斯坦先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后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90年10月25日,哈萨克斯坦宣布拥有国家主权,1991年12月16日宣布独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的形成经过了漫长、曲折和艰难的过程,是数代不懈努力和追求的结果。”21世纪的哈萨克斯坦影片中对于民族英雄的重述是以英雄史诗为主要元素的,以此树立伟大复兴民族的形象。
2005年上映的由谢尔盖·波德罗夫与伊凡·帕瑟共同导演的《游牧战神》是传统的英雄史诗电影,影片讲述了哈萨克民族阿布赉可汗的成长之路。哈萨克族文化史上 “阿布赉在18世纪时统一了哈萨克,在反对准噶尔蒙古,带领哈萨克人民归属清朝,以及反对沙俄侵略中,立下了特殊功绩,为哈萨克三个玉兹人民所爱戴和敬仰,‘阿布赉’成为哈萨克民族的战斗口号”,《游牧战神》中的主人公曼苏尔(阿布赉)出生后就被预言为准噶尔的敌人,他经历了种种磨难,成长为哈萨克民族英雄。影片中对于哈萨克英雄的叙事体现的是主人公对于民族归属感与民族身份感的认同,既有国家、人民的苦难历史,又有英雄的传奇经历,使民族形象的树立通过主人公英雄形象的塑造浮出历史地表。尤其在影片的最后,以阿布赉为代表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宣布 “从今日起,所有准噶尔人和其他哈萨克的敌人都要知道,从天山到咸海,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哈萨克人的居住之地,任何想要侵占这片土地的人,都会像准噶尔人一样被打败并驱逐出去。我们对朋友敞开心怀,对敌人毫不留情”。这段宣言表达了影片的主旨:聚焦哈萨克斯坦的民族精神。在对哈萨克民族历史的言说中,《游牧战神》完成了对哈萨克斯坦民族形象的塑造。2012年由阿罕·萨塔耶夫导演的《无畏一千勇士》创下了哈萨克斯坦年度最高票房纪录。这部影片同样是根据哈萨克民族伟大的诗人努尔玛甘别特·阔斯扎诺夫留下的脍炙人口的长诗《勇士萨尔泰》改编而成。影片以18世纪的昂拉海战役为背景,讲述孤儿萨尔泰一心要为被准噶尔人杀死的父母复仇,他集结了众多和他一样身世命运的孤儿投入了战斗,向着敌人发起决死冲锋,以少胜多,最终改变了整场战役的结果,挽救了哈萨克人的命运,表现出哈萨克族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保卫家园的故事。《无畏一千勇士》着力表现的是主人公萨尔泰的民族身份与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是“覆盖该民族并在民族成员身上反复显现的一种心理素质。也是渗透、贯穿一个民族或国家中的文化精神,在世界观、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方面,则是通过个别成员凸现出的现实态度”。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民族的勇敢、智慧、勤劳。
英雄史诗作为历史片的一种类型,其“叙事(narrative)聚焦于过去发生的真实事件或真实人物的生活经历。通过‘演义’式的改编,历史片赋予某个历史时刻或人物以‘丰功伟绩’(greatness)。这种语境中的‘真实性’服务于不同的意图。在这一点上,历史片承载着意识形态( ideology)功能:它们把一个国家的国家史呈现给本土人民,通过把我们共同历史中的‘伟大时刻’和‘伟大人物’——我们的文化遗产搬上银幕来教会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以《游牧战神》《无畏一千勇士》为代表的哈萨克斯坦英雄史诗类电影不仅承载了民族的历史,更是对哈萨克民族形象的彰显。这些影片在形式上包含了大量的国际化电影元素,在战争场景方面极具其史诗气质,在内容上则着力于表现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的辉煌奋斗和伟大人格,激发起民族群体的荣誉感与凝聚力,从而进一步强化本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的认同。显然,哈萨克斯坦以影像的方式重述了历史上的民族形象,“全世界在之前不为人知的哈萨克人身上看到了英雄和胜利者的形象”。
哈萨克斯坦电影中所追寻的“民族形象”的重大主题,显然是通过对民族英雄的影像表述,展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哈萨克斯坦21世纪的民族发展、独立自主等国家问题的思考。毫无疑问,影像成为联结民族、自我与历史的桥梁,哈萨克斯坦电影在对民族形象的历史重述中给出了答案:哈萨克斯坦在历史的大潮中,总能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建构以族群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哈萨克斯坦电影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起着传播先进民族文化,展示21世纪民族形象的重要作用。
二、影像符号中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民族特性的伴随物,它反映了特定族群的历史变迁及特质。哈萨克斯坦属于“草原文化圈”类型,“马背上的民族”是对哈萨克民族文化的高度概括,以游牧为主的哈萨克民族在21世纪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哈萨克斯坦现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使他们逐渐远离游牧民族特征,很多本民族的文化记忆已不被看重,或被淡忘。而张承志认为:“游牧社会的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它曾经内容丰富无所不包。无论拉水的牛,比赛的马,讲起来都是一本经,无论是语言的体系或一个单词的色彩,分析到底都会出现真理,闪起朴素的光辉。它深藏着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一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一些人的基本问题。”21世纪的哈萨克斯坦电影中对于游牧文化的影像展示极为普遍,显示了对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关注与传承。
在哈萨克民族的文化记忆中,民歌与草原的呈现是游牧文化的场景符号,它以外在符号的形式再现内在精神的意旨,成为哈萨克斯坦电影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方式,同时,这些带有民族文化记忆的影像符号又有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特征。鲁斯坦·阿布德拉什托夫是哈萨克斯坦优秀的独立电影导演之一,他2008年导演的影片《献给斯大林的礼物》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该影片有一首哈萨克族民间歌曲被反复吟唱:“无风夜里的明月,月光闪耀在水面,村野之人深沉的心,犹如湖水翻涌呼号。”纯洁美好的歌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民歌源自19世纪哈萨克斯坦的民间诗人阿拜,他在对草原生活的细致观察中曾写下大量的诗歌和箴言,不仅流传极为广泛而且对哈萨克民族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阿拜的诗歌已经成为哈萨克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导演阿布德拉什托夫以阿拜诗歌所代表的悠久的传统文化与影片沉重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歌在影片中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意旨,人类生命的意义与哈萨克民族文化符号联结在一起。同样由鲁斯坦·阿布德拉什托夫2011年导演的《我童年的天空》中汇聚了大量的哈萨克民族的影像符号。该影片主要讲述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童年故事。影片中最吸引人的是哈萨克民族的一系列文化符号的展现:美丽壮观的高山草场,主人公骑着驰骋的白色骏马,冬不拉、手风琴等乐器伴奏下的歌舞片段等,这些元素恰恰是哈萨克民族形象的构成物,导演鲁斯坦·阿布德拉什托夫从自然、音乐、语言等影像符号对哈萨克民族文化进行了演绎。如让米·特里所说:“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具体的艺术,是将具体事物变成符事情(或表意系统)的艺术。”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而言,这种以外在的民族符号建构其民族形象的表述中,鲁斯坦·阿布德拉什托夫导演的电影成为哈萨克民族文化最好的观照。
马与狼是哈萨克民族记忆的重要文化介质,21世纪的哈萨克斯坦电影中马与狼的出现成为体现其民族特征与文化记忆的影像符号。作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人,马在他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哈萨克斯坦电影中对骏马的设定显示哈萨克民族对马的崇拜与偏爱。无论是民族史诗的影片,还是阿迪克·埃米尔克斯坦导演的喜剧片《图班嫁给我》(2008),均有对马的不同呈现。马的存在与民族生存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游牧战神》中的哲人奥拉兹所称“每一个哈萨克人都懂马”。哈萨克斯坦在传统体育方面有在马背上进行的“姑娘追”、马术竞技等,其实质也是对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再现。“狼”是哈萨克文化中图腾崇拜的文化表征,2012年叶尔梅克·图尔苏诺夫导演的影片《老人与荒原》中,老人哈斯木与狼相遇搏斗,影片极力表现了哈萨克人对狼复杂的情感,狼残忍而狡猾,老人却是坚守和退让,反映了游牧民族对图腾物的尊崇与敬畏。
影像符号不仅以外在的个体形式存在,而且深深内化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叶尔梅克·图尔苏诺夫导演的影片《柯林》再现哈萨克地区古老的婚俗传统及巫术和天葬,充满了仪式感与神秘感。异域的哈萨克风情吸引着观众,导演不仅通过哈萨克民俗挖掘出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也开发出可资借鉴的电影产业创意策略。《老人与荒原》中的老人哈斯木在草原上遇到暴风雪的危急之际,途中突然出现了一棵古树,仿佛冥冥之中让他找到了部落的神灵所在。哈萨克族相信万物皆有灵,老人与这棵古树说话并挂上白布条。萨满教是哈萨克民族早期的原始宗教形态,“树”是萨满教中重要的仪式象征物。包括影片中具有色彩符号意义的白布条也有着民族象征的意义,隐喻着民族的某种理性和观念。影片《无畏一千勇士》中同样存在着向树祈愿辟邪、白色帐篷的镜头特写,这些潜存于影像符号之中的社会性文化记忆清晰地体现了哈萨克斯坦民族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在集体无意识中描绘了本民族初始、本真的生存状态,折射出21世纪的哈萨克人参差多样的民族本貌。
哈萨克斯坦电影中的影像符号不仅是表达哈萨克民族文化记忆的媒介,还通过具体的转化,确认了民族传统文化在民族精神与文化记忆中的具体途径,显示出哈萨克斯坦电影在呈现影像的文化记忆方面做出的探索。
三、民族情感中的多重话语
如果说历史是虚构的,记忆是变形的,那么,在哈萨克斯坦电影中有一点却是真实与无疑的,那就是民族情感的重新确立。深厚民族情感来自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媒介化的历史时期,哈萨克民族文化面临着民族性淡化的现状,21世纪的哈萨克斯坦电影应该如何应对民族情感的嬗变,民族和现代、城市和乡村,该如何选择?哈萨克斯坦的电影中以民族情感的多重话语方式表达出电影艺术家个体的思考与体验。
谢尔盖· 阿普里莫夫是哈萨克斯坦早期电影“新浪潮”导演,2004年他导演的《猎人》被称为是他最有趣的片子。电影中父亲一心想让他的养子延续猎人的传统生活,他教给儿子的是传统猎人生活的一切原则,尽管儿子面临着在现代社会的生存问题,老猎人希望儿子仍然是永恒的猎人。影片包含了对民族传统与现代发展的批判视野,导演谢尔盖·阿普里莫夫以一贯的幽默与讽刺的风格在影片中表现民族情感面临的矛盾。无论电影还是其他的艺术样式,归根结底是为了表达人们的精神索求,谢尔盖·阿普里莫夫电影中对民族意识的重建不是简单的倾诉,而是复杂而多义的,他带着一种审视和反思,对民族情感具有批判的话语色彩。这种对本民族进行省思的作品还有耶尔兰·纳姆努克哈姆拜德导演的《核桃树》,这部2015年上映的影片曾获第20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2015年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评审特别奖和国际评委大奖。影片主要讲述了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一个小镇上的主人公加比特婚礼后在小镇上种种的日常生活遭遇,影片通过几个小人物展现出现代与传统、世俗与宗教的文化传统,导演将人物个体表现的无力、无聊与哈萨克民族的调侃、幽默结合在一起,昭示了在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哈萨克斯坦民族情感话语的重建,整部作品充满了微笑与质朴,透过影片中不同身份、不同年龄角色的经历,看到的是哈萨克民族体认自我家园的心路过程。
在现代性空间逐渐强化的21世纪,哈萨克斯坦电影《图班嫁给我》以表现现代性焦虑而格外引人注目。“长期以来,农业景观是哈萨克斯坦电影镜头内的主体,对游牧传奇和农耕神话的反复再现已成为乐此不疲的故事范式。”哈萨克斯坦长期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历史现状决定了其城市化进程缓慢。“尽管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哈萨克斯坦人都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对城市的症候性陌生和犹疑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转型中普遍存在的文化裂痕。”2008年阿迪克·埃米尔克斯坦导演的《图班嫁给我》,从影像的视角下揭示哈萨克斯坦在现代化的城市进程中民族情感的重建过程。
《图班嫁给我》讲述了影片中的主人公、海军退役后回到家乡的阿沙,按照家乡的传统观念,如果一个男性想要成为牧主拥有自己的牛羊,结婚才是成全其身份的唯一途径。他去镇子上的单身女性图班家里相亲,却被图班嫌弃他耳朵太大,所以这部电影又称为《大耳无罪》。阿沙从城市返回乡村,而乡村的人们却想去城里。这部影片表现出世纪变迁之际哈萨克斯坦普通人的困惑,将现代文明与传统农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巧妙地在银幕上表现出来。《图班嫁给我》无疑是一部探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多重转向下哈萨克斯坦人对本民族的认同危机,“由于现代社会从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因而‘认同危机’已经是现代人的典型的传记性危机”。认同危机首先直接导致的是民族身份的焦虑,这种焦虑在影片通过阿沙送给图班父亲游牧民族完全无用的水晶吊灯时,图班父母面无表情的对视呈现出来,吊灯作为城市现代性的表意客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影片中阿沙姐姐的女儿玛莎固执地唱着哈萨克传统歌曲反映出导演阿迪克·埃米尔克斯坦的民族情感,城乡二元对立中,他没有简单地处理为叙事符号,而是在强调民族情感的同时,清醒而理性地表述出现代性包围和侵蚀下的民族话语显得怅惘、无奈而无望。
哈萨克斯坦电影中对民族情感的表述还体现为影片中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尽管性别角色、性别身份看起来已经被完全认知了,但是性别身份是一个远比用生理学的方法区别男性与女性的做法更为复杂的问题”。哈萨克斯坦传统文化中的母亲形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哈萨克文化中,女性是希望、未来还有祖国的化身。阿米尔·卡尔库洛夫导演的《别哭》(2002)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部数字电影,影片从三位女性的视角,表现在生活的需求下,她们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影片以三位女性分别代表国家的三个时期:哈萨克斯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影片完全以女性为主角的叙事方式和追求陌生化视觉奇观的效应,给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影片《母亲的心》描写了一个慈爱、勤劳的母亲,演绎的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之母”的形象,母亲为了孩子们操劳,当孩子长大,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母亲却躺在医院中即将失去生命。这时象征希望的小孙女用稚嫩的声音在手术室门口唱歌时,母亲苏醒了,又恢复了生命。影片中的母亲作为一种血亲的来源,充满了宽厚的母爱与善良的心灵。母亲使民族的话语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她所承担的不仅是哈萨克民族情感中的传统文化,同时连接着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想象与认同,仿佛使人触摸到了特定民族的精神之魂,文化之根。哈萨克斯坦电影中以女性形象的表述,实则是以一种性别影像空间的呈现方式,连接着影片的影像叙事、民族情感及文化反思。
哈萨克斯坦电影中对民族情感的多重表述描摹的是当代哈萨克民族面对民族和世界、现代与传统、宗教与世俗冲突的困境。
结 语
研究哈萨克斯坦电影中的民族影像建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哈萨克斯坦电影近年在国际电影节中的获奖,这也是国家民族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获奖对电影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具有双重强化的功能。国际电影节注重电影作品的民族文化特质,也强调电影的普世性追求。只有深刻地展现了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又蕴含着深厚的普世性价值内涵的作品才能折桂国际电影节。所以,国际电影节是哈萨克斯坦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本民族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更是民族影像建构的重要方法。
葛兆光认为:“真正绵延至今而且影响今天生活的是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反复思索的问题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影像无疑是记载一个民族历史的活标本,21世纪的哈萨克斯坦电影的民族影像如何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确认自我民族身份,或许其主体民族的特征仍会不断确立。可以预见的是,在“一带一路”的语境下,哈萨克斯坦电影走出去的文化策略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