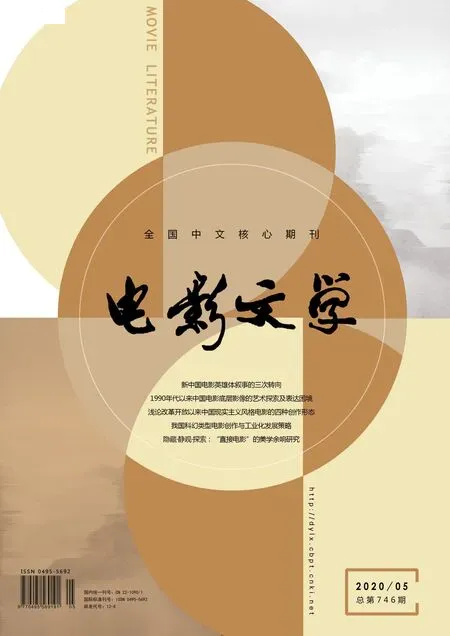新中国电影英雄体叙事的三次转向
徐玉梅
(临沂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从第一部电影《桥》(1949)开始,新中国电影就开启了英雄叙事之路。“红色电影的几乎所有元素都已经在这部影片中萌芽了。”故事发生在1947年这一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电影一开始就是激烈的战斗场面,骏马奔驰,尘土飞扬。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东北某铁路工厂组织工人修复炼钢炉,完成修桥任务。这部电影融汇了革命战争和工业生产两种题材,为后来的电影开创了两种叙事主体:革命战争英雄和行业奋斗英雄。“从广义上说,他们(英雄)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英雄叙事作为一种重要的形式,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功能,以精神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很大程度上,新中国70年电影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围绕英雄叙事主体进行话语阐释和社会建构的。什么是意识形态?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解释就是“倒现着的意识与现实的关系”。因此,意识形态是渗透在文化结构中的价值态度、情感倾向,并通过一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方式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以来,英雄叙事有效地参与并影响了中国史境。如何理解中国史境下英雄叙事话语与观念以及其演变过程?当前的文化环境下,英雄叙事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英雄叙事背后体现的艺术意志又是什么?本文将做出相应的探讨。
一、第一次转向:社会主义英雄叙事
“十七年与‘文革’电影中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代表了当时电影创作的主导思想。”那就是,“创造作为效仿对象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主要任务”。电影《桥》就将叙事重点放在铁路领导如何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过程上,表现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体现。
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者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电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一时期的电影叙事,以特定场景、英雄人物为依托,体现了政治至上的美学形态,注重影片的启发性与教育性。《新儿女英雄传》(1950)、《白毛女》(1950)、《大地重光》(1950)、《儿女亲事》(1950)、《钢铁战士》(1950)、《红旗歌》(1950)、《刘胡兰》(1950)、《吕梁英雄》(1950)、《保家卫国》(1950)、《在前进的道路上》(1950)、《赵一曼》(1950)、《团结起来到明天》(1951)、《保卫胜利果实》(1951)、《走向新中国》(1951)、《翠岗红旗》(1951)、《上饶集中营》(1951)、《人民的战士》(1952)、《飞虎》(1952)、《南征北战》(1952)、《智取华山》(1953)、《鸡毛信》(1954)、《董存瑞》(1955)、《平原游击队》(1955)、《铁道游击队》(1956)、《上甘岭》(1956)、《暴风雨中的雄鹰》(1957)、《柳堡的故事》(1957)、《牧童投军》(1957)、《狼牙山五壮士》(1958)、《党的女儿》(1958)、《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等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标志着社会主义电影体系的主体逐渐形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电影,大多着眼于历史上的“实事”,根据历史真实的事件改编。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军事片,《南征北战》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中野战军在沂蒙山区的凤凰山完成战斗,在大沙河切断敌人退路并击退敌人,最终粉碎国民党进攻的过程。电影对叙事外壳(情节)的关注要明显超过对于叙事内核(人物)的关注。
1959年,在国庆10周年的契机下,中国红色电影出现井喷爆发局面,并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创作高潮,如《聂耳》(1959)、《战火中的青春》(1959)、《青春之歌》(1959)、《万水千山》(1959)、《战上海》(1959)、《烽火列车》(1960)、《林海雪原》(1960)、《革命家庭》(1961)、《红色娘子军》(1961)、《延安游击队》(1961)、《英雄小八路》(1961)、《51号兵站》(1961)、《地雷战》(1962)、《英雄坦克手》(1962)、《红日》(1963)、《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小兵张嘎》(1963)、《英雄儿女》(1964)、《苦菜花》(1965)、《烈火中永生》(1965)、《地道战》(1965)等影片。这些电影中的英雄是力量、计谋的代表。无论面临什么险恶的环境,他们总是能够灵活地应变,并在逆境中取得胜利。如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感情充沛,心胸宽广,有勇有谋,意志坚强。这些历史场景中的英雄叙事具有仪式化功能,通过故事的“道义”,让观众形成比较稳固的印象。另外,还有一些反特故事片,如《国庆十点钟》(1956)、《虎穴追踪》(1956)、《边寨烽火》(1957)、《地下尖兵》(1957)、《激战前夜》(1957)、《寂静的山林》(1957)、《赤峰号》(1959)、《海上神鹰》(1959)、《冰山上的来客》(1963)、《跟踪追击》(1963)、《南海的早晨》(1964)等电影,表现了各族人民与特务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做斗争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电影重在反映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理想与热情、憧憬与想象。《桥》之后的几部工业题材电影,比如《光芒万丈》(1949)、《高歌猛进》(1950)、《女司机》(1950)、《在前进的道路上》(1950)、《走向新中国》(1951),都效仿了《桥》的英雄叙事模式。随着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电影《情长谊深》(1957)、《球场风波》(1957)、《青春的脚步》(1957)、《上海姑娘》(1958)、《生活的浪花》(1958)、《爱厂如家》(1958)、《渡江探险》(1958)、《冰上姐妹》(1959)、《五朵金花》(1959)、《船厂追踪》(1959)、《碧空银花》(1960)、《鸿雁》(1960)、《李双双》(1962)、《昆仑山上一棵草》(1962)、《锦上添花》(1962)、《生命的火花》(1962)、《北国江南》(1963)、《女跳水队员》(1964)、《青山恋》(1964)、《天山的红花》(1964)、《山村姐妹》(1965)、《龙马精神》(1965)、《女飞行员》(1966)、《红色邮路》(1966)等影片,以现实生活为叙事空间,聚焦各行各业奋斗过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红色邮路》以主人公于长水为叙事主体,描述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邮递工作的热爱和对新线路的探索。再如电影《女飞行员》以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真实故事为蓝本,描写一群身份不同但是都阳光健康、为新中国的飞行事业不懈努力的女青年。影片中提到毛主席对《愚公移山》精神的肯定,并将这种精神与飞行员勤学苦练进行结合,有效地呼应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此外,《情长谊深》是第一部以科学家为叙事主体的影片,《球场风波》关注体育运动,《爱厂如家》聚焦石粉厂改革,《碧空银花》讲述第一批跳伞运动员的成长经历,《冰上姐妹》反映冰上运动事业,《船厂追踪》表现造船工作,《鸿雁》描写的是邮递员的故事,《昆仑山上一棵草》则刻画了将自己一生奉献给高原的地质工作者,《生命的边疆》歌颂了开发边疆的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风貌,《渡江探险》描述了英雄的解放军修筑康藏公路的故事。除此之外,《李双双》《北国江南》《山村姐妹》《龙马精神》等影片展示的是农村生产队和北方农村农业合作社的生活,反映了新中国农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最终实现改造山村的愿望。
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艺方针下,“十七年”电影创作与社会进程紧密结合。当然,这一时期的电影,也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主题先行、艺术技巧后补的现象。进入“文革”之后,在“三突出”的原则下,“样板戏”和电影在对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表达上达到一种极致的境地。1953年,《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就提出艺术作品存在概念化问题。在《英雄、群众及其他》一文中,冯雪峰指出:“不可以把先进分子英雄们从实际生活的矛盾斗争中孤立出来,不可以把他们从他们在斗争中作为矛盾冲突的一方面的地位上孤立出来,不可以把他们从他们所反映的伟大社会力量上孤立出来,不可以把他们从实在的历史前进的力量和方向上孤立出来。”
二、第二次转向:电影观念的解放及主旋律电影对英雄叙事的传承与改写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出现了一些具有启蒙意识的影片。电影《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2)、《没有航标的河流》(1983)、《芙蓉镇》(1986)等积极探讨新的美学观念与新的艺术手法。这些影片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同时,聚焦在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物,关注他们在新生活中的选择。电影《牧马人》中,被打成右派的许灵均在“文革”结束后放弃了在美国生活的机会,选择留下来建设祖国。因此,80年代以来,英雄叙事不仅被传承,并且被改编和续写。这些电影中的主人公,一度是生活的失意者,但是他们却是具有反省与探索意识的主体。这代表着政治口号式的寓意阐释走向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诗性气质的“修辞性”寓意。一些表现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人士献身祖国各项事业的电影,如《李四光》(1979)、《海外赤子》(1979)、《沙鸥》(1981)、《人到中年》(1982)等影片,表现了创作者对新环境、新现实的期待。因为士和知识分子作为知识、价值的创造者、维护者和传播者,最能充分地体现时代文化的精神品格。电影观念的解放意味着电影叙事将人的命运作为叙事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创作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影片创作多样化的追求。比如电影《沙鸥》(1981)就用长镜头和全景镜头的方式,真实流畅地表现女排姑娘为国奋斗的精神。
这一时期反映革命战争的影片如《啊,摇篮》(1979)、《挺进中原》(1979)、《保密局的枪声》(1979)、《从奴隶到将军》(1979)、《小花》(1980)、《归心似箭》(1980)等,在剧情的节奏感、人物的传奇性、叙事手法的艺术性上,也有鲜明的特色。电影《保密局的枪声》中的人物模式、故事结构以及镜头运用,对后来的谍战题材影视剧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这种歌颂地下工作者的电影,以其惊险刺激和强烈的节奏感为观众所喜爱。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大渡河》(1980年)、《西安事变》(1981)、《风雨下钟山》(1981)、《四渡赤水》(1983)、《孙中山》(1986)、《血战台儿庄》(1986)等电影与商业片和艺术片一起,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
为了迎接建军6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电影局提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1987年2月,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主旋律”概念被提出。这里所说的主旋律指的是“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及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会议提出,要发展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的题材的作品。这一时期,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电影占据创作主流,如《开国大典》(1989)、《巍巍昆仑》(1989)、《百色起义》(1989)、《开天辟地》(1991)、《大决战》(1991)、《周恩来》(1992年)、《长征》(1996)、《我的1919》(1999)、《国歌》(1999)等影片,用全知视角和多重线索,全方位反映特定年代的战役,重点描述战争中的领袖和英雄形象,将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诗性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史诗的特点。革命英雄从历史真实走向艺术真实,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为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和时代精神,使得形象更加立体。
除此之外,在政治诉求贯穿电影创作的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歌颂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的电影出现,如《焦裕禄》(1990)、《龙年警官》(1991)、《蒋筑英》(1992)、《凤凰琴》(1994)、《孔繁森》(1995)、《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等影片,在时代呼唤中,回应着主流文化的诉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红樱桃》(1995)、《红河谷》(1996)、《红色恋人》(1998)、《黄河绝恋》(1999)、《生死抉择》(2000)为代表的影片,将主旋律和爱情片进行了类型融合,试图讲述战争中普通人的情感与命运。影片通过女性、爱情和完美的景致引发人对于美的感受,借此表达对战争的态度。由于爱情与战争天然的对峙关系,战争中的人物不再是绝对的超我,这体现了英雄故事由宏大叙事向个体行为逻辑转移的趋势。
三、第三次转向:新主流电影的当代英雄叙事
新世纪以来,新的时代和新的观念赋予中国电影发展的机遇。在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海外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主旋律电影也期望达到商业与意识形态的双赢。在电影类型化的趋势下,主流电影创作上出现了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和商业类型片的主旋律化两种倾向,也就是业界所称的“新主流电影”。前者如《云水谣》(2006)、《集结号》(2007)、《沂蒙六姐妹》(2009)、《风声》(2009)、《建国大业》(2009)、《南京!南京!》(2009)、《东风雨》(2010)、《建党伟业》(2011)、《金陵十三钗》(2011)、《听风者》(2012)、《一九四二》(2012)、《厨子戏子痞子》(2013)、3D版《智取威虎山》(2014)、《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建军大业》(2017)、《古田军号》(2019)、《红星照耀中国》(2019)、《决胜时刻》(2019)等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后者如《中国合伙人》(2013)、《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我不是药神》(2018)、《流浪地球》(2019)、《烈火英雄》(2019)、《中国机长》(2019)、《攀登者》(2019)、《我和我的祖国》(2019)等商业(行业题材)电影。这些商业类型片的主角,大多数依旧是行业英雄,而且是具备新时代专业和业务能力的英雄。
新主流电影因为对空间的高度关注而呈现出奇观化的视觉形态。无论是表现革命战争的主旋律电影,还是指向当下甚至是未来的行业故事,都是以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视听表现为主要努力方向。电影《湄公河行动》的空间行为涉及村庄解救人质、城市抓捕犯罪集团和水上与天空的集合。《红海行动》有大规模的战斗场面,大多数在摩洛哥拍摄,呈现的也是大的空间格局。沙尘暴、爆破、坦克对战,都是对普通观众经验现实来说完全陌生化的美学空间。这是电影商品属性使然,也体现了主流电影探索多样化的尝试。影片重点不再局限于意义的本质,更在于意象的强烈象征意义。3D版《智取威虎山》将红色经典融入武侠的成分,白雪皑皑的鹰嘴崖、独特的自然环境,使电影有一种神秘的气息。这种空间环境为电影提供了生动的故事背景。这正是影片对传奇性的重视。再如《战狼2》中非洲的原生态景象和异域风光,正是视觉文化时代的奇观化修辞。情节在虚幻中折射出奇异,观众从中体验到异域空间的陌生化美感。
空间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还是电影文本的关键点和叙事驱动。新主流电影呈现的大多是既有理想信念又具有丰富人性内涵的新时代英雄,其呈现的世界图景也必须是英雄人物行动得以合理化的逻辑背景。对空间的感受方式与理解方式,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体现。在1957 年出版的《空间的诗学》中,巴什拉认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流浪地球》同样设置了三重空间:国际空间站、各个城市地下城和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冰封“死城”。国际空间站是拯救地球的渠道。父亲刘培强在这里工作,承担着拯救地球的计划。地下城是人类的唯一避难之地。被迫在地下城避难的儿子刘启要逃到地面。情节的错综复杂、空间的变化挪移,影片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塑造了人格化的英雄。这是当下被普遍认同的英雄叙事模式。当然,在这场“拯救地球”的行动中,不仅需要智慧,还要依靠“愚公移山”的团队精神,其抗争精神成就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范本。无论怎样都要带着地球流浪的决心背后,是人的主体性迸发出的力量。在导演看来,选择“创世”还是“末世”,是一种态度。带着勇气迈出离开太阳系的那一步,便是创造历史的时刻。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电影从国家叙事跨越到了对整个人类的价值观思考。这是当下中国电影的自我建构,是全球化文化视野中的民族认同。因此,在这种想象的地理空间中,承载着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通过英雄叙事,观众不仅能够追思历史,更能够洞察未来。
无论是革命先烈还是各行各业的优秀模范,新主流电影的叙事逻辑和英雄人物的成长曲线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如果历史是一幅画,个人经验就是完成这幅画的材料。新主流电影大都具备商业电影的结构模式,人物行为逻辑凸显。这是因为商业电影是锁闭结构,往往从高潮开始,把矛盾冲突最激烈最刺激的部分呈现出来,引人入胜。因此,人物的行为逻辑必须是清晰的、可以把握的。3D版《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不再是样板戏中的高大全形象,而是在一种江湖气息下的革命英雄主义代表。尽管是群戏,但是黑白分明的世界中每个人的人物行为逻辑都是清晰的。杨子荣的骁勇与善战,小白鸽的美丽与聪明,体现出一种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活力。最重要的一点,3D版《智取威虎山》将以前版本中去夹皮沟发动群众打土匪的情节省略了,而是加入了老百姓对战争的种种不同态度。这是影片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在人性面前,政治概念被淡化了,英雄形象也更生动,更接地气。尤其杨子荣的形象,脱离了样板戏的神性,而是更倾向于普通人的一面。这就去除了样板戏中的政治至上,又符合观众普遍的心理模式。《我不是药神》用一种讽喻性的叙事,将人物置身于迷宫般的复杂环境。面临家庭、事业双重危机的商人程勇一开始就陷入了外部环境与内部精神世界的冲突。失败者程勇从一个单纯为利益挣钱的商人,转变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病人谋利益的殉道者,符合典型的英雄拯救模式。
需要提及的是,新世纪以来部分电影延续了主旋律影片对英雄的塑造方式,比如《张思德》(2004)、《任长霞》(2005)、《法官老张轶事》(2005)、《生死牛玉儒》(2005)等以道德模范为叙事主体的电影,以生活化的场景和纪实性的风格,再现了人物身上的英雄特质。还有一部分行业题材电影,主人公很多都是具有最朴素仁义思想的普通人,是各行各业坚持、不放弃或奋争的人。如公安题材的《一线缉毒》(2010)、《见习女警》(2018),表现精准扶贫的电影《十八洞村》(2017),表现中国公路发展的《大路朝天》(2018),表现抗震救灾的电影《生命的托举》(2009)、《生死时刻》(2009),表现乡村振兴的电影《梦想沂蒙》(2019),军事题材电影《目标战》(2014),表现农民进城梦想的电影《卒迹》(2013),表现科学家技术兴邦的电影《东方中国梦》(2013),表现农村放映员的《王长喜来了》(2004),表现中国企业创新精神的《首席执行官》(2002)……这些电影表现了新时代的个体选择与伦理姿态。
结语:英雄叙事何去何从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色电影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旋律电影,再到新世纪的新主流电影,中国电影的英雄叙事并非一开始就是定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电影英雄叙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变革,还与中国历史语境发生互动作用,参与了历史文化进程。对英雄的理解、讲述,折射出各个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文化取向。观众不但关心讲述的故事是什么,更关心故事讲述的方式是怎样的。这正是叙事性作品的两个关键要素:故事和讲故事的人。英雄寓言的背后,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意义关系。一个是创作者的观念世界,一个是经验世界。英雄叙事是否可以通过虚构世界契合新的现实情境以表达内在的观念?创作者都希望获得最大意义和最大乐趣的故事。如何将这种最大的乐趣与最佳的教育意义融合在一起,焦点集中在价值观念和修辞手法上,也就是永恒的叙事内核和外壳上。英雄叙事的讲述方式本质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