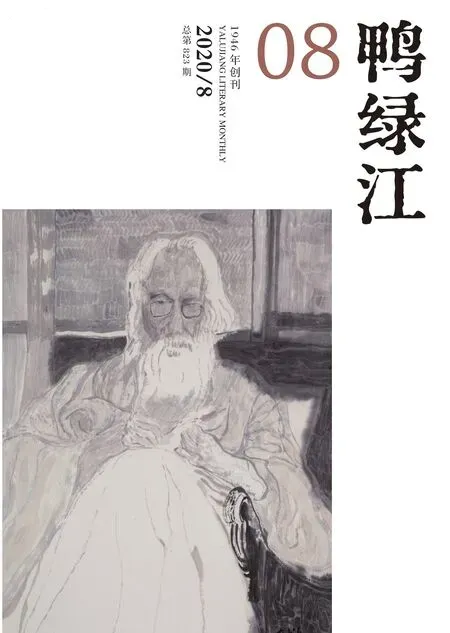枯树也是春天的一部分(组诗)
于成大
青山之青
它的青,就横斜在我门前
让木质的门框,也忍不住蠢蠢欲动
每绿一次,就是一次脱俗
百次后,它就是我心中虔诚的寺庙
清新得那么慈悲
一场薄雾都揭不开它的面纱
一片叶子,给不出谜底
所有的鸟鸣都被露水洗过
所有的草木都缺乏仇恨
宝石一样的星星,没有一点杂芜
纤细的山道,被想象成了叶脉
走在山中的一个人
正快速褪尽体内灰暗的部分
婆娑的林木不断地追逐下
他一晃一晃的身影,像掉下来的
树荫
反复梦见小镇
反复梦见小镇,那种淡青色的往事
一条小河带来临街的屋舍
一座店铺,带来面色红润的少女
梦见小镇
黄昏展开麻雀、灯火和忧悒
少女展开好年华和初恋
北风呼啸,书信比雪片密集
冻疮正被安抚,炉火醉心劈柴
无马的少年,正在经过
陈屯、草垛和梦境
冬天的山峦,在他眼中半梦半醒
反复梦见小镇,一只破碎的陶盆
一个人试图粘合与修复
然后,栽上一株好看的花儿
枯树也是春天的一部分
枯树也是春天的一部分
我从未想过剔除它
春天也没想过
拒绝绿叶与花朵的抚慰
在一个无言的位置上
无言
仿佛这个世界的所有沉默
都由它背负
从现场,退回到内心
用一个人的枯槁,加深
时代的繁茂、葳蕤
用一个人的缄默,加深
世界的喧嚣、噪杂
枯树也是春天的一部分
就像,坟墓也是大地的
一部分
空房子
被那么多人写过,被那么多首诗
打扰过
但我的空房子是另外的事情
坐落于蛛网与灰尘之上
只有我一个人能出入
桌子、椅子、家俱、地板、床
还在它该在的地方
墙上的相框,还框着旧时光
静止的空气小心翼翼地维持着
辽阔的空旷
蜘蛛有着足够的耐心
捕获悄然进来又悄然退出的
阳光
一行脚印
将什么打开了一道缺口
只有连记忆和往事
都消失了的房子,才称得上
空房子
我承认,我是旧故事中唯一留守者
我承认,旧书信已成了盘陀路
另辟蹊径,我沿着发黄的月色
走上河滩
毫不费力地揪出蒲苇、白露、杨柳
雁、荷
我承认松针依旧锋利
依旧带来了微微的疼痛
那片松林,一次次被我当成了
膏药
我承认,蓝色的河流
已流过水鸟的背,但不是逝水
破败的小镇,坍塌的月光
古典的溪水,久远的故事,老式的爱情
我承认,我是唯一没离开的
那个人
这个春天
读书,品茗,晒太阳,和朋友聊天
看窗台上长寿花把影子从日出
搬进日落
鸟雀回到去年的巢,雨水回到丛林
云朵接近去年的白
一个人找到了答案,类似于
夜晚找到了灯火
旧书信更旧
那些深居的文字和月光正在醒来
流浪的人更老,他已不适于说出爱
一条小路快速地穿过时光
有人为年代久远的爱情不惜眼泪
转眼春暮,经历成为记忆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该知道——
我一生的愉悦,十之八九
来自从前
风筝想从大地上拔出什么
龙,蜈蚣,蝴蝶,鹞鹰,鲤鱼
纸、布或丝绸
每天傍晚,它们准时出现在
我左前方的视野中
步调一致,和谐相处
统治这片天空已很多年了
风都无法驱赶它们
偶尔有一只凋零,另一只
会很快补上来——
风不允许长时间的缺口
它们极力向上,努力挣脱
并且咬牙切齿,使出吃奶的力气
想从大地上拔出什么
下面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尘世
一个空旷的广场,十几个老人
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线
维系着人间的平衡
艰难的树
这是一些新栽的树
从其他的地方移植而来
为了运输方便,它们不得不
卸掉大部分枝丫
光秃秃地站在春风里
异常艰难地萌发,并需要保持
足够的求生欲
现在,它们要尽快适应一切——
土壤、气候、环境、乡愁
它们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根部堆埋的土堆
要么成为坟墓,要么成为
故乡
大风
树木倾斜,大风扶不正它
只能使它更加倾斜
但只要一松手,它就会复原
草木的世界多么美好——
两朵花刚刚在左侧分别
转瞬在右侧重逢
浪像一个怒冲冲的醉汉
只有堤坝能扶住它
只有更小的风,能安抚它
柳丝,犹如飞舞的长发
这样想时,风不但不讨厌
还会带来一点小激动——
我轻易就能回到白衣飘飘的
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