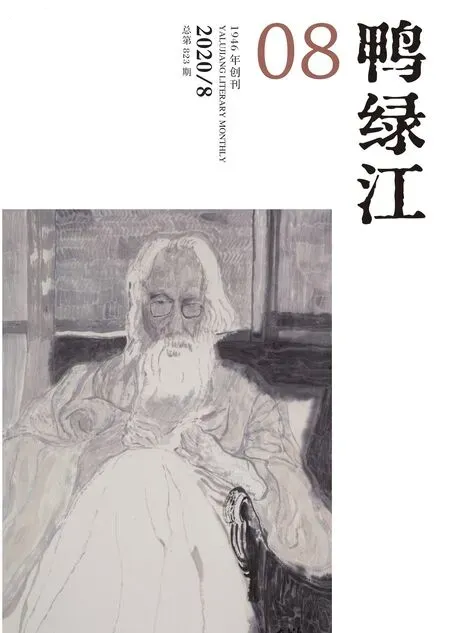母亲的采购商店
俞赞江
1
采购商店,这个充满历史印记的小镇收购站,如今早已消失于世,但我不敢忘却其中沉淀的故事。很多年来,我清晰地记得从辽宁南下的母亲留着齐耳的短发、端坐在那里拨打算盘珠的模样。显然,采购商店是母亲融入南方的最早领地,她在此厮守了十几年,彼此已水乳交融,它像是母亲另一个温婉的代名词。
采购商店并非临街店铺,它其实是一座狭长的大院子,银色的铁门朝西开,太阳落山时,铁门会泛出耀眼的光芒。里面有一排仓库式的平房坐北朝南,由西往东伸延进去,院子被粗粝的青石墙圈住,围墙外是一条坑洼不平的机耕路,连接小镇东头的几个村庄,南面是广袤葱郁的田野。
如果把穿镇而过的剡江当作X 轴,把纵贯南北的鄞奉公路当作Y 轴,采购商店地处X 与Y 轴相交处的东南区域。这个区域的北侧还有专门销售农资的生产商店,与南侧的采购商店遥相呼应,尽管中间隔着一座大牛场——当年号称“浙东第一牛场”,两大商店同属供销社旗下,不仅有连排的经营房,还有偌大的场院用来囤积物资。那时候,生产商店的职能是将国家的紧俏物资毫无保留地供应给民间,而采购商店的职能则是将民间的物资源源不断地收购进来。前者是卖,后者是买,买卖渠道不同。
母亲的商店从废铜烂铁、废纸塑料、碎头发,到蔺草席、稻草袋、黄麻片、苦楝果、桃子核、紫云英种、鸡蛋、鸭蛋、蜂蜜、泥鳅、黄鳝,以及屠宰后剥下的牛皮、猪皮、猫皮、狗皮、狐狸皮、黄鼠狼皮,还有猪骨头、牛骨头、牛油、鸡毛、鸭毛、鹅毛、猪毛……统统纳入收购范围。这让母亲的采购商店显得丰富而生动,比如每间仓库里、院子每个角落里常年堆积着新的旧的、生的熟的、死的活的、香的臭的、净的脏的、美的丑的、笨重的轻盈的、庞大的微小的、能吃的不能吃的等物资。
母亲是采购商店里唯一的女性,任职出纳岗位。各种物资收进后,所有需要支付的钱款,都得先经过母亲那面棕色算盘的核准(尽管那面算盘早被母亲娴熟的手指磨得褪了色,但在那个年代,没有比这更便捷的计算工具了),然后,一张张钞票、一枚枚硬币会经母亲之手,分毫不差地递到顾客手里。
2
1963 年,正值芳华的母亲毅然辞别辽宁阜新老家,跟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千里迢迢返回奉化。母亲的抉择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就像她任性执着、一往无前的性格。1963 年至1968 年的六年间,母亲先后完成了四个孩子的生育任务,并陆续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任。“文革”开始后不久,噩运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个羸弱的家庭,担任小镇税务所所长的父亲一夜间被扣上特务和反革命帽子,随后,隔三岔五遭受造反派批斗。母亲一边要保护和照顾父亲,一边要与造反派们周旋,直至父亲被送往县里的五七干校改造。
父亲离家后,母亲像一叶风雨中漂摆的小舟孤立无援,每天感到悲哀、压抑和焦虑,生活陷入困顿。那段时间,她开始艰难地改造起自身,也同时改造起我们这个带有南北文化背景的家庭,以适应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
但母亲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改造环节——语言。六七十年代,是中国人口流动最缓慢的年代,也是人们语言交流最薄弱的年代,小镇这弹丸之地,要接纳母亲这样的东北人,似乎并不具备合适的环境。那时强势的本地方言根本不把北方来的普通话放在眼里,而是千方百计排挤它。母亲初来乍到时那口标准的东北话,天长日久,没有守住它的韧劲和本色,语言体系被本地方言逐渐侵蚀。而且母亲在学练本地方言时,又遇到自身基础厚实的东北话的强力抵抗。以致于几十年来,她的方言能力一直徘徊不前,最终形成南腔北调。我深信,母亲一定是骨子里缺乏语言天赋,或者是有一种顽固的心魔阻碍了她学方言的积极性。
母亲的那口南腔北调,成为采购商店里别样的交流语言,镇上的男女老幼、乡下的农民们挑箩提篮来店里交易时,都要设法琢磨透母亲的语言,有人领悟得奇快,有人半懂半不懂,有人坠入云里雾里,总之,谁能率先听懂母亲的语言,谁就扬扬自得。时间久了,母亲渐渐不需要去适应人家了,而是让人家来试着适应她,角色从被动转为主动,母亲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信。
然而,母亲的自信却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自卑,死要面子的兄妹们,为母亲卓尔不群的发音而羞愧。尤其在学校,那些调皮的同学有板有眼地模仿着母亲的腔调,活像一把把刀子剜割着我们可怜的自尊心。我们兄妹不想被人嘲讽,从此刻意疏远母亲,避免让她去学校丢人,谁让她是个外地人呢,谁让她把话讲得南腔北调呢!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家庭内部从不讲普通话,似乎这样做可以提升母亲的方言水平,可以遵从母亲的语言现状。她这一生没学会讲地道的方言,但她完全听得懂每句方言的意思,并未影响到日常交流,我们实在不能再苛求她了。
3
采购商店幽深的院子,对我有种莫名的吸引力,百无聊赖时,我总想溜进去,一直走到院子深处,似乎在那里会邂逅许多美好,想象意念中的美好,会让我心旌荡漾,会让我信心倍增。现在想来,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有种心理期盼,对某个现象、对某件事情、对某项变化、对某种固有的神秘……
从大门进来十几米,要经过柜台边的一个大窗口,母亲就坐在窗口边,每天专心地拨打着算盘。尽管背对着窗外,但她直觉敏锐,似乎能感应我的脚步声,抑或能闻出我进来时的气息,她会疾速地回过头,看到我,立马沉下脸,叽里呱啦向我数落起来。我特不喜欢她的眼神,更不喜欢她独特的责骂声,能躲则躲,尽量不被她撞见。母亲生育的四个孩子,有三个她没精力抚养,只能寄养在镇上人家,时间长了,彼此缺乏接触,更缺乏感情交流。所以我天然缺失母爱,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不怪母亲,我的弟妹们也如此。
闯过了母亲这道关,我大大松了口气。一路进去,瞧见墙边摆满各种生锈的旧机器,琳琅满目,像是在举办一场旧机械展览会。前面草丛里终年躺着一大堆牛的头盖骨,白色的牛骨映衬着灰褐色的牛角,骨头上还没剔尽碎肉,但早已被风干,都是些鞠躬尽瘁的老牛,干不动活儿就被宰了。往前走,屋檐下整齐地码着一只只空铁桶,比柴油桶干净,那是用来灌装黄澄澄的蜂蜜的,嘴馋时,只要拧开小铁盖,用鼻子吸一口,甜香醉人。再往前,是洁净的草席仓库,蔺草的清香溢满整间屋子。那时候,年轻力壮的盛军海和他的伙伴们,每年都要从盛家村挑来一捆捆编织好的草席来售卖。谁也没想到,后来他会成为中国十大名牌西服——罗蒙的创始人,成为一位遐迩闻名的民营企业家;谁也没想到,当年镇上的采购商店旧址,今天巍然耸立着罗蒙集团的24 层高楼。
仓库边上建着个狗窝,终年拴着一条高大威猛的狼狗,那是店里的老张头养的,用来看家护院。我每每从大门进来,走到院子底部去,都须闯过这道鬼门关,接受狼狗的严格盘查。有时它狂吠不止吓你,有时它一声不吭上来嗅你,有时它心情烦躁咬你,但用力很轻,大概嫌我是小孩,嘴下留情了。总之,我每次路过,都要竖汗毛,冒冷汗,被折腾得够呛。那狼狗对母亲则是摇头摆尾,显得异常温顺,它眼里母亲是自家人,我则是可疑的外来者。
院子尽头,九十度拐弯,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边上有一排平房分六间,坐东朝西,那是采购商店职工的宿舍。
南面过来第一间是老张头的,窗台上总是放着五颜六色的酒瓶子。作为店里“一把手”的老张头,寝室面对百米之外的商店大铁门,整个院子全在他的监视范围,便于他掌控全局。老张头老家是鄞县茅山,满口操着鄞县话,大约两星期回家一趟。他清癯的脸庞几乎看不到笑容,也许他天性不喜欢小孩,从没有跟我们说过话。空闲时不是去钓鱼,就是逗着狼狗玩。
隔壁是母亲的居室,也是母亲的家。为何不敢称我的家,因为我没有钥匙,我不住在这里,这个家似乎与我不搭界。但母亲的家,我曾住过两三年。那年到上学年龄了,我不得不从养母家回归,正儿八经跟母亲住在一起。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煎熬,就像习惯飞翔的小鸟突然被系上绳索,扑棱着翅膀飞不出去,自由的天空骤然消失。虽在同一个镇上,离养母家也不远,但我被母亲严格看管,轻易不能去养母家,要去也得经过她严格的批准,孤独和痛苦让我整天郁郁寡欢。两三年后,我这只野性十足的鸟雀被采购商店的环境和母亲家的约束给完全驯化了,时间改造人,让我脱胎换骨,变成与从前全然不同的我。没过几年,弟妹们也到了上学年龄,母亲这个20 多平方米的家再也容纳不下家庭其他成员,于是,向镇上的胡姓人家另租了间房子,年租金18 元,供我们兄妹仨入住。
自此,我们家分隔两处。母亲家成为总部,那里放置着父母结婚时的全套精致家具,代表我们家唯一的固定资产。这总部是父母商讨家庭要事的指挥部,又是我们这艘家庭大船的掌舵舱。由于去母亲家少了,那里渐渐蒙上了一种神秘色彩,房内总散发出一股醇厚的樟脑丸气味,这气味像是从悠远的旧时光里飘过来的,我猜想,里面珍藏着父亲的抗美援朝史、母亲的青春热血史,也珍藏着父母的恋爱婚姻史、我们四兄妹的出生成长史,定然还珍藏着父亲的冤屈史。
从60 年代初至70 年代末,我们六口之家居然没有产权房,是镇上真正的无房户,这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母亲一直很淡定,从没为此操过心,生活也没发生什么异样。那个年代,这样的境况,肯定不只我们一家。已经拥有一份国家安排的工作,拥有一处公家提供的居室,再自己出钱租了一间民房,母亲早心满意足了,孩子多一点不愁,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再走过去是丁小彪的寝室。印象中他总是紧闭门窗,进出像院子角落的老鼠悄无声息。这是一位老实猥琐的可怜人,是长期来的政治环境压迫造成的。丁小彪在采购商店干着最辛苦的活儿,大凡最脏最累的物资装卸,都由他一人包揽,别的人常常袖手旁观。据说那年评“黑五类”,供销社给采购商店下达一名“坏分子”指标,七名职工要投票选出一人,于是大部分人把票投给了丁小彪,理由是他平时总是鬼鬼祟祟的,而且有人看到他偷过收进来的鸡蛋,还偷过出纳抽屉里的钞票。老张头要母亲出来做证人,检举揭发丁小彪偷钱的事,但被母亲断然拒绝了,母亲认为没证据是冤枉人家。老张头事后对母亲耿耿于怀。丁小彪理所当然成为采购商店的“阶级敌人”,每次搞运动,必定把他当“替罪羊”推出去。日子久了,众人眼里,丁小彪长得真像阶级敌人。
第四至第六间是大通间,中间的两道分隔墙被拆除,这样可以住很多人,平时多半空置,每当政治运动来临,供销社下属各单位的“牛鬼蛇神”们都来这里参加学习班,开展思想改造。参加学习班的人吃住在里面,态度认真而诚恳,我在那里看见好几位同学的父亲,但我假装不认识他们,避免由此带来的尴尬,那时谁能轻易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来这里参加学习班,环境安静,又能避人耳目,每个人都放下尊严与架子,互相袒露灵魂,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斗争与批判,也接受组织对自己的挽救与改造。学习班效果好坏,取决于每个人写的斗批改材料是否深刻,以及觉悟程度是否高低,外界的人谁都不知道。
屋内是严肃沉闷的政治环境,屋外是轻松快活的自由世界,但屋外的世界不属于屋内的“牛鬼蛇神”们,那时他们绝对没这份雅兴。
春天,院子里草木葳蕤,遍地是蓬勃的野花,成群的蜜蜂嗡嗡地缠着蚕豆花,妖艳的蝴蝶也出来争抢春光;夏天,柳树上的蝉儿从早到晚鸣奏着背景音乐,草地上和墙垛上结满了可爱的大冬瓜和南瓜,还有老张头种的西瓜和黄瓜,各种瓜看着就让人眼馋;秋天,待院子里的玉米丰腴饱满时,我们偷着掰下来,用火烤着吃;冬天是捕捉麻雀的黄金季节,仓库后墙的房檐上,每个洞穴里都藏有鸟窝,轻易就能捉到好多麻雀,还能在雪地里用竹筛子捕麻雀,用铁笼子捕黄鼠狼,让人惊心动魄。冬春时节,仓库后墙根一带长着密密麻麻的野芹菜,怎么割都割不完,那是学校兔场里的兔子最喜欢吃的上等草料(我们每周两次割兔草送学校),为此屡受老师的表扬。
4
由于母亲拥有特征明显的讲话口音,加上受到父亲事件的牵连,那些年里,为避免惹外界的麻烦,她低调做人,谨慎行事,尽量不卑不亢。采购商店共有七名职工,他们在彼此熟稔的圈子里,构成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公家单位,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谁也不会错位,一旦错位,这个生态圈就会动荡,就会破坏和谐。
我们哥俩在无聊的时刻,会模仿梁山好汉排行榜,给店里的七个人排座次:老大非老张头莫属,一店之主,一言九鼎。老二是老徐,是个老干部,讲话慢条斯理,曾被划为“右派”,经常被叫去参加各种学习班,后来在采购商店没待久,转了岗位。老三是高个子陈云飞,喜欢吹牛,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老四是母亲。老五是快人快语的江上游,退伍军人,大部分时间身穿绿军装。老六是阿贤叔,身材魁梧、为人憨厚、沉默寡言,家里有个患间歇性精神病的儿子,怪可怜的。有次我们去卖旧纸箱,里面裹了块石头增重,被他过秤时发现,他竟没向坐对面的母亲告状,悄悄把石头扔了,当啥事也没发生,这件糗事让我们兄弟仨愧疚一辈子。老七自然是丁小彪,是条多余的小尾巴,像是革命队伍中的落后分子。母亲恰好处在中间,在采购商店这个社会小阶层里,她的地位和人脉还算不错,这给我们带来了些许安慰。
父亲在五七干校后期,鉴于政治形势的缓和,政策也逐渐宽松,被允许半月一次回家。每逢父亲回家的那个周末傍晚,我们全家会按捺不住跑到采购商店的马路边,伸长脖子,兴奋地眺望县城方向,看父亲风尘仆仆骑着那辆28 寸“凤凰”,从遥远的五七干校归来。只要父亲一回到家,家里饭桌上的菜肴肯定丰盛,母亲喋喋不休的责骂声自然收敛,而且她会面漾笑容,说话和气。采购商店的院子里也弥漫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气息,连平时形单影只的丁小彪这会儿也偷偷钻出来,嘿嘿地笑着与我们搭讪,分享我们家庭的快乐。
许多人被历史伤害后,选择把这段历史隐匿,不去触动,也不去回想,更无意让后人知道,宁愿自己永久遗忘。比如我母亲,她对父亲去五七干校前后的经历就从不向我们提及,她认为父亲在“文革”中遭遇的磨难,是他人生中无法接受的屈辱。尽管后来组织上为父亲彻底平反,并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和行政职务,但父亲辉煌的人生履历上却铭记着这段痛苦的经历,它在母亲精神上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消除的。如今岁月更迭,过往的痛苦都早已被时间疗愈,唯有那段苦难的历史,我们谁也不会遗忘,尤其是母亲。
5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采购商店是芸芸众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去处,那里每天向外收购着形形色色的物资,这些物资,展示人们的劳动硕果,增加家庭的额外收入,也给孩子们换取许多零用钱。镇上的居民和乡下的农民谁没有跨进过采购商店?谁不认识讲话南腔北调的我的母亲?
也许是环境的耳濡目染,也许是母亲经常告诫的缘故,我们从小领悟了劳动创造幸福的朴素道理。空闲时间,我们常去农机厂大门外捡废铜碎铁,积攒多了,卖给采购商店;初夏夜晚,去周边的水田、沟渠里捕捉野生黄鳝,翌日卖给采购商店;夏天中午,拿着铁钳去镇上各处捡桃核,捡满一篮子了,卖给采购商店;秋冬时节,去公路边的苦楝树下捡苦楝果,装满一麻袋了,卖给采购商店;冬天,母亲竟然把晒牛皮这样的活儿也给承包过来,那是别人都不愿干的脏活儿累活儿,每张牛皮晒干给四毛钱,共有几十张,母亲觉得是一笔大收入,却忽略了它的艰苦程度。那些全是水牛皮,又大,又厚,又笨重,又臭不可闻。太阳升起时,母亲带领我们把一张张血淋淋的水牛皮从仓库里吃力地拖出来,摊晒在采购商店院子内外。中午时分,我们给牛皮逐一翻面。太阳西沉时,又把晒过的牛皮一张张折叠起来,这时的牛皮干硬得要命,感觉倍加沉重,折叠时得费九牛二虎之力,然后再一张张拖进仓库。第二天重复这样的动作与程序,一连得晒四五天,才算彻底晒干。每晒一个周期的牛皮,我们全身的臭味得遗留好多天,尤其那双手,怎么搽肥皂都无济于事。每张水牛皮的重量,都超过我们当时十二三岁人的体重,这是超极限的劳作,就像蚂蚁搬大山,干得实在不容易。这晒牛皮的活儿,母亲总共揽过三次,第四次我们说啥也不干了。
那些年,我们兄妹通过艰辛劳动,换得可观的零钱,用来补贴家用,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有了自己的积蓄后,我们会经常跑到供销社书店,挑选心仪的连环画,一本本买回家来阅读,这是少年时代无与伦比的幸福与快乐。我们家的连环画藏书量在镇上数一数二,几乎可以再开一家连环画书店,我们曾引以为傲。
60 年代初,母亲怀揣着梦想与激情,从大东北来到南方小镇,落脚在采购商店,留下跌宕起伏的足印,直至后来完成人生蜕变。而70 年代初,我是带着惶惑挣扎的心理,从养母家无奈回归母亲家,同样落脚在采购商店,留下少年艰涩的足印。不同年代的两代人殊途同归,但目标和过程迥异,母亲背负的是改观整个家庭命运的重任,我仅仅负责改造个体的那部分责任。所以,这是母亲的采购商店,也是母亲的精神领地,我仅是她精神大树上繁衍的一根枝丫。我想,地理意义上的采购商店早已被时光湮没,但精神意义上的采购商店却永远驻守在两代人的灵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