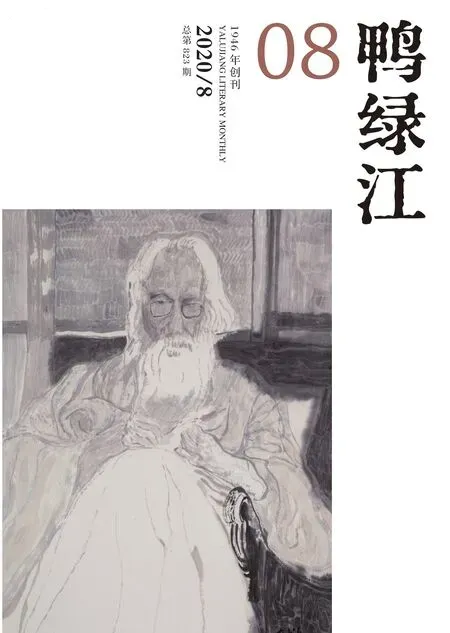匿迹
楸 立
漫天的大雪刚刚停下,大烟炮就顶着脑门儿呜呜地刮起来,风卷起大团大团的雪末,吹得林子里的松樟发出饿狗绝望般的呜咽声,隔着关着贼严的樟木木门,窜进满屋人耳朵里,让人听着心里发瘆。雪粒子一鼓劲儿向木屋里涌,却被三寸厚的门板挡在外面,不大会儿,木墙底下就堆起了半尺高的雪。
三间大木屋里大叶子烟的味道呛鼻熏眼,角落里挤满了屯子里的男女老少,或站或坐围拢在火盆周围,个个一言不发表情凝重。
里屋火炕东角,奎子爷的铜锅大烟袋吧嗒吧嗒地嘬成了一个点,像是夏季房屋漏雨的声响。人们你瞅我一眼,我瞅你一眼,嘴唇都抿得结实,生怕自己的目光和表情带出什么来,更多的人闷着头。屯子里那个叫拴柱的后生,挪动了一下棉靰鞡,嗓子干咳了一声,张嘴想说句什么,抬眼看到对面正揣着手瞄着他的自家娘们儿,瞪着个虎眼瞅着他,他心里一个寒噤,话到嘴边,又生咽了回去。
咣当一声,门被撞开了,冷风推进来两个浑身披雪的屯里人,屋里的人目光齐刷刷地聚过去,奎子爷和几个屯里人几乎异口同声:“怎么样?怎么样?”
进来的两个人在地上用力跺了跺脚上的雪,前头的那个解掉头上的狗皮帽子,脑袋顶上顿时冒起腾腾的热气。他摇晃了摇晃脑袋没有言语,蔫头耷拉脑地蹲到了一旁。
“咋办呢?”拴柱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冒出一句。
屋里所有人把眼光重新盯着老奎爷身上。奎子爷斜靠在火坯墙上,微闭着双眼,最后一拨巡山人也没有带回一丝消息,浇灭了他心中的最后一点希望,他从木板凳上坐了起来。
“这个东西南北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大家再想想还有哪个旮旯咱们没有走到?”奎子爷用眼撒搭了下可屋的人,屋里人又被他的眼光扫矮了一层。
炕头上。麻子婶的眼泪哗哗地掉:“他爹呀,你这是在哪里呀?你说你死我也得给你找到尸首哇。”屋内其他几个妇女有陪着掉泪的,也有人不住地解劝。
女人们唉声叹气男人们无可奈何,这茫茫的兴安岭,这山高林密的雪原,加上这个鬼天气,撒进头黑熊都找不到踪迹,上哪里寻个人去呢?
外面的风折腾了会儿,也开始懂世故似的安静了不少。屋里人开始七嘴八舌,这一句那一句,有的带着牢骚和埋怨,埋怨老天,也埋怨找不到人影的孙麻子,干什么都是独来独往不和群。
炕上偎在被摞上熟睡的憨妮醒了,她瞅了瞅屋里满满的人,从早上到现在,这些人都在自家窝棚憋着,人这么多,觉得好有趣,同时又感到与己无关。她又拿起她的玩具:一盒洋火柴。将一大把长火柴棍儿握在手里,然后从手里抽出,一、二、三、四、五……不停地呢喃着,数完一根就重新放到火柴盒去。
人们无处可放的目光都落在这个弱智女孩的身上,麻子婶和几个当家子女人脸上有些尴尬。年轻的堂嫂推了憨妮一下,瞪了一眼:“妮,别数了,没看都急着吗?”
憨妮倚在麻子婶后背上,白了堂嫂一眼,又十、十一、十二、十三……继续数自己的。麻子婶嚎嗓了一段,挪了一下屁股,那个憨妮身子仍旧依歪在她的背后,麻子婶止住声,转过身来,“啪”地把憨妮的火柴打落到炕上。“数,数,天天数,你大回不来,你连饭都吃不上了。”
憨妮显然不曾提防,瞅着散落满炕的火柴,干呵呵几声,像是笑又像是受了委屈,她呆了会儿,翻了翻单眼皮,然后下意识地用袄袖子擦了嘴上的哈喇子。
“大,大,回不来了?”她问了大娘,却没人理她。“大,大,会回来的,会回来的,会给妮弄狍子吃的。”
“你大,快两天没回了,给你弄狍子肉,甭想了。”麻子婶没地方撒气,把话全泼给了屁事不懂的憨妮。屋里人听着心里滚烫滚烫地难受。有人扭过头去,有人发着叹气的声音,有人偷着擦眼泪。
“大,大,哇!”憨妮醒过味来,四肢摊开腿脚乱蹬,扯开喉咙,嚎嗓起来,这次哭声是来真的。
奎子爷吼了她一声:“傻妮,别添腻歪!”
憨妮许是被奎子爷的嗓门唬住,一下子就止了声,胸口不住地起伏,大粗脖子两边扭了又扭,脸上显现出一副愤愤不平的表情。
“大,我去找大!”憨妮嘴里嘟囔了一句。
“快一旁待着!”奎子爷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躁,吼了一嗓子。
憨妮对奎子爷惊天霹雳的吼声,没有一丝惧怕的意思,她有些不痛快,一骨碌蹭下炕来,在火炕下边找到自己的靰鞡,然后费了好大劲儿才套到脚上,边提鞋边说:“我自个儿找大去。”说着就向门口跑。
麻子婶歪头瞅了眼奎子爷,又撇了下憨妮,满是疑惑。堂嫂本来就不稀罕这天生憨傻的丫头,过去拉扯住憨妮的小手爪就往回扽,憨妮使劲挣脱,可显然不是堂嫂的对手,她不停地反抗,嘴里发出嗷嗷的叫声,让人听着愈发心乱。
奎子爷在一旁,仿佛看出点什么名堂,分开身前的两个人,蹲下身子盯着憨妮:“傻……憨妮,你真知道你大在哪儿?”
憨妮趁机从堂嫂手里解脱出来,眼泪啪嗒地掉了一大颗,对眼前屯子里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重重地点了点头。
奎子爷脸上露出异样的光彩,抬手,招呼旁人:“来,给憨妮捂巴好了,跟着她。”
麻子婶找出一顶皮棉帽子扣在憨妮头上,又把一条厚毛巾给她围在脸上,憨妮就着麻子婶忙活的机会从炕上划拉划拉一大把火柴棍,塞进口袋里。
门外西北风停了,微弱的阳光从阴霾的云层里挺出来,天放晴了。奎子爷喊,柱子你背着憨妮。拴柱俯下身子,憨妮推了柱子后背一下,摇了下头,迈了一步子,小嘴囔囔地叨唠着,一,又迈了一步,二、三、四……人们跟在她的身后,排成了一纵长队,向山里走去。憨妮数到了一百步时候,从右边口袋里拿出一个火柴棍放到右口袋里,然后又一、二、三、四……
一溜人走出屯子,走过了大柳子河,曲里拐弯就进了莽莽山林,嗬!这北方最广袤的林海雪原呀,无垠的苍茫世界。
憨妮走路的样子又滑稽又相当吃力,有几次险些出溜倒,奎子爷在一旁,时不时地推着拽着她走上一段路。队伍一大长溜缓缓登上了一道高冈,人们站立一排,奎子爷面朝皑皑白雪和黑山密林跪了下来,人们跟着他跪了下去,密匝匝排满了整个山头。
奎子爷挺起腰板,双手作揖,向着远方的山林喊着:“山神爷,你给俺们指条路呀,都是你的骨肉血亲。山神爷!你发发慈悲,都是喝你的奶水在你身上打滚亲人哪。”
随后,男人女人们跟着奎子爷唱了起来:“山神爷,你醒醒神,
白山黑水哺育你的苦难子孙。
山神爷,你亮亮眼。
沟深林密保佑你的血脉族民
……”
2
麻子是在大雪封山前一天下午进的山,他在收音匣子里听到要变天的消息,便想抓紧进山再打点活物存起来。他背着猎枪出家门的时候,麻子婶剜着他耳朵叮嘱:“马上变天了,转几遭就回来。”
麻子嘴里应承着,看了眼炕上玩火柴的憨妮一眼,说了声:“妮子,晚上大给你弄狍子肉来,等着啊。”憨妮放下火柴,嘿嘿笑了笑几声,嘴里“哦”地应了一声,麻子转身背上砂子枪出了村子进了山。
麻子运气真还不错,半天时间打了五只稚鸡。麻子欢喜,大年根底了,到集市上卖点钱,换点年货给自己和憨妮添置点新衣裳。
一想到憨妮,麻子就想到了自己的二兄弟,本来日子好当当的,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先天智障的孩子,唉,麻子想想都是愁肠,索性就不去思想了。
麻子每回进山都不空手而归,屯里人都羡慕麻子的运气,便有好事的人想套出麻子个究竟。孙麻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别人问,嘴上吞吞吐吐指东说西,话说得不顺溜,满脸的麻子也愈发红。屯里人骂一句孙麻子,孙麻子就觍着脸笑笑,别人也没有办法。幸亏麻子心独手上不独,总会将榛蘑雉鸡那些不太值钱却能堵人嘴的山货拿出来与屯子里的乡亲们分享,屯里人也就不好和他计较了。
麻子抬头见太阳被大块黑云挡起来的时候,抓紧向回走,可在这时候,前面一阵声响,情况就出现了,在前面岩壁上站立着一只半大不小的狍子,它仿佛在眺望远方,又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麻子心中一阵悸动,比如山狍皮子可以给憨妮做个小皮褥子,比如叫上奎子叔、拴柱架上篝火好好地烤上一顿美餐,比如狍子汤是多么汁浓味鲜……麻子猫腰将打的猎物轻轻放到地上,手中的猎枪稳稳地端成水平状态。可这时儿,那只山狍感觉出什么似的,闪到一块巨石的另一面。麻子也移动方位,紧紧地盯住它,他的食指已经搭在了扳机上,随时可以搂火。那只狍子仍然没有一丝逃跑的迹象,它又稍稍扭动了下身子,正对着麻子这边,两只黑亮的双眼直视着麻子的枪口。狍子明亮的目光中充满着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麻子心口仿佛被什么东西尖尖地刺了一下,他脑海闪现出许许多多的内容,哎呀,他脚下猛然一空,脑袋天旋地转,身子坠了下去。
3
孙麻子的二弟是当兵退伍落户在绥芬河的。孙家兄弟三个,老二能留在城市工厂成了公家人,孙家自是欢喜得不得了,麻子在屯里逢人就说:“敬山吃城里饭了,老二光宗耀祖了。”
孙家老二没过几年就娶了绥芬河的女人,模样好看,也有文化,脸上戴个眼镜挺文气,结婚头一年,孙敬山带着媳妇回来在屯子东头西头地一转,更让老孙家门楣上添了光彩。麻子带着兄弟、弟媳妇见着村里人大呼小叫,这咱奎子婶,那是你东旺大爷,老二当兵的时候,你东旺大爷套着枣红马送到县里的。
一年后,麻子接到了老二写来的一封信,信里说想让大哥大嫂去城里住几天。孙麻子看完信心里乐开了花,拿着信和媳妇说:“你看老二非得让我和你去城里住住,这大忙忙的能去吗?”
老娘们儿终是心细,撅着腚正在灶锅上贴饼子,她眨了眨眼睛,思忖了一会儿:“这也不过年不过节的,干吗想起来让咱去城里待几天?”
“嗨,咱们屯子忙,人家城里那日子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呗。”
“我看不像是让咱们去享受去,老二家里头那是什么人呀,识字多,心眼小气得没法,过年回来都不带捎点腥活儿的,能让咱去白吃白住?。”
麻子没吱声,心里一盘算,这娘们儿说得还是有些道理,就把信重新塞好放在炕席下面了。
本来麻子没上心里去,可没过几天,老二的电报又到了。
孙麻子和媳妇儿把家里的事儿和老三交派好后,大包袱小包裹地上了路,先是奎子爷的马车,再搭了乡里的一辆拉货的嘎斯,再到了克拉新旗站上了绿皮火车,这火车坐了个晕头转向,咣当咣当了一整天才到了绥芬河。 俩人走出车站后,这花花绿绿高楼大厦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两口子正犯着蒙,听前面人群里有人喊:“大哥,大嫂。”才看到孙敬山在对面推着个自行车接他们来了。
三个人走了多半个小时,才到了老二家两间半的小屋。麻子一看,这哪是人家呀,还不如自己的窝棚宽敞。再一看老二媳妇怀里的孩子就明白了一半,原来老二家生了。
麻子媳妇问:“多会儿生的呀?”说完就想过去抱抱。
老二家脸上一红,往后直躲,弄得大嫂扎着双手挺不得劲儿。敬山忙过来说:“大嫂,大哥,先吃饭先吃饭,吃完饭我再给你们说叨。”
麻子和媳妇没滋没味地扒拉着饭,弄不清怎么回事儿。吃完饭后,老二把哥嫂让进了里屋,四个人,不对,是五个人。老二和老二媳妇,还有老二媳妇怀里的孩子。
“大哥,大嫂,是这么回事,这孩子生了仨月了,是个丫头,本来觉得为咱老孙家添了个人口,可是我和你弟媳妇吧,怎么看着孩子都不对。”
麻子媳妇心里早起疑了:“咋的啦?”
老二媳妇这次挺主动,给大嫂抱了过去,大嫂,你端详端详。
大嫂将孩子接过去,麻子也歪头凑了过来,孩子脸上红扑扑的,麻子没看出什么,大嫂倒是非常懂行,解开襁褓,把孩子的手拿出来,两只手仔仔细细地看。
“哎呀,”媳妇嚷了一嗓子,把麻子吓了一跳,“怎么咱家也摊上这事儿呢。”
麻子还是没看出来,狐疑地瞅着媳妇,说:“这孩子不很正常吗?”
“你懂屁!”媳妇说。
麻子扭过头看着自己的兄弟,老二低了下头:“哥,这孩子有毛病,是天佬儿。”
“天佬儿?咱家祖上也没出过这样的人儿呀!”麻子也知道“天佬”怎么回事儿,他说完也有些后悔。
“大哥,就是染色体综合症,不属于遗传。”兄弟媳妇怕大哥大嫂想的多了,也是为自己分辨。
麻子媳妇面色凝重,说:“老二家里呀,是不是怀孕的时候吃了什么药?或者是吃了什么好吧三的东西?二道沟子牛大白活的媳妇就是怀孕时候不注意,吃了不好的东西,那娘们儿人才不济呢,就是好吃。”
“没有,没有。”老二媳妇急得眼泪快出来了。
麻子瞪了媳妇一眼:“别瞎掰了,孩子现在这样了,老二俩人叫咱们来,肯定有事商量。”麻子回头问对面那俩人:“大医院有法子不?”
老二在膝盖上摩挲了两下手:“现在世界上还没有治愈的先例。”
麻子一听说是“世界上”三字都出来了,就清楚孩子这病到哪儿都没法子了,这老二家本来挺鲜亮的日子,摊上这孩子真麻烦了。
老大媳妇怀里的孩子这时候睡醒了,眨了眨眼睛,麻子抻着脖着实看了看,这一细看就觉得确实与平常的婴儿哪哪都不一样了。老大媳妇说:“这孩子倒是挺听说的。”
孙敬山瞅了媳妇一眼,呜呜囔囔地说:“大哥,我和你弟媳妇这么想的,这孩子在城里也不好养活,你弟媳妇还得上班,她爹妈又上点年纪带不了,孩子这情况真还不能打了撒手,我这不想和你商量商量,这孩子就是讨咱家债来的,让我给摊上了。”
麻子和媳妇听着老二的话儿,不明白老二怎么个意思,俩人就低头听老二下文。
老二咳嗽了一声,清了下嗓子,欠起身,对麻子说:“大哥,你出来说。”
麻子抬屁股就起身跟着出来,他回头瞧了瞧家里头,麻子媳妇眼睛狠狠向他眨了眨,嘴角又撇了又撇,麻子也弄不清她这表情是几个意思。
到了外屋,老二凑近了麻子跟前:“大哥,我想把孩子扔了。”
扔了?麻子脑瓜皮发奓,他没想到老二嘴里能吐出这么凶狠的话来。
老二满脸的苦大仇深:“我咨询人家大夫了,这样的孩子怎么也活不长,早晚也得坑咱,与其养大了难受,还不如现在……”
麻子脑袋嗡嗡的,脸上的麻子在暗黄的灯光下显得更重了。
麻子和媳妇儿晚上挤在老二家的小南屋里,思前想后。媳妇咬着他耳朵不停地叨叨叨。
“这老二家真是没安什么好心,你扔就扔呗,干吗把咱千里迢迢叫过来,告诉你,老二再怎么嘚嘚你,你也别拿主意,听了没?你听了没?”
麻子心里烦着,自己这个大哥也算是一家之主,怎么拿这个主意呢?真把孩子扔了?那也是条性命呀!不扔,养个十年八年再糟践了也是白养活了,这小户人家谁经得起这么折腾?
麻子见媳妇还在耳朵边吵吵,用屁股顶了一下娘们儿的身子:“没完了是不?我是大哥,老二把咱叫来也是理当的事儿,你说谁家遇到这个能不闹心呀!”
“你听着,再怎么也不能扔了这孩子,这个主意你别拿,要扔让老二自己扔去,坑财害命遭老天报应,再怎么说也是一条性命,亏他两口子想得出来。”媳妇儿说了一句,气囊囊地转过身去,给了麻子一个大后背,不再搭理麻子。
麻子没吭声,在心底深深地叹了口气。
麻子和媳妇抱着孩子回了屯子。老二媳妇拼命似的给大嫂包袱里塞着以前不穿的各种款式的旧衣服,大嫂大嫂叫个没头。
麻子媳妇脸上起着黑雾,嘴里有一句没一句的。麻子抱着孩子低着头不敢抬,敬山说:“大哥,每月我给你邮三十块孩子的生活费去。”
麻子“嗯,嗯”随口应着,像做了亏心事儿似的,这没和自己的娘们商量,自个儿就擅自做了主,回到屯里就是个麻烦。但自己这个大哥到这里了,真看着老二俩人作难也不好受,孩子回屯里养着无非多添了张吃饭的嘴,能养到哪儿算哪儿,总不能像老二说的那样扔了呀!
火车走了多一半的路程,麻子媳妇都没搭理麻子,其间麻子上厕所想让媳妇抱抱孩子,娘们儿嘴里不干不净,滚一边去,当着火车上的好多人给了麻子满脸的不露脸。
麻子没辙,他清楚这是刚刚开始,让媳妇转过弯来需要过程,麻子瞅着怀里的孩子,想,我说妮子呀,我上辈子哪位先人做了什么孽障事儿呢,你来到我们这穷主真是枉来一场,让我这辈给摊上了。得,尿再憋会儿吧。
又过了会儿,孩子好像是饿了,在襁褓里扭动,麻子尿憋得也够劲儿了,孩子这一闹,也没法子,摆弄孩子还得靠女人。麻子用胳膊肘碰了碰媳妇,说:“他妈,过来看看,过来看看。”媳妇倔驴一样尥了个蹶子,嘴上迸出一句话:“你自己招惹的,你自己管。”
麻子的汗下来了,噘嘴瞪眼着急还带央求,可媳妇就是无动于衷,害得周围坐车的人都过来看麻子两口子。
气氛有些滑稽又压抑,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了。麻子女人气势汹汹地扭过身来,一把抢过孩子,去尿你的泡去。
4
憨妮三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只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大,娘,哥,姐,从不多出一个字。麻子女人嘴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可对孩子不马虎,该管还管该疼还疼,按她的话说,当个小猫小狗养活吧!
老二头一年还不错,到月头上给大哥打点生活费,或者邮寄点孩子穿的衣裳,往后越来越没动静。麻子女人就和麻子叨叨,不行给老二送回去,在咱家什么事儿,孩子成咱家的了,他们两口子在城里吃香喝辣的,弄个累赘给咱了。麻子没办法,清楚自己的兄弟办事儿是不地道,屯里虽然花销小,但进项也少,大儿子在锦州上技校,丫头上初中了,这都是钱呀!女人缝完憨妮的小褂,让憨妮钻了被窝睡着。女人说:“等换了单衣裳给老二家送过去。”
麻子说:“怎么送?”
“怎么来的怎么送。”
“你送。”
“去你王八操的,你弄的你给我送过去。”麻子女人口气能宰人。
麻子就又不敢吱声了。麻子女人兀自咒骂着老二家不是人,老二媳妇前辈子做了坑人害人的事儿了。
麻子第二天徒步去了镇上找了个电话亭,给老二打电话,打了好几回,老二那头才接电话。麻子说:“敬山,你这段工作行么?”
老二说:“大哥,我忙得很呢,单位要改制了,媳妇又怀上了马上就要生了,生完我告诉你。”说完哗啦就挂了。
麻子举着电话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麻子接着又打,嘟嘟嘟,这次是敬山媳妇接的,老二家说话声音很轻:“大哥呀,大嫂好呗?我正在做饭,前一段去锦州老二去看了小辈(小辈就是麻子的儿子),小辈长得高了,我给小辈买了不少吃的东西,小辈……我有些肚子疼……哎,就这样大哥……”电话哗啦又挂了。
麻子这个堵心,俩人故意不提憨妮的事儿。麻子生气了,麻子心说,这俩没安好心的玩意儿,我真得就给你送回去,瞧你们怎么办!
麻子嘴上说,可仍然没有付诸行动,这又坚持了一年多,转眼又快忙秋的时候,麻子终于打定主意送憨妮回家。走的那天,麻子领着憨妮上了马车,憨妮说:“大。”亮亮的大眼珠一动不动地瞅着麻子,麻子不敢看,闷头抱起憨妮就上了马车。憨妮坐好,回头望了眼麻子女人,娘,娘,大眼又忽闪忽闪。麻子女人站在门口被憨妮这一喊,身子晃悠了一下,鼻子一酸,捂着脸进了屋。憨妮看到姐还在门口,喊,姐,姐。姐抿了抿嘴唇,几步跑到憨妮近前。“妮,别想姐姐,给你火柴,继续数,数到一百告诉姐。”憨妮大眼忽闪忽闪,表情挺糊涂又像特明白。
麻子到了镇上等了半小时的客车,上车前给憨妮买了颗棒棒糖,憨妮新鲜得要命,用舌头时不时地舔一下,舔一下自己就憨憨地笑几声,惹来周围乘客都看过来。麻子摸了憨妮的后脑一下:“别笑了。”憨妮就不敢笑了。
到了旗上又转坐了火车,这时已经过了晌午的饭食,麻子的肚子瘪得开始叫唤了,脚下的憨妮瞅着小吃摊不错眼珠,清楚孩子也饿了。麻子给憨妮买了几个包子,自己就吃了一个,等憨妮吃饱了,麻子又抱着憨妮到了车站的电话亭,掏出五毛钱给老二家打电话。
这次是老二家接的,麻子说:“他婶,我在车站呢,再过半个钟头就坐上火车了,带着憨妮来的,孩子不小了……”
麻子后面的话就是说,孩子不小了,你们也该自己养着了,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憨妮一年到头生病闹灾的也是不少的花销,我这日子也艰难着呢。麻子的这些台词在肚子里骨碌了好几天了,可还没朗读完,那头兄弟媳妇就吼起来了。
“什么,你带孩子来的,你怎么着?你怎么着吧?”电话那头兄弟媳妇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我们都和你说了,我现在带着二的,什么都做不了,你兄弟那边挣个钱给领导低头哈腰看人脸色,忙得跟鬼一样,你说有你们这个当哥当嫂这么干的吗?你们成家时候,老的怎么管的?敬山不就是自己给自己娶媳妇置房子置地,我们有了这个傻孩子,让你管着,就这么两年日子紧张没给你邮钱去,你们就这么狠心把孩子给我送回来。你们送吧,你甭来,来了我们也不要,你们最好把孩子扔了,扔山里去,扔车站上,让你们老孙家孩子快点死得了。”
老二家炒料豆似的电话里说了这一大套,本就笨嘴嗑舌的孙麻子在电话里一点插不上嘴,那头一见停歇,麻子说:“他婶……”俩字还没说干净,电话啪地就挂了。
麻子拿着电话愣了半天,公用电话亭里的小老板一脸漠然,一块。麻子醒过味来了,不是五毛吗?时间超了,一块。
既然兄弟媳妇拿着不是当理说,麻子心一横,掰开脸了我照样给你们送回去,你家的孩子你不要谁要?城里人真冷血。麻子后悔兄弟娶了个城里的女人做媳妇,就应该娶个厚道的屯里人。
孙麻子领着孩子上了火车,刚找到座,憨妮就嚷嚷:“大,大,水。”
麻子正闹心,冲憨妮就嚷了一句:“水,水,水什么你,就知道要吃要喝,现在都没人要你了,讨债鬼!”
憨妮被麻子发火的样子吓住了,咧咧嘴想号,麻子从提包里拿出装满水的大玻璃瓶子,倒在茶缸里,憨妮捧着,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喝完,憨妮喘了口长气,讨好似的喊了声,大。
火车又颠簸了六七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麻子抱着憨妮走下火车的时候,西边的太阳正在沉下山头,一长条灰色的云镶嵌了一层釉色金边,煞是好看,而山脚下的城市却很呆板。麻子眯起眼睛端详着眼前的景致,心想,屯里人在这种地方待着,连个脚印都留不下!
他背起憨妮,又给自己下了下狠心,迈步向前方走去。
麻子好不容易找到老二家,胡同的路灯都已经亮了,家里的门上了锁,麻子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憨妮坐了大半天的车也累了,偎在麻子怀里就睡着了。麻子坐在那里等呀等呀,不见老二家回来人,又等了两个时辰了,旁边出来个邻居,想来和老二家挺熟,问,你们哪儿的?
“老家的。”
“噢,他家两口子下午就出去了,看样子不回来了。”
“是么?”麻子说老二家真行,故意躲着,真做得出来。
“你们快点找个旅店住吧,孩子别沾凉。”邻居说完就进院子插门了。
麻子望着怀里的憨妮有些无奈,更多的是难过,这孩子才没福呢,你说要是好生生的,在城里一待,上幼儿园,上学,得多享福呀!
孙麻子再一想,敬山两口子也真歹毒,这是狼心狗肺呀,你不是不要孩子吗?我给你放着,看你要不要。
麻子打定主意,抱起睡得正酣的憨妮,轻轻把憨妮放在了老二家的门口,将衣裳包袱枕在孩子头下。麻子做完,一咬牙,扭头就蹽。麻子跑得飞快,他担心憨妮醒来叫他,喊他大,孙麻子对自己说:“别回头,这孩子不是我的,和我没关系,是老二家的,是孙敬山的,他就得养着,老二的孩子……老二的孩子……”
麻子跑到了车站,他感觉口干舌燥,找个厕所在自来水管里喝了几口凉水,又用凉水抹了几把脸。可心口还是七上八下地跳个不停,他找个空座倚上去就动不了劲儿,他闭上眼睛想静一会儿,可一闭上眼睛就是憨妮,睁开眼睛车站外面黑夜里也是憨妮的影子,“大,大,大……”
麻子捂住双耳,抱着脑袋,他感觉自己的脑袋快要爆炸,憨妮的声音如芒如刺扎他的脑浆子,他蜷缩在椅子下,身体不住地发抖。旁边过来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弯腰扒拉他一下,问:“咋的啦?”
麻子抬头说:“没事,没事。”
“生病啦,不行去医院看看。”这人挺热心。
麻子抱着头,痛苦不堪。
丢钱了?旁边有人过来插言。
麻子在地上喘了会儿粗气,最后再也控制不住,他跳起身来,冲出了车站闯进了黑得透顶的城市里。当他再次跑到老二家门口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没有,麻子急得脑袋发晕,他大声喊着,憨妮,憨妮,麻子四下里呼喊。
喊了一小会儿,就听不远处有人小声回,大,大……
憨妮,麻子顺着声音追过去,在前面昏黄的路灯下,憨妮屁股下面坐着包袱,手里拿着一把火柴棒,身底下散落了许多火柴棍,应该是数了一段时间了。孙麻子过去一把抱住憨妮,紧紧搂在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憨妮大眼睛眨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九十九……
5
麻子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山洞里,有六七米深,洞口龇牙咧嘴地敞着,外面好像起了风,麻子晃动下脑袋,感觉头没什么问题。他双手撑地想爬起身来,左腿发出钻心的疼痛,他定睛一看,裤子血淋淋的,撸开裤腿见小腿破了道口子,血已经凝住。他试了试抬了抬腿,疼得钻心,腿折了。他望了下洞口的天色,估摸自己昏过去了一晚。他强坐起身子,然后将内衣撕成条将伤口简单做了包扎。做完这些,疼了麻子一身白毛汗,他站不起来,对着洞口“哟,哟”喊了两声,声音到了洞口就被风刮没了。现在只能盼望有人来了,他首先要坚持下去,枪没有在身边,洞里幸好还有些柴草棍子。他半趴着身子,将树枝草棍扒拉成一堆,从口袋里掏出火柴,不错,几根火柴下去,火堆燃起来,麻子身上一暖,心里就舒服多了。他现在只有等了,等屯子里来救他的人。
天空阴沉沉的,他仰头从洞口向外望去,大雪下来了,大片大片的雪花飘了下来,不一会儿外面什么都看不出来,到处是白茫茫的雪和黑滚滚的天。
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憨妮自顾自地数着走着,已经翻过了三四个山岭,屯里人走得累了,问:“憨妮,往哪儿走呀?”
憨妮不理他,用嘴哈了哈手,拿了根火柴继续放到另一个口袋里,走,走,让背着他的拴柱继续向前。栓住喘着粗气对奎子爷说:“憨妮的话咱也信?这不带着大伙蹚山玩吗?”
奎子爷擦了把汗,喊:“都别问了,没好主意,大家都四下看着点,有什么痕迹没有,走,走,跟着走。”
又走了个把钟头,憨妮说,我得吃饽饽,麻子女人早知道这孩子胃口没底,嘴离不开吃。她拿出半张饼递给憨妮,憨妮找个被风的地方蹲下来就大口大口地嚼,人们哜哜嘈嘈说着什么。
憨妮才不管人们对她的议论,她嚼完最后几口大饼,从背风处走了出来,像个小大人似的,爬到山冈上,四下张望。然后踮着脚,嘴里“哟,哟”喊起来。屯里人都瞅着她,谁也不清楚傻丫头想干什么,有人心说,就这小嗓子,十五米都传不出去。憨妮喊了几声,就蹲下来,皱着个眉,堂嫂过来拉她,她仰脖子说:“大,睡着了。”
堂嫂不耐烦地拨拉她一下:“快起来吧!”
憨妮说:“走。”
拴柱过来蹲下身子,憨妮推开了他,大家又跟着走。没走几步憨妮忽然停了,奎子爷问:“又咋啦?”
“我要拉屎。”
麻子身上越来越冷,腿上疼痛倒是减轻了不少,麻子清楚腿上不疼不见得是好事,洞里的柴草逐渐烧干净,麻子眼里注视着面前渐弱的火团,又不时瞅瞅丈高的洞口。
麻子头脑昏昏沉沉的,麻子嘱咐自己别睡过去,他脑子不停地思想,想事儿,想家里头,想兄弟,想起了憨妮……
那年头伏,麻子女人回娘家了,家里就剩下麻子与憨妮俩人,麻子早晨给憨妮熬了锅山药粥。憨妮吃了两碗打了个饱嗝,麻子说:“妮,今天跟大去山里怎么样?”
憨妮高兴坏了,嗯,嗯,行,行。
麻子第一次带着憨妮进了山,憨妮九岁了,给麻子拎着水瓶,跟在麻子后面屁颠屁颠的。麻子也想让憨妮见识见识山里的风景,山里人不见见山哪行。
爷俩一前一后就上了路。憨妮手里攥着火柴:一、二、三……
麻子问:“妮,你数那个火柴干吗?”
“姐说了,数过一百就换别的数。”
“那你数过一百了没?”
“数过了。”憨妮狡黠地笑了笑,马上又有些不好意思,说,“没有。”
爷俩没话拉话地向山里走去。
麻子在山里转了好半天也没遇到什么猎物,麻子有些沮丧,憨妮倒是扽个花摘个蘑菇的挺开心。
麻子找了个石头,坐在上面擦了把汗:“今天点气不好,连个野鸡都没遇到,这个地方以前野兔山鸡多得很,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妮,看来晚上山鸡肉是吃不上了。”
憨妮手里拿着两朵蘑菇正在比当。听完麻子说完,嘴里冒出一句,能吃。
憨吧,麻子摇了摇头,勉强笑了笑。
憨妮扔掉蘑菇,走到麻子近前,用手一指山的一边:“大,听,鸡,鸡叫。”说罢,憨妮用手就拽麻子。麻子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过去,那是远在三四里外两山沟结合处。麻子以为憨妮在乱说,便去摆弄他的老猎筒。憨妮见麻子不动地方,嘟嘟着小嘴又说:“鸡,咕咕叫呢,鸡好多,走,大,走,大。”
麻子见时间还早,又见憨妮兴致很高,到那边瞧瞧也行,就当带她玩呢。憨妮前面带路走得很急,往树棵子丛里钻,麻子拽都拽不住。走了好大的一段山坷垃路,憨妮止住步子,喘了会儿,用手指了指前面。麻子正寻思孩子又犯了什么傻劲儿,用手摘了摘身上的树刺,不经意地顺着憨妮的手里瞧过去,我的个山神爷爷呀!麻子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那次麻子打了四只山鸡两只野兔,把麻子兴奋的不得了,麻子心里直犯玄,问憨妮:“妮子,你是咋知道那边有活物呢?”
憨妮一手一只血淋淋的山鸡,只顾咯咯地笑着,瞬时眼眉一紧:“大,我要拉屎。”
“去,去,到那边去。这孩子,吃饱就拉拉完就吃。”
麻子装好枪药,把地上的山鸡放进帆布袋,拄着枪等憨妮解完手出来。
过了一小会儿,旁边树枝呼啦一响,麻子以为憨妮出来了,他扭头一瞧吃了一惊,从草棵丛中钻出个东西来,鼻端黑黑的,下颌发着淡淡的黄,两只耳朵支楞着-----狍子。
狍子突然出现,让麻子有些手足无措,距离太近了。
那只小山狍子抬头看了下他,随即又扭动了身子,整个身体侧面正对着麻子,麻子小心翼翼地端起了猎枪,心说,正好,一枪就能打倒。
这时,憨妮出现在枪口的那头,她提着裤腰带,看着旁边一动不动的狍子,又瞅了眼前面的麻子,大眼睛眨了眨,喊了声:大。
狍子先是被憨妮的叫声吓了一个激灵,兀自站在那里不敢挪动。憨妮放下裤子用手抱住狍子的脖子,脸摩挲着狍子的脸,咯咯笑个不停。麻子被这一幕惊呆了,他缓缓放下枪,注视着眼前奇特的一幕。憨妮开心极了,不大会儿,狍子挣脱开憨妮的双手,醒过味来似的夺路逃走。憨妮瞅着狍子奔跑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
6
麻子面前的火光已经完全消失,那一团灰烬还散发着浓烟。洞底已经被雪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麻子又冷又饿,他抬了抬腿,撑起身子,看到洞口上方天有些蓝了,麻子哟嗬嗬喊了几声,喘了口气,又喊,哟嗬嗬。
麻子在心里祷告,山神爷,你保佑我,救我一命,山神爷,我麻子没做过亏心事,我死了,家里咋办呢,我以后再也不动山里的活物,哟嗬嗬,哟嗬嗬……
拴柱滚山沟里去了,老奎爷急得够呛,招呼小伙子们下去救人,费了好大劲儿,拴柱被人们弄了上来,还好,没有伤着骨头,只是破了皮肉。拴柱大哥不干了,说不能再这么瞎转了,为了一个人再把屯里其他人搭上不值,有几个人随声附和,说是呢,这要拴柱有个好歹怎么说呢。栓柱大哥和几个后生就嚷嚷着回屯里。奎子爷急了,抡了烟袋,说愿意走的都走,我这老骨头不想破了山里人的规矩,我这条老命不值钱,我自个儿去找孙金山。
屯里人不敢吱声了。
憨妮又带着人们在山里转悠了好久,连麻子的头发都没找到。孙家屯的人终于忍不住了,好几个人都停住了脚步说什么也不向前走了,奎子爷也按捺不住,薅住憨妮:“妮子,你大在哪儿你知还是不知呢?”
憨妮小眼珠转了转,摇了摇头。
旁边人气得直拍大腿,这半天合着陪着小丫头练腿呢,都回都回吧,没准麻子叔回家了。
大家气囔囔地坐在地上或依靠在树上,奎子爷叹了口气,瞅了一眼憨妮,拿出烟袋吧嗒吧嗒地嘬。
堂嫂过去就用手揪憨妮的小辫子:“死丫头,胡诌白咧,你看大家让你折腾的。”
憨妮“呸”地啐了堂嫂一下,然后俩手在身上两边口袋里翻弄,不一会儿把火柴都攥到手里,旁若无人地又数开了火柴棍。
奎子爷开始招呼几个腿脚麻利的后生,让他们先返回堡子,看有什么消息没。
憨妮数完了,站起来,用手推了小嫂子一把,走到奎子爷身边,口齿不清地说:“裤(奎)爷。火柴,对,火柴对。”奎子爷都没瞅她,说:“对什么对?”
憨妮一指被雪覆盖的灌木丛:“我在这里拉屎。”然后手又一指另一边:“大,在那儿抓鸡,还有一个火柴,大就出来了。”
奎子爷和周围人都被憨妮一席话给说得迷迷糊糊。麻子媳妇揣着手过来:“妮,你和你大来过这儿?”
憨妮使劲点了点头:“还有一个火柴大就出来了。”
麻子女人恍然大悟:“奎叔有火柴棍没,谁有火柴棍?”
旁边有几个男人都翻口袋,其中一个掏出一盒火柴,递给憨妮,憨妮憨憨地笑了笑,把火柴捡到手中,一、二、三……随后迈步走上了一个山冈,像个小指挥官一样,面向前方,她嘴里突然咯咯地发出笑来,笑得大家浑身发毛,以为这丫头又冒憨气,麻子女人拍给了憨妮一个脖掴:“又憨。”
憨妮止住笑声,哟嗬嗬,哟嗬嗬……喊了起来。麻子媳妇问憨妮:“你瞎喊什么?”
憨妮说:“娘,大,在喊我呢。”
麻子女人儿支楞着耳朵听了听,什么都没有,耳边只有呼呼的山风刮过的声响。
“发浪憨。”麻子女人说。
憨妮噘着小嘴:“大,哟嗬嗬,哟嗬嗬呢,就在那边,就在那边。”麻子女人顺着她指的方向,什么都没看到。
屯里人登上山冈,顺着憨妮的目光向前看,就是山和山,岭挨岭,茂密山林,什么踪迹都瞅不见。憨妮才不管他们,小嘴说得特有劲:“大,就在那边儿,在,哟嗬嗬。”
奎子爷上了火头,一把就将憨妮从山坡上揪了下来:“小毛丫头子,别给我胡扯,一屯子人让你耍把了。”
憨妮满脸视死如归相,抄起一把雪就摔到奎子爷身上:“大,在地里,哟嗬嗬,哟嗬嗬。你放的屁真臭,扑扑的!”
屯里人没有一个敢和奎子爷犟嘴说贫气话儿的,那是大不敬。这憨妮真不知好歹轻重,麻子女人过来想掴憨妮。奎子愣在当地,对麻子女人扬了扬手,惊奇地注视着憨妮:“你刚听到我放屁了?”
憨妮蹲在地上,点了点头。
奎子爷一拍大腿,跳起多高:“妮子,能听到我放屁,我的个山神爷爷显圣啦!”
麻子咬了口雪,心里就往坏里想,想自己这一辈子,想以往的事儿,爹娘在自己刚成家的时候就走了,把俩兄弟嘱托给自己,老二自己成家,虽说因为憨妮和自己断了道,但他城里算是享受幸福了,过得舒坦就行了,老三孙仰山家儿女也都成全了,自己这边,女人身体没毛病,儿女也能顾自己,就憨妮是个牵挂。人走到哪儿算哪儿吧,孩子养这么大了,我这个当大的也尽了义务。想起憨妮,麻子仍旧怪自己的兄弟,又一想敬山生活也不易,又转回来怪自己,当大哥的没带好头,这设身处地想了好多好多,再瞅瞅头上的洞口,麻子彻底绝望。
他头脑晕眩视线越来越模糊,他昏沉沉的,像是做了个梦,挂在天上的洞顶探出一个山狍的头来?是自己刚才要打的那只吗,还是那年和憨妮碰到的那只?
麻子浑身没有一丝气力,那只狍子在喊他:“大!大!大……”
“麻子,孙金山,麻子大,大爷……”怎么那么多人的声音啊!孙金山忽然万般轻松,仿佛自己的灵魂出了身躯,轻飘飘飞到了天上,雪好大呀!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呀,怎么地上这么多的屯里人望着他,他听到他们都在喊他。
麻子看到了憨妮、自己的女人、奎子爷、三兄弟、侄子、侄女、侄媳妇、二狗、刘满、拴柱……屯子人都来了,麻子想笑却哭出声来。
夜色蔓延下来,天上又飘起大片大片的雪花,后生们用担架抬着孙金山向屯子的方向走着,人们纷纷寻找来时的足迹,又像是寻找着生命中那个原来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