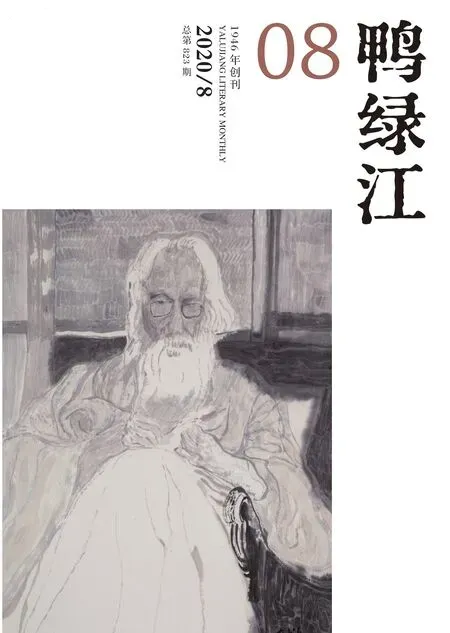小村记忆
翁 赋
村景
我出生的小村,位于长潭湖南岸。全村有五个自然村,南北长达二十公里。虽是同村,我自上学到工作一直在外,龙井坑离我所在的自然村较远,景色闻名遐迩,我却没有仔细地去品过。假期间,同村朋友陪我观赏后,令我感慨无限。
从南岸船埠头出发,顺溪南行约二三公里,便看到两岸群山连绵,一条银带似的溪坑随着蜿蜒的山谷盘曲而进。一路上,风景如画,浓荫的树丛和竹林,繁盛地伸展着叶子,织成碧绿的云,笼罩着白云深处的人家。溪涧时宽时窄,时缓时急,涓涓地流着,发出绝妙的交响乐。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见一块方方的黑色巨石矗立在溪中,陪我同行的牟先生告诉我,此石唤作“纱帽岩”。经朋友一说,我豁然大悟,太逼真了,远看正如一顶乌纱放在溪中,连帽褶帽翼都清晰可见,经历了不知多少风吹雨打和日晒冰冻,乌纱仍未褪色丝毫。自纱帽岩逆流而行三四十步,就到了塘丘路廊——这是行人歇脚的地方,路廊右边是一座古庙,左边的矮房是供茶水、卖烟酒糕点之类的小店。未进屋,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株直径约两米的大樟树,长着郁郁葱葱、密密丛丛的深绿色叶子,既像个大帐篷遮挡着烈日,又像一只慈善的大母鸡张着黑翼,仿佛把整个古庙都隐藏起来似的。我出神地看着这棵大樟树,心里正在猜测它的高龄,突然发现圆形的枝盖中长出不同形状的叶子来。我情不自禁地拍手称奇,朋友见我如此惊喜模样,忍不住笑了,说:“这树名叫‘樟抱柏’,你走近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秘密的。”我跑到樟树下,绕了半周,秘密终于发现了——原来这棵大樟树的肚里长出了一株大柏树,由于樟树紧紧抱住柏树,树干树枝上爬满了薜荔和苔藓,使人很难辨认出它们是“连理枝”。
过了路廊约一公里,便到了龙井。龙井与民用的水井一模一样,不同之处水井是人工砌筑而成的,龙井却是天然生成的,因为它的四周全是石壁,井口、井壁连一丝石缝都找不到,真可谓天衣无缝。井口直径不到一米,圆得像圆规画出来似的,毫无凸凹,井口光滑、清洁,东面山上一条小溪涧直冲而下注入龙井,我想这涧水的长期磨洗是龙井光洁的主要原因吧。井水似绿非绿,似蓝非蓝,既不透明,也不混浊,用茶杯舀起一瞧,却清澈得一尘不染。井底深不可测,我捡起一块鸭蛋大小的石子扔下,连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声音,也没有水花,便知这是一个险峭的深渊。我见不远处一位老伯在放牛,就上前询问此井的深度,老伯说:“我也不知道。但有人曾用十根谷箩绳接起,系着一位六七斤重的石头放下,还没沉到底。”一根谷箩绳三四米长,说明井深不止于三四十米。听罢老伯的话,我惶恐、惊骇、本能地倒退了几步,如果不小心滑入井里,则无疑与世长辞了。老伯接着说:“相传有一割稻客路过此处,把刻有名字的扁担插入此井,后来这根扁担在乐清大荆石门潭发现,可见这龙井是贯通乐清的。”我认为这是传说而已,也无意去考证。
离龙井以南三十余步,有一个龙潭,潭不大,比雁荡山的大龙湫潭要小一些,但比大龙湫险。大龙湫潭常有人游泳,且泅水到底证实深浅,而龙井坑的龙潭则不同,潭在深谷,人进入此地,便有一种萧瑟、阴森、肃穆之感,仿佛四周坠入了沉寂和神秘之中。三面是峭壁,溪水从南面三丈高的石壁上蹿下,如逢暴雨,急流抨崖转石,势不可挡,令人心寒。我站在龙潭口的下端观看,浅滩白石子、花纹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鱼儿忽尔远逝,往来翕急,与人逗乐。再往前看,就是深潭处,水色变得碧绿碧绿的,因为人的心境不同,有时觉得庄严,有时觉得凶恶,若独自一人在此伫立良久,的确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惊胆战。
龙井坑的景致是迷人的,然秀色不可餐,也不是久栖之地,我只好望景兴叹而已。
村邻
我幼年时,随父母经常到村邻走亲,这种走亲也叫吃糕,一般在每年的正月里。但从我家到娘舅、姨妈家,虽说邻村,步行却需要两个多小时,要经过东山、西洋、古岙岭、沈岙、温州坑岭、石库洋,一路上到处都是自然景物,一直伸到最远的蓝天白云间才消失。
从家到东山,路过一个叫猎獭岩的地方,此岩生得像一张斜床,长三四米,宽二三米,岩下有个深潭,藏着鱼虾蟹之类的水族动物,相传常有水獭爬到岩背上晒太阳,这里成了人们捉水獭的好地方,所以取名为猎獭岩。水路上端有一口叫回潭的水塘,与骆驼山之间有一涧,涧水来自莲花芯山,跨涧以一段大槠树锯成两爿铺着作桥,山麓有一棵斜生的槠树,横架在桥上。夜间路过此处,山陡,夜静,人往,惊动柴篷里的猫狸,发出簌簌沙沙的声音,一切都在神秘地飘游扩散,令人毛骨悚然。
东山到西洋,踏过清溪上的石丁,就看见一口清澈的大水塘,是附近中小学学生游泳、妇女们洗衣服的地方。过了西洋市场,来到萧疏稀烟的古岙岭,岭头有座庙,庙前是路廊,用于行人歇脚。左边放着一张矮桌,桌上有一口大茶缸,缸口盖着一顶大箬笠,缸边放着四五个竹勺,供行人喝水用。右边有两张凳,正中后壁立着一块神牌位,牌位前摆有香炉,炉中插着三炷香,香火未灭。牌位左右壁上贴着一副对联:凶吉凭我断,是非问君知。岭下前方便是沈岙,要跨越一座明清单孔石拱桥。此桥叫青龙桥,又名兴隆桥,南北横跨在后门溪上,全长21 米,桥面宽3.3 米,净跨11.6 米,矢高5.4 米。两侧浮雕石板为栏,桥基呈八字形,南北两侧各设27 级台阶,桥心石右侧横梁上有阴刻楷书“青龙桥”字样。桥栏的石柱,或许由于风雨的袭侵,或许由于世代游荡者的摩擦,棱角都磨光了。桥头有几株大柏树和樟树,郁郁葱葱,忠实地守护着渐渐被人遗忘的古道。桥旁边有个祠堂,曾做过学堂,据了解,明代布衣名人蔡元亓的“一品塘”也在附近。
沈岙的南面是温州坑岭,为何称温州坑岭?一,这是乌岩一带前往温州永嘉的必经之路;二,此岭有千级台阶,系温州师傅所砌筑。从下而上,一般需要一个多小时,中途有个半岭堂路廊,我们每趟都要歇歇脚;从上而下,比较快,一般需要半个多小时,到半岭堂也不用歇脚。温州坑岭那弯弯曲曲的山径犹如一条银白色的飘带,从山脚飘向天上。记得有一年正月,我与父亲一起到石库洋走亲,不料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整个岭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地毯,天地间雾蒙蒙一片,台阶深埋在雪下,七八天都没解冻。父亲要出勤,而我要上学,怎么办?姨妈家就住在岭头,二表哥给我们父子编制了两双稻草鞋,套在布鞋外可以防滑;三表哥叫来三五个亲友,拿着扫把锄头,从岭头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一直清理到半岭堂。因为半岭以下的山路冰雪薄了,虽尚未完全解冻,但可以小心行走。这趟走亲,使我终生难忘。如今,温州坑岭成了古道,依然保留着原始、野朴的神韵。
过去正月请客吃糕,亲戚间互相照排队的,哪家叫得早,先去哪家,不冲突,那时没有电话、手机,约定日期都是用口信,一般是在集市上相遇传送,必要时还派人专程叫客。为了不违约,有一年我们从石库洋下来,没回家,直接到前岸下洋岭的姑妈家、大哥家吃糕。
我印象中的下洋岭,极像《水浒传》中的野猪林,古树成林,主要是松树和槠树,大的要三个人牵手才能围抱,林荫小道间,一棵棵大树似一顶顶撑天的巨伞,密密层层的枝叶,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大树下,零星放着几具稻秆扇覆盖着的棺材,地上长满了杂草棘刺,显得格外阴森惨淡、荒凉冷落。岭下有口水井,一年四季不干涸,前岸人当作宝藏,常以为傲。前岸,是原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周炳琳先生的祖居,我少时听前辈介绍过,早存敬意,后来我的大哥、姑丈,都在此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则对前岸更为亲切,如家一般。现在的前岸誉为“台州香格里拉”,闻名遐迩的红杉林、黄岩湿地公园,那一条条沙石铺成的小径,恰似编在五彩缤纷花圃中的饰带,让人心旷神怡。而我却喜欢白龙坝的自然风貌,幽雅又悲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忘怀情调。前不久,与几位朋友一道去了那儿,回味起过去的时光,不禁兴奋莫名,随手拈了几句《乡愁》:
原始、自然、寂寥
令我初心不忘
当捧起家乡清甜的溪水
顿生初次触摸的感觉
风吹拂着荡漾的湖波
时乐时愁,时起时落
古桥、老宅、旧友
在眼前出现
久违的离别
毁了永恒经典的诺言
溪椤树、红杉林、船埠岸
便是我梦里的一个个完整的答案
温州坑的涧水汇入沈岙的后门溪(现称上垟溪),向上垟、山嘴头、下方、前岸、东济曲流而去,注入双溪堂;前思岙的涧水直泻清溪(现称小坑溪),经塘丘、白沙园、东山、西洋、后呈,流进双溪堂。双溪堂,是我祖父母、父母生息劳作过的地方,随着长潭湖水位的升高而荡失。往事和岁月的定格与重现,给人多了一份思念,而时间和生命流逝的落差仍留在我的心中。
村北
村北边一公里处有个七八十亩大的鱼塘,鱼塘与长潭湖仅隔一道堤岗,这条约4000 米长、2 米宽、5 米高的鱼塘岗,连接着东西三座小矮山,阻挡着湖水侵袭。徒步登上此岗,举目而见浩瀚的碧波、叠嶂的丛山,晴则水光敛滟,雨则山色空蒙。踏着如毯似锦的野草野花,迎着雍容凉爽的新鲜微风,其雅致不逊于西湖的白堤和苏堤。
站在岗上,能看到对岸的东晋名寺鸿福寺旧址,可谁知晓这座古寺,南宋鼎盛时,僧有900 多人,田拥2100 余亩,地据550 亩,山辖374 亩。在晚清时因两度大火灾,烧了寺院,烧走了僧人,留给后人的仅存一口叫“万工池”的水塘。自长潭大坝建成后,上游形成了很大的人工湖,湖面积达36 平方公里,相当于六个杭州西湖,库容量达7 亿立方米,鸿福寺旧址就濒临此湖,仿佛过世的美人,已经随着桑田沧海之变而香销玉陨。
鸿福寺西北方的湖中有一座小屿山,同行朋友告诉我,此山名曰“屿山顶”。我对此山甚感兴趣,同行为了不使我失望和遗憾,竟租船领我饱览。
天空和湖水一样蓝,乘小船在湖中行驶,犹如身登飞船遨游太空。船越往北驶,越感到湖面的宽阔,万顷碧波,浩浩荡荡,确有“风吹白浪千堆雪,水拍蓝天一色清”的气氛,令人诗意盎然,彩笔难绘。风平浪静时,一群群银白色的水鸟像一架架战机,一会儿直上天空盘旋,一会儿俯冲贴水低飞……我分辨不出是湖还是海,是景还是画,只感觉到这水比海水更清湛,这风比海风更怡人。船随山弯而行,兼得山水之乐,山因水而愈清,水以山而益幽,此中空灵之境界,缥缈之情趣,非到此不足以领略,我整个身心感受到了圣洁的洗涤,心中的一切晦气都不见了,只有蓝天、水光、山色、船舫……
约半个小时,船至屿山顶下,我仔细打量了一番:山不大,却也有四五亩方圆;山不高,却也有十几层楼高。四面环水,要画成地图,极像宝岛台湾,南面的“海峡”仅有二百多米阔,其余三面烟波荡漾,浪翻澜滚。我们把船停泊在南面山下,登岸而上,不一会便到了山顶,山顶是平坦的,约有半亩大,有个无人居住的寺院,由于湖水包围了屿山顶,香客断了路,僧人不能坐吃山空,也只好另择佛地了。离寺不远处有一口井,虽不到半米深,但终年不涸。我以为是湖水压力形成,同行完全否认了我的观点,因为长潭水库没建之前便有此井了。他还告诉我,有一年旱灾,长潭湖干了三分之二,山下的四周还原为龟裂的田地,此井水却一往如故。
我痴痴地望着澄清的井泉,望着浩渺的湖面,望着连绵的群山,望着穿梭的船舫……犹是言之亦尽,湖山之间近烟远岚,如诗如画。暗暗思量:于此孤岛,可以种橘、梨、枇杷、蜜桃、葡萄等水果,也可以种白菜、蚕豆、番薯、洋芋,湖边还可以种茭白、芋头等作物。辍耕丘山,抛下垂钩,兴起则钓,兴尽则走,多么随便,多么飘逸。如果不是俗务缠身,拔冗至此安居,出入于烟波,流连于山水,相忘于江湖,自在自乐,岂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