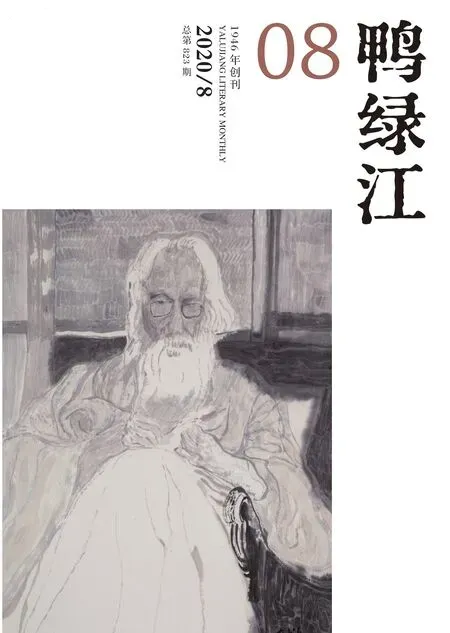闲话
汪庭竹
老人的城垣里面,只有岁月俯拾皆是。宛然的岁月,长亭小山,晨钟暮鼓,都是过去的事。
爷爷待这世界很温柔。他喜欢小动物,到哪里都能找到小河沟钓鱼。姑姑说她小的时候有只黑猫,我小时候有兔子,现在还在养鱼和乌龟,花花草草一直不断。
我小时候,爷爷接我,在路上一直哼歌,忽然停在文具店门口,给我五块钱让我买花里胡哨的笔去。
奶奶管他很严,可能他的身上只有五块钱。
现在想来,像是小孩子不会讲话,就把自己折的一只小花送给喜欢的人。
爷爷看电视的时候,嘴里会小声重复台词,看京剧也是,嘴里学得很像。爷爷还喜欢敲鼓吹号,屋里贴了满墙简谱。
爷爷跟我下五子棋,嘴里念念有词,什么“我叫你心服口服,暗暗佩服”之类的话。我小时候不知轻重,因为输棋发过一次脾气,摔崩了一颗白色棋子,他就没再跟我下过棋。
不久前我回家看二老,爷爷在午睡,我去屋里打招呼,他只是说好好,你出去把门关上点。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他与我、与世界,断了联系。他不再给我买笔了,他回到了他的世界里,那里小号的乐谱响亮辉煌。
我想起刚考完大学回家时,他专门给我买了个瓜,家里其他人都没有想起来。在他的世界里,小恩小惠就是情义千金,说话总是过于表演,不忍听顾,更加羞于启齿。
曾见过一张老照片,奶奶的怀里抱着我爸,笑得春风得意。照片里我是依据我爸认出奶奶的,我认识的奶奶年老富态。照片里我爸眉头紧锁,肉乎乎的。但是奶奶,我惊讶于她怎么会消瘦到那种地步。手肘的骨头几乎要撑爆皮肤,衬得大臂极细,小臂像老式自行车的前梁一样架着我爸。奶奶的下半身没有拍到,脸上有神采但是没有光彩,高颧骨,有一点朝天鼻。那大约是1968 年,据她说是靠吃萝卜缨生活的时候。
奶奶一生要强,到老也干净体面,思路始终清晰,逻辑像是年轻人,处事极其圆滑,婆媳妯娌之间处得八面玲珑。只是近些年身体每况愈下,见我的时候少了,见了面就塞钱,也开始说些无关痛痒的家常了,重复的也有不少,似乎慢慢地老了。
最近还张罗着要给我介绍对象,总是偷偷摸摸地跑到我家来,专门跟我说话。说男孩子的家长硬要照片,还说:“那个男孩子是飞行员,长得好,脾气好,你脾气不好,得给你找个能容人的。”结果人家机长已经找了一个地勤做女朋友,她又愤愤地说:“不管你们,年轻人的事情,看缘分吧。”
奶奶近两年病了几场,消瘦了,这次见面,我居然联想到那张照片。据说奶奶在病中同我妈讲了她跟爷爷的事。
根据我妈七零八碎的转述,大约整理了一下:
汪友全是家里养不了了,过继给汪家的儿子,他本来应该姓朱,是朱家的老幺。
汪家早早没了主母,他到了汪家也没有娘,爹也不是亲的,虽然就他一个独子,也没很大差别。汪友全的继父也很早就没了娘,晚年又是早早鳏居。后来他常常告诉晚辈的故事有两个,一个是初中捡粮票,另一个就是他上了高中,总问养父要钱,养父问你最近怎么这么花钱,这才知道他已经上了高中。
因为汪友全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体会过与“母亲”相关的情绪,所以在他此后的生命里,妻子儿子说,他不知冷热。
庞朝兰是弃婴,她老的时候还津津乐道地说,托她嗓门大的福气,雪地里哭得太响,给人捡回家里。
她念书念得极好,性格也要强,中学时候家里不让念了,让她去化工厂上班,为了哄她,给她买了一辆洋车(自行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处处要强的个性,她在那个粮食短罄的年代,人倒是也长得高挑,但瘦弱。
庞朝兰在化工厂也要强,中午加班时老是看见有个男青年拿着脏衣服到化工厂的水池里洗,心想男同志还要自己洗这么多衣服,觉得他有点可怜,动了恻隐之心。
庞朝兰远远看着洗衣服的汪友全,汪友全抬头看她,满池旧衣,二人四目相对。
汪友全洗的是父亲和自己的很脏的衣服。渐渐地,庞朝兰帮衬着洗衣裳。
汪友全年轻时长得硬朗结实,晒得很黑,能把自己空手在一根旗杆上撑起来,身体和地面平行,全靠手臂的力量把自己撑成一面“人旗”。他饭量大,做事利落,只是少言寡语,不太讨姑娘们喜欢。
庞朝兰人高,样貌却不佳,鼻子塌塌的。
他们一直不捅破窗户纸。
当时厂里还有个女工姓邢,很娇俏。有一回,嘴上客气了一句和汪友全说赶明来玩。汪友全少不经事,不知道女性为何物,当真了。第二天兴冲冲地跑去庞朝兰那里借自行车。窗户纸也不用谁捅,不禁雨打风吹。
汪友全和庞朝兰经历了那段艰难的日子,育有一男一女,儿子又有个了独女,女儿又生了一女一男。
我就是那个独女。二老都还健在。
只是爷爷近来添了糖尿病,觉也多了。奶奶那样强势一个人,前些日子又摔了一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