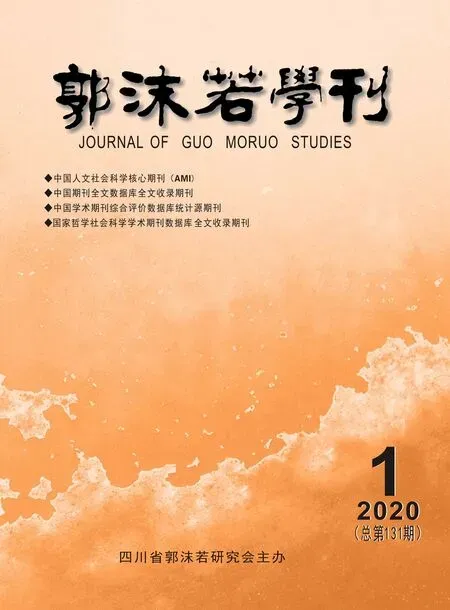《未有天才之前》中的“说”字恐非“手民之误”
——与刘玉凯先生商榷兼及对2005新版《鲁迅全集》两处注释之补正
孟文博
(山东大学(威海)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2期曾发刘玉凯先生《〈未有天才之前〉中的“说”字疑》一文,在此文中作者列出鲁迅著名讲演录《未有天才之前》的最后一段话: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作者对这段话的最后一个“说”字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当为‘话’之误排,属‘手民之误’”;“‘……的话’是口语中常用的形式,不可能是‘……的说’,这纯粹出于‘手民之误’”。此文发表已经二十余年,期间未曾见有学者提出异议,似乎已成定论。近期笔者因相关研究之故对此文又进行了版本校勘,在校勘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刘玉凯先生的观点似有不妥,由此笔者又查阅近年来语言学界对“……的说”句式的探源及研究,最终认为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的讲演记录稿和鲁迅日后整理发表的各版稿件中出现的此“说”字,应不属于“手民之误”。下面笔者将从以上两点具体分析阐述,并同时对2005新版《鲁迅全集》中关于此文版本问题的注释做出一些补正。
1924年1月17日,鲁迅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发表了一次“讲话”①在此文的第一句中,鲁迅称“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由此本文在此处使用鲁迅最初所用的“讲话”一词。在同年12月27日,此文被《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正文之前有一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讲演,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矫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在这段以信函的形式刊登的小引中,鲁迅称此文为“讲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77页的注释〔1〕中,这段“小引”被全文引用,但是原文中的“讲演”则被误写成了“演讲”。事实上,此文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会刊》初次发表时,在题目的下方就有“鲁迅讲演”字样,而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未能查证核实,出现了引述错误。,此“讲话”后以《未有天才之前》为名,发表在该校《校友会刊》1924年第1期上,在题目的下方有“鲁迅讲演”和“高级一年 万超恒记”②《京报副刊》转载此文时,在题目下方保留了此字样,只略加改动为:“鲁迅讲演万超恒记”,在文章的末尾又加了两句说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大附中校友会讲。从校友会刊第一期转录。”可以说无论是在题目下方保留记录者名字,还是在篇末增加“转录”说明,都体现了《京报副刊》对记录者和原刊版权的尊重,非常有必要。但在新版的《鲁迅全集》注释中关于此文最初版的说明只一句:“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而忽略了“鲁迅讲演”和“高级一年万超恒记”字样,而在描述《京报副刊》的“转载”时,也只引述了正文前的“小引”部分,却未注明篇末还有一个转载者所加的说明,因此似有不尊重原著,未描述完整之嫌。另外笔者还注意到,新版《鲁迅全集》对《坟》中《未有天才之前》的前一篇《娜拉走后怎样》一文的最初发表情况和转载情况的注释,不仅注明了该文“最初发表于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时,“曾署‘陆学仁、何肇葆笔记’”,而且把该文在同年8月1日由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转载时,杂志编者在篇末的“附记”也完整的引述出来。同样是鲁迅发表的讲演,同样由听众记录之后加以发表,同样在最初版本中显示有记录者的名字,同样被其他报刊转载,而转载时又同样都在篇末加有“附记”或者说明,但新版《鲁迅全集》对这诸多同样情况的注释却大不一样,这在体例和方法上似乎也很不当。的字样。同年12月27日,《京报副刊》转载了此文,并在转载时于篇首处附上了一个小引,在这个小引中,我们可以看到“校正寄奉”的字样,因此可知鲁迅是把原刊于《校友会刊》上的文章经过“校正”之后又“寄奉”给《京报副刊》加以发表的。这样看来,在《校友会刊》和《京报副刊》的文章分别是此文文字版本的最初版和第二版。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编定了文集《坟》,并于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了,其中便收录了《未有天才之前》。关于这最初版《坟》的编定工作,鲁迅曾在《〈坟〉的题记》中说:“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③鲁迅:《〈坟〉的题记》,1926年11月20日北京《语丝》周刊第106期。之后又曾在《集外集·序言》中说:“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先前自己编了一本《坟》,还留存着许多文言文,就是这意思”④鲁迅:《〈集外集〉序言》,1935年3月5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1期。。此外鲁迅还曾在1926年10月29日给陶元庆的信中向其要一个“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作一个书面”,并对“书面”的字如何写都做了具体要求⑤鲁迅:《致陶元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1卷第593页。。在1926年11月4日鲁迅又致信韦素园“寄上《坟》的序和目录,又第一页上的一点小画,请做锌版”⑥鲁迅:《致韦素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3页。。从以上几份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编定《坟》是非常认真的,不仅请“几个朋友”帮忙“搜集,抄写,校印”,还在“书面”、“序”、“目录”等方面的设计上与友人反复交流,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推定鲁迅对收入《坟》中的各篇文章也进行了相当认真的审定,因此其中的《未有天才之前》则可看作是经鲁迅之手形成的第三个版本。1929年3月,北京未名社再版了《坟》,而这次再版同样经过了鲁迅的“校正”,鲁迅在1928年7月17日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坟》的校正本及素园译本都于前几天寄出了。”⑦鲁迅:《致韦素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2卷第123页。这一版《坟》中的《未有天才之前》,应是其第四个版本。1930年4月,《坟》由上海北新书局再次印刷出版,关于这次出版,鲁迅没有留下说明性的文字,但因出版社和出版日期都发生变化,因此可以看作是该文的第五个版本。
以上是笔者对《未有天才之前》一文各版本情况的考证梳理,经过这一梳理工作,我们可以较为直观地以图表形式列出此文的版本流变历程:

在厘清了《未有天才之前》的版本流变历程之后,我们再回到此文最后一段的那个“说”字,这个“说”字是整篇文章的最后一个字,其位置当然是非常显眼的。而鲁迅对于此文,从最初版到第二版、第三版至第四版,每一版的形成,都明确表示亲自进行了“校正”、“编”等,如果这个字是“手民之误”,那么经过这么多次的“校正”、编排,鲁迅竟没有发现吗?对于这一点,刘玉凯先生在其文中提出两种“解释”:“或者是鲁迅讲演中这样说过,由记录者如实记下,鲁迅为保持口语而未加删改;或者是鲁迅没这样讲,记录者为清楚地表述语言而加上了‘……的话’,鲁迅‘校正’时认为可通也就默认了。但无论何种情况‘的说’应为‘的话’,是合情合理的。鲁迅大概不会在讲演时用似通非通的‘的说’”。笔者认为刘玉凯先生的解释有其道理,但也相当牵强。前一种解释的前提为鲁迅讲演时“误说”,后一种解释的前提是记录者在记录时“误改”,而认真严谨如鲁迅者,对自己的“误说”和记录者的“误改”,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大可能一直采取“保持”和“默认”的态度,而在屡次的“校正”中将错就错,得过且过。事实上,笔者认为此文最后出现的“的说”,并非“似通非通”,也非“手民之误”,而是鲁迅先生正常的一种表达。
刘玉凯先生发表文章是在1995年,其时在我国的各种语言环境中,都还没出现过“……的说”这种句式,但就在几年之后,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的说”句式却随着网络迅速在青年人群中流行开来,一时间成为非常时髦的语言表达,由于这一语言现象发展迅速且影响很大,相关语言学的研究也很快跟进,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笔者为写此论文,基本查阅了所有直接涉及“……的说”句式的研究成果,结果发现研究者们最为主流的结论是:“的说”乃是一个日源词,“……的说”句式则源于一种日语表达。具体来说,“的说”一词对应的是日语中的“です”,而“……的说”句式则由日语中的“……です”转换而来。这一结论主要的根据有以下三点:
首先,“的说”和“です”发音接近,“です”罗马拼音标记为“desu”。
其次,“的说”和“です”位置相同,“です”也用在句子的末尾。
第三,“的说”和“です”功能相似,“です”是助动词,在日语句式中可用于表达判断的语气。
从以上三点可看到,日语中的“です”与“的说”的核心功能是类似的。①以上参阅尹露:《ACG时代背景下的青少年日源流行语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届语言学专业硕士论文。
那么鲁迅是不是在此处使用了日语式的表达呢?笔者认为应该是这样。就像孙郁先生所说的,鲁迅进行创作的时代,正是一个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替,海内文化与域外文化大碰撞的“混血的时代”②孙郁:《混血的时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在这个时代中,大量外来词汇和语法形式被引进、改造,并运用到各种写作中去,而鲁迅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先行者,他在谈及翻译问题时曾言“中国的言语简直(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语言,(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语法。世纪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可以说是一种病,而“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①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第380-391页。原文无“对”。鲁迅不仅从理论上这样提倡,还在具体的创作中积极践行,由于他长期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润,谙熟日文,同时在他看来,日语的“文章里”“装进”“欧化的语法”又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因此鲁迅在其一生的译介和创作中,都在不断的运用日语元素,而在他的作品里,日语词汇和语法的运用,也是“极平常的了”。关于鲁迅在其各种文体的作品中是如何使用日语词汇或者日语语法进行表达的,早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②相关研究论文有:武殿勋、高文达:《谈鲁迅作品中的日语词》,《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徐桂梅:《鲁迅小说语言中的“日语元素”解析》,《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2期;张霞:《鲁迅杂文里使用日语借用语的研究》,宁波大学2009届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毕业论文等。,本文不再赘言,而具体到这篇“讲话”,鲁迅其实也运用了不少日语式表达,比如就在这个“说”字之前有这样一句话:“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这句话就是典型的日语式表达,可以直接翻译为:“逆に大いに期待が持てるところでもある”。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鲁迅当时把这篇“讲话”进行到末尾之时,在情绪稍激动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进入到了日语语境之中,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日语式的表达,而最后的这个“的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日后,当鲁迅在对此文不断进行“校正”、“编”之时,应当注意到了文章中最后一个字这么显眼的位置的表达方式不符合汉语语法,但是这却与其用“新的字眼,新的语法”来“创造新的言语”的观念是相符的,因此便对这一表达方式一直都加以保留,而我们作为后来者,现在借助新的语言知识,透过历史的语境再去审视鲁迅的这一表达方式,甚至可以看作这是鲁迅利用机会,以“新的字眼,新的语法”来“创造新的言语”的一次践行或者尝试,因此如果仅仅简单地把其归为“手民之误”,则不免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