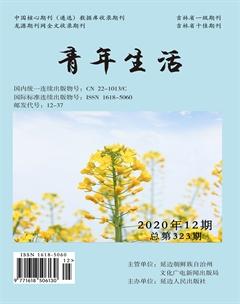表征与本相,文本与情境
周宇涵
摘要:《羌在汉藏之间》作为王明珂族群边缘理论的过渡之作,以汉藏双重边缘的羌族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记忆、族群认同、表征与本相、文本与情境、文化展演等核心概念,深人思考了长时段视域下羌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以及形塑与展示这一切文本与表象背后的社会情境与本相。
关键词:表征;文本;现实本相;社会情境;历史记忆;历史文化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主要从事关于华夏及其边缘人群——由过去的“蛮夷戎狄”到现在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类学探索,《羌在汉藏之间》便是其中重要结晶之一。羌族是一个特殊的中国少数民族,特别之处在于虽然只是一个夹缝于汉族与藏族之间的人口仅有30万的民族,却与汉族、藏族、彝族、乃至纳西、哈尼、普米等十余种西南民族都有密切的族群关系。对于这样一个联结十多个民族的“粘着剂”,它的历史如何?历史过程如何?现在又如何?对于汉族、藏族以及部分西南民族族群变迁的形成与变迁的影响又如何?带着这些研究问题,王明珂将本书分为社会篇、历史篇与文化篇,试图将三者串起一条学术脉络来分析解答:社会篇主要描述了羌族的地理分布、资源环境、人群与聚落形态,用形象的“一截骂一截”和“毒药猫”理论探讨了人们如何在资源竞争与分享体系中认同与区分彼此,历史篇则是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阐述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忆造成了当今的羌族,从边缘视角观察羌族史的再建构,并结合调查所得口述资料分析了弟兄祖先故事和英雄祖先故事所蕴含的历史心性,文化篇主要从三种角度(事实、叙事、习行与展演)来解读文献中有关羌人文化的描述,提出“羌人文化”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建构与变迁的过程中。王明珂运用其细致淋漓的笔触将羌族的社会、历史、文化描述得生动形象,即使不是专业背景的人读起来也是兴趣盎然,每读完一篇都忍不住回味思考一番。
与其说王明珂是一位歷史学家,我觉得他更是一位历史人类学家,或者说是一位走向人类学的历史学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看似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领域,一个研究时间,一个研究空间;一个注重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一个注重田野考察和口头资料。但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融合趋势,1949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宣称:“他们(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是在同一条道路上、沿着同一方向走着同一个旅程……”。后来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历史人类学开始逐步发展,法国年鉴学派促使人类学从科学的理论范式建构转向有深度的历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体验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文献训诂、考据、文本解读等方法结合起来,重视展现和分析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随着学术界交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逐渐开始出现比较有规模、成体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王明珂自然也在这样的学术大潮中逐步由历史学转向历史人类学,这本《羌在汉藏之间》清晰展现了他将历史进行人类学化的研究倾向。就像李亦园所评价的那样:“王明珂这些详尽的田野资料使我们自认为是田野老手的人类学家至为折服,尽管他一再自谦说他并非一个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前言中曾说:“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更准确的说是一本描述与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作为一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将历史学与人类学两者结合的表现形式乍一看在于将在羌族收集到的田野调查资料、录音口述数据与史料文献、考古文本相结合,但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在于其历史与“历史”、表征与本相、文本与情境的研究取向。
传统的历史学追求的更多是过去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便是王明珂所说的历史,然而何为真正的历史事实,或是说“事实上,历史本身就不具有绝对的真实性,所有的历史均与话语权有紧密的联系”。在明白历史真相本就令人怀疑且极具争论性后,王明珂由此引入“历史”。“‘历史是指人们经由口述、文字与图像来表达的对过去之选择与建构”。人类更多的是生活在选择、建构的“历史”中,因此无论是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田野调查或是口述资料,乃至当今所见关于羌族的文化、民族与历史现象,都被王明珂视为一种呈现人类所建构“历史”的文本或表征,“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情境也依赖文本呈现与活化,或者说,文本是某种社会本相的表征”。他的旨趣则在于透过文本探究出社会特定情境下的社会本相,这也符合一位历史人类学家并非考察历史真相,而是思考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特点。拿书中例子来说,王明珂在不同历史文献中看到羌族到底是三苗后代还是周仓后代的争论,对他而言都是一种文本或表征,他真正需要探求的是这个争论之后的社会情境或社会现实,是怎样的利益需求或社会情境使得古代华夏认为羌为三苗之后,使得当代羌族认为周仓是他们的祖先。王明珂对历史与“历史”等概念的阐述引发学界充分讨论,大部分学者对此观点也作出了肯定,他们认可历史的构成单元并非许多文献记载中的历史事件,而是造成这些文献记忆与相关事件的社会本貌。刘朦、王磊裔学者更是直接提出“我们就生活在一表征化的世界中,各种权利关系与社会现实造成如此表征世界。我们在文化所界定的语言、词汇、符号中认识此世界”。
如上所说,王明珂所认为的文本概念超出一般的文本概念,任何能被观察、解读的社会文化表征都是文本,我们能透过这些文本表相来分析情境本相,因此王明珂在书中也提出不同于结合各种史料以归纳、发掘事实的“模拟法“的“文本分析法”。相较于模拟法,文本分析法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尝试从近代建构的文本中找寻一些多元、边缘、异常或断裂的现象,并分析其情境意义;二是以询问“为什么”为目的去考察文本取材、组织、制造、使用的原因。于是,作为华夏的一个边缘异常地区,作为汉藏之间的一个多元特殊地区,羌族的社会、历史、文化成为王明珂进行文本分析的有效研究对象。他主要依靠两种田野调查获得文本资料:一是观察、记录当地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并将当地人的口述资料、实物、照片转化为文字;二是将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当做古今华夏各书写主体在某种社会情境下是选择与建构性描述。面对收集来的文本资料,王明珂以“为什么”为切入口探究文本背后的原因脉络:作者为什么如此取材;为什么以特定的逻辑语句与文本结构进行组织;作者借此期望说明什么;为什么在各种权利争论与制衡之下,这个文本得以保存。按照如此的分析脉络去探求这些文本之下的社会历史情境,力图还原历史本相。正是这样“在历史上做田野,在田野中思历史”的文本分析方式,使得王明珂对羌族形成、伸缩、变迁过程以及本质的分析更具时代真实感与历史延续性。
像王明珂在书中开篇提出的那样:“透过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们希望了解所反映的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及其所映照我们所熟悉、信赖的文化与历史之本质”。从社会篇到历史篇,再到文化篇,王明珂一直秉承着“聆听文本弦外之音”的理念在关于羌族的各类文本描述以及历史文化表征中去剥丝抽茧,探索背后的本相与情境。社会篇通过羌族内部“视情况而定的族群认同”这一表象探索出当地资源竞争与分享的社会本相和羌族人特殊的的本土情境;历史篇通过几种说法不同的“羌人历史”以及其中体现出的两种“历史心性”来说明羌族的历史只是特定时期被选择、想象与建构的记忆与表述;文化篇更是通过锅庄舞、羌历年等羌族人与外来者共同促成的文化展演现象去透析背后的社会权利关系与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由此看来,他所说的要探究文本背后的情境其实就是探究羌族背后个人与群体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并尝试了解羌族相关“历史”与文化的建构过程,正如作者在书中前言部分所提及到的本书的“野心”:“由人类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及其在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征,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
不仅仅是王明珂,受福柯所强调的话语、权力以及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关注“文本”与“情境”的互生映射关系,探讨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社会权力如何博弈并引导、规范各种论述文本以及建构“历史”;或探讨透过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们怎样去反观反思其中潜藏的情境、社会本相及其变迁。例如张应强在《清代黔东南地区一个苗族村寨的改姓与宗族的演变》一书中直接指出:“在宗族历史叙述中,无论是真实记录也好,附会虚饰也好,都是后来被刻意记录下来的,因而是人们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记忆,而这种集体记忆, 在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更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简美玲在《汉语、苗泾浜、汶类——贵州苗人家谱的混声与界线》一文中也描述了苗族精英在以汉字书写的家谱里,以差异、混成的苗汉语言经验的混声以建构出可摇摆的苗汉族群界线这一现象,探究出苗族在当代中国多族群的意象中寻求族群主体性与文化资源的行动策略的特定情境;王勤美《传说故事·历史情境·文本书写:禄丰高峰彝人村落社会研究》一文探讨了彝人群体和文化精英如何在观照本土历史文化的同时,借助巧妙的历史附会、文本加工和重构,通过对彝文典籍《火把经》及其祖先传说故事进行新的解释和书写,完成对王朝国家的想象和对汉文化的接纳与吸收,在文化自觉的意识中“发声”,向其他族群表明“我们是彝”。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研究逐渐成为人类学或历史人类学的热点,学者们也逐渐采用“透过文本观察社会情境本相”的反思性研究方法,这样能够更真切地感知各个少数族群在历史文化的选择、书写与建构之间的鲜活生命抉择,他们如何选择如何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定位,如何在行动间顺应形势,或者突破,甚至违反种种模式与边界,分析他们的情感意图,探究其背后深层次的本土情境與社会结构。
回到王明珂,作为一位历史人类学家,他在田野中所看到的现象都是文本,也都是表征。他关注着与羌族有关的各类表征与文本分析,并期望借以了解羌族社会本相及其历史变迁过程等问题,特别是独属于羌族社会中的族群认同与区分、典范历史观点、文化习俗等等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言谈、行为、文字表述。而这些言谈、行为、文字表述作为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下的表征或文本 ,如何依循某种模式以顺从或强化社会结构性的现实本相与情境。历史的真相常常是难解之谜,既然如此,研究者的眼光就应该从寻求历史的真相转移到历史背后的社会情境和社会真相之解读上。
王明珂曾经强调:“我们要把田野的概念放宽。我们在田野里所看到的那些现象,比如,人家在娶亲,或者在办丧礼,或者在路边吵架,或者是讲个故事,都是我们关注的表面现象,也是一些文本。包括人们所说的本地历史或传说等,录音下来,然后变成文本,这也是田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不是人类学专业,但我深深赞同王明珂生活就是田野的观点,我们不需要专门进入某一特定田野去观察记录,去了解那个特定社会的情境本相,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表相化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做的是聆听生活中的弦外之音。广袤繁杂生活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田野点,我们可以关注与我们自身相关的,或自己感兴趣的现象,或琐碎或笼统,或浅显或深奥,只要它在发生,其背后必然藏着特定社会情境下一种本相。打开视野与心境,透过一切的表征去探究背后的情境,我们便能在生活中做田野调查,田野皆生活,生活皆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