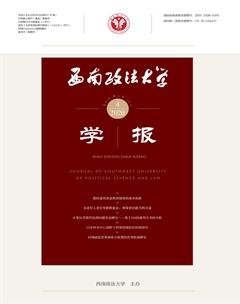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刑事错案防范机制研究
摘 要:防范刑事错案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我国正是在防范错案这一背景下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防范刑事错案的可行方案。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作为一项宏大的改革议题,内在包含了诸多的构成部分,需要区别对待和分析。如何通过以审判为中心进而实现对刑事错案的防范,应当细化具体的技术路线,分别理清司法理念、证据规则、辩护制度以及庭审实质化与刑事错案防范之间的关系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予以回应。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司法理念;证据规则;辩护制度;庭审实质化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4.08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以审判为中心一直是我国司法领域的改革重点。回溯以审判为中心这一改革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有不少学者予以关注,但是并没有被改革者所采纳。而在当前,随着一系列刑事错案的曝光和纠正,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了挑战,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背景下构筑刑事错案的防范机制,需要立足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具体技术路线,分析现存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从而对改进现状有所裨益。
一、问题的引出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审判为中心这一议题逐渐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①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改革语境中,学界的单方面“主张”并没有被改革者采纳,侦查中心主义在司法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利益博弈中权利保护不足等诸多原因,使得“维稳”“反腐”以及“保发展促民生”成为司法领域的工作重点。[ 季卫东:《中国的司法改革》,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2-73页。]在此背景下,如何从重从快惩罚犯罪备受关注,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得以不断加固,导致冤假错案发生,[ 从近年来已经平反的冤假错案来看,如“张氏叔侄案”“赵作海案”“于英生案”“张海生案”“佘祥林案”等,这些案件都是发生在21世纪之初。]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这一世界性难题”,[ 马骁潇:《十八大以来法院纠正34件重大冤假错案涉54人》,载新浪网2017年10月14日,http://news.sina.com.cn/c/2017-10-14/doc-ifymuukv2010863.shtml.]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自此,以审判为中心成为司法改革的“重头戏”,这也就为冤假错案的防范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
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构成部分,很多学者发表了独到的观点,比如:有论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包括“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完善的辩护制度、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证人出庭制度、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及“保证侦查、审查起诉的质量”四个部分;[ 陈光中、步洋洋:《审判中心与相关诉讼制度改革初探》,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第120-128页。]也有论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包括控诉、审判和诉讼程序“三个面向”,即“控方证明责任的有效履行、法院审判的严格把关,以及庭审实质化。”[ 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846-860页。]还有论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包括“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之关系”“庭审中心主义”“一审中心主义”三个部分。[ 魏晓娜:《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86-104页。]此外,一些论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还包括“改革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观念”“诉讼职能的定位”“证据裁判原则”“非法证据的排除”“庭审实质化”以及“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等。[ 相关观点参见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4期,第93-97页;何家弘:《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载《中国高等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29-144页;闵春雷:《以审判为中心:内涵解读及实现路径》,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第35-43页;叶青:《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若干思考》,载《法学》2015年第7期,第3-10页;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载《法学家》2016年第4期,第1-15页。]但总体来看,主要是由“司法理念”“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庭审实质化”四部分构成,这为探讨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下如何防范刑事错案引入了具体的技术路线。
二、司法理念的拨正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从语义来看,理念是指“人们在对客观事物进行反映、评价和创造的统一认识过程中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客观性、价值性和理想性的认识内容在认识论中的理论表现。”[ 赵君:《理念应作为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载《哲学动态》1987年第6期,第34-35页。]这一表述具有相当的抽象性,同理,司法理念的内涵亦是如此。但在诉讼活动中,司法理念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一方面,以立法者为主体视角,司法理念通过对立法人员思维观念的统摄,进而直接作用于诉讼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并对诉讼行为的实施产生间接的支配力。另一方面,以司法者为主体视角,在业已形成的司法理念影响下,司法人员的行为往往带有一定的倾向性,甚至是造成实践效果有违立法原意。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语境下,司法理念带有“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重实体正确、轻程序合法,有罪推定、罪疑从轻,司法服从行政、侦查决定审判”的浓厚色彩。[ 李建明:《刑事错案预防视野下的刑事司法理念现代化》,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3期,第7-21页。]受制于传统的司法理念,当案件被侦查机关立案之后,为了迎合侦查终结的条件,在侦查技术有限、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不高以及完整证据链条的严格要求等诸多因素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成了侦查人员首选的“突破口”。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被传唤到案后且执行拘留前,犯罪嫌疑人并不需要立即送至看守所,而看守所之外的讯问为侦查机关顺利获得口供提供了有利的外在保障,这一时间段因此也被称之为获取口供的“黄金时段”,[ 方文军:《供证关系与事实认定探微》,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2期,第62-66页。]其后侦查机关通过口供进而收集一系列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且能够扎实证据链条的证据,形成“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值得强调的是,在我国侦查权过于强劲、刑讯逼供不绝的侦查环境下,由于犯罪嫌疑人作出的口供缺乏自愿性,致使口供的真实性大打折扣,那么据此得出达到侦查终结条件的推论也将存疑。不过,即便如此,在实体真实论占主导地位的司法语境中,加之公检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过度亲密,公诉和审判机关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否定侦查机关的有罪结论,而是尽可能地吸收侦查人员移送的诉讼“产品”,根据现有证据的完备程度作出有罪或者疑罪从轻的认定或判决。这样的话,当案件被侦查机关立案之后,如果人们被贴上犯罪嫌疑人的标签,也就很难逃脱无罪的嫌疑。 如何對错误的司法理念加以纠偏,进而避免因理念层面的误导致使立法和司法人员没有客观公正地行权,其关键在于遵从以审判为中心的内在要求,对现有的司法理念进行重塑。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内在逻辑,人权保障属于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追求,因此,贯彻以审判为中心需要与人权保障的价值导向紧密联系。[ 王芳:《审判中心主义趋向中的刑事侦查权重构》,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第218-225页。]在人权保障的价值要求下,刑事诉讼的功能不能仅局限于打击犯罪,应当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二元并重。此外,司法理念与行权行为均应当以有利于被追诉人和被告人为轴心予以展开。
具体而言,一是转变实体优于程序的片面认知。在肯定程序本身具备独立价值这一前提下,当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发生冲突时,不能只是为了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强调实体公正比程序公正更为重要,以至于一味地扩充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并为其权力的行使减小阻力,而更应当通过完善相关的程序和证据规则,赋予被追诉人充分的诉讼和救济权利,对违反程序法的行权行为及时进行否定性评价,并对相关的行权主体加以制裁,树立“程序先于实体”的理念。[ 孙长永:《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二是树立无罪推定的观念。无罪推定是域外各国诉讼规则中的共识性理念,尽管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也都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由于如实作证义务的设置、刑讯逼供的存在以及沉默权制度的阙如,使得无罪推定这一理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在我国诉讼活动中实现。为此,需要从立法层面出发构建无罪推定的配套性规则,而且应当改变实践中的刑讯逼供以及“疑罪从挂”等现象,推动无罪推定观念的真正实现。三是确立控诉服务于审判的观念。在以往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下,审前的作用和地位凸显,“逮捕绑架审判”“侦查中心主义”等奇异诉讼景象司空见惯,审判程序几乎沦为确保定罪合法的一种工具,侦查决定审判、审判服务控诉也便成了三机关之间关系定位的生动诠释。但在刑事诉讼中,审判居于主导地位,所有审前机关及其相应机关的权力行使也都是围绕审判权这一中心,因此需要明确侦查服务于审判这一观念,避免法院对于案件的审查流于形式。
三、证据规则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司法裁判应当以案件事实为基础,但案发场景具有时空上的不可逆性,因此如何尽可能地还原案件事实需要一系列证据的充分介入。不过,除物证、书证等部分证据外,其他种类的证据形成具有事后的人为性,证据的客观性也就随之有所克减。结合目前学界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来看,很大程度上将错案生成的原因归结于证据层面,比如:何家弘教授认为,错案是由实践中的十个误区所造成,涉及证据事项的有“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科学证据的不当解读”“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以及“证据不足的疑罪从轻”五个方面。[ 何家弘:《当今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第47-67页。]其中,与证据相关的实践误区占据半数之多,足见证据规则在刑事错案中的重要地位。
从思维逻辑来看,一般而言,由于侦辩双方对于案件定性的判断方向截然相反,侦查人员侦破案件需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取证活动也是以假设犯罪嫌疑人有罪为前提,这种思维模式必然会直接促成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结果。根据前述,在各类证据中,口供备受侦查机关的青睐,但是在趋利避害的本位主义驱使下,犯罪嫌疑人通常并不情愿主动地作出陈述,此时通过刑讯方式逼迫犯罪嫌疑人便成了侦查机关的惯用手段。另外,鉴于刑讯逼供的外在表现形式较为直观,容易受到人们的诟病,致使诱供、威胁、疲劳审讯等隐蔽型非法取证方式在侦查实践中逐渐兴起并受到推崇。而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通过隐蔽型非法取证方式获取口供的现象也不少见,例如在日本的“袴田事件”中,警方在审讯之前便坚信“犯人百分之百是袴田”,因此负责侦查的警察每天对被告人袴田的审问时间为12小时左右,最长时间为16小时,而且被告人日常的大小便也会在审讯室内多名审讯官面前用简易的便盆完成,此种不人道的取证方式最终酿成了冤案。[ \ 四、辩护制度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在刑事活动中,理想的诉讼构造是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目的,以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权利对等为必要条件的“正三角结构”。但在实践中,检察院作为公权力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权的配置,促使其取得了凌驾于被告方的诉讼地位,理想结构下的控辩平等对抗机制被破坏,影响着司法公正的正常实现。[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在此背景下,为了避免公权力过分膨胀致使私权利不断被克减,缩小控辩之间的实力差距,保障被告方诉讼权利的充分实现,此时便需要辩护律师的有效介入。正因如此,一国辩护制度的完备程度通常与民主法治水平息息相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错案的产生也是由于辩护力量薄弱、辩护不到位,以及辩护意见没有引起司法机关的足够重视等原因所造成。[ 陈光中:《完善的辩护制度是国家民主法治发达的重要标志》,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版,第1-4页。]结合以往的冤假错案来看,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较为有限。具体而言,首先,辩护人在审前阶段的作用受限。以“杜培武案”為例,在庭审之前,杜培武曾向检察官展示了他手腕、膝盖以及脚上被办案人员殴打留下的伤痕,控告侦查人员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并说明驻所检察官在看守所中为他拍下了可证明遭受刑讯逼供的伤情照片,但并没有得到理睬。本案中的两位辩护律师也为他作无罪辩护,提出杜培武并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但均没有得到采纳。[佚名:《杜培武案》,载洗冤网,2014年7月3日,http://xiyuanwang.net/html/gnya_1271_1870.html.]其次,辩护律师在审判中的作用受限。以“李怀亮案”为例,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李怀亮先后共做了10次供述,其中前两次没有供述犯罪事实,第三次至第八次做有罪供述,第九次之后的供述一直否定实施了犯罪。受案法院在开庭审理此案时,被告人李怀亮当庭翻供,其辩护律师也提出故意杀人证据不足、应判无罪的辩护意见。对此,受案法院并没有认真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最终,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怀亮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邓红阳,赵红旗:《李怀亮涉嫌杀人案:12年悬案压垮两个家庭》,载洗冤网2014年9月23日,http://xiyuanwang.net/html/gnya_1271_1863.html.]再次,辩护律师在审判结束后的申诉中作用受限。以“聂树斌案”为例,2014年12月,在社会的舆论压力之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了辩护律师的阅卷。在此之前的10年内,“聂树斌案”的几任代理律师总共提出了50多次的阅卷请求,均未得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意。阅卷权是辩护权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律师行使辩护权和开展辩护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保障,刑事辩护也就很难得以实质性地开展。[ 邢婷:《聂树斌案代理律师首次获准阅卷》,载《中国青年报》2015年3月18日,第4版。]通过分析上述错案发现,辩护律师阅卷难、辩护意见采信难等现象在实践中比较多见。而在已经平反的冤假错案中,原审辩护律师的意见几乎都没有被采纳,只是简单地驳回辩护意见,并未对为何没有被采纳及其驳回的缘由进行细致说明。[ 徐跃飞:《刑事错案的成因及其预防机制》,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91-97页。]“如果说司法公正是一座大厦,那么,侦查、起诉、审判、法律监督和律师辩护是支撑这个大厦的五根不可或缺的支柱。”[ 朱孝清:《冤假错案的原因和对策》,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2期,第3-9页。]在吸取以往办案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更大程度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突出强调了“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辩护权利。辩护人申请调取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而在2015年6月,为了建立值班律师制度,进而实现法律援助服务全覆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但这一文件的规定过于“粗线条”,难以为具体实践提供全方位的规则指引。因此,为了细化文件的要求,2017年8月,“两高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要求在法院、看守所内设置值班律师。在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的前提下,一方面,各诉讼阶段相应的主导机关需要向被追诉人告知享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另一方面,如果被追诉人以及近亲属提出请求的,相应的主导机关需要及时通知值班律师。此外,在2018年10月,第三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值班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实现全覆盖,而且将原本认罪认罚试点中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扩大至所有的刑事案件中,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化解我国辩护率低、被追诉人权利行使不充分的司法积弊。
诚然,随着我国辩护环境的不断改善,能够避免因辩护律师的缺位或者辩护权行使不够充分,从而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但是,对于辩护制度目前的完善措施仍然不够完善,不足以防范刑事错案的再发。其一,辩护律师的现有权利缺乏救济。尽管《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赋予了辩护律师一系列的权利,不过,权利的赋予与实现历来是两个范畴的问题。类似于“纸面上的法”会由于错综复杂的司法现状发生异化,辩护权也会因为主客观的原因而导致行使效果不尽如人意,此时,如何对相应的辩护权加以救济,是保障权利实现的重要屏障。反观我国的刑事立法,当辩护律师行权受阻时,要么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要么救济措施几乎形同虚设。在上述的“聂树斌案”中,几任代理律师数十次的请求阅卷无果而未得到救济便是明证。
其二,辩护律师的核心权利处于缺位状态。观察《刑事诉讼法》以往的修改内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实现了不断增量,但这一进步并不意味着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律师在场权,而正是这一核心权利的缺位,致使刑讯逼供、诱供、疲劳审讯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也多为有罪供述或其他证据的重要来源渠道。其三,值班律师的定位及其权利保障不到位。自值班律师制度试点以来,便对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作出了严格區分。区别于辩护律师,值班律师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服务,并不参与案件的阅卷与调查阅卷,更不参与本案之后的庭审。实践中,值班律师更侧重于作为诉讼活动的监督者与见证者,甚至是异化为一种“站台效应”。[ 姚莉:《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的角色与功能》,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第42-49页。]另外,值班律师的报酬偏低,全国各地多是以补贴的形式进行发放,这极易挫伤值班律师的积极性。其四,值班律师的设置过于理想化。如前所述,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检察院以及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其提供便利,该规定因过于理想化而难以落地,这是因为各地经济、律师行业等发展水平不一致,部分地区的值班律师队伍储备不足,[ 据笔者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调研发现,部分县级法院每年办理的刑事案件有400多件,而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仅有1人。如果在这些地区推行值班律师制度,要么值班律师将面临“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要么值班律师的数量显然不够。]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如何激活辩护制度的功能,进而实现对刑事错案的防范,有如下途径:其一,构筑双轨制的律师权利救济机制。“无救济,无权利”是对权利保障的基本阐释,而为了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及时得到救济,需要构筑以同体与异体救济为构成的双轨制救济机制。也即当辩护律师的权利行使并未得到司法机关回应,或者对拒绝的理由不服时,一方面,可以向当地的律师协会反映,并提交相关的线索和材料。律师协会经审查确实属于不当拒绝时,应当与作出拒绝决定的司法机关及时沟通、协调。另一方面,辩护律师既可以向作出拒绝的司法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复议之后或者直接向上一级司法机关申诉。其中,复议、申诉的结果需要及时告知辩护律师。其二,增设律师在场权作为辩护权的内容之一。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两大法系的多数国家也基本确立了律师在场权,并将其作为律师的核心权利。而在我国,随着人权保障的进步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完善,设置律师在场权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邵聪:《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的域外考察与中国构想》,载《学术交流》2017年第10期,第124-132页。]为此,可以尝试开展律师在场权的试点,并及时总结经验而后吸收至刑事诉讼立法之中,自侦查机关讯问之时需要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律师在场,在律师缺席时可以拒绝作出供述。当然,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书面放弃这一权利。其三,准确定位值班律师并给予相应的物质保障。实践中,值班律师被见证人化,常被理解为诉讼程序的见证人。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值班律师的定位,从立法上肯定其辩护人的身份。不过,这只是一种立法技术层面的变动,还需要赋予其辩护律师享有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相关性辩护权。另外,还应当改变目前对值班律师按日支付补贴的“一刀切”做法,在提高报酬基点的前提下,[ 例如,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作为值班律师的私人律师的薪酬为84澳元/小时 (约430元/小时)。参见贾午光:《国外境外法律援助制度新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以案件量与案件难易系数相结合的方式支付报酬,提高值班律师的办案积极性。其四,因地制宜对值班律师规定作出适度变通。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水平很不均衡,这是思考中国法治问题必然要直面的基本问题。[ 李昌盛:《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研究》,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247-274页。]对于部分经济落后地区,如果严格要求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设置值班律师,显然不切合实际。比较妥当的做法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案件的繁简程度加以区别对待,对于较为疑难复杂的案件,由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对于部分简单或认罪的案件,由青年或者从事综合业务性的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五、庭审实质化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庭审实质化是庭审虚化、庭审形式化的相反概念,是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庭审“走过场”现象的回应。从官方话语理解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几乎可以将以审判为中心等同于庭审实质化。[ 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861-878页。]但客观而言,庭审实质化的外延要远比以审判为中心狭窄,其只是以审判为中心在庭审这一诉讼场域所作出的要求。不过,这至少反映了庭审实质化在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框架中的重要地位。
在传统刑事诉讼语境下,按照《宪法》及《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定位,彼此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而在国家治理犯罪的宏观目标之下,三机关均与刑事案件的裁判结局存在某种利害关系,[ 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以至于在实践中,三机关之间呈现出“制约不足,配合有余”的运行样态。有学者曾将公检法三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工作模式比作“做饭、卖饭、吃饭”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我国在以往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卖方市场”,即“买家吃什么饭由卖家决定”,换言之,法院的判决结果取决于公安机关,侦查决定审判。[ 何家弘:《公、检、法=做饭、卖饭、吃饭?》,载《政府法制》2003年第2期,第12-13页。]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三机关之间“重配合、轻制约”的现象。正是在此背景下,公检法之间表现出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法院对于先前阶段已然确认的证据、事实只作形式上的审查和认定,庭审的应然功能被很大程度地削弱,没有对刑事错案进行足够的“拦截”。
根据上述,庭审虚化、“走过场”是造成刑事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落实庭审实质化必然有助于刑事错案的防范。结合当前对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措施来看,关键在于实现“四个在法庭”,也即“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这是庭审实质化的四个基本支点。
其一,证据质证在法庭与刑事错案的防范。证据质证在法庭是指控辩双方应当在庭审之中就证据的“三性”以及证明力的大小、有无进行说明和辨别的过程。在诉讼活动中,由于查明案件事实是以证据为中心的叙事活动,这指明了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重要性。而在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通过在庭审之中对证据的相关问题进行充分的质证,能够为法官了解案件的证据事项,进而形成有罪与否、罪轻罪重的心证提供必要保障。分析以往的刑事错案发现,很多案件中的证据都存在证据资格存疑的问题,如果经严格审查后予以排除,被告人可能会因此而获得无罪的结果,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但因为法官对于证据的质证并不重视,忽视了这一庭审环节的功能,对控方提供的证据偏听偏信,致使酿成了冤假错案。当前,落实证据质证在法庭,一是需要发挥庭前会议的“过滤”作用。这是因为,在员额制改革的背景下,相对比以往而言,法官队伍朝着精英化的方向发展。在提高质量、压缩数量的同时,随着案件总量的不断上升,人案矛盾较为突出。因此,倘若将某一案件的所有证据均交由庭审时质证,势必会拖延我国刑事审判的进程。此时,便需要发挥庭前会议的“过滤”作用,确认控辩双方达成合意的证据,并且将有争议的证据以及争点加以提炼,交由庭审时质证;二是突出控辩双方质证的重点。在庭审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果对所有证据的质证均投入同等的诉讼资源,这种“平均发力”的做法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从以往错案的证据种类来看,有罪供述既是证明被告人构罪的关键支撑性材料,也是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所获得的证据。倘若将其作为控辩双方质证的重点,一旦有罪供述被推翻,案件的印证证明体系可能也会遭到毁坏,进而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的证据链条,被告人也就实现了出罪。[ 龙宗智:《印证证明在证据审查与事实认定该如何运用》,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8日,第3版。]其二,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与刑事错案的防范。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为了达到证明标准(条件)的要求,每一诉讼阶段的主导机关均有责任查明案件事实,而且这种责任并不会因为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条件)而实现豁免。不过,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会由于先前两个阶段的事实确认而弱化庭审时的查明,或者通过查阅案卷的方式實现查明,在此基础上作出有罪的心证,出现“庭外审”“书面审”等问题,进而忽略了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的功能,最终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如何做到查明案件事实在法庭,排除法官的庭前预断,保证法官裁判的作出不受侦查行为与侦查结论的影响,[ 党建军:《防范冤假错案的制约之方与理性之法》,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602-604页。]应当从法官庭前获得案件信息的“源头”加以考察。实践中,刑事案卷是由侦查机关负责制作、起诉机关加以补充和移送,而且由法院进行审查和运用,以文字为载体、以卷宗为形式的书面证据材料。[ 牟军:《刑事案卷:以文字为起点的证据分析》,载《法学论坛》2016年第6期,第5-17页。]从案卷所指向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证明的是被告人构罪。如果法官在庭审之前接触案卷,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作出有罪的预断,从而弱化庭审中查明案件事实的功能。但在全案卷宗移送的背景下,通过庭前阅卷实现庭前审查是开启审判程序的必经程序,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为此,从短期来看,可以将庭前阅卷事项交由法官助理完成,以此减小法官的预断。从长期来看,可以效仿域外国家的先进做法,设置专门的法庭,并由专门的法官负责审查。[ \
Study on the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Misjudged Criminal Cases Under the Reform of Trial Centralism
GAO F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Abstract:
To prevent crime is a worldwide difficult problem, our country is in huge clumps, judicial credibility is being challenged is propo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ial centered lawsuit system reform, this is to prevent feasible scheme of criminal misjudged cases but trial centered as a kind of great reform, the reform of inner contains many components, need to discriminate and analyze how the trial centered and realize the prevention of criminal misjudged cases, shall be detailed specific technical route, respectively to clarify the judicial idea of evidence rule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lationship and problems between the defense system and the substantive trial and the prevention of misjudged criminal cases, the author gives the response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entered on judgment; judicial philosophy; rules of evidence; system of defense; substantive trial
本文责任编辑:周玉芹
收稿日期:2020-06-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司法中的运动式治理”(20YJC820058)
作者简介:
高峰(1974),男,四川南充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①代表性的成果有:周士敏:《刑事诉讼法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由审判中心说到诉讼阶段说》,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49-54页;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第9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