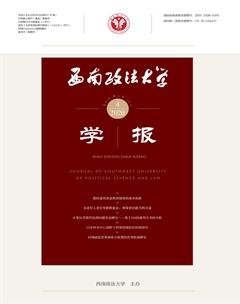论章太炎理解的平等和自由
摘 要:对平等和自由的论述,是章太炎法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民族主义,章太炎理解的平等,首先在于启动摆脱清王朝制度性民族歧视的革命,但需遵守原则,且即便是革命成功之后,也将面对“平等难”的现实。章太炎理解的自由,重在“明群”和“明独”,且大独必群,小群则为大群之害。彼时,体现平等和自由的政体形式通常被认为是代议制,但章太炎认为并非如此。章太炎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以民族主义为根基,而以超越民族主义为归宿。
关键词:章太炎;平等;自由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4.02
引言
自1840年開始,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中国似乎丧失了其“中国”的本意,即所谓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策二》)——那个诸夷环伺、四海臣服的中国,不得不因遭遇冲击而有所变化。或者说,那个以“天下”观念自我定位的中国已经开始做出改变,从“天下之中国”向“万国之中国”转向。①
上述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表达,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文化主义倾向,其间经过器物之变、制度之变乃至文化之变的更迭后,“中国”这一概念与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具有民族主义萌芽的征兆。或如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所言,那个存在了数千年的儒教中国已经“作为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 就平等而言,在对统治者压榨、列强欺辱和民风不古的叔世作出一个清晰判断并找到一条解决之道之前,谈论平等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对于革命者章太炎来说,近代中国的种种遭遇使救亡压倒启蒙的风气成为了传统,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政治不平等和数百年的民族不平等之后,逐渐认识到亡国灭种的根源就在于此时,谈论平等又显得迫在眉睫。
从自由统摄下的群己关系来说,章太炎处于一个中国语境意义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分水岭之上,这一点类似于卢梭,或者说是有些类似贡斯当描述的那个介乎于“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人,“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相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
一、民族主义的平等
按照西方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和定义,其涵盖范围相当广泛。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所理解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指一条政治原则,即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合适的界定。同时,在盖尔纳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在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隔开,族裔跨越疆界的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就被正式排除了。
二、平等难
如果能够成功解决上述制度性民族不平等问题,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安排和改善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平等(这里的“中国本土意义”是指立足于帝制中央集权与乡村乡绅自治并存的现实状态),似乎更为意义深远。民族革命中谋求的平衡其侧重毕竟仍在于破坏,而所谓“不破不立”的精髓却在于破坏后的建设,如何理解并促进平等,章太炎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展开。
从形而上的层面讲,章太炎取法佛学,汲取西方哲学,主张人类社会及其个体无论信仰、精神、个性均应平等,亦均可平等。
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在古汉语中并不以相连的形式出现,更多是用“平”来表示现代意义上平等的部分含义。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隐含着程序正义,但其价值取向更接近于分配正义,即“不患寡而患不均”式的平均。平与等连用,是东汉时期翻译佛经创作的一个新词,体现了古印度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其渊源自婆罗门教的传说,四大种姓之一的刹帝利种姓的始祖“劫出之王”,名摩诃三摩多(梵语Maha∧sammata),汉译即为“大平等王”,职司赏善罚恶,公正执法。后来的译经者把Maha∧sammata音译为“阎摩”“焰摩”“阎摩王”,其意译则为平等王。唐代以后汉传佛教文化中的“阎摩王”,又演化为阴间的十殿阎王,而“平等王”仅位列十王的第八位,称其为观世音菩萨化身,在冥途掌管亡人百日,此为佛家平等由印度文化融入汉文化的渊源。其后,在世俗的汉语运用中却另有一番曲折的经历,即印度佛教主张的一种无差别的事实判断,一种平静、无欲无执的、斯多葛式的立场,以及一种“舍弃一切”故“一切平等”的教义追求,在汉唐以后其彼岸性在充斥着此岸性的“儒教中国”中消磨殆尽,“平等”一词更多地被使用为表示“等第”的名词而非形容词。甚至“平等”就是中等、劣等而非优等,现代意义的形容词平等的褒义氛围全然不见。[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378页。]至于近现代“自由平等博爱”所指的平等,却正是章太炎所处时代懵懂欲知的理念。
西方意义上的平等,关注的更多为程序正义,较少涉及分配正义,如韦伯所提出的新教徒不遗余力地创造财富为获取上帝的选民资格而努力,是资本主义奋发图强的一种伦理,通过竞争产生的实际不平等并不属于平等价值取向的讨论范围,程序正义意义上的平等提供的只是一种平等资格罢了。章太炎从形而上的方面讨论平等,是按照程序正义资格平等的预设,遵循佛家平等的进路,主张人的信仰、精神、个性均应平等,亦均可平等。从信仰的方面出发,章太炎提出产生信仰的资源有三种:惟神、惟物、惟我,并对这三种资源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其中,“主惟神者,以为有高等梵天;主惟物者以为地、水、火、风,皆有极微,而空、时、方、我、意,一切非有”[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无神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而“主惟我者,以为智识意欲,互相依住,不立神我之名”[同上注。]。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三种资源对平等的贡献是存在差异的。章太炎认为:“惟我之说,与佛家惟识相近,惟神、惟物则远之。佛家既言惟识,而又立言无我。是故惟物之说,有时亦为佛家所采。”[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无神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396页。]也就说基于个体智识、意愿和欲望的相互支撑,惟我更接近于佛家的平等,而惟物有时被佛家援引是因为佛家虽然立足众生平等但仍不放弃“无我”的终极追求。惟神者认为在人世之上存在更为高级的“梵天”,所以惟神说“奉崇一尊,则与平等绝远”[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无神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6页。],要实现众生信仰的平等就必须破除神教,即所谓“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同上注。]。打破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和无所不备的各种神祗的光环后,平常百姓的平等在信仰领域就有了发展的空间。而对于中国及中华民族而言,因理性早启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与其是说破除神教的不平等性,毋宁说是张扬普通个体在形上层面的平等性。
从形而下的层面讲,章太炎立足于传统中国在1840年以来命运多舛的遭遇,提出“平等难”的新主张,遵从名实相符的原则,力图还原真实的平等。
章太炎推崇庄子,尤为看重《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但章太炎指出:“其唯《逍遥》《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作论者有其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 章炳麟:《齐物论释·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也可以说章太炎所处的接近亡国灭种的时期,正是“人与人相食”的时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产生的影响,使章太炎必须做出根植于传统合理性和现实迫切性的雙重努力,而洞见并阐发“平等难”,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易·泰》有这样的语句:“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是章太炎“平等难”立论的根源。他从自然现象的观察中(“水平而不流”和“云平而雨少”),提出“政平则无威”,并进一步认为“天地之道,无平不陂”[ 章炳麟:《訄书·平等难第二十八》(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5页。],而对前文所论述的平等学说起源于印度的原委,章太炎有与前人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佛教讲求平等的目的是拯救时弊而不是一味的恣意妄为,而它所救的时弊是存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严格划分的状态。这个划分悬殊的体系所具有的永恒性和合法性,致使佛教的平等理论去“矫枉”,但这在章太炎看来却已经“过正”,以至于飞禽走兽皆有佛性,其体悟的最高境界可以与人类同等。因此,章太炎对一味地追求普天同庆式的平等提出了警告:“觊以齐一四类,而闳侈不经,以至于滥,由牛鼎之意焉。愚者滞其说,因是欲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是其于浮屠也,可谓仪豪而失墙矣。”[同上注。]“仪豪而失墙”的做法,即是对于平等问题没有做到具体状况具体分析,也不再注重分别应对。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平等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须有弘扬与贬抑的区分,即“行之南北朝,则足以救弊,行之唐宋以后,则不切事情”[ 章炳麟:《訄书·平等难第二十八》(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5页。]。其原因在于南北朝时门第观念极为深厚,公卿与囚虏的高低贵贱完全不依照他们的职位、处境,而是依照其出身门第。所以如果能够在南北朝时期倡导平等,对于当时的政治、民生良益颇多。但在唐宋以后,门第观念日益淡漠,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构架使得门第、出身的“身份”稳固性和影响力,已经不及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制而拥有的“身份”稳固性和影响力,且不论科举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究竟是“吏的儒化”还是“儒的吏化”,仅就其为四民社会之间的交流和变迁提供的途径来说,梅因意义上的“从身份到契约”在中国的影响力也远不如西方封建社会时期浓烈。其中,士与农、工、商的互动,尤其是士农之间的互动使得在乡野耕读和通过科举栖身官僚士卿集团产生了十分微妙的互动,形成了一个与西方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梁漱溟先生名之为“职业分途”:“他们(生活在西方封建社会)若想开拓自己的前途,只有推翻这种秩序,只有大革命。但在中国这种职业分途的社会,便不然。政治上经济上各种机会都是开放的。一个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初无限制,尽可自择。”[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169页。]基于如此的社会现实,即选择个人身份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在于个体的天资以及更为重要的努力奋斗时,一味地强调平等就显得有些问题。或者说,既然已经存在着可以改变个体生存状况的手段和方法,只要遵从一定的原则就能实现个体抱负时,强调平等的确不如提倡读书追求功名更具有吸引力。况且,尽管某些特殊的群体,比如伶优、娼妓,并不享有参加科举的体现基本程序正义的资格平等,但大部分普通百姓享有并通过科举受益(尽管其难度很大,成功的概率不高)。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士农工商之间在其权利、义务、待遇、资产和生活状况等方面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才使得四民社会得以互动。如果四民平等,那么通过科举、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从农到士、从商到士的转变,如果不是出于响应某种类似“苟利国家生死以”的道德感召,从个体的角度看将不再有具有吸引力和价值。切中要害地、针砭时弊地以及目的明确地追求平等,在章太炎看来无可厚非,但不切实际地罔顾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状况强求平等,则是“非拨乱之要也”[ 章炳麟:《訄书·平等难第二十八》(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5页。 ]。
此外,章太炎从男女平等的问题入手,进一步分析了在传统中国平等难的原由。他认为之所以存在男女不平等,是因为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战乱、饥馑、苦役和犯罪,导致男性数量减少,男性成为相对于女性的稀缺资源。为解决女子的婚配和性需求问题,男子拥有一个以上的女性因而顺理成章,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其强势地位;其二,古代社会人口稀少,为了人类自身的繁衍,从究竟是一个女子配数个男子利于繁衍,还是一个男子配数个女子有利于繁衍,出于此种生物竞争策略的考虑,男性的强势地位也无可避免。[章炳麟:《訄书·平等难第二十八》(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6页。]章太炎对平等的理解,其实质就在于与其名实不符地倡导平等,不如名实相符地坦陈不平等,即如庄子所说:“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庄子·列御寇》)。
但是,男女不平等并不是完全的、绝对的,章太炎举东汉樊英为例。樊英有病卧床,樊英的妻子安排女佣人问候病情,樊英立刻下床拜谢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后汉书·方术列传七十二上》。]这说明君子与其他人在礼仪方面是平等的,不平等处在于其审时度势的能力。同时,君臣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平等也不是完全的、绝对的,至少在评论、褒贬时可以是平等的,并指出在古代中外君主下葬的时候,都存在臣下可以褒贬君主的惯例。古埃及的法老下葬前或者颂扬其功德,或者指摘其过失,并将功德与过失相比较,过失大于功德的法老将被剥夺下葬在墓室及金字塔中的资格。我国春秋时期,也要对下葬前的君主的功德、过失进行列举、点评,称为“诔天王”,过失太多以致有失德、罪过者,《春秋》就不再记录其葬礼。[章炳麟:《訄书·平等难第二十八》(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7页。]这些行为、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男性有所收敛,会使君主有所忌惮,但在总体上说并不能为平等的天然合法性在现实中提供过多的支撑,更无法改变事实上不平等的格局。
平等难的挑战,来自于名实相符原则的落实程度,章太炎提出平等难的原因也在于此,如其所言:“兼爱酷于仁义,仁义憯于法律,较然明矣”,而这些不切实际的努力的结果不过是“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 章炳麟:《齐物论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在阐明章太炎对平等理解的基础上,或者说立足于民族革命成功并认识到“平等难”的现实状态及其必要性之后,我们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转向章太炎对自由的理解,转向其独树一帜地对“群”和“独”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从“群己关系”入手的。
三、群己关系中的“群”与“独”
先秦儒家中讲求“隆礼重法”且具有朴素唯物思想的荀子,一直是章太炎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章太炎对群己关系阐述的理论起点,即来自荀子。
就群己关系,荀子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命题(他认为此命题是礼法产生的原动力):“明分使群”(《荀子·富国》)。之所以可以明分使群,其前提在荀况看来是他所主张的人性本恶的人性论。很显然,如果人性本善,人人皆有善根,自然不会生出恶果,不会有离经叛道,不会有违法犯罪,但人类的历史却非如此展开。相反承认人的私心杂念和种种罪恶的念头,就可以未雨绸缪加以预防和矫正,或者说荀子主张的人性本恶,不仅仅是说他认为的“人之性恶”,而更为紧要的是荀子所提出的“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主张。而所谓“伪”的本意,并非虚伪,其意指为后天人的作用,即认真学习就能学会,学会就能做好,做好就能成功,这种人的作为叫做“伪”。荀子在此用“化性起伪”和“明分使群”当作矫正人性本恶的两条重要措施,也可以理解为礼与法的兼收并蓄、并行不悖——也即,强调由内矫正的礼充任化性起伪的职责,强调由外规范的法充任明分使群的職责,从而实现秩序的养成和存续,实现人本身的存续和发展。此种存续和发展的目的,荀子给出的是人文主义的回答:“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荀子·富国》),法律在此也应该是百技之一,法律的目的也在于维护这种存续和发展。
推崇荀子的章太炎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赞同荀子群体的产生必然伴随争夺的命题,认为:“群者,争道也”,而且此种“争道”具有相对于“明分使群”来讲的基础性和先决性,“古之始群其民者,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其义则取诸《噬嗑》,而明罚饬法自此始。吾是以知先有市井,而后有街弹之室;其卒则立之天王、大司马,以界域相部署,明其分际,使处群者不乱”[ 章炳麟:《訄书·明群第二十三》(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2页。]。由于存在群体,必然要产生纷争,要解决纷争则必须要养成和维持一种秩序,要规范这种秩序就必须要制定法律,这个逻辑通情达理却并无什么高妙玄奥之处。章太炎探讨群己关系从群体入手也不在于阐明这一逻辑,而是要反对任何违背这一逻辑的举动和措施。
在章太炎看来:“有正、乏之义,而后有议官,其职则置于定法之后。初定法也,一致而已矣,非有正乏,则奚噂沓以持其议,”[同上注。 ]就是说,法律的产生在先,由于法律在施行中存在的缺憾和问题,才使得议官褒贬其得失,议论其存废,商讨其改善。新形成或是新制定的法律,只是具有“一致”即形式上的统一性,至于其褒贬、存废和改善则付之阙如。章太炎在此援引了欧洲法律形成的例子:“昔者欧洲十有八周之世,严刑厚敛,民无所聊赖。拿破仑出而更之,播及领国,皆厥角稽首,若弟子之受命于先师,非甚难也。然而英吉利之更制也,米入不征,则老农阻之;宽假佣保,则敞主阻之;禁奴黑人,则豪右阻之;免他国商税,则大驵阻之;讦讼三十年,然后大定。”[
同上注。 ]这两种情况的差别,实际上反映出某些或某种法律的诞生,无法摆脱历史和现实的左右。身处横征暴敛、无所聊赖的水火之境,民心思变革,因而拿破仑的诸多改革水到渠成。而在深具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凡事当然也包括法律却要经过经验的诸多考验,在不同势力的博弈下最终胜出者自然就是法律。此种成王败寇式的法律产生机制,最具合理性和效率,在章太炎看来它要远胜于由议院、议员所制定的法律,后者制定之法律只具有“一致”的表象罢了。从此意义上看,章太炎展示出浓郁的经验主义偏好,议院或是立法者的工作,应该在群体的纷争(在某种限度内,比如政权的安全运转或某种意识形态的确立)产生并找到消解之道后,对这种做法展开评判,或接受或修改或否定,然后以法律的形式公之于众。这很接近哈耶克描述的“合格的立法者”,立法者的任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地型构起来并得以不断重构。[ \ 四、代议制批判
章太炎所批判的代议制度,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代议制度,即分上院(贵族院)与下院(平民院)的议会制。对代议制度,章太炎有极深的洞见,他认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尤其是其上院(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代议然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
在此,就涉及到一个中西方关于封建概念的定义和理解的问题。章太炎所谓的封建,是指一种本初意义上的或是说周初分封制下的封建,即并非是如牟宗三先生所批评的那种“象征的观念”[牟宗三先生认为:“照西方讲,封建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各地方各民族退而自保的时代。若是反封建是反这个封建,那么罗马帝国未崩溃之前,即不能算封建;封建时代以后至于今,亦不算封建。那么你反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反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那一个散落的状态吗?照中国讲,封建是西周三百年周天子的封侯建国,作用乃是集体开垦,充实封地,以‘拱周室;封建在这里带有积极的意义,与西方的恰恰相反。然而中国自秦汉以后即无封建,那么你反封建是反什么呢?难道是反西周三百年吗?我们在此可以看出,‘反封建并没有一个清楚而确定的意义。其实,它只是一个笼统的象征的观念,实即反对一切‘老的方式,而以‘封建一词代表之,概括之”。参见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因而无论在能指还是在所指方面均与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截然不同。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既与周初本初意义上的封建不同,也与诸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封建遗毒”中提到的封建不同,同时基于封建而扩展的封建主义,也另有寓意。如伯尔曼所说:“封建主义据说是中世纪期间存在于西方的一种社会类型;而且,它据说也是在非西方文明历史的‘中古时期存在过的一种社会类型。这种习惯用语隐藏着一种种族中心的设想,即,属于西方的社会经济历史的一定特征也被拿去界定其他社会的社会——经济秩序。”[ \ 结语
事实上,在革命等于进步、反革命等于落后的语境中,章太炎的位置显得有些尴尬,既革命又反革命、既激进又保守,悖论式的实践和思想的历程不惟在革命中,也反映在学术上。统观章太炎的法政思想,如何梳理并阐释他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并不容易。章太炎可以费尽心智,以史实为依据论证传统中国法制的合理,也可以不顾生死投入现实革命,反抗民族压迫和外辱。章太炎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反映出他不是偏颇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章太炎对平等和自由的见解,其特立独行处就在于谋求民族平等的同时,极其深刻地论证了西方意义上的平等,在近代中国必须做出根植于社会实际的调整。任何对于平等的理解,既要承担起谋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责任,也要时刻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带来的风险。如何承担责任并警惕风险,章太炎已是倾力而为,恰如鲁迅 “做学术的革命者”之评价,“并世无第二人”:“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无第二人——而太炎先生风范即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556页。]章太炎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这种礼崩乐坏与孔子在周朝末年提到的礼崩乐坏有相同之处,即传统的、统一的、具有当然合法性的统治权力被其他权利/权力侵扰、分割直至取而代之。也具有不同处,不同在于侵扰、分割和取而代之的不仅有民族框架之内的势力,还有西方列强势力。多方势力的共处和博弈,使得章太炎的学术、思想、言论和革命行动都不得不有一个纲领,而这个纲领,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自救并找到复兴之路。因此更确切地说,就平等、自由而言,这个实现民族自救并找到复兴之路的纲领,起于平等而导向自由,包括获得民族整体意义上的自由和个人物质的、精神的自由。
总体上看,章太炎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以求寻民族主义的同质性为正,以论证平等难的个体的异质性为反,而终以超越民族主义的自由为合。在此意义上, 通过梳理章太炎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钩沉历史,或可展望未来。
On Zhang Taiyans Understanding of Equality and Liberty
QI Tonghu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berty and freedom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Zhang Taiyans law and politics idea. Based on nationalism, to Zhang Taiyan, equality means the antidiscrimination revolution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even after the success of revolution,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realize equality. Zhang Taiyan believed that understanding autocracy and collectivism would be essential for liberty, a big autocrat must be popular, while the small groups must be harmful to the whole society. Then representative system wa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can embody equality and liberty. However, Zhang Taiyan did not think so. His understanding of equality and liberty is based on nationalism and aims to surpass nationalism.
Key Words: Zhang Taiyan; equality; liberty
本文责任编辑:龙大轩
收稿日期:2020-05-25
作者简介:
亓同惠(1976),男,山东莱芜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日本东北多文化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
① 这一转向发生的时间,学界有多种看法:如果以《南京条约》为参照,意味着中国在1842年开始以向英国割地赔款的方式放弃天下观;如果以《天津条约》为参照,就意味着中国在1858年开始放弃天下观而加入国际社会。参见Immanuel C.Y. Hsü,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如果以《馬关条约》为参照——不仅是因为战败而向日本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社会结构内部转型,则意味着从1895年开始放弃天下观。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第29-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