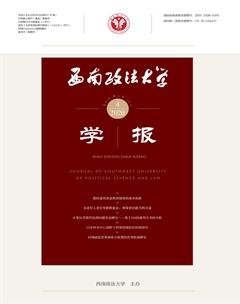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基本问题研究



摘 要: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应否降低,是立法层面的一个问题,关系到规范性评价和刑罚作用等方面,虽有较强的综合性但不复杂。只要承认任何人都应当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承认被害人比加害人更值得保护,承认当前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低于1979年已满14周岁的人,就会发现一味反对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显得偏执。对因未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罚措施无用武之地,家庭管教基本无效、收容教养适用太少、工读学校日渐式微,现有的处理机制聊胜于无,呼唤着立法的变革。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观点颇有市场,却不符合当前的我国国情,并不可取。若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罪行负刑事责任,是比较合理的。这有利于妥善处理此类事件,增加其违法犯罪成本,可以有力地威慑相关未成年人、减少未成年被害人,从而保障未成年人整体福利,符合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这是修正法的滞后性的现实需要,符合且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责任年龄; 恶意補足年龄规则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4.06
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违法犯罪行为频发,一些涉案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却依法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慨。关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应否降低、如何降低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法律界的激烈争论。2019年3月,刘希娅等30名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议案,包括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建议将我国目前的刑事责任年龄降低2岁,即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2周岁;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鉴于此,笔者撰写本文建言献策,权作引玉之砖。
一、我国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规范与现状
(一)我国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指导思想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权益保障,在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就显著。早在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已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2006年修订后的该法第54条第1款沿用了这一规定,2012年修订该法时仍保留了这一条款。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第1款也有相同规定,2012修订该法时亦予以保留。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66条第1款、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第1款、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06条、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第2条均重申了这一指导思想,甚至《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辩护工作指引》也不例外。201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57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坚持优先保护、特殊保护、双向保护,以帮助教育和预防重新犯罪为目的。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青年发展和青少年犯罪预防明确了指导思想、根本遵循和总体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
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性规定已经落实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方方面面。至于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亲情会见、心理干预、强制辩护、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犯罪记录封存、一站式询问法、“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工作室、普法进校园、检察官担任小学的法制副校长、组建未检科、少年法庭等诸多制度和工作机制创新,均使广大未成年人受益良多。
(二)我国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行法律概况
我国现行刑法体系由1997年《刑法》加一部单行刑法、十部《刑法修正案》组成。1979年《刑法》第14条规定,“已满十六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997年全面修订1979年《刑法》时有所调整,其第14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以下简称14~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14~16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罪行以外的犯罪行为,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刑法规定的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尽管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小于符合“三性”的犯罪,属于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只是因为未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也意味着不能展开追诉活动,刑事立案、起诉、定罪量刑均不合法。
14~16周岁的人只需对这八种特定的严重罪行负刑事责任,是否有必要增加或者减少罪行?几乎无人对此提出明确主张,可以推断主流观点认为不必增减。笔者亦认为无甚必要,故主要探讨另一个问题——不满14周岁的人(暂不考虑年龄下限)对其实施的哪些危害社会的罪行应当负刑事责任?很显然,不满14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罪行只能小于或等于这八种罪行,而不能超过这八种罪行。如果认为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保持现有规定不变,则可简称为“现状派”。笔者不赞同“现状派”的观点,后文将展开论述。
(三)未成年人罪行数据及实例
可以说,1980年1月1日(或1997年10月1日)至今的未成年人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均是未成年人对刑法规范的反映,也是体现“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实效的重要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体系。2009年至2017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未成年人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从司法大数据看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预防》,http://www.court.gov.cn/upload/file/2018/06/01/10/12/20180601101246_54227.pdf,2020年5月18日访问。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故意杀人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这并不是我国《刑法》不应规定故意杀人罪的理由。同理,“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未成年人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并不能成为反对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理由。若其罪行恶劣、后果严重且绝对数相当巨大,那么予以某种惩罚是必要的。]应当承认,这一成就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离不开全社会的艰辛付出,不过并非完美无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里的未成年人犯罪,只是指进入审判阶段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当然小于现实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数;因“轻缓化”思潮影响而不立案、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也未纳入统计;同样的危害行为若由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则根本未纳入统计范畴。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校园暴力案1000余件,2016年、2017年分别同比下降16.51%、13.37%。其中,11.59%的案件受害人死亡。2015~2017年,57.5%的校园暴力案件为故意伤害案件。可以推断,全国每年约有100名未成年人因校园暴力而死亡,其残酷程度不难想见。现实中,未成年人弑师、杀害校园之外的人、杀害或故意伤害成年人致死的情况,不会纳入上述统计数据;未成年人之间的侵害行为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恐怕有相当多并未立案,也不会纳入上述统计数据。那么,在分析要不要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时,有必要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自觉超越“信息茧房”及其局限性,从而找到正确的途径。
2019年12月20日,在“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披露: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8.06万人,起诉10.07万人,其中2018年全年批捕、起诉人数同比分别上升18.39%和6.8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高检等举行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犯罪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发布会》,http://www.scio.gov.cn/xwfbh/qyxwfbh/Document/1670581/1670581.htm,2020年5月20日访问。]其中,14~16周岁、16~18周岁的人分别有多少及所占比例如何,多少人在14周岁前已经实施过《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未成年被害人有多少,均不得而知。
由于法律规定及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等方面的原因,新闻媒体报道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往往相当少,且使用化名,语焉不详(如年龄往往用“岁”,而不是“周岁”),不乏“烂尾新闻”。即使判决有罪,其犯罪记录也会封存,难以运用大数据分析。案例分析法、简单枚举法虽然欠缺代表性和说服力,但也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笔者基于自己收集的近年来14~16周岁的人的恶性犯罪行为和不满14周岁的人的触法行为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制成下表: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的案例因其恶性大、有传播力,故能引起巨大反响而被收集到。虽然发生了恶性犯罪,但学校、家庭等“捂盖子”以致不为外界所知,当地部分人知道但新闻媒体不知道,新闻媒体采访了但因某种原因未公开报道,或其报道被海量信息湮没而笔者未掌握的情况,肯定是大量存在的。由于样本偏少,要素不全,分析其罪名、比例等也无甚说服力。不过,由上表不难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如下规律性特征:其一,其犯罪几乎都是自然犯、鲜有法定犯;相当部分未成年人的罪行是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恶性犯罪,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抢劫等犯罪,与已满14周岁的人实施同种犯罪基本没有区别。这些不是极端个案,而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其二,十二周岁以上不满十四周岁(以下简称12~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罪行明显多于不满12周岁的人的罪行,很可能与其生理机能更强、犯罪能力增长有关。至于敢于加害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其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更大。其三,都是有被害人的犯罪,被害人大多是更幼小、更弱小的人和同龄人,同样是未成年人。其四,相当部分的未成年人的犯罪,是蓄谋的、积极追求犯罪结果发生的。其往往公然宣称“我是未成年人,不用负刑事责任”“我是未成年人,不能判死刑”“犯罪要趁早”,甚至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绝不是因为不懂法、不懂事,甚至很难谓之“法律意识淡薄”。有预谋,蓄意为之,主观恶性大,这些特点在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中均得到了体现。其不是偶然犯罪人,而是犯罪人格的外化,至少是行为时的人格表现——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其可塑性。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并研究了“犯罪低齡化”问题,成果颇多,兹不赘述。
对未达相应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依法不能追究。可以说,现行法律对于未成年人之间发生的不法侵害事件中的被害人保护,存在严重缺陷。当然,法律不可能规定:未成年人伤害其他未成年人,造成严重后果或情节恶劣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伤害成年人却不负刑事责任。如果规定未成年人应当对某个罪行负刑事责任,就不应当、也不可能限定被害人为未成年人。
二、分析刑事责任年龄的方法论
讨论任何问题,都需要以一定的共识为基础。下列论断是不言而喻的:一是任何人不能因自己的错误行为而获得利益,而应当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道德谴责、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二是守法的人比违法的人更值得保护,被害人比加害人更值得保护。
皮艺军教授认为,降不降刑事责任年龄,取决于三个标准:生理标准、心理标准和社会标准。“一般而言,青春期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生理差距上最小,心理次之,社会经验上差距最大。”[张盖伦:《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年龄只能一刀切?》,载《科技日报》2019年10月30日,第04版。]鲜为人知的是,1954年我国《刑法原则指导》草案规定,12周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1957年《刑法》草案规定,13周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提升,青少年的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平均身高明显提高,甚至早熟现象已是众所周知。可以说,近十几年出生的人在12~14周岁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信息获取量和心智成熟程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979年时已满14周岁的人的水平。即使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也几乎没有人认为当前12~14周岁的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未达到1979年时已满14周岁的人的水平。如果认为不需要降低,则实质上等于认为1979年《刑法》规定14周岁是偏高的。如果既不认为1979年《刑法》规定14周岁是偏高,又认为现在不应降低,则是自相矛盾。
此外,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2005年失效)第9条、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均规定,受治安管理处罚的年龄下限是14周岁。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受行政处罚的年龄下限是14周岁。1986年《民法通则》第12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是10周岁;2017年《民法总则》第19条、第20条以及2020年《民法典》第1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是8周岁。也即,8~10周岁的未成年人此前被认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17年10月1日后被认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总体而言,未成年人对某个行为的法律意义的认识水平在提高,法律责任年龄呈下降趋势。固然不可将三种法律责任年龄混为一谈,而刑法规定——特别是自然犯可以说是道德底线,认识犯罪行为的错误属性并不比认识买一件文具的法律性质更难。如果其连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自然犯的后果也没有正确认识,恐怕没有人会相信;那么,其明知故犯,则说明其是道德感差、易冲动、易怒或有暴力倾向的法冷漠者——这可能更符合实际。
美国精神病医师埃里克森(E. H. Erikson)把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即心理社会发展(psycho-social development)的八大阶段,其中青春期(12~18岁)的自我意识主要是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主要包括矛盾心理、逆反心理、好奇心理、从众心理、模仿心理、报复心理、义气心理,这在我国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中也有具体体现,除了逆反心理和好奇心理外,与成年人犯罪心理并无太大不同。就犯罪原因而言,未成年人易冲动、自制力较差、考虑问题不周全——很多成年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不是减轻罪责的理由。除了一些盛怒之下实施的激情犯罪(主要是故意伤害罪)以外,其故意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并无本质区别,唯一区别是行为时的年龄。可能有人认为,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是因为心理不成熟,不应负刑事责任。其实,心理是否成熟,不是分析其刑事责任能力应考虑的因素,至少不应占较大权重。事实上,很多成年人的心理也不成熟,仍不影响其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报应刑论实际上是尊重了犯罪。因为等价的报应刑是对犯罪人理性的荣誉待遇,报应是恢复理性的平衡过程。”[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那么,只要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就存在值得尊重的“犯罪人理性”,通过刑罚来帮助其恢复理性有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讲,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心理不成熟的成年人无甚区别。
(一)关于犯罪的规范性评价与非规范性评价
1.不能将对犯罪人的规范性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混为一谈
所谓规范性评价,是国家有权机关适用法律规范对于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评价,是特定主体依据道德习惯以外的规则,对客体的属性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所谓非规范性评价,是指社会公众、媒体等对于犯罪人及其行为的非正式评价,是由某一事件引发的,以有权机关的规范性评价或者道德习惯为依据进行的价值判断,体现为民意、舆论等形式。[于志刚:《犯罪的规范性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第29-32页。]某人犯了某罪,依法应当承担哪些不利后果,如定罪判刑、禁止令、前科报告、开除公职等,属于规范性评价;公众如何看待、是否排斥,则属于非规范性评价。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通常会判决有罪——必然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还可能构成徇私枉法罪。不少人认为,判决有罪就是标签化、污名化,会造成社会排斥(歧视)、不利于其回归社会。然而,《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那么,一个人因犯罪被法院确定有罪,人们便认为其有罪,是无可厚非的,除非法院又宣告其无罪,或者司法公信力极低。犯罪的人因有罪判決而贴上犯罪人标签是正常的,是其犯罪行为必然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其犯罪的“副产品”,不是污名化,有利于保障他人的知情权、节约社会成本,也有利于社会防卫。如果因“政治正确”之考量而自缚手脚、不予处置,可谓助纣为虐。
诚然,一个人被确定有罪后,会面临一些不利后果,未成年人被定罪也不例外,其人生轨迹可能大不相同,甚至面临更曲折的人生道路。人们认为某人是犯罪的人,不愿意与有犯罪经历的人来往,是个人自由,也是人之常情,根本原因是某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不是因为法院判决其有罪,更不是社会偏见。从表面上看,这是有罪判决造成的,但追根溯源是其犯罪行为造成的。从不利益的范围和可能性来看,主要不是刑法的规范性评价造成的,而是非规范性评价造成的。
2.他人对犯罪人的态度取决于具体罪行而不是有罪标签
他人只有有限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只会根据一个人的主要经历来判断其如何。一个人做过什么事,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引起刑事追诉,还是人心的波动。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知道的犯罪人及其罪行其实是很少的,可谓沧海一粟。各案颇为复杂,与司法公信力、信息传播力也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并不因“犯罪人标签”而排斥其犯罪的亲属,譬如,杀人犯的母亲对儿子的爱几乎无一例外超过对被害人的“爱”。一个40岁出狱的故意杀人犯可能横行无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者出狱后仍可能威风八面,有几个人敢歧视他们呢?人们普遍认为,相比13周岁的故意杀人的凶手,17周岁的盗窃犯更可亲近;人们宁愿和因犯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的人交往,也不愿意和一个因猥亵幼女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的人交往。有不少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人们对其颇为理解和同情,不乏捐款捐物、积极帮助其申冤平反者。假设其是冤枉的,则在平反之前人们一般会相信他是有罪的;平反后一般不会认为其是有罪的人,谈不上标签化。有相当多的人,被法院宣告无罪,或者根本未被追诉,而人们内心普遍认为其有罪,往往不愿意与之交往,也是很正常的。
列举这些事例,并不是为了说明“犯罪鄙视链”的存在,而是说人们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其罪行有关,与其行为时的年龄关系不大,至少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人们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判断是复杂多变的,比简单化的“标签理论”更可取。不能简单化地认为,标签化等于偏见,会产生锚定效应。
(二)关于刑罚的作用
法律是一定历史时期人民意志的体现,不完全是演绎推理的产物,更不是专家造法的产物。只要立法者经利益衡量、利弊权衡,认为有此必要,选择一个最佳方案,经合法程序就可以成为法律。规定刑罚不是为了消灭犯罪,而是惩治和预防犯罪,只是为解决现实存在和将来会发生的问题提供当时认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立法者不可能幼稚到以为规定了罪刑规范就能威慑所有的人都不实施犯罪行为。可以说犯罪是对罪刑规范的否定,但不能简单化地认为某个(些)犯罪现象证明罪刑规范无效。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应否下调,也涉及对刑罚目的的认识——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抑或并合主义。将报应主义和目的主义结合起来,可以充分解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正当性。笔者认为,报应为主、预防为辅是比较合理的。真正的问题是:如果现实中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恶性犯罪,何种处理方案才是最合适的?所谓“最合适”,无疑应当体现当下的民意,包括沉默的大多数的意见。如果依照现行法不可能采用这种方案,或者无解,或者束手无策,还是修改法律以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如果时过境迁,法的滞后性越来越明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难以或无法实现公平正义,那么修改法律势在必行。
(三)一些认识误区及其澄清
从现有相关规范来看,“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已经有了充分的甚至过度的体现。如果对其进行片面化、教条化、绝对化的理解,则难免走向反面。在部分学者笔下,犯罪有正面价值,犯罪人几乎被描述成“只身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的可怜人(甚至勇士)”,犯罪的少年似乎是“承担了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受害者”,至于法益如何被侵害、被害人如何悲惨,均不可见。人们对被害人的痛苦往往视若无睹,却因犯罪人的一句“我认罪”“我很后悔”而同情不已,似乎从来不曾想过这可能是表演、言不由衷。
在很多人看來,未成年人犯罪却不付出任何代价,似乎更有利于其社会化——至于实效如何在所不问,可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不满16周岁(或14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如果未被收容教养,无异于不必承受规范性评价范畴内的任何不利后果,其违法成本为零。期待触法少年在社会上自动改造好,可谓缘木求鱼,不仅是对触法少年不负责,也是对全社会不负责。那么,如何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质呢?如何认识到不能实施这类危害行为呢?
是否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应着眼于未成年人的整体福利。长期以来,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相当于证人而非当事人,除非其还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这就造成了被害人的缺位、失语状态。由于被害人缺位,不少人潜意识里认为未成年犯罪人被处罚是一种恶,是福利减损,却忘记了:如果规定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一部分未成年人很可能不会实施犯罪行为(或有所节制),被害人不会遭受侵害(或只受到有限侵害),加害人也不会受到刑事处罚。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才能更有力地威慑潜在的不法侵害者,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增进未成年人的整体福利、社会的整体利益,也符合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恤幼”的传统。
三、相关处置措施及其实效
《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2012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9条也有类似规定。那么,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也不能依据《刑法》第37条处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也即,这些非刑罚处罚措施没有用武之地。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有可能以民事责任的方式存在,但不属于刑事责任。现实中,“未成年人没有自己的财产,父母有钱但与其无关,所以不代为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的现象也是很常见的,由此会给被害人(及家属)造成二次伤害。如果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处以财产方面的处罚,以此促进管教,对于经济状况欠佳的家庭可能是雪上加霜,未成年人会面临更恶劣的环境;还会面临如下诘问:“是否违反了罪责自负原则?是不是株连无辜?”所以,这一路径是行不通的。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其家庭教育的彻底“破产”以及学校教育的个别失败,也证明了其不能适应正常的学校教育,应当受到特殊的教育。治安拘留(往往不执行)、罚款等处罚措施,相比被害人所受的凌辱、痛苦,可谓无关痛痒、隔靴搔痒,连治标的效果也不佳。《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28条规定:“凡是可以由其家长负责管教的,一律不送(收容教养)。”现实中,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且父母双亡的是极少数,其家长往往不同意,也就意味着多数涉案未成年人并未被收容教养。如果其罪行极其严重,或其监护人同意收容教养,则可能被认为家长(或监护人)无管教的条件,会被收容教养。如果由家庭管教,相当于未脱离原生环境,其效果很可能是不好的;如果一律剥夺其父母的监护权,则可能正中某些无责任心的、不想管教孩子的父母的下怀。如果认为“哪怕他故意杀人了,也要保障其受教育权(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无异于机械执法。如果将其受教育权置于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利之上——等于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显然是利益衡量出了偏差,是教条主义,弊远远大于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进入工读学校的标准改为“在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由少年的家长(或监护人)、或原学校提出申请,且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也即,工读学校招生不再具有强制力。在自愿原则下,很多家长不愿将孩子送入工读学校——哪怕自己无力管教。据调查,“过去50余年间,国内工读学校数量不断减少。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统计,与1966年的200余所学校相比,数量下降过半。截至2017年年底,国内工读学校有93所,北京现存6所工读学校,且都存在招生难题。”“招生难题在其他地区的工读学校也很常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抽样调查的国内21所工读学校中,多数学校的在读学生不饱和,有两所学校甚至没有学生。”[黄哲程、吕银玲:《工读学校“生存录”:半世纪减少过半,有学校多年无生源》,载《新京报》2019年2月12日,第A08版。]这意味着,以工读学校为模式的“收容教养”制度面临着凋零、消亡的危险。如果将犯有严重罪行的未成年人全部送至工读学校,仍存在“交叉感染”、拉帮结派等诸多弊端。可见,欠缺强制性以及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父母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架空了工读学校制度。
近年来,不少学者建议引进英美法系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Malice Supplies The Age)规则。“恶意”包括违法性认识、错误行为的可谴责性认识、行为危害性的严重性认识、恶性意志能力的强化认识与错误行为的指引性认识等,往往由控方在法庭上开示未成年人与受害者的特定关系证明、犯罪前后的行为表现、经验阅历、受害者受伤表征等证据,[ 陈伟、熊波:《校园暴力低龄化防控的刑法学省思——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切入点》,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94-95页。主张引进这一制度的学者还有郭大磊、张俊英、张颖鸿、李振林、曾粤兴、李玫瑾等。可见:郭大磊:《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应对——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借鉴》,载《青年研究》2016年第6期;张俊英:《“恶意反控责任年龄”规则的刑法本土化构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6期;张颖鸿、李振林:《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适用论》,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0期;曾粤兴、高正旭:《“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引入论之反思》,载《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9月增刊;李玫瑾:《从刑事责任年龄之争反思刑事责任能力判断根据——由大连少年恶性案件引发的思考》,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使得未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被视为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从而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英国法律规定,未满10周岁的儿童,认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绝对不负刑事责任;14周岁以上的,负刑事责任;对10周岁以上不满14周岁的儿童被推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但可以用证据反驳。[兹举一例:1993年2月12日,英国利物浦默西塞德郡两名10岁男童罗伯特、乔恩偷窃后,诱拐2岁小詹姆斯,对其又打又踢,将偷来的颜料泼进他的眼睛里,又把电池塞进他嘴里,朝他扔石头,用大扳
手砸碎了他的颅骨,将他的尸體放在铁轨上被火车轧断。英国民众要求警方公布凶手的真实姓名,还要求重判。官方公布了两名凶手的信息,法院原本决定判刑8年,增加至15年。
类似案例还有:2018年5月14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两个13岁男孩将14岁少女安娜骗至一个废弃的农场,实行性虐并锤杀致死。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2年后方可复审;从犯被判处15年监禁,8年后方可复审。]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少年犯条例》、美国多个州的法律均规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7周岁,也有相似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为了防止徇私舞弊,一般还设计了严格的特别程序予以保障。
笔者认为,任何建议都不能脱离我国国情,不能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而带来更多大问题,简单比较便草率得出结论是不可取的。在法治社会、法治信仰尚在建设中的当前,司法权威较之应然状态存在较大差距,贸然引进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欠缺可操作性,表面上弊端只是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徇私舞弊,实际上给司法系统、司法人员带来的难题和危害远多于现在。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款、第176条第1款、第200条分别规定了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判决有罪的证明标准均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恶意”的内涵和外延过于模糊,认定标准难以把握。如果法律确立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则预示着侦查机关会揣摩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是否认定某个未成年人具有恶意,公诉机关会揣摩审判机关是否认定某个未成年人具有恶意,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预判的范畴,而是无意义的内耗。就前述未成年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案例而言,行为人具有恶意是显而易见、毫无疑问的,也充分暴露了其反社会人格,并不需要社会调查所得的边缘证据来证明其具有恶意。从所需的间接证据来看,会有相当多案件很难说达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会每每引起巨大争议,可能导致功亏一篑、前功尽弃——至少在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看来如此。就此而言,人人皆知其具有恶意却因收集的证据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有争议而放纵某些犯罪分子,可谓做无用功、自讨苦吃。
从表面上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恶意则判决有罪,无恶意则宣告无罪,似乎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体现了实质正义。事实上,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特别是刑法的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不符合类型化思想和经济原则。一个人是否具有“恶意”,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很主观的、不易把握的标准——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司法的严肃性所排斥的。如果公检法提前沟通好意见,又有先定后审之嫌,是不可取的;如果审判机关先介入,认为具有恶意,经庭审发现不宜认定为恶意,则会进退两难。那么,相关法官可能硬着头皮判决有罪,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会遭遇错案;若相关法官及时纠正为不具有恶意,则可能被怀疑不客观中立、有廉洁问题,其自身也可能遭遇错案。
综上,引进“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弊远远大于利。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一刀切”或“两刀切”的规定,看似简单粗暴,也许不够个别化、精细化,却是类型化、明确性的必然要求,还有利于保护司法人员正常履职。
四、解决方案及其比较
(一)解决方案是年龄下调加罪名选择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主要在于现实必要性,而非理论正当性。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降或不降,表面上是“如何降”的先决问题,实际上将问题过分简化了。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案可供选择:(1)保持现有规定不变;(2)上调刑事责任年龄;(3)降至13周岁;(4)降至12周岁;(5)降至11周岁;(6)降至10周岁;(7)不设年龄下限+恶意补足年龄规则;(8)仿英国例不作规定,规定年龄下限+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等等。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规则最低限度的标准规则》规定,在承认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中,起点不应太低,应考虑到情绪和心智成熟的实际情况。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建议,以12周岁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2007年《〈儿童权利公约〉第10号一般性意见——少年司法中的儿童权利》规定,各缔约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至少规定为12周岁。就此而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不宜降至12周岁以下,为12或13周岁较妥,即降低1~2岁是合理且可行的。
从罪名来看,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至12或13周岁后,已满12或13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应当对哪些罪行负刑事责任呢?可以沿用当前的8种罪行,也可以减为1~7种罪行,如此排列组合,可以有504种选择。如果只保留三种罪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应当入选,估计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当然,立法者还可以专门规定罪名和法定刑(如更轻的法定刑)。哪怕只是一律判处缓刑,也比不予追究要好。考虑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果判处缓刑,原则上宜公开审判,应当公开其判决书、公开姓名,并规定其永远不得改名——这比美国“杰西卡法案”(也许有人会认为没有可比性)仍宽松得多。此举可能造成其“社会性死亡”,却是提高其犯罪成本所必需的;考虑到我国已经进入陌生人社会,其实际效果并不会如此严厉。
(二)横向比较:下调1~2岁是否偏重?
在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规定方面,瑞士、新加坡、约旦、黎巴嫩、也门、印度为7岁,孟加拉国为8岁,菲律宾、墨西哥为9岁,澳大利亚为10岁,荷兰、墨西哥、土耳其、埃及、乌干达为12岁,法国、以色列为13岁,日本、意大利、俄罗斯为14岁,丹麦、芬兰为15岁,西班牙、葡萄牙为16岁,波兰为17岁,卢森堡为18岁。可见,世界主要国家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要么与我国相近,要么低于我国。郭烁教授指出:“即便非要从比较法上找灵感,12岁是各国主流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才是真正的客观描述。”[郭烁:《应当毫不犹豫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腾讯大家https://xw.qq.com/iphone/m/category/5e4d0656bb64e3eb 891d872e4c705b57.html访问日期:2020年6月10日。]有趣的是,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很少说与国际接轨。
美国50个州有37个州没有规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下限。从理论上说,哪怕3岁小孩杀人,也要负刑事责任。实践中通行做法是,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负法律责任,推定7~12岁的未成年人没有犯罪能力,除非检方能提供相反证明,若被指控的未成年人不满14岁,检方需要证明该未成年人了解他做的是错事。1973年至2002年,共有21名未成年人被执行了死刑,到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废除18周岁以下的人的死刑。美国联邦调查局汇编的年度犯罪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8年,美国至少有30467名10岁以下儿童被捕,但均未起诉。兹举一例:2019年4月6日,一名9岁男童在伊利诺伊州伍德福德县古德菲尔德村放火,致五人死亡(三人为不满2岁的幼童),当地检察机关以5项一级谋杀罪名,起诉了这名男童。
《德国刑法典》第19条规定,“行为时未满十四岁者,无罪责能力。”《少年法院法》第3条规定,如果少年在行为当时的道德和精神发展成熟到足以意识到行为的不法以及并根据这种意识去采取行动的程度,则该少年应负刑事责任。《少年法院法》第105条规定了人格整体评估制度,即召集少年心理学或少年精神病学的鉴定人进行成熟度审查。《青少年福利法》《青少年刑法》也有相关规定。
法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罪錯未成年人的责任年龄、罪错行为的严重程度、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措施、对罪错未成年人适用的诉讼程序等方面都建立了发达的分级制度。我国未来在构建和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时应当从正确理解和贯彻教育优先原则、确立罪错责任年龄、适时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完善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措施几个方面做起。[俞亮、吕点点:《法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及其借鉴》,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55页。]通过比较可知,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无论是降至12周岁,还是13周岁,均不存在偏小的情况。笔者倾向于一次性下调至12周岁。如前所述,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罪行负刑事责任,是可取的。截止到2020年2月,我国有965个市辖区、387个县级市、1323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合计2846个县级区划。假设每10年一个县级区划发生一例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的犯罪案件(暂不涉及另外两个罪行),那么平均每年有284.6人会因此种恶行得以受到刑法制裁。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这种恶性犯罪很少,不值得为罕见事例而大动干戈。
(三)对可能的质疑的回应
有人会质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会使一些犯罪的未成年人被刑罚处罚,这种“强加”的不利益违反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且可能导致犯罪的未成年人自暴自弃、更难回归社会。是的,其确有可能自暴自弃、重操旧业,更难回归社会,也可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即使其更难回归社会,也不一定是有罪判决造成的;不作任何处罚,其仍有可能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或者继续犯罪,难道就容易回归社会了吗?其实,无论持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未成年)犯罪人处遇和社会化改造之间因果关系都是复杂的而非线性的。现实的易变性、社会的复杂性、个体的差异性,不容忽视。总之,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做什么事、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其自主选择的。不能因为犯罪人没有变成“好人”,就一味地指责是有罪判决害了此人,或认为违反了某原则、未实现刑罚目的。
有人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什么是问题?什么是解决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何处理最为合适?如果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无法实现,可以考虑修改法律使之实现。诚然,法律不是万能的,刑法也不是万能的。我们只追求一个顺应民意的、相对最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追求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完美方案、万全之策。立法者不可能天真到认为立法就能杜绝犯罪的地步。只要能减少一些犯罪,哪怕只能在十个案件中适用,哪怕只能减少一个犯罪,也是值得的。如果条文适用较少且不是因为有案不立造成,则说明其显示了巨大的威慑力、家庭管教有所加强,而不宜解读为条文无意义。
有人会问,如果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周岁,出现不满12周岁的人实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怎么办?要不要继续下调?不满12周岁的人实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的现象难免发生,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行为也难免发生,立法是杜绝不了的。依照法律,其不负刑事责任,只能由家庭管教或收容教养。现在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并不代表几年后会继续下降至11周岁或10周岁。当然,若干年后民意如此则除外。
五、结论
当代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比1979年的同龄人早熟,具有充分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是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基础。因未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其违法成本接近于零,客观上放纵了其罪行;如果未被送至工读学校,则事实上处于脱管失控状态。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观点考虑欠周全,不符合当前的我国国情,并不可取。建议在我国《刑法》第14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原第三款修改为“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作为第四款。相同的条款如果规定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并无不可,只是人们不易接受而已。这样有利于增大其违法犯罪成本,可以有效地威慑潜在的触法未成年人、减少未成年被害人,从而保障未成年人整体福利,符合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这是修正法的滞后性的现实需要,体现了法的民主性和与时俱进的特性,并不违反“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反而有利于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和原则。
On the Basic Problems of Reducing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Minors
WANG Denghu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Abstract:
Whether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minors should be lowered is a problem in the legislative level,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normative evaluation and the role of punishment. As long as it is recognized that everyone should bear some adverse consequences for his or her wrongdoing, that victims deserve more protection than perpetrators, and that minors aged 12 to 14 are maturing earlier than their peers in 1979, one finds the arguments against lowering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minors to be bigoted. For minors who do not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ecause they have not reached the appropriat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nonpenal measures are useless, family discipline is basically ineffective, the use of internment and upbringing is too limited, and workstudy schools are in decline, existing mechanisms of disposal are better than none; they call for Legislative Change. The idea of “maliciously supplementing age” rule is quite marketable, but it does not accor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is not advisable. It is reasonable to stipulate that a person who has reached the age of 12, less than 14 years of age shall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homicide, serious injury or death caused by intentional injury, and rape. This would be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the cost of their crimes, effectively deterring undesirable minors and reducing the number of minor victims, thus safeguarding the overall welfare of minor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ldren. This is the actual need of the lag of the amendment law, which is in line with and conducive to th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education, probation, rescue” and the principle of “education first, punishment second”.
Key Words: juvenile delinquency;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malicious completion of the age rule
本文責任编辑:李晓锋
青年学术编辑:张永强
收稿日期:2020-06-25
基金项目:第64批面上资助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的课题(43XB3785XB)
作者简介:
王登辉(1985),男,湖北随州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