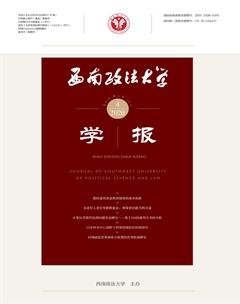股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思路
李亚超
摘 要:股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直倍受质疑,原因在于主要围绕制度理念以及要件等方面的差异性,忽视了其内在共通性以及现实制度需求等因素。基本理论上必须认识到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建构本质上都指向一种利益衡量后的结果,值得信赖的权利外观本身也是立法性建构,并非完全“天然生成”,加上考虑到股权交易的必要性,以及促进交易进行的客观需要和风险规制的必要性等因素,股权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必要性。而在制度建构和适用中有关股权善意取得的质疑则充分反映出了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建构中的复杂因素,包括商事外观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公司人合性以及股权转让的特性、双重公示主义等方面的要素,这要求我们对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进行改造,并在利益衡量的基本原理上,对于各种具体适用情形进行有效区分,建立更加规范合理的股权善意取得制度。
关键词:权利外观;登记对抗主义;利益衡量;登记错误;权利人可归责性
中图分类号:DF 5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4.01
2011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27条关于股权善意取得的规定自发布后一直饱受诟病:一方面是围绕着适用类型的困扰,即是否仅包括名义股东处分和一股多卖情形。另一方面是直接针对本条规定两种情形的质疑,对于前者普遍认为是有权处分,而不符合适用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后者一股多卖有学者认为是有权处分,也有的则认为直接用登记对抗主义的特殊规则解决而无须另借助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从总体上来说根据笔者检索的二十余篇文献的分析结果,对于股权善意取得制度持否定的态度,仅有个别观点提出应有选择地吸收善意取得制度或者对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修正。通过对检索的有关股权善意取得制度论文分析发现,对于股权善意取得的质疑虽然不少,但均未进行系统的梳理,并未区分究竟是基础理论性冲突还是具体制度性的障碍等问题,而往往只要股权善意取得和一般的善意取得稍有差异便排除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空间,因而本文拟从三个层次分别阐释:第一层次是股权适用善意取得基本理论层面的不同,这种阐释主要是决定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第二层次是股权特殊性引发的制度障碍,这种阐释回应是否应该直接否定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以及是否应该使善意取得制度结合前述股权特性等内容进行变通问题;第三层次的阐释则是具体适用类型中的争议,主张不会直接导致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否定,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即可。
一、基础理论层面的质疑与回应:以权利外观为核心
(一)理论正当性视角下存在股权权利外观基础
1.值得信赖股权权利外观的“缺失”
有学者提出,善意取得的制度理念设计之初主要针对动产,关键是在交易安全和静态安全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动产数量庞大且价值较小,而动产占有具有权利推定效力,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反而要求受让人(第三人)查明权利来源的真实性,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甚至会使得交易无法正常进行,在实践中也缺乏可操作性。然而这种理论基础不能直接适用于不动产,不少国家因此否定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对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制度保护。不动产登记具有公信力应当作为权利外观受到保护,不再是单纯促进交易的进行或者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本质上是一种登记公信力的绝对保护,区别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实际上在德国也有学者从法律效果角度将二者均称为善意取得,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二者在原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善意程度以及善意时点、标的物移转等构成要件方面应有所区分。[ 参见杨洋:《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81、82页。]有鉴于此,有关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质疑从未停止过,有观点提出公司股权登记制度的宗旨并不在于构建外部交易信赖之基础,而只是公司人合性维护,不能因此发生善意取得的保护效力,欠缺制度正当性,受讓人的善意亦欠缺制度保障的信赖基础,不存在需要保护的价值或者至少不需要适用善意取得保护,强行适用善意取得是对真实权利人权利的公然掠夺,鼓励非诚信交易行为。这里工商登记欠缺信赖正当性基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理由:(1)程序性的欠缺导致无法反映真实的股权取得的基础关系;(2)工商登记要求的材料无法保证股权取得的真实性;(3)公司登记的内容无法证明股权的重要内容;(4)登记错误情形下真实权利人没有救济措施保障;(5)公司负责工商登记申请容易引发伪造签名盗取股权等情形。[ 参见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144-147页。]总之,这种登记制度体现出来的信息难以作为股权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工商登记由于不进行实质审查,在公示公信力上无法和不动产登记薄相提并论,也就不能作为权利存在依据,甚至很多人认为工商登记根本不具有外观功能。
也有学者从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两方面分别否定了值得信赖权利外观的存在:(1)股东名册仅存在于公司内部,而无法向公众展示,加上实践中大多数公司也并未置备股东名册,同时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3款的规定股权变动的知悉是工商登记而不是股东名册,信赖可有可无的公司内部股东名册不具有合理性,工商登记似乎应当是唯一的权利外观;(2)工商登记中股权记载内容是较为随意的,只要求变更股东姓名、名称,对于登记格式规定则是欠缺的,加上公司作为登记义务人虽然应当在30日内申请变更,但是对于怠于履行的后果并不明确,而且也不需要提交转让人的身份证明而完全在公司手中掌握,这样会导致事实归属和登记状态的分离大量长期存在,也会频繁引发冒名转让情形。[ 参见谭津龙:《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质疑——基于〈公司法解释三〉及其扩大适用》,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158、159页。]也有观点提出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双重公示这一特点容易造成权利外观的混乱。[ 参见杨洋:《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82页。]同时股东名册变更同工商登记都是股权变动后公司的一项法定义务,无论公司在被告知后是否履行,都应不影响股权变动的发生。[ 参见郭志京:《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3期,第96页;参见吴勇敏、张桂龙:《论股权多重转让中善意取得规则的修正适用》,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88页。]总之,善意取得制度本质上是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保障交易顺利进行,但同时也要避免为保护不合理信赖反而对无辜的原权利人利益置之不顾,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存在能够引发合理信赖的权利外观。[ 参见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133页。]而股权转让缺乏这种值得信赖的权利外观,也有观点提出善意取得只能适用于资合性更强的股份公司,其股份流动性要求善意取得制度保护,[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这里的区别主要在于将是否有流通性作为利益衡量的要素。
2.善意取得制度理念的基点和共通点:利益衡量
从动产善意取得到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制度发展和变迁当中,不难发现股权善意取得制度本质上都是利益衡量后的结果,不应因个别构成要件方面的差异而绝对排除其适用正当性,虽然股权权利外观和不动产相比呈现出一定差异,但并不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任何权利外观,尤其我国《公司法》明文规定了股权的登记对抗效力,登记公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为保障交易安全,肯定这种权利外观信赖的正当性,也更符合立法目的。因为如果单纯通过外观构造去否定权利外观的正当性,那么会使得动产占有原因更加复杂,因此,似乎也不应当适用善意取得。事实上,动产善意取得中考虑到了动产交易的频繁性和大量性等特征,这种权利外观建构本身就是经立法权衡后对于“外观信赖正当性”的事后肯定,这也就是说权利外观的构建本身是一种立法性的建构,与利益衡量密不可分。基于此,股权转让虽然复杂,同时存在着登记、股东名册,以及公司经营介入等复杂因素,但并不影响其具有相当程度上权利外观的属性,“一刀切”的排斥反而是商事交易对于制度需求发展的一种否定和背离。诚如有学者所言,股权工商登记制度虽然无法像不动产登记达到直接确定权属的公示效果,与股权关系甚至也微乎其微,但仍不因此而绝对否定其权利外观价值——对于交易相对人来说,对股权信息的最低需求在于知晓交易方会否是公司股东,工商登记事实上仍充当了相当程度的权利外观的作用,只是具体适用中,应寄希望于改造登记系统完善公示效果,而现有的方案应当是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在“权利外观”薄弱的情况下,应重点考虑外观的可归责性以及受让人善意的认定。[ 参见于焕超:《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再思考》,載《研究生法学》2017年第 1期,第120页。]也有观点提出了从实践需要角度应当一方面通过外在技术手段和相应的配套机制来增强权利外观的真实精确性,满足公众信赖保护的需要,同时也要严防冒名转让而禁止其适用善意取得。[ 参见谭津龙:《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质疑——基于〈公司法解释三〉及其扩大适用》,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63页。]有观点强调我国有限公司股东对外公示方式是工商登记,纳入工商登记才有对抗效力,因此只有错误登记为公司股东才能产生受让人信赖的虚假权利外观,并基于此种信赖受让股权。[ 参见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5页。]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说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有关规定立法理由时指出的,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3款的规定,第三人可以凭借对登记的信赖,接受名义股东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该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如果第三人明知股权应属于实际出资人,仍然接受该股权,那么就不应当助长第三人和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应当否定行为效力。[ 参见:最高院民二庭就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答记者问,访问链接:http://www.148com.com/html/4450/488971_4.html,访问日期:2020年7月29日。]这里本质上是一种反向的利益衡量,即“登记的内容构成第三人的一般信赖,第三人可以以登记的内容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但实际出资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也就不能终局地取得该股权。”[ 参见最高院民二庭就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答记者问,访问链接:http://www.148com.com/html/4450/488971_4.html,访问日期:2020年7月29日。](二)理论可行性之内在冲突的可协调性
1.股权登记对抗主义与善意取得的“冲突”
有学者指出,善意取得制度和登记对抗主义天然地存在冲突。正如有观点提出善意取得制度并非为了弥补无处分权人法律行为效力,而是在物权公示外观这一单一原因基础上拒绝原所有权人的权利,因此善意取得只适用于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不动产交易,登记事实在登记对抗主义中仅有证据上的优先效力,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国家的不动产中善意取得制度也难以成立的。不仅如此,二者适用的第三人范围并不一致,登记对抗中第三人的范围不仅包括纯粹善意的第三人,还包括知情的恶意第三人,但是不包括利用有利地位牟取暴利的背信恶意第三人(类似于德国法上的恶意侵害债权),有利于知情非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促进交易实现。[ 参见张笑滔:《股权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138、139页。]也有观点指出登记对抗和登记生效的区别在于有权处分和无权处分,登记对抗主义主要是针对特殊动产设计,参照2012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2款规定,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里先后买受人地位平等,关键在于谁先完成交付或登记,而无权处分的观点则忽略了二人的平等地位,即均可对世主张绝对的消除妨害请求权,而相互之间不可主张,只有先登记的可以获得完整所有权。[ 参见张畅、吕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刍议》,载《社科纵横》2020年第3期,第81、82页。]我国有限公司股权采登记对抗主义,赋予了第三人否定物权变动的效力,而非其有权利取得的效果。
2.登记对抗主义和善意取得的可协调性
对于登记对抗主义下发生有权处分的法律效果的观点,即使是一股多卖情形,虽然可以将登记对抗主义规则解释为“对善意第三人而言发生有权处分的效果”,但是这里的善意第三人范围,在我国当前的制度建构中是有欠缺的,而且缺乏其它有关要素的评价,反而在法律效果上同善意取得一样,最终是要赋予善意第三人群体取得股权的法律效果,在一物二卖情形坚持有权处分情况下,肯定前合同效力基础上,难免要借助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违背公序良俗条款来进行限制,与其说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不如说是只能在极端例外情况下才能排斥第二继受人取得效力,在实际法律效果上比不动产的登记生效主义对外部交易安全的保护更大,严重背离社会生活实践。考虑到登记对抗制度会容易引发原权利人和登记为准的两条线上移转,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为确保法律的统一性并考虑到价值衡量的不确定性和我国登记对抗公信力规则的不完善,采取善意取得制度进行处理有其合理性。[ 参见朱晓娟、姚篮:《论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一般结构》,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47页。]实际上,善意取得制度的关键在于前述权利外观的立法建构,即使在登记对抗主义之下,只要有适当的规则制度产生可信赖的权利外观,就有善意取得适用的空间。一方面登记对抗主义制度本身适用具有极大不确定性,放弃善意取得制度而另行建构登记对抗主义的适用模式是否有可行性值得质疑;另一方面即使登记对抗也会发生登记错误情况,这时候完全否定这种权利外观的正当性无疑也是不恰当的,同时登记对抗主义的视为“有权处分”规则的不完善性实际上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具体界定“善意第三人范围”。换句话说,登记对抗主义对第三人而言是有权处分实际上并未解决范围问题,而只是一种事后的视为有权处分,很难在当下的规范建构中发挥实际作用,而在具体的适用范围认定上似乎借助善意取得的相关构成要件最符合现实。龙俊教授亦认为登记对抗主义应采权利外观说,具有公信力,能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只是股权登记对抗主义下,需要进行更多的利益衡量,[ 参见王洪亮:《论登记公信力的相对化》,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5期,第31-44页。]如有关善意的认定不能按照传统善意取得制度规则处理。[ 参见孙宪忠:《制定科学的民法典——中德民法典立法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三)现实必要性视角下存在适用空间
1.适用余地不足的几点理由
有学者提出,股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空间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理由:(1)无权处分情形的概率极低,公司人合性优先于交易安全,包括公司法限制和章程限制,对外转让需要经过同意;(2)受让人必要注意义务,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享有股东具有公示效力,受让人只需查阅即可确定股权归属,如未尽到注意义务则不可以以不知情对抗真正享有股权的人,而应自己承担风险;(3)善意很难出现,有限公司股东人数较少,互相知情,善意取得适用余地更小。[ 参见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2页。]也有很多学者特别针对一股多卖情形认定由于后受让人在完成股东名册变更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时候,很容易获取之前的股权转让的事实,尤其是需要通知其他股东并获得同意,其他股东极可能会告知其有关转让事实。[ 参见王涌:《股权如何善意取得?——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疑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33页。]同时考虑到股权无权处分中,善意应当持续到完成登记过户,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参见谭津龙:《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质疑——基于〈公司法解释三〉及其扩大适用》,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160、161页。]而在一般的登记错误情形下,公司对于该事实显然是知情的,尤其是涉及到之后的股东同意等事项,也几乎不会出现善意取得的适用空间。
2.存在适用空间的现实依据
首先,有限公司人数虽少,彼此之间相互知情,虽然会减少善意取得的适用空间,但是并非绝对排斥,只是在第三人的善意认定上会较为严苛。而对于公司人合性的保障则在后文会专门提到,主要会通过立法阶段利益衡量角度限制善意取得的适用。其次,虽然股权转让的流程上需要经过股东同意,甚至需要公司认可等使得善意几乎不可能存在,但这同样只是在认定第三人善意的时候进行从严把握,客观上第三人不知情的可能性也较低,但同样不影响会出现由于串谋等情形而使得善意第三人对于权利外观的信赖需要受到法律保护的情形。最后,从本质上来说,善意取得的适用关键在于真实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登记不一致的情形,而股权登记作为权利外观对于善意第三人而言,应当可以作為信赖的基础,对于因此发生的无权处分应有善意取得适用的空间,至于学者提出的公司权利外观的复杂性,股权转让的经过股东同意,公司人合性保障等方面在相对人的善意认定和利益衡量等方面会有影响,但是并不因此股权整体是否有适用善意取得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模式不断出现,传统的物权和债权划分的界限不断模糊,传统规则的适用也不断受到新事物的冲击,但是根本上来说要实现法律关系的有效规制,商事法律关系的关键就在于符合社会发展现实基础上的交易效率和安全,以及整个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股权善意取得作为现代商事交易的一种模式,具有其现实存在的土壤,如果不能有效平衡各方法律关系,最终只会影响交易的进行,而制度建构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利益衡量实现交易的安全和效率。但是作为以制定法为主国家,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商事基本原则进行审理,而仍应有具体的制度基础,因此在发生股权无权处分情形,当然也必须借助善意取得制度,并根据有关商事原理特性进行调整,反之一味地禁止,对于商事交易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同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前提不应单纯从构成要件上解读,而应主要围绕是否会存在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和外观权利人不一致、外观权利人是否会处分股权、是否存在外观表征使得善意第三人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完成交易进行。[ 参见徐小平:《股权善意取得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审视——从有限责任公司角度》,载《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72页。]也诚如有观点所说的,股权无权处分,和不动产善意取得一样,主要适用于登记错误,而股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导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股权和真实情况不一致,进而有善意取得的余地。[ 参见冯威:《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规范分析》,载《研究生法学》2015年第1期,第13页。]
(四)规范合理性视角下的立法漏洞
1.不存在法律漏洞的理由
有学者提出,针对现行法股权转让是否需要借鉴善意取得制度,有观点指出按照《公司法》第32条第3款的字面理解,非经登记不可对抗第三人,似乎倾向于直接保护善意的股权受让人,这里另外在创设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存在疑问。[ 参见姚明斌:《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第82-93页;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132页。]也就是说,在登记对抗效力的观点之下,对于善意的股权受让人,可以直接认定为有权处分的效果。即可以直接借助登记对抗主义规则进行处理,而不需要再借助善意取得制度。
2.补正立法漏洞的创举。
事实上登记对抗主义在我国当前的规范体系之下本身并非有其具体的适用规则,有学者认为登记对抗主义之下,对于第三人而言,权利人并非取得所有权,那么之后新的受让人取得股权就是继受取得。这种观点看似逻辑上较为一致,然而却忽略了以下两方面内容:一则登记对抗主义规则本身并不完善,需要借助更为具体的规则去解决实践问题;二则登记对抗主义对第三人而言不发生股权,没有对抗力,也就认定为有权处分效果,实际最终效果和善意取得制度是一样的,通过善意取得确定受让人何种情况下取得所有权(确定此种情况下第三人的范围)之后,再反过来认定是“有权处分”,增加了法律的冲突,也不符合我们当前的立法目的,应当认为这里的没有对抗力更像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认定,而不是用一种手段工具的规范处理股权归属问题。因此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公司法‘解释三明确准许参照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法律制度,这显然是一个补正立法漏洞的创设之举。”[ 参见师安宁:《股权流转中的善意取得》,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5月9日,第7版。]同时登记对抗主义即使可以解决一股多卖情形,却仍旧无法解决登记错误的问题。
需要认识到法律本身具有不完善性,规则本身适用范围也需要根据社会现实不断进行调整,发现其共性和个性,并进行优化和借鉴。一方面在于旧的制度规则通过调试适用于新的法律关系,另一方面相较于重新建构特定规则甚至适用一般原则不如对法律规则进行修正解释,不仅有利于法律的稳定性,也能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制度建构过程的质疑与回应:围绕股权特性
(一)客体差异的外观统一性:股权相对性特征
1.股权相对性特征引发的障碍
有学者提出,善意取得制度是在物权的绝对支配性、对世性基础上,考虑到存在一定权利外观,在原所有权人和受让人之间利益进行权衡,通过利益权衡保护受让人的信赖利益。但是在债权转让中,这种“外观信赖”是不存在的,考虑到股权本身主要是针对公司行使的特性,不存在直接排他支配的特性,而与“物权属性”差异较大,因而应当排除善意取得的适用。不少观点主张股权的内容只能向相对人公司主张,股权实现的关键也在于公司对其履行义务,因而其更偏向于债权,也就是相对权,有别于绝对权属性的物权,而相对权本身无法进行有效公示,从性质上来说不具有适用善意取得的空间。[ 参见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137页。]股权区别于民法传统物权,是各种权利的请求权,并非绝对对世性,客体也有别于动产、不动产,是纸质或者电子化的权利记载,加上股权的社员权等人合性,这也都在实践中降低了股权善意取得的可能性。[ 参见张笑滔:《股权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138页。]2.股权作为财产权利和物权具有内在一致性
股权虽然看似主要是针对公司的权利而带有债权特性,但实际上股权具有公示性而有别于债权,能够形成权利外观。正如有观点所说权利在不断的通过以相对固定的方式确定下来,而股权在股份公司中通过证券化表现为股票,而在有限公司中则表现为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股东记载来表征。[ 参见刘江伟:《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规则的检讨与适用》,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5期,第61页。]也有观点认为虽然股权转让与债权转让有很大相似之处,相对方是公司,转让程序无法像物权处分那样,权利人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但是必须认识到股权有别于普通债权,主要以通知和确认程序为核心构建公司和股东关系,公司确认是二者发生关系的开始。[ 参见吴勇敏、张桂龙:《论股权多重转让中善意取得规则的修正适用》,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86页。]也有观点指出股权中的目的权利和手段权利只是股权具体内容,而非独立权利,属于股权权能,像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權能等,股权是单一权利而不是权利的集合或总和。[ 周友苏著:《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股权是单一权利、民事权利、财产权利,股权和物权具有同质性,为有效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促进交易效率,适用善意取得具有合理性。[ 参见王丽美:《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及适用性分析》,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64、65页。](二)构成要件不符的解释思路:股权意思主义的缺陷
1.股权变动意思主义引发的障碍
有学者提出我国股权变动规则有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等主张,通说是意思主义模式,股权变动是意思主义,而登记仅有对抗效力,主要理由是:(1)《公司法》第73条规定了受让人成为股东后,再由公司进行股东名册变更,也就是说在股东名册变更前已经是公司股东,变更股东名册只是程序性事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同样规定取得股权后才可要求修改股东名册;(2)置备股东名册是公司的义务,但不能因此而证明股东名册是转让要件,而只能作为受让人得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的依据——对抗公司,[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它是内部行使权利的证据功能,并非当然有对外效力;(3)股东名册作为变动时点过度依赖于公司,公司拒不履行情况下对于受让人极为不利;股东名册虽必须置备,但实践中却大多不是,如果将股东名册纳入变动要件会影响股权流转,也不利于受让人利益保护;(4)股权更偏向于债权的相对权特性,即使认定存在原因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也应认定双方意思一致即可发生权利变动,二者同时发生;[ 参见张畅、吕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刍议》,载《社科纵横》2020年第3期,第81页;于焕超:《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再思考》,载《研究生法学》2017年第 1期,第115、116页。]比较法上,德国的物权变动实行形式主义,但其股权变动却遵循权利转让(债权转让)的一般规则。[ 参见[德]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58页。]对以上问题一则,有学者提出股权变动意思主义,登记对抗效力之下,更类似于债权变动模式,与参照《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相矛盾,因为该条的适用前提是“权利变动登记生效主义”,[ 参见张畅、吕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刍议》,载《社科纵横》2020年第3期,第81页。]善意取得解决的是登记错误情况下真实权利关系不对应问题,[ 参见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 条释义》,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第76页。]但一股二卖情况下两个受让人地位相等,是否发生股权变动关键在于登记与否,并不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不可对抗可以视为不存在,两次转让都是有权转让行为。[ 参见张畅、吕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刍议》,载《社科纵横》2020年第3期,第82页。]加上公司负责登记导致受让人处于不利地位,无法有效防范。有观点提出受让人根据合同生效取得股权,但是尚不能对公司行使该股权,在与公司的关系中,仍待经过公司认可后才能对公司主张权利,记载于公司名册后方取得公司关系中的股东资格,但是不必也不能是股权变动的生效或者对抗要件。[ 参见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138页。]正如德国法上股权变动采意思主义,仅需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股权让与合意,受让人取得股权,而股权受让人欲行使股东地位,需要向公司申报,该申报既不是生效要件也不是对抗要件。[ 参见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58页。]二则,意思主义模式下股东名册的记载与真实情况无法保持完全同步,记载中自始存在的不正确可能性是股东名册的先天缺陷;另股东名册自身的缺陷在于,公司执行人难以完全保持中立地位,难以有效维护中小股东利益,而损害赔偿不足以救济股东利益,而且公司执行人也缺乏法律专业性,无法进行有效审查,权利人难以有效防范救济;股东名册自始就会给受让人是否取得股权增加风险,难以单纯信赖股东名册记载,而影响其主张善意的构成,同时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往往表现为不作为或消极行为(即怠于及时查阅并更正股东名册记载错误),在法教义学上证成这一可归责性存在难题。[ 参见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72-174页。]2.意思主义的固有缺陷以及解释思路
股权变动意思主义模式将股东和其他股东排除在股东变动模式之外,而并未考虑到股权特性和双重公示形式,略有不妥。買受人在未向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通知公司)之前,根本无法行使任何权利,这种情况下认定为股权持有人的股东,与股东内涵相悖,彻底隔绝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参与,进而有学者主张债权形式主义,坚持股东名册变动的效力,虽然实践中很多公司并不置备股东名册,但是这是应然法的问题,并不影响股东名册的立法定位与功能,坚持贯彻债权形式主义,有助于推进股东名册制度的完善,而英国、德国、日本等也均是采行股东名册制。[ 参见杨洋:《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79页。]甚至有观点提出的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上是附法定生效条件,在转让股东通过公司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同意转让同时放弃优先购买权则合同生效,股权转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生效。[ 参见冯威:《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规范分析》,载《研究生法学》2015年第1期,第12页。]比较法上,德国法考虑到股权不能善意取得,使得股权转让容易引发冒险和投机,围绕股东名册构造了人为性的权利外观基础,包括股东名册事项完善记载并提交至商事登记法院,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公示,并且只有在提交到商事法院后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同时任何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记载事项,这样就达到了社会公示目的,使得股东名册反映真实的股权归属,保障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 参见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60-165页。]构成要件是(1)须为法律行为方式的股权取得;(2)信赖基础是股东名册记载;(3)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仍无法与不动产登记薄等同;(4)没有异议登记。如果不可归责于权利人,需要经过三年。[ 参见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67-169页。]另不少观点主张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转让是两个不同的行为,除合同外还需要所谓的“交付行为”(载入股东名册),才能完成权利的转移。[ 参见叶金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初探——兼论〈公司法〉第35 条之修正》,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6期,第31、32页。]有学者认为,受让人的取得需以股东名册之变更登记或公司登记中的股东变更登记为要件。[ 参见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311页。]总体上,持此立场的学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仅产生履行义务,而非股权的当然变动,股东名册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工商登记具有对抗效力。虽然有观点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 《担保法》第78条第3款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认定股东名册之记载可以发挥表征股权的功能,故股权变动效果应经股东名册变动记载方可发生。”[ 参见叶金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初探——兼论〈公司法〉第35 条之修正》,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6期,第32页。]但事实上,这种观点忽略了股东名册不置备情形,以及股东名册变更是公司负责的特性,不宜过分强调该形式要件,在2019年《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实施以前,从整体上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主要持以下观点:股权转让合同并不能直接导致股权变动,[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70号。]应当结合股东名册变更或者工商登记变更,实际行使权利等综合认定,问题在于股东名册多不置备,而且外部人多无法审查,因此应主要结合公司是否对于该股东资格的认可等因素,而不过分要求形式要件。也正如有观点提出的为了维护公司的人合性而提出的要求建构“公司受通知和认可的程序”来确定股权变动,[ 参见李建伟:《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模式研究——以公司受通知与认可的程序构建为中心》,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18-29页。]虽然公司是否有权拒绝尚未形成通说,但是股权关键在于向公司行使,不应当仅仅依靠合同发生股权变动效力。
(三)利益衡量因素的增多:股权特别利益
1.原有善意取得制度忽略了股权特别利益
有学者提出股权具有有别于一般的财产利益的特征,还带有股东资格享有以及对于公司的管理、控制等,代表着复杂的商业利益,虽然本质上和民法的外观主义相符,但本质上商法和民法的理念存在差异,[ 参见全先银:《商法上的外观主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应当运用商法中的权利外观责任以实现利益平衡。[ 参见陈彦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质疑》,载《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12-116页。]因而考虑到股权中的特别利益保障需要,直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容易造成有关利益保护的缺失。
2.股权特别利益保障的可行方案
针对前文有观点提到考虑到民商事理念的不符,主张运用商事外观主义去解决商事法律关系,应当看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商事外观主义本身就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肯定前述善意取得本身是利益衡量结果的基础上,关键在于这种股权特别利益在进行善意取得的构成上如何进行有效权衡的问题,但是并不需从根本上去否定善意取得的适用,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所有的商事关系的建构直接依据商事法律原则进行处理,反置具体规则于不顾,这实际上在立法技术上不仅难以实现,也在司法操作上增加不确定性。最佳的方案仍是在善意取得的具体使用要件上针对股权特性进行有效权衡有关权利义务关系。
(四)组织法的立场:公司人合性的保障
1.善意取得对公司人合性等的“破坏”
有学者提出,善意取得制度原本适用流动性较强的财产,利益衡量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也相对简单,而股权并非完全是自由流动的财产,股权作为股东财产具有流动性的前提应当是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同时有别于一般善意取得制度中交易安全具有优先性,股权交易中涉及的利益较为复杂,除了股东的所有权外,还有其社员权以及有限公司人合性等的价值保护,后者似乎更为重要。[ 参见陈彦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质疑》,载《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13页。]诚如有观点所说的,股权转让同样应当符合公司意思,受制于公司目标等影响,善意取得制度仅仅作为一种商业需要,但是考虑到股权的封闭性,承载着社员权和股东间的信任,流转不是完全自由的也并非主要价值,不能单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参见张畅、吕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刍议》,载《社科纵横》2020年第3期,第79页。]德国法上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考虑到对外公示效果,德国法上的章程提交于商事登记法院,完成公示,受让人也就不能主张其善意且不知情,章程限制具有对抗善意受让人的效力。[ 参见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71页。]2.公司人合性的维护路径
正如学者所提出的只有符合必要程序股权变动才是有效的,这是对于公司独立性和经营存续的保障,由此不会破壞公司的人合性。[ 参见朱晓娟、姚篮:《论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一般结构》,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47页。]有学者支持提出《公司法》第71条赋予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涉及公司秩序,违反情况下受让人不存在善意保护,《公司法》第71条第2、3款属于立法性限制,同理不存在善意保护的问题。[ 参见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137页。于焕超:《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再思考》,载《研究生法学》2017年第 1期,第118页。]股权转让涉及众多当事人的利益,有观点提出必须采取书面方式进行, 如果法律要求经过批准的则必须履行手续,如果未经同意或者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则受让人不能善意取得。[ 参见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4页。]显然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和公司人合性的维护是可以有效协调、并行不悖的。
三、典型适用类型的质疑与回应
(一)名义股东的特别处理
1.名义股东的“矛盾”界定
有学者提出,名义股东处分股权一般认为是有权处分,无法适用善意取得。名义股东是合法股东,即使出资来源于实际出资人,但股东权利义务的履行均指向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只能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约束名义股东行为,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权利,名义股东处分股权本身是应当由实际出资人承受的风险,不应通过赋予受让人调查义务的方式来进行风险转移。[ 参见于焕超:《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再思考》,载《研究生法学》2017年第 1期,第117页;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2页。]名义股东和出资人以及股东和公司之间是两组独立法律关系。[ 参见张畅、吕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刍议》,载《社科纵横》2020年第3期,第80页。]尤其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和《公司法》第7条的规定,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实际出资人成为股东情形下,名义股东处分股权为有权处分,即使同意实际出资人成为股东但是如果尚未办理登记也仍旧缺乏善意取得构成要件,而只有此时进行质押或者其他方式处分股权才可能构成善意取得。[ 参见张钰涵:《代持股善意取得之界限——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130、131页。]也有观点提出名义股东无权处分的做法否定了登记的绝对公示效力,公示效力以维护和承认所有权人的外观状态为前提,而善意取得实际上承认了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协议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参见张笑滔:《股权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134页。]2.名义股东的特别处理规则
名义股东身份的关键在于凭借股东身份,可以向公司直接行使有关权利义务内容。这里的问题在于:多数观点一方面在否定股权适用善意取得的股权特性时候认为股权是一种相对权,应该适用债权规则,但是在此处又肯定其偏向于物权的属性,因为股东身份的存在便自然应当享有股权的一切权利,包括处分权等。实际情况是,按照通说股权是一种社员权,在和公司的关系上固然是肯定名义股东的股东身份,但是在财产权属性上不妨碍其不享有因此带来的财产处分权等内容,因此应该肯定司法实务观点认为名义股东处分股权是一种无权处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观点提出将股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而应当有特别的规则。总之,股权善意取得的关键在于真实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问题,虽然二者主要是基于约定达成的财产归属,却合法有效,应当得到保护,并有适用善意取得的空间,否则只能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况下否定处分行为,对于实际出资人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只是这里考虑到这种不一致状态是由实际出资人造成的,应当承担必要的风险,具有相当的可归责性,在此种情况下认定善意取得更为容易。
(二)一股多卖与一物多卖的区分
1.立法层面的障碍
有学者认为,一股多卖情形下,考虑到工商登记是对抗要件,这里的未经登记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可以解读为“对第三人来说未发生股权变动”,第三人可以主张是有权处分,善意取得制度只是由于公示对抗规则过于简单的一种参考。[ 参见姚明斌:《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第83、84页。]正如观点所提出一股二卖中登记名义人具备处分权是登记对抗主义下的必然逻辑,[ 参见冉克平:《论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物权的变动——兼析法释〔2012〕8号第10条的得与失》,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153-162页。]不符合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前提,而且登记对抗主义中的善意第三人比善意取得中第三人更广,甚至包括恶意第三人,这也更有利于激励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完善,加上股权工商登记的可信赖性有限。[ 参见吴勇敏、张桂龙:《论股权多重转让中善意取得规则的修正适用》,载《浙江大学学报》(人社版)2017年第4期,第188-190页。]也有学者在坚持股东名册变更的债权形式主义基础上对一股二卖的适用进行区分,在没有股东名册变更也没有变更工商登记时有权处分,而对于变更股东名册却没有变更工商登记的情况下,由于需要公司参与也很难构成善意。[ 参见杨洋:《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80页。]司法实践往往集中在第二买受人善意与否,而忽略了出卖人动机并直接推定第一买受人没有及时登记存在过失,但实际上股权签订阶段不能获得比26条股权实际出资人更多的保护,合同相对效力不足以对抗后买受人,法院也不会认定其股东资格;但是如果已经记载于股东名册或者经过过半数股东同意,只是尚未工商登记,后买受人的善意认定就需要结合前述因素。[ 参见张笑滔:《股权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135页。](1)结构性错位。在前受让人与后受让人均签订转让协议而未取得股权情况下,转让人仍有权处分,后受让人通过该处分行为,完成股东名册变更和工商登记变更此时股权是继受取得,而非善意取得,也就是说只有在前受让人已经完成了股东名册变更,但是尚未办理工商登记情形才属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8条情形,同时考虑到一物二卖中不会出现善意取得问题,贸然适用于股权一股二卖情形会出现结构性的错位。[ 参见王涌:《股权如何善意取得?——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疑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32、33页。](2)公司反悔权的出现。这里一股二卖如果允许后受让人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获得股权,事实上等于肯定了公司在接受前受让人后仍旧可以继续选择受让人,否定前受让人。[ 参见王涌:《股权如何善意取得?——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疑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33页。](3)前买受人不存在可归责性。有观点从诱因原则出发提出,在名义股东情形要求实际出资人承担此种风险有合理性,因此,是其自愿托付第三人,但是在一物二卖情形下,难以认定诱发了此种风险。
2.一股多卖的司法认定
事实上学理层面多数观点肯定一股多卖适用于善意取得。关于登记对抗主义引发的有观点主张此种情况是有权处分的争议,前文基础理论部分已经回答,此处不再赘述。
针对有观点提出的和普通一物二卖规则不同,实际问题恰恰在于一般财产权利变动主要采取的是公示生效主义的模式,在未完成公示前,不需要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前后行为均是有权处分,而此处股权一股多卖情况下,根据司法解释股东已经取得股权只是没有变更登记,是有无权处分的情形和善意取得适用空间的。也正如有观点认为虽然股权是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双重公示,但是可以参照特殊动产允许一物多卖适用善意取得,该观点中的无权处分除了无所有权处分财产外,还包括所有权受到限制而处分财产、虽有所有权但是无处分权以及代理人擅自处分被代理人财产,善意取得制度就是通过设定一定条件来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 参见傅穹、尹航:《利益平衡视野下的股权善意取得》,载《净月学刊》2016年第1期,第34页。]而有观点提出的在肯定“有权处分”的前提下,寻求制度借鉴和利益衡量,积极借鉴善意取得制度,但是注重考虑先买人的可归责性以及第三人的主观状态和注意标准。考虑到我国股权外观的可信赖度较低,考虑先买人可归责性有利于保障其利益,商法中的外观主义本身也包含本人行为可非难性的考虑,一方面促进登记制度的发挥和完善,另一方面可以有效保护登记不完善下的善意先卖人。[ 参见吴勇敏、张桂龙:《论股权多重转让中善意取得规则的修正适用》,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91、192页。]实际上看似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但更增加了适用的不确定性,似乎倾向于重新确立专门适用股权领域的特别规则,相较之下,不如去根据股权结构特性等改造善意取得制度。
至于公司反悔权问题,该观点实际上建立在股权变动形式主义模式基础上。一方面这种观点把公司当作无干第三人,也就是认为把股权转让效果放在第三人手中具有不合理性,实际上公司并非完全无干第三人,有参与的空间,或者可以将这种风险理解为商业经营中的必要风险,受让人在完成登记之前,应当承受该类风险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有关董事等承担责任,能够
预防此类情形并对受让人进行救济。前述有关“反悔”不能理解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而是一种事后的各方权利义务结果的状态,否则按照这种理解是否意味着善意取得制度实际上赋予了无权处分人一种“有权处分”的权利呢?这种权利义务的平衡本身就是立法在充分进行利益衡量后的结果,所以该“反悔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层面上的解构,和现行法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不相符的。
针对有观点提出的诱因原则,认为一物二卖情况下权利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此类风险,但实际上在于如果认为受让人应当促进交易完成,实现权利义务的真实流转进行公示,以免二次处分,相较于该无辜第三人,第一受让人对于出让人的错误信赖以及没有达成权利的公示本身就是应该承担此类风险的,尤其是我们在商事交易当中,过错并不是仅仅在过错情形下,有关必要风险的分配以实现商法的效率和安全,也是归责的正当性,总之这里受让人相较于第三人而言是具有可归责性的。当然也有观点提出如果尚未变更股东名册,可以善意取得,但是内部转让已经变更股东名册不能善意取得,在外部转让仍有串谋的可能。[ 参见冯威:《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规范分析》,载《研究生法学》2015年第1期,第14-16页。](三)夫妻共有股权的认定
1.夫妻共有股权转让的争议
有学者提出,夫妻以共同财产向公司出资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登记为股东,登记为股东的夫或妻转让其名下的股权,虽未经另一方同意的,也不属于无权处分而是有权处分。尽管从婚姻法的角度而论以夫妻共有财产出资形成的股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但是若未根据公司法的要求登记为夫妻共同享有股权,在这种情形下,共有财产只能體现为股权收益或股权转让金归夫妻共有。至于股东资格及股权,根据外观主义法理和公司法关于股东显名主义的规定,只能由登记为股东的夫或妻享有包括转让的股东权利。[ 参见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3页。]2.夫妻共有股权转让效力
前述观点认为夫妻共有股权按照登记宜为有权处分,但实际上这种方式看似符合商事效率,却严重背离社会公平要求,并非具有天然合理正当性。考虑到商事经营特性以及股权特性,由夫妻双方承担可能被处分的风险即可。正如有观点所说的,股权应当是夫妻共有财产,关键在于善意的认定处理上,应当将“股权买受人信赖登记”作为适用善意取得的判断标准,不应当要求受让人去核实有关登记事项,而只要信赖股权登记信息即可,这里的善意是推定的,而应当由否认受让人善意的一方举证证明受让人恶意。[ 参见李如霞:《夫妻共有股权转让问题探讨》,载《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45页。](四)冒名转让的恰当处理
1.可归责性“缺失”
有观点提出,冒名转让股权中,事实上等同于盗窃行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知情的买主买得的赃物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除了具有一般善意取得一般构成要件外,还应当在公开市场上经交易取得。[ 参见谭津龙:《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质疑——基于〈公司法解释三〉及其扩大适用》,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62页。]对于一般的无权处分,从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角度,应当由所有人承担相应风险,但是对于赃物、遗失物等脱离物,丧失占有并非所有人意志,所有人并无风险防范的可能,继续坚持善意取得对所有人过于严苛,不符合法益平衡原理,相应的对于伪造签名,在股东不知情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应适用善意取得。[ 参见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3页。]
2.冒名转让的适用限制
正如有观点提出的冒名情形虽然原权利人可归责性较弱,但并不因此而完全否定善意取得适用空间,也正如有学者提出应当提高善意取得的适用标准,为第三人增加注意义务,防止股东权利被随意处分。[ 参见张畅、吕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刍议》,载《社科纵横》2020年第3期,第83页。]正如德国法所采取的在错误登记三年后,有善意取得的适用空间,当然这本身是利益衡量后的结果,我们可以有效借鉴的不是制度本身,更是这种利益衡量的思路以确定善意取得的适用类型和要件。
四、股权适用善意取得的基本建构思路
(一)目前学界制度建构路径观点
1.商事外观主义的前置性构建
学者有观点坚持商事关系和民事关系的差异化,以及股权转让的复杂性,主张采用以商事外观主义为核心,并借鉴善意取得的制度,在肯定股权善意取得一般逻辑基础上,充分考虑了股权特殊性以及商事外观主义,并进行价值衡量。如有学者提出:(1)认可本人失去股权后,并非仅仅财产权的损失,更会涉及到管理公司得利或者其他商业目的的落空;(2)直接适用善意取得过分关注第三人利益而忽略原权利人的非难性,进言之,先用商事外观主义判断原权利人的行为是否产生让第三人信赖的权利外观,用以弥补股权特殊性造成的原权利人保护的缺位,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即可获得正当性基础。[ 参见朱晓娟、姚篮:《论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一般结构》,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48-54页。]2.围绕登记对抗主义特征进行一般性建构
有观点主张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扩张适用,在法律规定的具体情形之外,在“登记错误”框架下进行一般化尝试,排除名义股东和违反章程和法律规定情形。[ 参见于焕超:《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再思考》,载《研究生法学》2017年第 1期,第116页。]也有观点提出考虑到股东资格内部主要遵循意思自治,而外部关系则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通过公示公信原则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商事交易效率特性,相对人只要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尽到一般注意义务,不需要采取积极行为,只有在重大过失时才排除善意,但是坚持这里的善意应当是持续到股权变更登记之时。[ 参见王晓琴:《股权转让中善意取得问题的研究》,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期,第28-30页。]善意取得的修正适用应当围绕股权登记对抗主义前提展开,综合考量先卖人可归责性和第三人的主观状态和注意程度,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激励股权登记并贯彻股权登记效力的长期立法目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为第三人设置难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股权的多重让与,从而保护股权外观效力缺陷状态下的善良先买人。[ 参见吴勇敏、张桂龙:《论股权多重转让中善意取得规则的修正适用》,载《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92页。]3.从注意义务切入进行类型化建构
这种观点坚持善意取得制度应当通过风险分配,一方面鼓励促进商业交易,另一方面有效抑制“盗窃行为”。(1)实际出资人承担大量风险,明知被处分的高风险,应当适用合同相对性原理,只要不是明知,甚至即使是明知的,只要不是恶意背信,实际控制人不能主张名义股东处分行为无效,偏向于善意第三人;(2)一股多卖在股权让与,程序上需要经过其他股东同意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签章等,后受让人同样如此,后受让人不可能是善意,但是仍然存在着股东和公司存在合谋或者欺诈的情形,任何人不能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受益;(3)夫妻共有股权包含在夫妻双方信任范围内,处分行为为可预见,这是倾向于保护买受人;(4)登记错误情况下通过权衡双方过错对股权归属的影响,不是买受人善意即可取得股权,反过来也不是买受人明知(非恶意)权利瑕疵就一定不能取得股权,关键在于衡量双方应尽注意义务的履行情况,受让人的最低义务是尽职调查工商登记、股东名单以及过往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记录中,登记股东是不是从未出现过;(5)冒名股东,对于冒名案件一般认为应当适用《物权法》第107条关于遗失物和盗窃物的规定,否则普通人必须整日为房屋产权被冒领而担惊受怕,影响市场交易效率,同时原所有权人的过错应当纳入裁判考虑,如果原股东对于冒名处分没有任何过失而仅因登记机关过失应类推适用前述遗失物、盗窃物处理规则,相对于不能主张善意取得,但是如果尽到注意义务,除了可以主張违约责任或者缔约过失责任外,还可要求登记机关的重大过失承担责任;如果原股东出于信任,使得前述冒名行为更容易发生(如出借房屋权利证书或者自身身份证),应当承担此种冒名风险。[ 参见张笑滔:《股权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141-143页。]也有不少观点主张引入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如伪造冒充处分股权情形,但是这里并不等于要求过错,可归责性仍主要指向风险归责。善意认定标准这要考虑到交易背景和公司的人合性,但是不应当过分要求,同时也要肯定商事活动中注意义务要高于一般民事主体。[ 参见刘江伟:《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规则的检讨与适用》,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63页。](二)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以利益衡量为基点
1.一般原理的建构和完善
由于股权善意取得相较于动产善意取得或者不动产善意取得,涉及的法律关系和利益冲突更为复杂,也因此需要进行更多更为具体的利益衡量,也正基于此前述不少学者提出了从商事外观主义角度建构善意取得制度,或者加入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因素,实际上这本身涉及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的问题,本质上都是价值判断,本文主要基于立法价值衡量进行的选择,根据前述分析,笔者倾向于以善意取得制度为根本,并根据股权特殊性和商事外观主义等因素对有关适用要件和适用情形进行改造。具体分析如下:
(1)登记对抗主义效力的分析
一直以来对于登记对抗主义的效力争议,从未停止,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登记对抗主义如果要采取认定为“有权处分”的效果,既背离生活实践,也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此处的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实际上考虑到登记对抗主义本身并不当然直接指向权利归属,也因此对于受让人而言,本身应当尽到更多的审慎注意义务,包括查看其它股东身份证明文件,甚至应当向公司核实等,尤其是股权转让需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而且善意取得本身需要最终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认定登记对抗主义本身并不单纯制造出登记对抗规则,而在于减弱了这种公信力,受让人比不动产转让应当尽到更多的必要注意义务。
(2)权利外观公示效力的减弱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股权的公示不仅仅有工商登记还有股东名册,双重公示不仅没有增强公信力,产生可信赖的权利外观,反而增加了权利公示的不确定性,加上股权变动并不当然需要股东名册的变更和工商的登记变更,虽然这都是有争议的,但是至少目前是普遍认同的观点,因而受让人不能单单凭借工商登记,就认定是善意且无过失,同时考虑到这种公示状态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在确定善意取得的类型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种因素。
(3)商事外观主义法理的介入
股权转让的发生是一种现代典型的商事交易活动,应当符合商法的基本理念,效率和安全,当然也要遵循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保障外部信赖主体的信赖利益。前述有观点基于此否定善意取得的直接适用,但是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来说,存在无权处分,应当有适用善意取得的空间,商事外观主义在外观可信赖基础上确实应当注重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符合商事交易的效率和安全,但是不能单纯靠着一项基本原则进行审理,而是在权衡有关外观是否可信赖以及可信赖程度基础上,多方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权衡,商事外观主义同时是价值衡量中的较小一环,并不意味着可以作为规则直接进行判断。
(4)公司人合性的保障
正如前文谈到的公司人合性的保障,在有限公司中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很多学者主张违反章程限制规定或者侵犯有关股东同意权、优先认购权等的股权转让不发生善意取得,但是一方面这是一个立法价值选择的问题,并非有确定的结果,另一方面这并非善意取得制度的关键,善意取得关键是解决真实权利人和无处分权人以及受让人的法律关系,这里涉及内部限制的处理问题,因而并非本文拟解决的问题重点。当然考虑到公司人合性的存在,也要求受让人对于受让过程中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
(5)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立法定位
正如有观点提出的,我国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外观基础是股权工商登记,相较于股东名册而言,更具公信力,加上现代商事交易侧重于交易安全的维护,进而有学者认为有关占有丧失物回复的规定应当从严把握。[ 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8页。]但是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2款:“受让股东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也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这种做法将真实权利人过错作为权衡当事人责任轻重的作用。[ 参见冯威:《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规范分析》,载《研究生法学》2015年第1期,第13页。]正如善意取得制度应当限缩在基于信赖关系的无权处分的范围内,当无权处分的产生不存在可归责于所有权人事由的,应当倾向于保护原所有权人的利益。[ 参见张笑滔:《股权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132页。]当然这里的可归责性并不是要求存在过错,商事交易过程中存在风险归责的余地,在原权利人和受让人之间进行风险利益权衡,正如前文提到的名义股东情形,一股二卖情形,夫妻股权处分情形等认定真实权利人具有可归责性应无疑问,但是在冒名处分情形之下,相较于无辜的受让人而言,权利人对于控股股东、董事等的信任导致了商事交易外观风险的出现,也不应该绝对排除善意取得的适用。
2.一般构成要件的分析
(1)股权无权处分行为
股权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主要针对股权登记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况,除了一般登记错误的情形之外,还包括有前述提到的名义股东处分股权,一股多卖情形以及冒名处分情形。
(2)受让人善意的认定
善意的程度。善意取得的善意认定,对于动产一般认为是善意,而不动产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考虑到股权登记同样具有较强的公示效果,同样应当认定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因为《公司法》中无类似《物权法》第16条规定,故股权的工商登记的公信力难以与不动产登记簿相比,受让人的善意程度应比不动产的受让人高,要求受让人不知且非重大过失不知权属状态不实,这又因股权是内部转让或外部转让而有别。[ 参见冯威:《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规范分析》,载《研究生法学》2015年第1期,第13页。]这里考虑到前述提到的登记对抗主义以及股权双重公示的适用,受让人的无重大过失要求其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结合后文提到的善意的时点,认定善意程度应当结合注意义务内容,包括审查股东名册,查看公司章程,经过过半数股东同意以及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程序,并最终完成工商登记过户等。
善意的时点。有观点认为是在意思主义下合同生效时“善意”即为已足,但是结合动产善意取得等的适用,应当持续到完成工商登记股权变动完成之时。只有这时候受让人才可以具有优先效力,对抗原权利人,同时这样也有利于认定善意的程度,也就是受让人的注意义务,有效平衡原权利人和受让人的利益。
善意的证明。对于受让人的善意的证明,并不能直接从登记外观可以推定出来,尤其是考虑到受让人应当履行必要的审查义务,审查股东名册、其他股东同意等决议以及请求公司变更工商登记等内容,这个过程中受让人应当证明其尽到必要注意义务。而权利人也可以通过必要证明前述材料如章程等内容否定受让人善意的情形,或者证明受让人恶意等。
(3)以合理价格受让股权
这里的合理价格受让股权的认定并不以注册资本为要件,而是应当主要參照市场价格,不应过分低于市场价格,同时由于是合同义务并不以实际履行为要求,而只要约定合理价格即可。
(4)股权完成股东名册变动
工商登记工作人员与股权交易当事人串通予以违法登记,则应当认定登记无效,受让人不能适用善意取得,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相关登记人员与无权处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参见王丽美:《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及适用性分析》,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68页。]有观点提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无权处分人使得股权移转产生了可信赖表征的要求,另一方面股权转让完成,受让人形成法律上的交付,并使得善意受让人的保护优先于原权利人的重要依据。[ 参见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5页。]通过检索有关案例不难发现司法实务也主要认定要求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才能适用善意取得。[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594号民事裁定书。]3.具体适用情形的法律差异思考
(1)名义股东
名义股东情形下,一方面该代持是名义股东所产生的,具有可归责性,另一方面由于该代持情事较为隐藏,主要是合同效力,不为外人所知,因而受让人的善意认定较为容易,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倾向于肯定善意取得的成立。除非该代持情形为受让人知情,否则不应轻易否定善意的成立。
(2)一股多卖
一股多卖情形下,有观点虽然主张前受让人不存在过错,而且由公司负责完成有关工商登记变更等事宜,这种情况下相较于前述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类型而言确实可归责性较弱,但是虽然主要是一种风险的承担,但并不意味着毫无可归责性空间,从效率角度应当认为适用善意取得。但是如果前受让人仅仅签订合同,而未经过股东同意,获得公司认可,则应当鼓励竞争,认定为有权处分。只有在经过公司认可环节,才能认定取得股权,可以限制这种情况下的适用空间,即只有在公司,其他股东等参与串谋等才会发生善意取得,这种情况下如果股东名册尚未变更或者已经变更但是公司隐藏而导致受让人无法发现仍可发生善意取得。
(3)夫妻共同股权
夫妻共同股权甚至有观点认定是有权处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不应当过分要求受让人知道该事实,受让人也无从获悉,否则会增加审核成本;因此一般情况下,除非明知,否则应认定为善意为宜。当然如果在股东名册有记载或者章程等有记载而受让人可以获悉的仍应认定为存在过失的可能。
(4)冒名处分
对于冒名处分,考虑到原权利人几乎没有可归责性,如果要求原权利人经常性的检查工商登记记载事项过于严苛,因此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不发生善意取得。但是如果受让股东能够证明自己仔细查阅了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记录、股东会决议等,履行了必要审查义务,而根本不可能发现冒名事实,笔者倾向于肯定善意取得的适用。或许会有观点提出质疑,也就是受让人的审查义务内容在不同的情形中应当是具有一致性,如股东名册记载、章程、工商登记记载,股东同意的股东会决议等,对于认定善意与否尤为关键。但是问题在于善意取得的本质是利益衡量,是一种综合分析后事前的立法推定,也就是这种情况下,即使受让人或许并不知情,仍然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看似不合理,但是实际情况是动产善意取得中,将盗窃物等受让人不可能知道的情形直接否定善意取得的适用,除非是在市场公开受让,有异曲同工之效。
五、结论
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建构有其必要性,本文从善意取得制度的发展、特征认定善意取得的关键在于无权处分情形下的利益衡量,而股权的特殊性以及登记对抗主义、双重公示等的特性,加上公司人合性的维护对于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要件进行有效的变通,同时在不同的适用情形中虽然有一定的差异性,但不影响无权处分的认定,关键在于和一般构成要件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利益衡量,并在对于受让人善意的认定应当提出比一般不动产登记提出更高的标准。即便存在冒名处分情形也不宜直接适用盗窃物排斥善意取得,而应该在利益衡量基础上对受让人提出更高的义务标准,并在具体的类型化基础上进行事前立法层面的利益衡量。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Applies to Equity
LI Yachao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icial Economics,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of equity acquisition in good faith has always been full of doubts, but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system concepts and requirements, and ignores its inherent commonality and actual institutional needs. Basically, it must be recognized that the legisl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essentially points to a result of interest measurement. The appearance of a trustworthy right itself is also a legislative construction, which is not completely natural, plus considering the necessity of equity transactions, As well as the objective need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necessity of risk regulation, the system of equity acquisition in good faith has its necessity. The question about the acquisition of good faith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fully reflects the complex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for the acquisition of the good faith of the equity, including commercial appearanceism,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is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ny fit and equity transfer, dual publicity, etc. In terms of aspects, this requires us to transform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goodwill acquisition, and to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various specific application situations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benefit measurement, and establish a more standardized and reasonable system of equity acquisition in good faith.
Key Words: Appearance of rights; Registration adversarialism; Benefit measurement; Registration errors; Rightholder attributability
本文責任编辑:林士平
青年学者编辑:赵 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