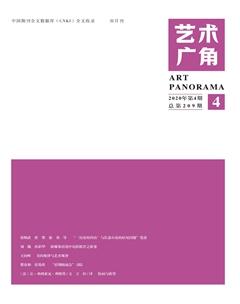“大团圆”之“影响的焦虑”
我们常津津乐道于古今中外诸多长篇小说精彩的开头,却往往忽略了它们是如何结尾的。结尾不仅仅意味着故事的结束,它还可能如电影的“彩蛋”,留下突如其来的惊喜和让人充满想象的期待;而且,结尾作为情节的最后一环,并非“开端—发展—高潮—结尾”这一叙事链条自然顺延的结果,它还牵连乃至调控着其他部分的书写。可以说,很多时候,结尾的设置关乎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准。比如众多关于《水浒传》《红楼梦》结尾的续写或改写,最后都被读者所抛弃,究其原因,除去先入为主的阅读体验,还在于原著结尾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收束力和感染力。所以,如何结束一部长篇小说,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并非易事。就中国古今长篇小说结尾的差异来看,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的长篇小说往往复制着“大团圆”的结局模式,主人公无论经过多大的挫折和苦难,最终都能破镜重圆、阖家团聚、功成名就、满门封赠,这种重复本身就意味着作者在突破前人叙事模式上的困难与无力;而五四以来的长篇小说则倾向于采用开放性的结尾,将故事和人物命运的诸种可能性留给读者想象,这看似灵活多变,但也未尝不是作者不知如何结束自己的小说所致,近百年来,就有诸多名家承认自己的某部长篇小说是未完成之作,原因当然很多,但艺术上的难以为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我们还是很难判定这两种结尾模式孰优孰劣。特别是,后者的推广和风行主要得益于近代以来新文学先驱对前者的批判,如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傅斯年、钱锺书等都对传统长篇小说“大团圆”的结局叙事有过不同程度的批判。鲁迅就认为“大团圆”的模式折射出国民的劣根性,即作者不敢正视现实社会人生的黑暗和苦难,只好用虚幻的圆满来自我欺骗和麻醉,这就有意无意地粉饰现实,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反现实主义手法。[23]此等观点尽管意在消除“大團圆”模式的审美疲劳,也确实为之后长篇小说结尾模式的革新提供了无限可能,但另外一方面,也不无哈罗德·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之意味,亦即新文学作家为避免自己的小说沾上“大团圆”习气,千方百计地设计出与之相背离的小说结尾,以此显示出反传统的进向。就此而言,我们认为不能把中国古今长篇小说结尾模式的差异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文学革命”,相反,百年来中国长篇小说花样百出的结尾设置还折射出了反“大团圆”模式下的焦虑表达与自我调适。因此有必要重审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今长篇小说结尾模式的转换,首先与时间观念的变革有关。古代中国主要操持一种循环的时间观念,《三国演义》开篇所谓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是以天道轮回的思维来认知历史的发展,小说的情节结构本质上是时间的隐喻。循环论时间观影响下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亦随之形成一种追求圆满的叙事修辞,“大团圆”的结尾模式就是藉此生发出来的。譬如《水浒传》以悲剧结尾,此时一百零八将已所剩无几,但小说却通过宋徽宗的梦境,让宋江与部分兄弟魂聚于楚州南门蓼儿洼,尽管他们主要是想向皇帝诉冤,但实际上也是梁山兄弟以另外一种方式团圆,小说的悲情由此得到了些许抚慰,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张力。而在五四以后的长篇小说中,循环的时间论被打破,文学上多采用线性的时间叙事,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兴起,正是对这一线性时间观念的回应。在这类小说中,每一部的结尾既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同时又开启了下一部的故事,甚至最后一部的结尾仍然是面向未来敞开,正如巴金在“激流三部曲”最后一部《秋》的“尾声”中所说的:“对于那些爱好‘大团圆收场的读者,这样的结束自然使他们失望,也许还有人会抗议地说:‘高家的故事还没有完呢!但是,亲爱的读者,你们应该想到,生命本身就是不会完的。那些有着丰富的(充实的)生命力的人会活得很长久,而且能够做出许多、许多的事来”,“至于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也不能向读者作任何的预言。”[24]特别是随着西方进化论的引入,很多力图反映社会时代广阔内容的长篇小说常以“现在”想象“未来”,充满了“进步”与“成长”的叙事欲望,结尾不再有休止的意味。如茅盾《虹》的结尾,讲述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后,女主人公梅行素积极投入其中,在游行过程中,梅被巡捕的高压水龙淋湿,她来到一家旅馆换好衣服后,再次奔上街头,投入战斗。小说就此结束。按茅盾的解释,小说还未完成,他本意“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只是“人事倥偬”,“遂不能复续”。[25]实际上,这样的结尾也未尝不可,甚至是恰到好处。因为以梅行素的性格,她无论身在何处,都不会很好地与周围环境融合,她进入革命队伍后同样会时刻感到不被理解的痛苦与失落,最后很可能落得与“倪焕之”一样的结局,如是结局固然可以反映“中国近十年之壮剧”,但未完成的结尾的开放性更具有让人想象的空间:时代女性从五四到“五卅”的时代波澜中的种种挣扎、反抗,中国知识青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艰难历程,都可以在这戛然而止的场景中延伸出无限的意义。
古典小说“大团圆”的结尾模式也与古代中国因果报应的信仰密切相关。发端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则是善恶对立,最后善战胜恶,故事以完满结尾。即使小说讲述的是悲剧的故事,恶战胜了善,最后也可能通过“游冥”的形式,让恶在阴间得到惩罚,这其实也相当于加上一个喜剧的结尾。如明代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里,岳飞精忠报国,驰骋沙场,最后却被秦桧假传圣旨杀害于风波亭,但小说却将此归因于宿命因果律。同时,又通过岳飞显灵,让秦桧夫妇得到阴报,消解了小说的悲剧气氛,形成了一个圆形结构。与此不同的是,五四以来,随着科学的昌明,因果报应思想被抛弃,同时基于启蒙或救亡的工具理性,个人之恶、群体之恶、社会之恶在小说中被频繁书写乃至无限放大,而善良、正义、光明则被任意践踏,恶不再有报应,甚至是“损不足奉有余”。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在“三起三落”后最终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茅盾在《子夜》中,原本的结局设计是吴荪甫与赵伯韬在庐山相会,握手言和,但最后接受瞿秋白的建议,改为一胜一败,以更深刻地反映当时中国的阶级矛盾。[26]茅盾对《子夜》结尾的更改,虽然主要是出于阶级斗争叙事的考虑,但也内在说明他对于传统“大团圆”的结尾模式有着自觉的警醒。
除去因果报应律,宿命论在古代中国也深入人心。天人合一,人命天定,大至国家大事,小到个人命运,一切都已注定,这是宿命论所宣扬的观点。在这一观念的主导下,小说情节的展开从不具有偶然性,人物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推动,因此小说的结尾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只不过是命运操控的结果,这实际上跟经典“大团圆”模式的自我欺骗和麻醉无甚差别。如《南宋志传》在描写赵匡胤的行侠仗义时,常以“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手法暗示其王者风范,最后在智勇人士的辅佐下,赵黄袍加身,成为大宋开国皇帝,小说的结尾毫无悬念,只为确证赵为天选之子。而五四以来的长篇小说中,随着“天人合一”观念及宿命论的破除,小说成为对人生和生命的不确定性的诠注,小说人物如海德格尔所说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他们的命运充满了偶然性,因此这类小说的结尾常常出人意料。比如铁凝的《大浴女》有着一个看似难以自圆其说的结尾。小说女主人公尹小跳即将与陈在举行婚礼的时候,陈却到南方出差,其前妻万美辰找到了尹小跳,一番长談后,尹小跳决定放弃与陈在结婚,并告知万美辰随时可以和陈复婚。小说中尹小跳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情感经历,陈在的婚姻也不美满,且他一直在等待着小跳。然而在有情人即将终成眷属之时,尹小跳却为了走进“内心深处的花园”而取消婚礼,这一反转明显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的团圆模式。或许在有些读者看来,这样的结尾显得突兀、不自然,但实际上,这样的结尾才符合生活的本然,因为现实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古代文学有着鲜明的抒情性。有论者指出,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以来,主要以抒情为主导,诗性的抒情精神成就了中国文学的荣耀,也造成了它的局限,“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27]而且这一抒情传统渗透到古代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所以,在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中,无论是充满奇幻色彩的神魔题材、英雄传奇题材,还是较为写实的历史题材、世情题材,都具有明显的抒情倾向。其故事的离奇和引人入胜,其情节的波澜起伏,都可以看成是抒情底色的显影,这也使整个小说具有了形而上的诗性意味。而按弗莱的看法,诗的情感节奏是不断循环的,这一反复性节奏的达成是靠诗句尾部的押韵来实现的。[28]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大团圆”的结尾看成是小说诗性情感的押韵,亦即小说中诸种矛盾和对抗在结尾处得到解决,人物都有各自的归宿,读者的情绪也得到了相应的安抚,有如诗歌的押韵一样,它与小说其他部分的情感修辞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圆圈。相比之下,五四以来的长篇小说虽也受到“抒情传统”的影响,但这种抒情不再来自于奇幻和浪漫,而是日常人生应有的情感表达,因此小说的结尾往往在平淡无奇中结束,不尚完满,不追求苦尽甘来,小说结束的只是人生某一片段,未来还在继续展开,而且还可能一如既往地波澜不惊。换言之,小说的结尾不再向形而上的诗性封闭,而是面向形而下的俗世敞开。正如耿占春所说的:“正像没有故事的状况成了我们平庸生活的特征,现代小说总是结束于一个细节,结束于未完成的现在进行时。”[29]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结尾,孙少平为救一个醉酒的工人受伤毁容,从医院出来,他又回到了矿山,生活既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而是按照既定的轨道继续往前。这样的结尾平淡得让人有点失望,历尽磨难的孙少平为何没有苦尽甘来,而是继续做一个矿工?他以后的人生之路是否有进阶的可能?这一切作者都没有交代。然而,这也正是路遥的伟大之处,因为他没有粉饰现实,也没有调暗现实的亮度,而是让现实本色演出,这样的结尾在传统长篇小说中是不可想象的。
上述几个方面意不在比较中国古今长篇小说结尾的差异问题,而在于揭示古今长篇小说转型后,作为古代长篇小说最为流行的“大团圆”结尾模式,如何以一种“影响的焦虑”的形式,迫使新文学作家设计出与之相对的结尾。这种“修正”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在此过程中,当然也深受西方长篇小说结尾叙事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两者内在的对话关系。或者,这也是我们考察中国小说现代性进程的一条通道。
【作者简介】
曾 攀:文学博士,《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
徐 勇: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
颜桂堤: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郑 亮:文学博士,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王龙洋: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王炳中: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现代文学史、现代散文研究。
注释:
[1]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马桥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3]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4]陈平原:《危急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5]〔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阿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7]〔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04页。
[8][10]〔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9]〔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7页。
[11][12]〔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第137页。
[13]林那北:《锦衣玉食》,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页。
[14]〔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王士盛、周子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1页。
[15]〔美﹞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灾异手记:人类,自然和气候变化》,何恬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16]〔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17]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0页。
[18][19][21]〔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第5页,第26页。
[20]〔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18页。
[22]〔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3]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252页。
[24]巴金:《秋》,《巴金选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3、619页。
[25]茅盾:《虹·跋》,《茅盾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6页。
[2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27]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7-48页。
[28]﹝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387页。
[29]耿占春:《叙事美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责任编辑 苏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