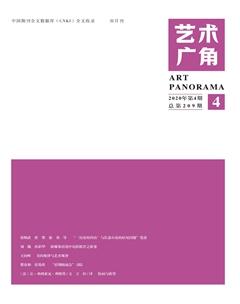“历史的终结”与开放的文学
颜桂堤
历史向何处去?这其实是一个重复已久的话题,也仍然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自福山享有盛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出版以来,“历史的终结”这一宣言振聋发聩。[5]或许有人会问:这一观念难道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历史衰弱的标志吗?显然,一方面这种想法: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对历史的完全而彻底的否定,并致力于消除关于历史的认识的所有深化;另一方面,在后现代社会之中,一种充满裂缝和空隙的分歧蕴藏其间。尽管“上帝死了”“历史的终结”“人的终结”“作者之死”等一些末世学的论题,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但是这些论题所隐含的理论谱系及其当代影响绝不容忽视。在德里达看来,这种“终结论”只是解构理论分化出来的一个部分。一方面,它是建立在对戏称为“终结论”的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分析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它是“我们已经知道或者说我们中的某些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不再讳言的东西”。[6]事实上,“历史终结论”忽略并遮蔽了历史的错综复杂性。
“历史的终结”之后会发生什么?文学如何想象与叙述历史?“历史的终结”之后,我们远远不是抛弃了历史,世界也并未被虚无主义所吞噬。我们既非丧失了历史意识,也非缩小了我们的历史视野,更不是把自己局限在恐惧、悲观的情绪之中。如果历史意味着对我们生存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仍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现今,我们依然生活在历史的轨道上。卡尔·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一书中写道:“我断言,历史本身可以是有趣的,但是它只是在试图解决有趣的历史问题的程度上才是有趣的。……这些本来就是有趣的历史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更有特殊的趣味了”,而“好的历史学家会增强这种好奇心,他会使我们想去理解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人们和情境。”[7]显然,好的文学也应当如此,好的作家也应该增强这种好奇心。当代作家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时代,通过自己的经验与独特视角去表达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理解,深入分析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诚然,作家的创作正是在不断寻求对历史、社会的理解,并以文学特有的“趣味”方式与话语去凝视、表达当代世界的丰盈。
长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大观园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一部接一部的长篇小说,以特有的方式、特有的逻辑,展现了世界的繁复多彩。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述:“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森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都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说探索时间:马赛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8]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都蕴藏着小说精神的复杂性。不可否认的是,每一部长篇小说时时提醒着我们: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当然,小说精神也具有延续性,以互文性的视角观之,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其之前作品的回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之前的一切经验。当代小说之所以具有价值,正在于其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追寻“生活的意义”,使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
历史的终结是否带来小说的终结?或许,我们可以借用保罗·利科的一句话来回答:“在历史之下是记忆与遗忘。在记忆与遗忘之下,是生命。书写生命却是另一种历史。永未终结。”[9]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终结”并不是它消失了,而是它的历史停滞了,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它们并没有发现存在的任何新的方面;它们只是确证人们已经说过的;更有甚者,它们的存在理由,它们的荣耀,以及它们在所处社会中的作用,就是确证人们说的(人们必须说的)。由于它们什么也没发现,所以不再进入被我称为发现的延续的小说历史之中;它们游离于这一历史之外,或者说:这是一些在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10]显然,这种形式的小说未能有新的发现,只是重复,重复制造着已失去了精神的形式。然而,中国当代文学70年,可以说是长篇小说风头正健的70年,也是长篇小说开拓创新的70年。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文体类型和庞大体量,展现了更为全面、立体地审视、书写生活的强大能力。换言之,长篇小说通过其独特方式有效地把握了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不可否认的是,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现代世界复杂性的一种独特把握。比如莫言的《蛙》、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贾平凹的《老生》《山本》、余华的《活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毕飞宇的《推拿》、金宇澄的《繁花》、李洱的《应物兄》、林那北的《锦衣玉食》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现。我们在这些作品的形式或意识中可以发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世界与人这一图景中发现新的意涵。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兰·昆德拉宣称他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执着的观念: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才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对于长篇小说而言,开篇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卡尔维诺曾经就开篇与结尾做过一番有趣的考察:“文学史上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开篇,但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独具特色的结尾却寥寥无几,或者说很难让人记住它们。对于小说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小说的开篇就像开始进攻那样,觉得有必要充分展示自己的能量。”[11]普魯斯特的鸿篇巨制《追忆似水年华》以“很久以来我晚上都是早早上床睡觉”开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激起我们的探秘欲望;《傲慢与偏见》的“有一条真理举世公认:拥有大笔财产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个妻子”;《好兵》以“这是我听过的最悲伤的故事”启动;《百年孤独》的“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以上都是文学史上声名赫赫的标志性开篇。不言而喻,这些小说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在告诉我们:它们愿意被怎样阅读,暗示我们可以寻觅到什么?如果说小说的开头告诉我们将往何处去,那么,结尾则告诉我们到达了何处。一部小说的结尾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童话故事往往以英雄战胜邪恶结尾,传记体小说以主人公的死亡而结束,教育小说结束于主人公长大成人,侦探小说则是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我们尤其耳熟能详的是传统小说经典的大团圆结局。简单易懂、皆大欢喜的结尾,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大团圆”,小说结尾了,问题解决了。然而,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
卡尔维诺认为,小说的结局应该化解对现实的幻想,让人记住小说属于文字世界,它叙述的事件实质上是留在纸上的言语。“尽管小说结束了,也不管我们决定什么时候结束那个故事,我们都会发现,记叙那个故事并非要把我们引导到这里来;重要的事情,即此前发生的事情,不在这里而在其他地方:这才是从可以讲述的世界中脱离出来的那个故事的意义。”[12]有一些经典长篇小说声名赫赫,它们的结尾家喻户晓。我们在列举这些伟大作品的时候,一定不会漏了《安娜·卡列尼娜》《城堡》《芬尼根的守灵夜》《螺丝在拧紧》《魔山》《情感教育》,等等。在昆德拉看來,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有未完成的一面。一个平铺直叙、结尾明显的故事似乎更像是神话,而不是小说。在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以一句未完成的句子——“一条孤独的最后的被爱的漫长的这”——作为结尾。《螺丝在拧紧》中亨利·詹姆斯则提供了“一个自我解构的漂亮结尾”:“我抓到他了,是的,我抓住了他……宁静的日子里只有我们两人,而他那小小的心灵,没有鬼魂附身,已经停止了。”托尔斯泰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结尾的修改同样令人深思。初稿的结尾,安娜是一个非常不可爱的女人,她悲剧性的结局是应该的,是她应得的下场;而定稿的结尾则不大相同,托尔斯泰展现出了小说结尾的智慧。
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打开了。托马斯·曼的《魔山》缓慢地记述了主人公在疗养院里度过的岁月之后,其结尾突然将我们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汉斯·卡斯托普站在泥泞中,枪弹在他头顶上呼啸而过。这样的小说结尾,托马斯·曼拒绝告诉我们,汉斯·卡斯托普最后是死了还是获救了。《情感教育》的结尾堪称是小说结尾的一个另类经典,福楼拜用四百页的巨大篇幅描绘了主人公青年时代的爱情、巴黎的生活和当时的革命情形,但却以主人公和一位老朋友的一场戏谑谈笑而结束。“福赖代芮克道:那是我们顶好的时辰!——戴楼芮耶道:是的,也许是吧?那是我们顶好的时辰!”这种结尾回顾了那些充满情感、事件、等待与期望的日子,最后将这一切全部化为灰烬。而林那北的长篇小说《锦衣玉食》的结尾则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类型。它以开放式的结构叙述了三个家庭的四个人物,他们都各自以自己为中心,背负着各自的过往与隐痛,交错共生,相互进入视野,然后所有的故事都终结在同一事件上。主人公们从不同方向走来,故事犹如一把扇子扇形地展开,而结尾则归拢为一个联结点。[13]诚然,这种扇形的结构蕴含着诸多可能性,作为结尾的联结点并非是终点,也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可能突然复活,经由他们的视线重新出发,那么,世界将是另一副模样。结尾不再只是一个寻求与开篇相对应的故事结局,不再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确定性意义,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萌生并包孕着各种可能性。
如果一位作家只是局限于自我满足的冥思苦想,那么,他势必无法有效应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历史的终结”之后如何保持“历史意识”,如果作家不去探究这一点,那么文学就可能沦为娱乐消遣或谎言。或许,这是个相当普遍的趋势:当代长篇小说不再为故事设想一个封闭式的结尾,而是终于意识到:不仅仅各种作品是未完成的,甚至连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本身也像是一件没有完结的作品,是一件我们不知终究会不会有结局的作品。[14]这样的小说结尾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开放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