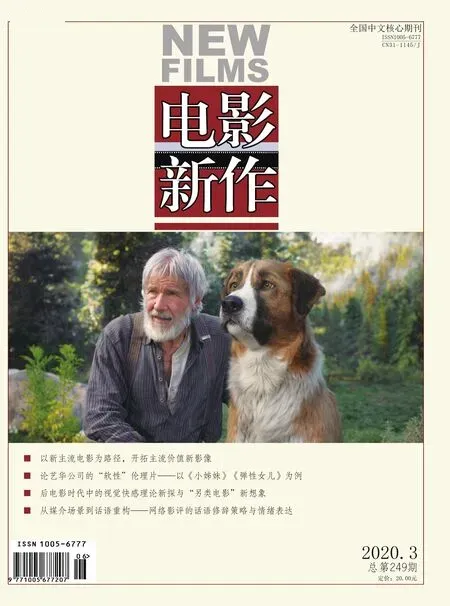《乔乔的异想世界》:喜剧叙事策略下的创伤性历史
李 辉
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获得6项提名的《乔乔的异想世界》最终拿到了最佳剧本改编奖。这是一部由塔伊加·维迪提导演并参与编剧的喜剧电影,剧本改编自新西兰作家克里斯汀·鲁南斯的长篇小说《锁闭的天空》(Caging skies)。电影讲述了希特勒青年团的积极分子乔乔和母亲生活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乔乔偶然在家里发现了被母亲秘密庇护在暗橱中的犹太女孩艾尔莎,在假想出来的“希特勒”的教唆下,乔乔想把艾尔莎逐出家门,但通过与艾尔莎的多次谈判,他逐渐改变了对艾尔莎的看法,并开始对艾尔莎产生好感甚至爱慕。
大屠杀是一个相当庞大和独特的历史话语,在所有表现大屠杀的电影中都必然会面临审美和伦理的两难。《乔乔的异想世界》作为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产物,无疑浸染着以受众为导向的好莱坞商业美学,电影的创作者采用了喜剧电影的叙事策略对原著小说进行了类型化的改编以实现其商业目的。而同时,将沉重的二战和大屠杀历史进行喜剧化的描绘无疑使该电影陷入了历史阐释的道德伦理困境。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的剧本改编获得了代表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奥斯卡金像奖的青睐。笔者认为该电影剧本对原著小说最重要的改编体现在对原著小说视角和叙事风格的双重改写上,对比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与原著小说《锁闭的天空》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我们观察和了解电影创作者在电影叙事效果和历史阐释之间做出的权衡取舍,并便于我们进一步探析使用喜剧电影类型叙事策略叙述创伤性历史事件可能产生的道德伦理难题。
一、战火童心:儿童视角的引入
电影剧本改编是否应该忠于原著是在电影界和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迈克尔·克莱因和吉利安·帕克将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方式分为三种,一是把文学作品转化为电影语言的紧密型改编,二是重新演绎文学故事,但保留故事核心结构的居中型改编,三是仅仅将文学作品视为原材料,只简单借用作品中一个情景的松散型改编。这种分类方式突破了电影改编是否忠于文学原著的单一评价标准,通过观察电影创作者对不同改编方式的选用,对比电影作品与文学原著之间的异同,便于我们了解创作者的主要意图。
塔伊加·维迪提作为该电影的导演和主要编剧之一,在对原著《锁闭的天空》的改编上采取了上述提到的居中型改编策略,即在保留原著故事核心结构的基础上,对小说风格和内容进行了重新演绎,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改编之一体现在对主人公年龄的重置上。在原著小说《锁闭的天空》中,作为第一视角讲述者的主人公约翰尼斯·贝茨勒于1927年出生在维也纳,在小说的故事的主要发生时间,约翰尼斯的年龄为16岁,到故事结尾二战结束时其年龄已满18岁。而在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中,主人公约翰尼斯(乔乔)的年龄被编剧重新设定为10岁。根据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儿童的年龄范围被界定在0到15岁之间,毋庸赘言,儿童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与青少年有着很大的差异,电影创作者通过对主人公年龄的重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著故事的叙述风格和基调。通过电影主人公乔乔之眼,观众获得了一个与原著极为不同的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的选择既关涉到儿童的心理结构,同时也是一个叙事形式的问题。影片中,儿童既是社会现实的观察者,也是控制着影片视听呈现的叙述者。在以往的以儿童为主要叙事视角的电影中,创作者往往会有意识地消除各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判断的影响,力图以纯真无邪的孩童心理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做出与成年人不同的看法和判断,这是由儿童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经验决定的。例如同样是以儿童为叙事视角的二战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2008)中,出生在纳粹军官家庭的8岁男孩布鲁诺始终保持着对现实世界的“无知”,他始终活在成人编织的谎言中,天真的布鲁诺不知道隔壁的农场实际上是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他误以为犹太孩子身上的囚衣是条纹睡衣,影片的最后他穿上犹太人的囚衣混入集中营,最终死在用来杀害犹太人的毒气室。电影创作者选择用一种游戏的方式来呈现这场悲剧,透过布鲁诺纯真的视觉和心灵,观众获得了一个纯真的儿童视角去观察和体悟这段非常历史时期的现实悲剧。而相比布鲁诺对战争和政治的无知,《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主人公约翰尼斯在影片开始就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在电影中编剧给了他一个更具童趣的昵称——乔乔。电影伊始,乔乔穿着带有法西斯标志的军装站在镜子前用稚嫩的嗓音一本正经地对着镜像宣誓,表达对纳粹德国的忠心,随后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成年的纳粹军官的人物形象,这是乔乔想象出来的纳粹元首,“希特勒”由导演塔伊加·维迪提亲自出演,他留着希特勒标志性的发型和胡须,但这位“希特勒”的表情、动作和台词却十分滑稽可笑,与以往希特勒的银幕形象形成极大的反差。“希特勒”用令人夸张的身体动作和极具煽动性的台词给缺乏自信的乔乔加油打气,受到鼓励的乔乔进入了非常狂热和亢奋的状态。在训练营里,乔乔因为不敢动手杀害一只兔子而被青年团其他营员嘲笑和排斥,“希特勒”安慰了乔乔,并建议乔乔做一只狡猾而又勇敢的兔子,再次受到鼓励的乔乔勇敢地抢过克伦森多夫上校手中的手榴弹向空中抛去,手榴弹却尴尬地撞在树干上并反弹回地面炸伤倒乔乔。影片至此,电影的叙事视角和风格已基本得到呈现,观众接受了这个被糖衣包裹的纯真可爱的儿童视角,并由此进入到纳粹儿童乔乔异想中的世界。

图1.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二、类型叙事:风格化的喜剧策略
《乔乔的异想世界》作为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产物,无疑浸染了以受众为导向的好莱坞商业美学,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电影中类型电影叙事手法的运用。类型化叙事是电影创作者和观众在长期的互动、沟通和反馈的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性生产系统,可以将其视作一种集体的文化表达形式,深入分析类型电影的叙事策略,是我们了解电影创作者、电影观众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有力途径。《乔乔的异想世界》的类型化叙事涉及对原著小说《锁闭的天空》的另一重要改写,电影创作者将原本沉重、黑暗的小说文本进行了喜剧电影叙事的程式化改编,使电影呈现出标准的好莱坞类型喜剧的形态。
从故事的情节结构上看,轻松幽默的基调贯穿了电影的整条故事线。在结构上,编剧给《乔乔的异想世界》设置了一个好莱坞合家欢式的大团圆结局,从而根本上改变了原著的故事走向。在影片的最后,纳粹战败,盟军占领了德国,乔乔向艾尔莎表达爱意后将她带出了囚禁她已久的房子,两人在自由的空气中开始快乐地舞蹈。而在原著小说中,约翰尼斯在战争结束后不仅没有帮助艾尔莎逃脱,还谎称赢了战争,由此又将艾尔莎囚禁了四年之久,艾尔莎发现真相离开以后,约翰尼斯陷入了极度的纠结和痛苦之中。电影剧本对结局的有意修改从根本上改变了故事的性质,使一个原本沉重复杂的悲剧故事摇身变成了一部轻松愉快的合家欢喜剧。在情节表现上,影片对战争采取了侧面的表现形式,战争在人物的口中成为无害的调侃,通过简单的台词,观众了解到战争的进展。在影片唯一的一场正面表现战争场景的段落中,导演对视听语言进行了风格化的处理,伴随着宗教色彩的音乐,升格镜头随着乔乔的视线缓缓移动,大人和孩子拿着武器激昂地抵抗盟军的入侵,一个全景镜头,上尉克伦森多夫和下级军官芬克尔穿着他们自己设计的色彩鲜艳的制服威风地站在画面中央,上尉向前方开枪进攻时不忘回头给了乔乔一个俏皮的微笑。随后镜头跟随乔乔目睹了成为废墟的城市和四处散落的尸体,盟军的坦克开进城市结束了战争。在风格化的镜头语言下,战争似乎成了一场浪漫而悲壮的舞台剧,对残酷场景的回避确保了影片轻松基调的连续性。
从人物塑造来看,《乔乔的异想世界》将影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泛喜剧化。演员的表演风格是电影人物形象塑造最直接和关键的因素,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大多采用了一种夸张且带有神经质的戏剧化表演风格。如前文所述,电影创作者通过对主人公乔乔的年龄的重置,为影片建构了一个充满童趣的儿童视角,也塑造出一个可爱的“小大人”人物形象,电影中乔乔用儿童的心智思考着严肃的政治问题,努力模仿着成年人的样态,对现实做出令人捧腹的判断,他的纳粹价值观和单纯善良的儿童本性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罗茜作为乔乔的母亲在影片中发挥了导师的作用,她小心守护着乔乔内心深处的善良单纯,并以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个俏皮可爱的单身母亲形象。在一场餐桌戏上,喝了酒的罗茜穿上乔乔父亲的军装,并在脸上抹了一把黑色的炉灰,她用父亲的口吻教育乔乔要照顾好妈妈。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在成年纳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添加了不少滑稽的喜剧元素,导演塔伊加·维迪提亲自出演的“希特勒”是乔乔想象出来的盟友,他会突然出现在乔乔身边,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古怪的表情和荒诞的台词教唆、鼓励乔乔。纳粹上尉克伦森多夫除了表现出滑稽可笑的表演风格,还两次帮助乔乔脱离危机,展示出人性善良的一面。
此外,《乔乔的异想世界》的美术、配乐和剪辑等视听语言要素无一不呈现出喜剧类型电影的风格特征。影片正是在这样一个喜剧的叙事策略下讲述了一段毫无喜剧色彩的悲痛历史。
三、道德置疑:美学化的历史创伤
如上文所述,《乔乔的异想世界》是一部以儿童为视角的喜剧电影,在形式上它具备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全部特征。回到内容本身,影片的故事建立在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实行集体迫害的历史背景上,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实行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动是全人类的创伤性经验,其残酷的屠杀特性和对现代文明的极端否定使历史学家常将其描述为历史意义的“黑洞”,如何对这段极端特殊和悲痛的历史进行合理的阐述始终是困扰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创作者的难题。
德国历史哲学家约恩·吕森认为历史化是一种普遍传播的文化策略,用以克服创伤性经验的令人大受刺激的后果,在他的著作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历史就是创伤性经验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当人们开始讲述历史,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一刻,就跨出了将破坏性事件融入对世界的理解和对自我理解的第一步,在这个事件获得“历史”意义的时刻,它的创伤性特征也就随之消失了。吕森认为,这一通过历史化消除创伤性质的过程,可以通过将创伤性事件放入历史背景的各种不同策略来完成,他将这些策略归纳为匿名化、分类化、普通化、道德化、美学化、目的论化、理论化和特殊化。
根据约恩·吕森的理论,用电影表现大屠杀历史属于美学化的消除创伤策略,在电影美学的处理下,大屠杀变得直观而生动,它的意义能被人们掌握。吕森以罗伯特·贝尼尼的电影《美丽人生》为例,批评该电影用闹剧的形式和一个动人的家庭故事使创伤不再令人精神错乱。在《美丽人生》中,导演贝尼尼饰演的圭多和儿子乔舒亚被送进纳粹集中营后,圭多将他们的遭遇编造出一个虚拟的游戏谎言来保护了乔舒亚的童心,影片最后圭多在寻找妻子多拉时被纳粹残忍地击毙,乔舒亚和母亲多拉在盟军解救后团聚。相比《美丽人生》对残忍历史的局部修饰,《乔乔的异想世界》对历史创伤的修复和消除显然更进了一步,其美学化策略也更为明显直观。在观赏《美丽人生》时,观众尚可直接地感受到纳粹的残忍,进而无保留地投入到对受害者的同情中,而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纳粹儿童乔乔相较犹太女孩艾尔莎更像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弱者,影片中的其他纳粹形象也纷纷展示出滑稽、善良和迫不得已的性格特征,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受害者(犹太人)和施害者(德国纳粹)之间的对立被模糊化处理,二者一同成为观众移情的对象。如果说《美丽人生》是一部以悲剧为内核的喜剧电影,那么《乔乔的异想世界》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好莱坞合家欢喜剧。
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二战和大屠杀的历史再一次经由好莱坞商业美学的包装,转化成为一种可被现代大众流行文化所消费的商业元素。影片用喜剧电影的叙事手法抚慰了沉重的历史创伤,在“普世价值观”的修饰下,历史的悲痛和恐怖成功匿名化,战争和大屠杀成了可被轻松理解和接受的情节元素,在对悲痛历史的美学化阐释的光滑表面下,观众难以获知二战和大屠杀历史中的破坏性事实。
如福柯所言,电影允许拥有一种与历史的关系,创建一种历史的存在模式,电影的历史效果与我们通过记载所了解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乔乔的异想世界》的喜剧的叙事策略与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残酷性之间产生的冲突使影片陷入了伦理的危机。电影叙事中的历史意识影响和重塑着人类的回忆,我们应警惕电影的历史阐释效果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思考电影在叙述创伤性历史事件时可能会面临的道德伦理困境对今后的影视创作者无疑具有警示意义。
【注释】
①李洋.大屠杀的目光伦理——西方电影的大屠杀话语及其困境[J].电影艺术,2009(04):52-60.
②[美]约翰·M·德斯蒙德,彼得·霍克斯.改编的艺术:从文学到电影[M],李升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4.
③[德]约恩·吕森. 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162-168.
④ 同3.
⑤ [法]米歇尔·福柯.声名狼藉的生活:福柯文选Ⅰ[M],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