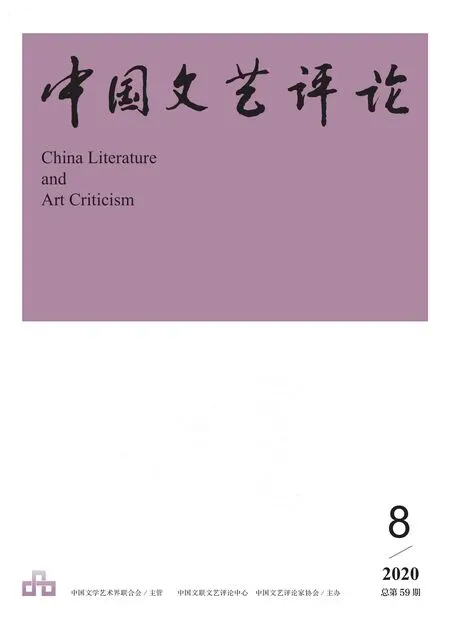中华美育精神在文明碰撞中的“再创造”
王 杰 高晓芳
2020年开年以来,人类社会遇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重大的社会事件,这就是从2019年底开始暴发,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正在成为世界现代史上一个重要“拐点”。此次重大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危机,包括认同危机、信任危机等共同凸显了当代社会的一个严重悖论:在全球化已经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全人类经济、文化、医疗等方面都呈现出高度的合作和一体化;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越来越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与深入的交流。当代人之间的信任的缺失以及如何重建这种信任的基础,成为了当代人文学科以及美学关注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现实的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努力从社会和文化的不同方面打破现代性的悖论,就格外引人注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该切实有效地“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在新修订的《教育法》中也增加了对美育的要求,把美育提升到与德智体相同的地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对美育工作进行部署和论述。[2]《十八大以来新发展新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在理论的意义上,自启蒙主义以来,欧洲的美学就研究且论证了人类审美认同的共同基础,在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和德国古典美学那里,审美教育是资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重要内容。[1]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导言》,王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0世纪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共同文化的建设及其基础也在雷蒙德·威廉斯、理查·霍加特等人文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论述。在近现代美学的理论框架中,审美教育的基础是审美交流,而审美交流的基础是审美认同。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域里,美育问题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也是一个主体再生产的问题。一方面,审美教育是一个通过个体的提升来达到与社会相认同的过程;另一方面,审美教育又是唤起个体的文化解放和促进人格升华的一个过程。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建设,一方面要建立文化共同体以促进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审美活动指涉着自由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审美教育的辩证特征决定着审美教育的复杂性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环。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基础,从中华美育精神传统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再创造的角度出发,阐述中华美育精神的基本内涵、在当代艺术中的呈现,论证当代社会生活中审美革命出现的可能性,从而论证当代中国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功能及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华文明的美育精神
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在货币和资本出现之前,人类不存在自我中的自恋现象。在西方,随着私有制、一神教和货币的出现,在中国,则是随着井田制的废除、西周战乱纷争之后,利他主义倾向和以血缘、自然为本的生活方式土崩瓦解了。然而,中西文明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天人合一” “礼化成人”这个思想观念在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家张光直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将中华文明表述为建立在“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基础上的一种连续性的文明,与西方文明建立在“破裂的宇宙形成论”基础上,作为一种人类与自然资源分割的“由生产技术革命与以贸易形式输入新的资源这种方式积蓄起来的财富为基础而建造起来的”[2][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静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8-118页。文明不同:
……中国的形态是个例外……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这种宇由观在中国古代存在的特殊重要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明在它的基础之上与在它的界限之内建立起来这件事实。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3]同上。
李泽厚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从实用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即一种审美的抒情性的乐感文化情结,与西方追求的“圣爱”和“酒神精神”不同,中国文化把人的情感、观念和仪式,中和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俗和现实生活中,从而避免主体与社会的断裂,即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中华文明在它的早期阶段,就有对审美认同及审美教育的认识和阐发。从《尚书》舜典篇、《道德经》、《乐论》、《乐记》、《论语》,到孔子编撰的《诗经》,都呈现了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特性,用现代美学术语表述,即把具有完整性的审美经验作为个人和社会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境界,从主体层面,追求一种“天人合一”式的境界;在社会层面则有儒家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桃源式社会理想以及当代社会的乡愁乌托邦。“从先秦到两汉,中国美育思想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就是礼乐教化。因此,中国美育思想产生的根本标志是礼乐教化观念的自觉。”[1]曾繁仁:《中国美育思想通史·总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中国文学艺术的表现方式与西方追求接近宗教的“净化”效果不同,在中华文明中,一方面诉诸于感官愉悦及个体情感的抒发,同时重视审美效果上性、情、理的统一,强调文学艺术的道德教化功能。
正如拉康和罗蒂等当代哲学家所指出的,西方文化自柏拉图以降,美本身被推向无限遥远的幻象性存在之后,欲望表达的目标与具体形象的关系因此断裂,分裂为两种相互矛盾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现实与理想、感性与理性相矛盾的“喀索斯式”[2]对“喀索斯式”文化的阐释参见王杰:《中国审美经验的理论阐释与文艺美学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02-108页。的文化。这是一种以主客体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文化。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的核心结构在“轴心时代”以来并没有走向二元对立,而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哲学和文化。我们认为,如果说以“两希”文明为基础的欧洲文化是一种“喀索斯式”的文化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也许可以概括为“艾科式的”。艾科(Echo)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回声女神”。以回旋性和缠绕为基础的文化更接近中国古典文化中怀柔守拙的传统以及对“韵”的审美表达机制的强调。在中国文化中,“韵”是古典美学的范畴之一。对“韵”的论述见于中国古代的乐论、诗论、画论以及书论之中,甚至在人物品藻之中。《文心雕龙·声律》中刘勰将其阐述为:“异音相从谓之和, 同声相应谓之韵”。在宋代以后,“韵”逐渐成为一个美学范畴,苏轼、黄庭坚、司空图、严羽等人均有论述。
作为审美范畴的“韵”,其内涵是多层次、多结构的。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即 “有余之韵”,审美对象有余意,余意既藏于内又发于外,既曲尽法度又妙在法度之外;处于中间的层次即“诸妙之韵”,审美对象具备某一方面的特长的余意,且能淡而有味,大巧若拙;最高层次的“妙”则是“众妙之韵”,是指审美对象“包括众妙,经纬万善”,令人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蕴含着深远无穷的意味,与“道”接近。[3]对“韵”历史流变和内涵分析,参见彭会资:《古典美学范畴“韵”的破译》,《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4期,第67-73页。近代学者宗白华将“韵”解释为艺术形式中“潜伏的”音乐感[1]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强调这种音乐感存在于诸多艺术体裁之中;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将“韵”解释为:“取之象外,得于言表(to overhear the understood)……曰取之象外,曰略于形色,曰隐,曰含蓄,曰景外之景,曰余音异味,说横说竖,百虑一致”[2]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33页。,则着重于“韵”的“象”外之意。直至当代,周来祥、孙玄常等人也对“韵”做过进一步的阐发。在《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一书中,笔者曾将“韵”的学理根据梳理为“和谐”和“远出”,通过声音的远出而达到和谐,“这种远出是一种回旋的声音,即所谓余音绕梁,它以交感式的欲望表达方式为基础,把感性的存在转变为具有灵性的对象”;这种“回旋、远出”通过交感、想象力、声像的优势超越时间,用“一唱三叹”的程式,“缠绕意识形态镜像的核心隐喻,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难给予想象性的解决”[3]对“余韵”的阐释参见王杰:《审美幻想研究——现代美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综合来说,“余韵”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指代的是一种超越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循环往复式的审美表达机制,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尤其是在“中国式”悲剧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哀而不伤”“意在象外”的美学风格,其精神实质从社会的层面上来看,是一种对“过去”和“传统”的怀旧与融合,在个体层面则是以自身的审美习性对苦难或绝望在感知的同时不断净化,从而达到一种指向无限的审美思维方式。
由此,我们认为,如果说欧洲文化是一种以一神教文化为基础的自恋式,以视觉性隐喻为基础、以内卷型为特征的文化,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以礼乐文化为基础的他恋式,以音乐式表达机制为基础、以外播型为特征的文化。中华文明将审美经验和艺术体验置于文化的核心位置,使得这种文化呈现出丰富性、流动性以及在不同语境中“随物赋形”的文化机制。借用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内卷型文化”和“外播型文化”的术语,我们认为可以将宗教作为最重要的认同和表述手段的文化称为“内卷文化”,而将以艺术和审美作为最重要的认同和表述手段的文化称为“外播文化”。与前者相比,“外播文化”因为较少受到宗教中关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划分的影响,没有将神圣性与世俗性对立起来,从而具有更大的可交流性和包容性,同时仍然保留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和批判。我们认为,中华文明一直是以审美经验的完整性为基础的文明,强调人生和审美的完整性,而这一点,正是审美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欧洲文化传统中,审美教育是与启蒙主义哲学相联系的。在17世纪的英国经验论美学和18世纪的德国古典美学中,审美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被提出来。德国文学家和美学家席勒从18世纪末德国的社会现状出发,把审美教育与培育完整人性和理想公民的目标联系起来,将人性分为“感性的人”“理性的人”和“审美的人”,即自然的人、道德的人和自由的人。席勒认为美是拯救现实人性异化的唯一手段。[1]参见[德]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我们认为,在席勒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虽然在他的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美育”这个概念,但关于艺术及审美与人类解放的内在联系,以及一种人类的共同文化或者说关于共产主义理念的论证,正是马克思一生中研究和阐释的基本主题。早在1844年春夏之际于巴黎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就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提到了对人性、友谊、信任、爱情的理解: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马克思在工业化文明的条件下,在一种不同于席勒美学的意义上,重新提出并且思考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的悲剧性就是造成了人的严重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断裂,造成了人类对爱、同情和信任能力的丧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大工业的发展,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一种新的以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以共产主义的理念为基础的人类的社会模式和共同文化呼之欲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这种人类的共同文化,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文化的某种断裂式的否定为前提的,是一种能够表征出人类的共同性,表征出人类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生活和审美的经验层面上能够达到一种共识或者说共享的人生经验的基础上的共同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和剩余价值的发现表明,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种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优越的社会形态是有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比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深刻和冷静的地方就在于,他明确地意识到,在历史条件尚不足以实现这种更美好的人类社会之前,用悲剧性艺术的形式,可以通过感性的和朴素的形式,表达出“最现代的思想”。在1859年4月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写道:
……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而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市民的统一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二、中华美育精神的现代化再创造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传统在前工业化社会阶段曾经十分辉煌,但是都没有主动迈进现代化的门槛。我们认为,在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中华文明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甲午战争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1]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脱亚入欧”,实现了近代化。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虽然在形而下的层面有所进步,但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中古时期。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同时使得中华文化原有的自身发展逻辑和轨道受到了颠覆性的解构。因此,重塑中国文化的脊梁,重新形成中华文化富有凝聚力、可以支撑现代化的强大冲击的文化内核成为了“甲午战争”之后先贤和人们思考的重点。正如聂振斌所言:“人们的认识,总是由浅到深,人们的眼光总是先见到形、质的力量(如机器、技术、制度),然后才认识到无形的精神力量(如人心、国民性、观念、理想)。随着前一种认识,‘西学东渐’主要是应用科学和政治、法律;随着后一种认识,‘西学东渐’主要是哲学、美学、文艺和理论科学。中国近代美学美育思想正是在后一个认识过程中诞生的。”[2]聂振斌:《中国美学思想述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9-320页。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蔡元培是第一个把审美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力量来思考和认识的思想家。蔡元培在继承中国“礼乐教化”及“诗教”“乐教”的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康德与席勒的美学理论,明确提出了美育理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设计了一种以美学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蔡元培写道:“夫人类共同之鹄的,为今日所堪公认者,不外乎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性,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性之良药也。”[3]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6页。故“感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4]同上,第70页。在“五四”运动前后,除蔡元培之外,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人皆有关于审美教育的相关阐述,而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美育思想家一般都把美育作为情感陶养的工具,认为美育之宗旨在于立人,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并且均接受了康德的知、情、意三分之说和审美无利害关系说,并在此基础上阐述自己对美与美育的看法。……王国维的美育观比较侧重于个体人格完善的角度,而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则更倾向于审美效应的社会指向,着眼于群治和国民性的改造。”[1]谭好哲:《语境意识与美学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借助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批判锋芒来改造社会的设想,蔡元培所设想的“以美育代宗教”来匡正时弊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回应,这是十分遗憾的。
应该明确的是,审美不等同于艺术。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中辨析的:Aesthetic(美的,审美的、美学)的源义为感官的察觉,其意涵强调人的主观认知是艺术与美的基石;而Art(艺术、技艺)源义为技艺,“艺术作品实际上被视为商品,且大部分艺术家被视为是属于独立自主的工匠或技术人员的范畴,可以生产出某种非主流的商品”[2][英]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66页。。审美教育也不等同于艺术教育,审美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以培育自由人性为旨归。而艺术教育则偏向于形式和某种功利性价值的传播,而丧失了审美教育的重要灵魂——人的解放即审美经验的完整性。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自由”是现实的、充盈的,在人和社会的充分发展之后个人或人类才能获得的自由,而形式上的自由则是空洞而乏力的。我们认为,“五四”以来中国审美教育的偏差跟康德美学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它把艺术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割裂开来而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需求。中国传统式的美育思想中艺术与现实虽不是对立的,但礼乐文化只针对士大夫与上流阶层,缺少现代文明式、属于人民大众的审美愉悦。而从康德到席勒,及至受其影响的近代中国的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美育理论,在历史哲学上是悲观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艺术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之间是一种类似于“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从审美效果上达到真正的主体与历史、现实、社会的和谐,即一种日常经验与审美经验上的全面而自由的融合。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通过审美获得自由和解放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3]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6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4]同上,第7页。在现代社会治理的框架内,文艺与美育必然是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共通的。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指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拒绝千禧年主义的躁动,都认为潜在的狂热精力必须通过文化理想进行升华”[5][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84-285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与真正解放是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一方面是社会化的合作性的大生产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另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业化文明中,包括后工业文明和文化经济时代,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都是人类扬弃异化、实现解放的一个途径: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186页。
马克思关于哲学最重要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华文化的信仰和信念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塑,或者说中华文明面向现代社会的再创造,是中国的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核心任务,也是美学学科的核心任务。按照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是结构性的,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与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在一种生产方式的自我发展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也就是说,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2]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随着生产方式的更迭,社会和意识形态,包括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审美制度都会发生断裂式地飞跃。这种飞跃在现代观念中也被称之为“革命”。在当代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审美的革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命题。
三、审美的革命与当代艺术创作
审美革命的理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事实证明,通过审美的方式改变世界不再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我们认为,实质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十分典型的后发展模式和非欧洲模式。这种模式的特殊机制的出现不是隐藏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中,而是深藏在文化特别是艺术和审美的情感结构中,这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审美现代性形成的基础。从学理上说,美学革命植根于德国美学的一种理论传统,从康德到席勒,再到马克思。在这一传统中,马克思与康德、席勒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马克思把人性的本质与乌托邦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特别是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审美启蒙和审美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它表述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而康德和席勒则是把“美”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相联系。
1795年,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把“自由冲动”作为游戏的理论内涵,在游戏活动中,人类把艺术形式的完美与现实生活中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联合起来,人类在游戏以及类似于游戏的活动中才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15封信中,席勒提出了以下影响深远的观点:
1. 美不仅是生命,也不只是形式,而是生活形式,即美。
2. 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感受到美,只有感受到美,才能自由游戏。
3. 人只有处在人类这个词的充分意义上的时候才能自由游戏,而只有当他游戏时,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1][德]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3-290页。
在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里,美学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与席勒不同的地方在于,席勒努力通过审美教育来改变人,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改造,马克思则从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思考和论证美学问题。在马克思的视域里,审美活动是人类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重要基础,对于社会进步而言,美是一种重要的力量,而不是一个乌托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和文化条件下,马克思的思想是更为重要、也更为本体性的。在《审美的革命与20世纪先锋运动》一书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提出并论证了一个重要的观点:20世纪存在着一种从特定的艺术经验拓展到广泛的、整体的生存领域和想象经验,蕴含在社会、政治、身体、技术等诸多维度内的先锋艺术,存在于全球现代性的后现代艺术之间的中间地带,在地缘上,主要出现在东欧、拉丁美洲、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3]对第三种形态的先锋派的分析,参见Ales Erjavec:Aesthetic Revolu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Avant-Garde Movements,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don, 2015.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审美经验和“美的规律”一直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文化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源一方面来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十分悲壮的现实,另一方面来自中华美学精神十分强有力的文化基因。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出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自己的先锋派。我们认为,延安时期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系列文艺作品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先锋派,不仅充满了民族激情和革命英雄主义,而且在艺术上有着大胆的形式创新,以富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直接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情感,是另一种形式的“先锋派”,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初期“审美革命”的经典。[1]对延安时期文学艺术的阐述,参见王杰、王真:《中国悲剧人文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当代意义——为纪念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创作80周年而作》,《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36-45页、第175页。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2]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全文)》,2014年3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28/c_119982831_2.htm。。在当代进入“文化经济时代”的背景下,新媒介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文艺创作和美学在滑向“市场化”“平面化”的同时,愈加“大众化”“时尚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共生,文艺由曾经少数人的闭门游戏变成了大众共同创作、共同传播的精神产品,审美乌托邦的出现成为可能。由此,中华文明及民族精神如何介入到当代中国艺术的“再创造”和美学批评的思想中去,成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发展,对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格局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在疫情这一悲剧性事件发生的同时,艺术创作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激发出人们巨大的创造力。我们高兴地看到,2020年5月5日在湖北武汉“解封”的前一天,中国音乐家谭盾创作的《武汉十二锣》由美国、中国等十几个国家的上千名艺术家同时演奏,音乐所产生的强大情感力量成为鼓舞人民、团结人民战胜疫情和由此引发的各种次生危害的强大力量。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平台发布的“DOU艺计划”,在疫情期间号召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用短视频进行艺术创作、艺术记录和艺术传播,以释放正能量、抚慰大众情绪、振奋抗疫精神。与此同时,自1月27日起,上海、四川、河南、内蒙、重庆、广东、安徽、湖南等地方文艺界联合抖音发起了“艺起战疫”系列话题,带动网友以短视频形式展示学习成果,截至3月27日该系列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22亿。此外,疫情发生以来,抖音艺术直播课堂已举办超5000场次,近1000位艺术家在抖音直播艺术教学,直播时长超过6000小时,直播观看达2037.9万人次[3]相关数据参见抖音APP#艺起战疫#等系列话题实时数据。;并特别推出“方舱直播时间”,将艺术家们的抖音、头条直播课堂搬进湖北各方舱医院,在不影响医护工作的前提下,通过直播、短视频、图文展示等形式,用艺术帮助医护人员和患者保持乐观心态,提振与病魔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这里,审美活动、艺术创作和审美交流无疑已经成为“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这决不是席勒的“审美教育”概念和“游戏冲动”概念所能够解释的。高尔基曾经说过“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人们情感结构中的强烈情感驱动力,这是一种具有本土色彩和丰富内涵的乌托邦冲动,我们相信,其中的强大情感力量会通过不同的形式转化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