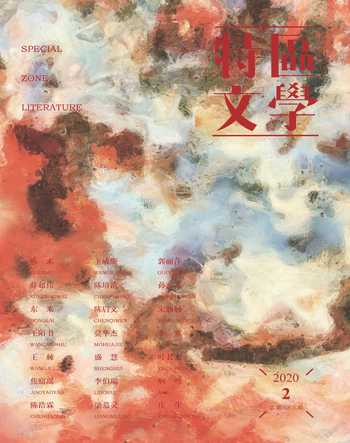敦煌的月亮
歌舞正演到热闹处。月亮上
霜白又加了一层
怀揣银色的锣鼓,敦煌沉入水底
风沙在其中辗转迁移
沉默的供养人走到门口,看看天色
发下了第一个誓愿
月亮從未反悔,从未松开
咬紧的耳边清凉
马蹄声穿过天宇的洞口
落入人间
那些提灯的头颅,
有的无声行走,有的手捧烛火,
正上到高高的树梢
徐敬亚:诗一旦写出,立刻成为活体
2018年10月,在安徽繁昌县长江南岸的新港镇,一位年轻人送给我一部诗集《分身术》,这首诗从那么多页码中突然跳出来。粗粗一阅,感觉相当不错:敦煌的月夜,景色清朗,词语都选得素气,一个个位置也安放得十分安稳。
不错啊,在这荒凉的大江之畔,能读到一首安稳之诗。
前两节的6行,甚至可以说写得十分飘逸—“怀揣银色的锣鼓,敦煌沉入水底”,天地交映,沉静而矜持,有大诗之气!往下,风沙迁移也可以。再往下,出现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场景:“供养人”发下“誓愿”—注意:在这两个意象前诗人加了“沉默”与“第一个”的修饰。这两行立刻成为全诗的重心,即诗意内核出现了。
在这里,我要突然停住。
我想说:诗一旦由人写出,那些词语组合,立刻成为一种活体!即语言组合一旦产生了新的意义,新意义中便立刻涌出了新的逻辑、新的线索与情绪。这些逻辑、线索、情绪,会使诗暗中产生某种类似生命力的方向。这种新生命的胚胎里,还包括语感—每个字的色彩、强弱,甚至形态,字与字之间的关联、节奏,都会立刻变成一种暗中的秩序命令,要求诗人予以遵从或相向变异。
以更高的标准,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变弱了。语感明显由沉稳、安谧,变为急顿、明快(全诗的最后一句语感稍稍回缓)。
从诗意延展上看,月亮与誓愿之间,很难形成对应的关系。“从未松开……清凉”,是月亮咬着耳朵清凉地叮嘱么?“马蹄声……穿过……落入……”,是以马蹄声暗喻向人间传达某种意愿么?最后一节“那些提灯的头颅”,是眼前的月下人影么?是死去的鬼魂般的前一代供养人么?总之语焉不详。上面两节刚刚形成的诗意胚芽,没有得到延展,而是变得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无所依指。
记忆中的小伙子思不群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样子够聪明的他,或许过于沉溺、受限于某种真实的场景?当日敦煌的一场大型演唱会可能成了他的诗歌陷阱。第一行“歌舞正演到热闹处”和最末行“正上到高高的树梢”或许可为他泄密并作证。
我常常想,一首诗内部的“诗意”演化,简直就是一部小小的历史。它的最初缘起、中间的延展、最后的定形,包括它意外的转折、异化、变奏,甚至还包括它可能存在着的神秘与不可知……既没有定式与规律,又充满着暗中的生命般限定。写出一首无可挑剔的好诗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