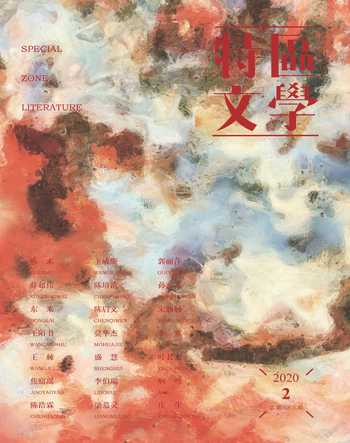世界荒诞如诗
许多年后,我又开始写诗
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在道路
像逻辑一样终结的时候
在可说的道理变成废话的时候
开始写诗,在废话变成
易燃易爆品的时候,在开始动手
开始动家法的时候,在沉默
在夜晚噩梦惊醒的时候
活下去不需寻找真理而诗歌
寻找的是隐喻。即使键盘上
跳出来的词语是阴郁
淫欲,隐语,或连绵阴雨
也不会错到那儿去,因为写诗
不需要引语,也无需逻辑
在辩证法的学徒操练多年之后
强词夺理如世界,就是一首诗
吴投文:面对世界不得不说的生命冲动
一首诗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对称于世界的真相?这对诗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挑战。我们经常指责所谓的“无效写作”,大概就是那种无法呈现世界真相的写作。当然,写作的技艺也非常重要,需要对称于世界的隐形象征结构,也需要契合诗人的才情与个性,恐怕如此才能达到世界真相与语言形式的均衡与对称。
耿占春的这首诗似乎带有以诗论诗的性质,在一首诗的深层内涵中传达出对诗歌本质的某种理解,其聚焦点是诗与世界的关系,诗与生命的关系。也许在他看来,诗是生命的一种焦渴形式,是面对世界不得不说的一种生命冲动。这实际上涉及到对诗与世界的关系的深层理解。为什么“世界荒诞如诗”?显然,这并不符合一般读者对诗歌作为艺术的惯常理解。此诗的开头颇有意味,诗人“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在可说的道理变成废话的时候”,重新开始写诗,可谓不合时宜,而这正是一位诗人所面临的真实处境,也是一位诗人内在的生命驱动。现实的荒诞不是诗人逃避的理由,反而恰恰是诗人介入时代与现实的职责所在。可能诗人的天真也正在这里,不计利害得失,与现实短兵相接,在荒誕中呈现出生存的真相。诗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这是一种近乎本能性的怀疑。世界的确定性被重新质疑,荒诞作为生存的一种普遍形式,被归位到“介入诗学”的视野中。
此诗在写法上是反逻辑的,或者说,诗人力图揭示出一种符合诗的本质的逻辑。在此,诗人之为诗人,是在看似无懈可击的惯常逻辑中发现荒诞的实质,“强词夺理如世界,就是一首诗”。大体说来,此诗是从荒诞中发现另一首诗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作为诗歌理论家的耿占春反思当代诗歌写作带来的一个结果。然而,此诗完全不是某种理论的图解,而是一位诗人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诗的基调沉郁悲慨,呈现出一种刚硬的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