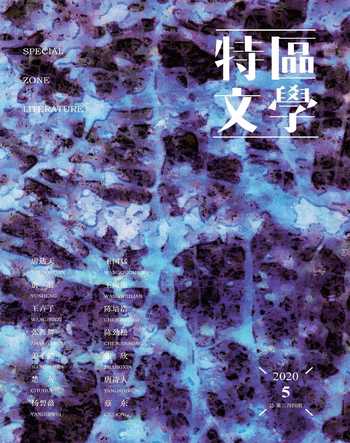新经典导读
母亲的火葬场
母亲缓缓出来了
腓骨
胫骨
膑骨
……
骶骨
肱骨
胸骨
……
最后是头盖骨
它们全是白色的
我望向曾经孕育了我的位置
那里空无一物
空得晃眼
也许那是我母亲身上
最先焚化的部分
甚至早于我放在她遗体上的花束
徐江:湮没與激活
亲情的诗最难写。尤其是写给亡故的亲人,尤其是写给母亲。古诗也好,当代先锋诗也好,都是一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话反过来说,写亲情太容易了,尤其是写给去世父母,“眼泪哗哗的”,比那些电视小品里看得还过分,这种语言和情绪双重泛滥的情形,独属于汉语新诗,为世界诗歌所绝无仅有。
为什么母亲最难写?因为子女和母亲的关系最复杂。尤其开始进入成人期以后的儿女。不再仅仅是依恋、依赖。有挣脱,有生命个体各自对时代、生命的不同认知、读解(如果是母女,可能还要加上一些相互间的挑剔)。短短的一首诗,如何能承载这样的重量?
中华文化的源流中,亲情伦理对人的影响力,远大于宗教及其它后天型信仰,这是独特的一个存在。父母离去,对儿女犹如山崩,新诗简单,民俗一般地哭天抢地,在词语的海洋中痛嚎宣泄一下,别人读了头大,自己表演一下过过瘾,任务就算完成了。现代诗则不然,一方面,它无法像处理其它题材那样始终保持“零度”式的冷凝状态;另一方面,那种对生活真实的忠实,使得作者既要面对那种“至亲离世后的语塞”状态,却又不得不直面“生命的短暂与长存”这一矛盾关系的撞击。
《母亲的火葬场》便带有上述明显的现代诗特征。通过刺目视角场景所运载的悲伤到极处的绝望,带出的是对“我们生命的来处”消失后的震惊与巨大惶惑—“我望向曾经孕育了我的位置/那里空无一物/空得晃眼”。是啊,亲人、来路已无,人生的漫漫长路上,生者何其孤单、无助。生命悲伤至此处,同时激活着肉身和灵魂出窍的形而上(却不是那种枯燥的经院式的超验)回看。一首诗由此推进至它的完成部分,告别,然后回归常态智性表述下的叹息……
张小波的诗,素以其想象的多维、思辨的奇崛和语言的穿透性著称。这首诗,则很好地示范出现代诗在极致情绪状态下,是怎样完成表达的。它不是一个技术示范,它是美学和生命体验合一后的激活,这也正是现代诗在汉语中比新诗高明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