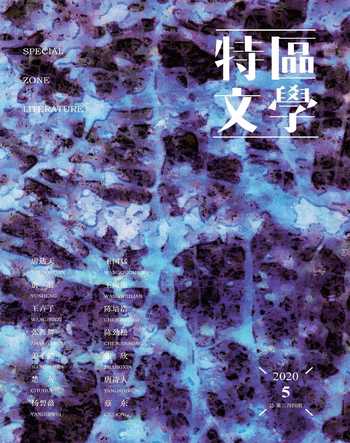壳
姜子健
我坐在甜品店角落的凳子上,等待南秋下班。我还是头一回见她穿工装,老实说,如果她不是我的女朋友,我准不会记住她的样子。原本她要工作到晚上十点,但是今天,她和一位同事—那个她在我面前称为“张大胖”的女孩,我们在一次家庭聚会中见过—调了一下班,再过一个钟头就可以离开。我又看了一眼手表。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块表盘,秒针、分针和时针,在它上面缓慢、有序地旋转。
“你要是不耐烦,可以去其它地方转转。”南秋走过来,递上一块蛋糕,说:“马上就过期了,免费的。”她看上去心情很好,不像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那样垂头丧气。有顾客进来,她走到收银台,微笑,伸手,找钱,“欢迎下次光临”。
蛋糕还不错,至少我吃不出它即将过期。没人进来的时候,她俩就聊天,先是窃窃私语,接着恢复正常的音量。
“你为什么想要养狗呢?要我说,不如生个孩子。”张大胖说。
“这不一样,小孩子会让我失控。”南秋说。
“不管是人,还是一条狗,只要你付出感情,总会有让你受不了的时候。”张大胖朝我瞥了一眼,又在南秋耳边说了点什么,两人笑起来。她又用胳膊碰了一下南秋,说:“你敢承认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吗?”
南秋把目光转向我。她的表情逐渐平复,最后保持着嘴角微微扬起,就那样看着我。我尽力避免与她视线相撞,但是来不及了,我连转动一下眼珠都没法做到。我得说点什么,当我准备开口,突然想起两年前发生在海边的一件小事。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沿着一条漫长的海岸线散步。我们一直在描述各自期待的生活,并且相信它们不再遥远。日落之前,我们在海边遇见一个写生的画家,他请求为南秋画一幅画,她没有拒绝。海浪朝她扑过来,又轻轻退去,沙子埋过她的脚背。她站在那儿,嘴角微微扬起,就那样望着大海,海风从她发丝的缝隙穿过。画作完成后,我招呼她过来。她提议把我也画进去,但是画家构思了好一会儿,发现把我放在哪儿都不像一回事。没过几天,她搬进我租的房子,把那幅画挂在客厅,盯着画中的她,问我:“你猜她在想什么?”
我忘了自己当时的回答,但是现在,当我准备开口,满脑子都是这个问题。
“好啦,快走吧,反正也没什么顾客,”张大胖一个劲地把南秋往外推,笑着说,“你俩待在这,就好像我是多余的。”
“我们要不要给老彭带点甜品?”南秋说。
“太见外了,我跟老彭是什么关系?”我说。
她走进更衣室,换上一条红色碎花裙,戴着红色渔夫帽,几乎是跳着出来,在我面前转了一圈。“你觉得大福会喜欢红色吗?”她说。
“你忘啦,狗是色盲,它才不关心这是什么颜色。”我说。
“我才不管它是不是色盲。”她朝张大胖挥挥手,喊道,“明天一早我就来替你的班。”
按照计划,我们先来到一家宠物店。她径直走到狗的零食区域,停留在货架前,详细查看每一件产品,然后问服务员:“请问,一岁的拉布拉多最喜欢吃什么?”服务员介绍了很多关于狗的饮食知识,给出的结论是:每条狗的喜好都不一样。最后,她从进口的那一栏,拿了几款不同口味的鸡肉干和牛肉粒,放进购物篮。我的手从一排价格标签上扫过,这些大约是我们半个月的房租。
“它不可能都喜欢吧?”我说。
“总会有它喜欢的。”她说。
结完账,我又跟着她逛了一圈其它区域,她还想买些漂亮的笼子、食盆、牵引绳和玩具。“这些东西,老彭会全送給我们。”我说。
“这样不太好。”
“有什么不好呢?反正他也用不上了。”
“我是想说,大福的新生活应该有些不一样。我们最好再给它取个新名字。”
“你这是一厢情愿,万一它不习惯呢?你太热情了,会吓着它的。”
离开的时候她没有再买其它东西—她决定明天带着那条狗过来,让它亲自挑选。
我们坐上一辆公交车,去往和老彭约好的地方,一个我们常去的小酒馆。一路上南秋都在念叨,该给那条狗取个什么新名字比较好。我即兴想了几个,她都摇摇头,干脆不再和我讨论。
她掏出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养狗的注意事项),每想到一个名字就写下来。她的头发只够遮住耳朵,一低头就会垂下几束,遮住眼睛。她把它们捋到耳背上。我们刚住在一起时,她还是一头长发,每天至少要花上半个钟头来打理,哪怕不用出门。
有一次我们在超市购买日用品,结账时她想起洗发水又快用完了,就叫我先去排队。轮到我了,她还没有回来。我在洗浴用品那儿找到她,看见她拿着一瓶洗发水,站在那儿发呆。没过几天,她下班回家就变成了短发。我问她为什么要剪短发,她只是笑笑,问我好不好看。
“你还想留长头发吗?”我说。“什么?”她猛地抬头,看着我,先是惊讶,接着笑起来,说,“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没什么。”我说,“一开始我就不应该反对你养狗。”
她第一次提出想养条狗,大约是在半年前,我和老彭出差回来的第二天。关于那次出差,我和老彭后来都没再提起,我也没告诉南秋发生了什么—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小事。
那天一早,我走出地铁口,看见老彭的车停在路边,开着双闪,不停按喇叭。他下车打开后备箱,把我的行李箱塞进去。“看看我带了什么?”他朝我招了一下手。我走过去,是几套钓鱼装备,从鱼竿到太阳伞,整整齐齐。
“走。”他关上后备箱去开车,我坐进副驾座。
“今天晚上先和那帮人吃个饭,饭后应该还会有活动。明天上午我们再约处长去钓鱼,下午开标。钱我也准备好了。”老彭说。
他启动发动机,我们一路向西开去。到了中午,路程只剩下三分之一,我们在一个高速服务站吃完泡面,出来抽烟。“拿下这个项目,咱们今年的日子就好过了。”我说。
老彭慢悠悠吐出一口烟,指着不远处的一条江,说:“你看那儿,应该有鱼。”
“那是沅江。”我说。
“管他妈的什么江,这么好的天气,我们去钓鱼吧。”他说。
我看了一眼手表,说:“就钓到四点吧。”
我们把车子开下高速,停在江边,老彭拿出其中两套钓鱼装备。“这玩意儿要怎么弄?”他举着一根鱼漂在我面前晃动。
“给我。”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好了,你看着鱼漂,动得厉害就迅速提竿。”我说。
我们在那儿待到了四点,鱼漂动都没动一下。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说。
“再等等。”老彭说。
“快!提竿!”我看见老彭的鱼漂沉入水下,大喊道。
他一把抓起鱼竿。鱼竿前面的四节弯成一个半圆,鱼线紧绷,跟着鱼的挣扎左右甩动,发出“嗖嗖”的声音,像是要把水面切开。“让我来。”我拿起抄网,看着有些慌乱的老彭。
“别,这可是我第一次钓鱼。”他喊道。
“那你别急,不要用蛮力,先跟它耗着,慢慢往岸边拉过来。”我说。
“快给我拍照,手机在我屁股兜里。”他说。
手机还没完全从他的裤兜里抽出,就有电话打进来。他一个扭身,手机掉进水里。“别管它,防水的,先用你手机拍。”他说。我抓拍了几张照片,还录了一小段视频。老彭把鱼拖到岸边。是一条草鱼,看样子得有七八斤重。我把鱼扔到岸上,老彭坐在草地上喘气。
“把照片发我,”他想起来手机还在水里,又爬起来去捞。他用衣袖把手机擦干净,点开屏幕,说:“妈的,刚才是处长的电话。”他回拨过去,先是说了“嗯”“好”“明白”这几个词,然后是“您再等一下,我们就快到了”。他放下电话,“哼”了一声,又盯着在草地上扑腾的草鱼。
“标没了。”他重新把手机塞回屁股兜里,穿上饵料,把鱼钩抛出去。
“那我们回家吧。”我说。
“刚才真他妈带劲。”他站在那儿,注视着鱼漂,说,“我还没过瘾呢。”我们一直待到六点钟,总共钓到了三条草鱼、一条鲤鱼和十几条巴掌长的鲫鱼。
“真他妈没白来。”老彭又给鱼拍了几张照片。我们收拾好所有东西,回到车上。我给南秋发了一条信息,告诉她我们已经入住酒店,正准备和领导们去吃饭。她嘱咐我尽量少喝点酒。回去的路上换我开车,老彭躺在后排座位上睡着了。天黑透了。我把车开到他家楼下,叫醒他。
“你急着回家吗?”老彭说。
“回去也没什么事。”我说。
“你会做鱼吗?”老彭问。
我跟着他把鱼提上去。一条黑色的小狗跑过来,冲着我叫个不停。老彭蹲下来,抚摸着那条狗的脑袋,温柔地说:“大福,别叫。”它趴在地上,不再出声。
老彭家的厨房比我那儿客厅还要大,我花了不少工夫才搞清那些高级玩意儿要怎么使用。我做了一锅鲫鱼汤、一条糖醋鲤鱼和一个剁椒鱼头。老彭打开冰箱,翻找半天,拿出两瓶威士忌。“你应该买个房子的。”老彭说。
“我们就不应该去钓鱼。”我说。
“忘记这件事吧。”他递给我一瓶酒。
“我来告诉你,我们应该忘记什么!我们应该忘记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我们应该忘记公司现在只剩下两个老板和一个员工了!得了,我们干脆忘记这个狗屁公司吧!”我站起身,换好鞋子准备离开。
“你他妈手艺可以啊!”他喝了一口鱼汤,说。
我摔门而出,走到楼下才想起行李箱还在老彭的车上。明天再说吧,我想,现在我需要好好喝一杯。我穿过两条街道,走进一家小酒馆门口,看到里面只有一个身影。
“欢迎光临。”是一个年轻的前台姑娘。我微笑地点了一下头,坐在吧台前的凳子上。我低声念着小黑板上的酒单,又在她身后的酒柜搜寻一番后,指着和老彭家一模一样的威士忌问:“那个多少钱?”她朝着我指的方向拿出那瓶酒,说:“这个吗?一杯两百,一瓶九百八。”我坐下来,掏出钱包里最后的一千块放在吧台上。
“不用找了。”我说。
“加冰吗?”她问。
“加点吧,这鬼天气。”我笑着说。
她打开酒瓶盖,连同一只加了球冰的玻璃杯一同递过来。我几乎没有看清她把钱收起来的动作。
“我以前没见过你。”我说。
“我上班才几天,”她说,“你经常来吗?”
“我和我的合伙人来过几次。今天我们还去沅江钓鱼,”我掏出手机,点开老彭的照片和视频给她看,“你知道沅江吗?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合伙人啊。”她一边擦桌子,一边瞅着我手机上的照片。
南秋打电话过来,我挂断了,回复她一条信息:“老彭睡着了,不方便说话。你早点休息,我明天就回来,晚安。”
“你刚才说什么?”我把手机翻过来,搁在酒瓶旁边,问她。
“我说,看不出来你还是个老板呢!”她说。
“老板有什么稀奇,现在满大街都是,比员工还多。”我喝了一口酒,说,“甚至比垃圾桶还要多。”
“你说得没错,就像我们这个酒馆,两个老板,就我一个员工。听说上一个员工两个月都没发工资,跑了。万恶的资本家。”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我说,“对不起,我不是说你。”
“是吗?这么惨。”我说。
我们沉默了片刻,接着她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就这样,直到我喝完大半瓶威士忌,也没有进来第二个客人。
“你几点下班?”我问。
“早上七点,”她像是在等我开口,一只手拖住下巴,胳膊撑在吧台上,看着我说,“如果下半夜实在没生意,我也可以早点关门。”我点了一下头,继续喝酒。
“你问这个干什么?”她盯着我说。
我指着角落的一张沙发,说:“我可以在那里躺到天亮吗?”
“当然可以,不过你為什么要睡这儿。”她犹豫了一下,说,“楼上就是酒店。”
我喝下最后一口威士忌,摇摇晃晃朝沙发走过去。“要我扶你吗?”她朝我喊了一句。我朝她摆摆手,没有停下来。我摸到沙发就躺倒下去,醒来天已经亮了。我检查了手机、钱包和钥匙,都在身上。我爬起来,看见她趴在吧台上酣睡。我轻轻打开门,走出酒馆。
我在公园消磨到下午,中间吐了两回,酒气散得差不多才回家。我刚插进钥匙转动一下,门就开了,南秋站在门口。我和她拥抱了一下,蹲下身换鞋。
“今天没去上班吗?”我说。
我起身时看见客厅角落的行李箱。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说:“昨晚老彭送来的。”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是该进屋还是出门。
“我想养条狗。”她一字一顿地说。
我列出了很多反对的理由,最重要的是钱,其次是时间和精力,还有一堆诸如掉毛、咬东西、生病的小问题,都被她反驳了。而她坚持的理由,在我看来都有些可笑,其中一条是,我经常出差,她一个人在家会感到害怕。这一点我还能理解,但是关于她的另一个说辞——“你能不能试试,不只当它是一条狗呢”,让我有些恼火。
这之后她又提起过几次,我最终妥协的原因,并不是被她说服,而是我从她的话中受到启发:当她感到糟糕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可不少),有条狗可以代替我去安慰她,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也许我早就该这么做了。不过,现在也不算太晚。
天黑时我们才赶到酒馆。老彭在和前台的姑娘说笑,那条狗被拴在一把椅子上,趴在地上无精打采。我们互相打过招呼,南秋就朝狗跑过去,坐在它身边。“真漂亮。”她说,“我可以摸它吗?”
“当然,大福很温顺,从来不咬人。”老彭说。
南秋掏出一袋牛肉粒,拆开,开始喂那条狗。我和老彭坐在一旁,前台姑娘走过来,问我们喝点什么。我们各自要了一杯啤酒。老彭拿出一个文件袋,说:“养狗许可证、健康证、疫苗证、体检报告,都在里面。”我接过文件袋,没有拆开,放在一旁。他又指着门口的一个大纸箱,说:“它的东西都在那儿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说,“这顿酒我来请。”
老彭朝前台姑娘露出一个微笑,转过头对我说:“大福和我儿子关系很好,要不是我们实在没时间照顾,真希望他们可以一起长大,你知道,狗是有感情的。”南秋在不停地和它说话,小心抚摸着它背上的毛,但它仍然没有站起来,趴在那儿嚼着牛肉粒。
“它看上去好像有些不高兴。”我说。
“当然,我说过了,狗是有感情的,它大概知道今晚会被送走吧。”
“我女朋友很早就想养一条狗了,她也看了很多,一直没有喜欢的,但是她一见到大福的照片,就认定它了。女人的心思啊,反正我是搞不懂。”
“你搞不懂没关系,相信缘分就好了。”他又看了看前台姑娘。
“没错,我们真幸运。”
我和老彭干掉啤酒,又把酒杯满上。我们聊了几句各自的工作,又聊了几句当下的经济形势,然后都扭过头,看着南秋和那条狗玩耍。
“吃太多零食可不好,日子还长着呢。”她又拆开一袋鸡肉条,倒出几根在手掌,它伸过舌头,舔走一根开始咀嚼,脑袋在南秋的裙子上摩擦了几下。她兴奋地叫起来:“你看,我就知道它喜欢红色!”就是这会儿,那条狗跳起来,朝着南秋的脸上咬下一口,狂叫不止。南秋愣在那儿,鼻子上糊了一团血,手里剩下的鸡肉条掉落在地上。我抓起她的胳膊,后退几步。老彭呵斥着那条狗。它重新趴下,舔起地上的鸡肉条嚼起来。
“快,先去卫生间用肥皂洗一下。”老彭有些哆嗦,小声嘀咕着,“它咬过我儿子一次,但那是很久前的事情了。真的太抱歉了。”他又朝那条狗骂了几句。
我在前台要了一块肥皂,递给南秋。她走进卫生间,关上门,接着传出来一阵哭声。
“哥们,太对不住了,虽然狗打过疫苗,但最好还是去一趟医院。”老彭脸色很沉,看着我说,“对了,只能去市传染病医院,那边整个晚上都有人值班。”南秋还在哭,我敲了敲门,她吼出一句:“别进来!”
老彭去前台结完账,回来时手里牵着那条狗,说:“哥们,我先把它带回去,医院要花多少钱,我出。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你也是好心,我怎么可能会怪你。”他点点头,又去和前台姑娘说了几句话,就牵着狗,带上文件袋和门口的大纸箱离开了。我坐在那儿,喝完剩下的啤酒,南秋才从卫生间走出来。她还在抽噎,鼻子两侧的伤口鲜红,不过血已经止住。我叫来一辆出租车,扶她上车,告诉司机去市传染病医院。
“为什么呀?”南秋望着我,和那次我出差回家她看我的眼神一样,一字一顿地说:“它为什么要咬我呀?我那么喜欢它。”我回答不了,只好搂住她的头。她趴在我怀里,又小声哭起来。
“它为什么会咬我?”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安静下来。
“它只是一条狗,怎么会知道你在想什么呢?可能是你太热情,吓到它了。你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说。
她没有说话。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睡着了。司机停下车,指着路边的一条巷子,說:“那里面不好掉头,你们走过去吧,一直走就能看到,只有一百多米。”我叫醒南秋,扶她下车。巷子很窄,有一家面馆还在营业,里面坐满了人。我想起来我们还没吃晚饭,于是问南秋要不要来碗面。
“我不想吃东西,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你饿了就吃点吧。”她说。
我没有停下来,牵着她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还有这么长的路,我快走不动了。”她说。
“再忍忍吧,过完今晚就好了。”我说。
我们走进医院已经十点多。我把南秋扶到椅子上,去给她挂号,回来时发现她靠在那儿睡着了。我在她旁边坐下。大厅里堆满了人,聊着各自的遭遇。大多数人是被狗咬了,也有猫和老鼠,一个女孩说她被自己养的狐狸挠伤。她伸出胳膊向大家展示伤口,看上去和任何动物的抓伤没有区别。有人问她为什么养狐狸,她收起胳膊,得意地说:“好看啊!”
我掏出手机,看到老彭发来的几条信息。我没有打开,只是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背景照片,一张我和南秋的合影。
那天是我们在一起的两周年纪念日,就在上个礼拜。第一年我记得这个日子,还为南秋买了一顶红色的渔夫帽。但是这一次我忘了。晚上她拎着两瓶啤酒回来,说要庆祝一下。我懊恼不已,不停向她道歉。她笑着说:“既然这样,那就罚你做明天的家务吧!”我打开瓶盖,去厨房找酒杯,听到她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们去楼顶吧,外面凉快。”她慢慢吐出那口气,说,“直接拿着瓶喝吧,可以少洗两个杯子。”
天台开阔,风没有方向地吹来。我们举起酒瓶,碰了一下,她一口喝下半瓶。
“你慢着点,明天还要工作呢。”我说。
“去他妈的工作!”她说。
“今天老彭说他想把狗送养出去,我见过那条狗,黑色的,拉布拉多,刚满一岁。”我掏出手机,找到一张照片,递给南秋。
“哇!”她叫出声来,马上又压低音量,说,“真漂亮,你快告诉老彭,我们要了。”
我给老彭发消息的那会儿,她一直说个不停。我打开老彭发来的信息,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带它回家了。”
“它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
“放心吧,它会喜欢你的。”
“你说,我要给它带什么见面礼呢?改天我们去给它准备点零食吧。”
我们又聊了一些接下来的计划,喝完剩下的酒,拍了一张合影,准备离开。
“对了,它叫什么名字?”
“大福。”
医生叫了一声南秋的名字。我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揉揉眼睛。
“轮到你了。”我说。
医生检查完她的伤口,询问事情的经过以及狗的情况。她睡眼惺忪,看不出是在回忆还是打盹。我回答了所有问题。医生在病历本上写上一大段话,让我们先去缴费、领药,再排队等候注射。南秋坐在椅子上,我领完药走过来,她一直看着我。
“一共九针,今晚是四支血清和一支狂犬疫苗,剩下的四支疫苗,三天后一针,七天后一针,十四天后一针,二十八天后一针。不能喝酒,也不能吃辣。”我说。
“可以一次全打完吗?”她盯着装满药瓶的袋子,说,“我不想再来这个地方了。”
“那怎么行呢?忍一忍就过去了。”我说。
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医生再次喊到她的名字,我把她叫醒。她打完针出来,脸上挂着眼泪。
“疼吗?”我说。
她摇摇头,从包里掏出狗的零食,扔进垃圾桶。她把头发挽到脖子后面,用一根橡皮筋扎起来,以免碰到伤口。
“那天在甜品店里,有个顾客对定制的奶油蛋糕颜色不满意,我跟他解释,说这是正常的色差。他也不听,就把整个蛋糕摁在我头上。我洗了一个下午,怎么都洗不干净,然后我就去理发店,剪了短发。”她扎好头发,扭过头问我,“好看吗?”
“我已经快想不起来你长头发的样子了。”我说。
我们还要等半个小时,观察南秋是否有不良反应。我打开老彭发来的信息,全是他道歉的话(没有一条说到医药费)。我打过去电话,接听的是酒馆前台姑娘,她说老彭下楼买烟去了,问我有什么事。
“告诉老彭我们已经没事了。”我说。
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南秋又睡了一会。
我催促南秋快点去睡觉,但她坚持要先洗个澡。我躺到床上,翻了几个身,直到她上床也没睡着。她缩在床头的边缘,我从后面抱住她。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我们开始做爱。
我們望着天花板,大口呼吸,像是要把这房间里的空气都吸进肺里。天亮了,白色的微光透过浅蓝色的窗帘,均匀地布满房间。南秋流了很多汗,细小的汗珠颗粒分明,晶莹剔透;我的手一触碰,它们就会破裂,连成一片。
“我感觉现在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被一个温柔的壳包裹着。”她说。
“快点睡吧,今天请个假,等你休息好了,再去上班。”我说。
中午我醒过来,发现南秋不在身边。我叫了她的名字,没有回应;我又拨打她的电话,没有接听。我起床拉开窗帘,阳光照射进来,真是个不错的日子。
我走到客厅,看到桌上有张纸条,被水杯压着,上面写了一段话。有几句我不太明白,总之,她离开了。我环顾整个屋子,所有东西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除了挂在客厅的那幅画,不见了。
(责任编辑: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