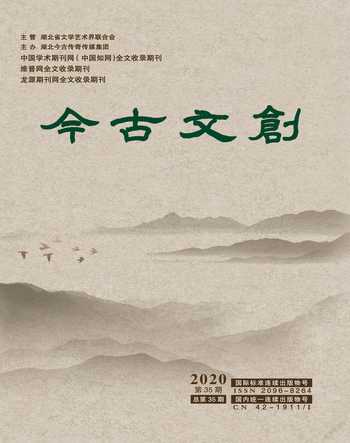《奥兰多》中的异托邦建构
【摘要】 本文以米歇尔·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为理论基础,探讨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奥兰多》中的异托邦建构:作为异族异托邦的吉卜赛部落展现了边缘的吉卜赛种族与英国人激烈的思想文化碰撞;作为时间异托邦的长诗《大橡树》记录了主人公奥兰多在生活与文学创作中“重要的时刻”;作为偏离异托邦的写作房间为主人公奥兰多提供了逃离男权社会压迫,建立女性话语权,实现价值追求的空间。通过分析以上异托邦的构建,本文窥见了伍尔夫的帝国与殖民情节,充满革新与先锋性的写作主张,和对女性争取生存空间,追求自身价值的美好期盼。
【关键词】 《奥兰多》;弗吉尼亚·伍尔夫;异托邦;帝国主义;“重要的瞬间”;女性生存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5-0013-03
《奥兰多》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 · 伍尔夫创作的一部具有浪漫与传奇主义色彩的著作。它讲述了主人公奥兰多从伊丽莎白时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近四百年的传奇经历。奥兰多本是受伊丽莎白女王喜爱的年轻贵族少年,在出访君士坦丁堡时经历一场大火,变成了一位女性,而后游历于吉卜赛部落,最后返回英国,出版了长诗《大橡树》,成了获奖女诗人。随着《奥兰多》情节的发展,场景的变换,一些特殊场所起到了推进情节发展,加强主题的作用。
本文拟用米歇尔 · 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分析《奥兰多》中的异托邦建构,揭示伍尔夫在殖民关系、写作偏好以及女性生存空间上的态度。
“异托邦”是米歇尔 · 福柯仿照“乌托邦”概念自创的一个术语,最早出现在《词与物》一书的绪言,而后他在《另类空间》的演讲中加以具体论述。异托邦是“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1]54。因此,异托邦的存在对现实造成了中断、消解甚至颠覆。《奥兰多》中的异托邦体现为:充满异域风情,与英国形成对照的吉卜赛部落,伍尔夫在其中渗透了她的帝国与殖民情感;体现时间积累,存档瞬间思绪的诗作《大橡树》显现了伍尔夫写作中强调的“重要的瞬间”;偏离男权社会标准,女性自由写作的房间则表达了伍尔夫希望女性摆脱男权制与家长制的束缚,实现思想独立,追求自身价值的期盼。
一、吉卜赛部落:异族异托邦
奥兰多成为女性后投靠了伯鲁沙城外的吉卜赛部落。吉卜赛民族作为生性爱流浪的游牧民族自然与出身于英国贵族的奥兰多在文化与信仰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因此,他们之间不断地产生着隔阂。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们对大自然以及家族宗系不同的态度。
热爱大自然是奥兰多作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特性。她沉溺于吉卜赛部落比英国更宏大更强悍的自然,渴望与别人分享那壮美的河山平原。然而,在吉卜赛人眼中大自然是最邪恶、最残酷的。
吉卜赛人曾向奥兰多展示自己被霜冻坏的手指和被岩石砸伤的脚来批判大自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奥兰多却用英文说“但是多美啊!”另外,令奥兰多引以为豪的英国豪宅以及自家四五百年的宗系在吉卜赛人看来是不值一文的。吉卜赛家族至少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奥兰多的公爵甚至伯爵祖先,在吉卜赛人看来,不过是巧取豪夺者或强盗而已,从他们这些不在乎土地和钱财的人中攫取这些东西。奥兰多试图以吉卜赛是粗鲁而野蛮的民族来解释这些隔阂。这样的种族冲突分裂了奥兰多与吉卜赛人,他们不相信彼此的信仰,对彼此的文化底蕴持怀疑否定态度,因此奥兰多无法融入吉卜赛部落,吉卜赛人也无法接纳奥兰多进入他们的家园。最后,奥兰多不得不主动选择离开吉卜赛部落,也正是这样的举动才使她免于被吉卜赛人暗杀的命运。
吉卜赛部落具备了异托邦有打开和闭合系统的特点。奥兰多虽进入了吉卜赛部落,但由于无法服从内部的规则,始终处于被隔离的状态,最终吉卜赛部落还是为她关上了大门。
吉卜赛部落需要保持其异质性以维护他们的家园与民族文化。文学上广泛存在这样的“异托邦”想象,许多作家热衷于表现这样的异族想象。“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中的异族想象是根据其在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来表现的,当作家根据某种话语表现异族,展现某国优越性或劣根性时,异族形象就成了文学上的‘异托邦’”。[2]伍尔夫呈现了一个充满异域情调和神秘色彩的吉卜赛部落,其目的就是将大英帝国与吉卜赛部落形成对照,来确立大英帝国“高大”的自身形象。正如赛义德所说“存在只有在他性的映衬下才显露底色,才具有意义。他性就是与宗主国相对的殖民地他性”[3]。
伍尔夫出生在英国维多利纳时代的知识贵族阶层,她的亲族有曾在殖民地工作的经历,这潜移默化为她打上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烙印。伍尔夫描述中的大英帝国是繁华、富裕、文明的,然而吉卜赛部落是偏远、落后、野蛮的。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描绘了吉卜赛部落与吉卜赛民族,凸显了英国及英国人的优越感。但吉卜赛部落这样一个异族异托邦的存在实际上消解了伍尔夫理想中的大英帝国光辉的霸权主导地位。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元气大伤,逐渐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随着其经济的持续低迷与战争带来的死伤,英帝国对殖民地领土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很多英帝国殖民地开始独立。英帝国的由盛转衰可以说是贯穿伍尔夫生活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一名敏锐的作家,伍尔夫意识到本来自信乐观的维多利亚精神已摇摇欲坠,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为捍卫帝国的尊严,她通过塑造吉卜赛部落这样一个异族异托邦来巩固帝国地位,寻求心灵上的补偿,满足自己的帝国主义思想。
二、诗作《大橡树》:时间异托邦
《大橡树》是奥兰多从童年时期创作的一首诗作,得名于她独处时最爱去的山顶大橡树,在那里她总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大橡树》记录了奥兰多从一位伊丽莎白时期贵族美少年到一位二十世纪获奖女诗人的思绪见闻与心灵历程。《大橡树》的出版取得巨大成功,为奥兰多赢取名利,她却回到了她心爱的山顶大橡树,想把诗作埋葬于此以回馈这片土地。她不禁发问“赞美和名望与诗有何相干?出了七版又与它的价值有何相干?难道写诗不是一种秘密的交流,即一个声音对另一声音回应”[4]315。由此可见,奥兰多視《大橡树》为与自己内心交流的媒介,积累了自己在不同时期思绪上的变化与成长。
存在一种与时间的积累相联系的异托邦。“这个场所本身即在时间之外,是时间无法啮蚀的,在一个不动的地方,如此组成对于时间的一种连续不断的、无定限的积累的计划”。[5]56
显然,《大橡树》是这样一个与时间积累相联系的异托邦。随着奥兰多的人生历程,它积累了从伊丽莎白时期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三百多年的时间,储存了奥兰多成长中的记忆,为她重返过去,追溯自己曾经的思绪,进行心灵谈话,审视过去,提供了可能性。当她面对吉卜赛部落的自然风光时,她将美景记录在手稿中。当她犹豫是否进入嫁人为妻时,她将婚姻的困扰记录其中。这些瞬间的思绪见证了她的成长与变化,使她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 当她进行《大橡树》最后一次写作时,她发现无论经历多少改变,“她还是同样内向,喜爱沉思默想,她依然喜欢动物和自然,酷爱乡村和四季”[4]225。作为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认为艺术能给予生活意义,给人们带来快乐避免生活中的不幸。写作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为伍尔夫提供了捕捉生活中完美时刻的机会,她通过语言的媒介使这些时刻变得永恒。伍尔夫将她展现的这样的时刻称为“重要的瞬间”。这正呼应了伍尔夫推崇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即通过表达人物飘忽不定、稍纵即逝的瞬间思绪与浮想来呈现事物的本质。这些时刻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真正反应,是属于他们的人生真谛。虽然《奥兰多》不是一部典型的意识流作品,但从主人公奥兰多在《大橡树》中记录思绪的行为中,可以窥见伍尔夫对意识流写作手法的偏好,以及她推崇的“重要的瞬间”对人们审视自我,寻求精神满足具有重要作用。这其中蕴涵了伍尔夫在写作创作中的先锋与变革精神。
三、写作的房间:偏离异托邦
“奥兰多回到屋里。屋里静悄悄的,一片沉寂。这里有她的墨水瓶、她的笔,还有中断了的诗稿”。[4]252这样的一个房间构成了专属奥兰多的写作空间。她拒绝进来为她端茶的仆人。她会在热闹的宴会时,自己逃离回房间独自写作。这样一个用于写作的房间起到了一个偏离异托邦的作用。福柯认为,与所要求的一般或标准行为相比,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偏离异托邦中,比如休息的房间或精神病院。奥兰多的写作行为无疑在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是一种偏离行为。写作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时女性写作会遭到非议与嘲笑。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女性还不具有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更不用提通过写作获得财富与社会肯定来养活自己的能力。正如伍尔夫的个人经历,虽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她和姐姐只能通过在家中自己读书和请私人教师学习,而她的兄弟们都进入了剑桥大学学习。
此外,女性也缺少在社会事件中的话语权。尽管作为聚会的主人,奥兰多能为蒲柏先生、艾迪生先生那些文人墨客做的只有斟茶倒水。奥兰多清楚,尽管文人才子讲诗作给女子过目,征求她的意见,但并不代表尊重她的观点。在这样一个围绕在以男性为中心氛围的时代中,女性的行为与思想被男权中心的观念与价值标准束缚,于是伍尔夫为奥兰多创造了一个具有补偿作用的偏离异托邦。它像外部世界一样同样地被安排得很好,有自己的一套秩序,秩序的制定者就是奥兰多本人,解除了外部世界对她的桎梏。她可以随意地写作发声,弥补自己曾经受到的忽略与歧视,为自己营造出舒适的写作与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她处于非常幸福的状态,不需抗拒屈服自己的时代,因为她可以自由写作,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奥兰多写作的房间呼应了伍尔夫在她重要的女权思想论著《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一个女人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5]。这里的一间房子不仅代表着物质上的空间,更代表着女性的生存空间。维多利亚时代给予了女性“房间中的天使”的普遍形象,她们按部就班地帮助丈夫料理好家中的各项事务,照料好丈夫孩子生活起居。然而这一形象虽看似是对女性的赞誉,实则是男性权威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标签与规定。女性受到赞美与崇拜的同时,必将牺牲自身的个性与个人价值追求。女性的生活范围被圈定在以父权制为统领的家庭中,生活活动围绕着家庭琐事,丧失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女性需要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使自我意志独立,进行自由的价值追求。
伍尔夫的价值追求无疑围绕在写作上,面对受男性霸权压制女性丧失话语权的社会时代背景,她试图通过具有女性价值观的写作与时代抗争,改造男权制社会,重构属于女性美好的世界。她也呼吁其他女性拿起笔进行写作,将自己不同于男权社会文化的话语写入历史。《奥兰多》的结局定格在1928年女主人公奥兰多以自己的女性身份出版诗集并获得社会认可,成为获奖女诗人。也正是在1928年,英国所有妇女拥有了平等选举权,妇女终于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伍尔夫如此安排结局暗示了女性话语已逐渐进入历史,寄予了她对女性摆脱男权社会束缚实现自身价值的美好愿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伍尔夫在《奥兰多》中构建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异托邦影射了她的殖民与帝国情感、写作中的变革精神以及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思考。异族异托邦吉卜赛部落以异域原始的特征与先进文明的英国形成对照,通过意识形态与文化的碰撞凸显了英国与英国人的优越感,实则为挽留捍卫动摇的帝国尊严,抚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英国的损失与创伤,重振帝国“宏伟”形象。时间异托邦诗集“大橡树”记录了主人公奥兰多生活与创作中“重要的瞬间”,它如编年史般供人随意翻看查阅,令主人公审视自我,寻求精神满足。“重要的瞬间”作为伍尔夫写作中极力推崇的元素,体现了她写作中的先锋与变革精神。作为偏离异托邦的写作房间集中了主人公奥兰多写作的偏离行为,是她逃离男权制社会控制,建立自我独立意识,实现精神追求的生存空间。伍尔夫借此空间批判了男权制与家长制对女性自由发展的欺霸,鼓励女性通过写作将女性话语写入历史,实现女性自身价值。
参考文献:
[1]福柯.另类空间[J].世界哲学,2006,51(6):52-57.
[2]宁云中.“异托邦”:西方文化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他者”想象[J].湖南社会科学,2016,29(5):185-188.
[3]爱德华 · W · 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0.
[4]弗吉尼亚 · 伍尔夫.奥兰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5]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M]. London:Penguin Books:4.
作者简介:
李悦莹,女,汉族,天津人,天津財经大学人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