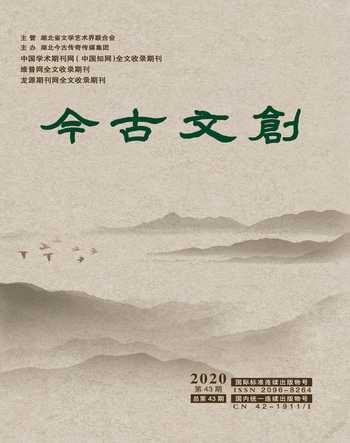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中的忧郁情结
【摘要】 忧郁情结是俄罗斯精神的重要印记,形成了俄罗斯文化特有的厚重与苍凉。俄罗斯白银时代各个流派的诗歌语篇都蕴含着忧郁的元素,显现出俄罗斯精神文化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诗歌;白银时代;忧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3-0015-02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继普希金的黄金时代之后辉煌再现,迎来群星璀璨、空前繁荣的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在历史转折、风云激荡的世纪之交,宗教哲学的复兴、文化的转型和审美的多元化催生了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的三大流派,即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派。著名诗人包括象征主义的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勃洛克,阿克梅派的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塔姆、古米廖夫,未来派的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新农民派的克留耶夫、叶赛宁,以及具有鲜明个性却不属于任何流派的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
尽管人文思想和文艺手段不断创新,审美标准愈加层次丰富,白银时代诗歌仍然洋溢着浓厚的俄罗斯文化气息。无论是追求神秘感和音乐性的象征主义,还是倡导回归“优美的明晰性”的阿克梅派,抑或是醉心于标新立异的未来派,诗歌中始终彰显或隐含着挥之不散的忧郁情结。忧郁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点之一,汪介之先生称其在文学中的投射为“俄罗斯文学与艺术的共同底色”。
二、忧郁的语词
海德格尔说:“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须经由语言的本质去理解。”白银时代俄罗斯诗人的忧郁情结首先就外显地体现在这一时期抒情诗的语词当中。忧愁、忧伤、郁闷、悲伤等词汇经常出现在不同诗人的诗作里。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勃洛克认为,忧郁是他艺术创作的“潜在的原动力”,也是善和光的源泉。他在充满爱国主义深情的《在库利科沃原野》(1908)一诗中写道:
啊,我的罗斯!我的爱妻!我们深知
旅途是那么漫无边际!
……
我们的路是草原之路,我们的路在无尽的痛苦中。
在你的寂寞忧愁里,啊,罗斯!
勃洛克的象征主义哲学把“美妇人”的形象视作“永恒的温柔”。他几乎是第一个把祖国喻作妻子的诗人,但与其他俄罗斯诗人一样,他在罗斯的预设里暗含了忧愁与痛苦。因为俄罗斯的历史历经风雨,多舛的命运与严酷的生活孕育了漂泊的民族心灵,由此产生了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称之为二律背反的俄罗斯性格。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既有率真明朗的欢乐开怀,又始终萦绕着悲天悯人的忧郁与彷徨。在勃洛克著名的诗篇《俄罗斯》(1908)中愁容惨淡的祖国更是牵动诗人的百转柔肠:
俄罗斯啊,贫困的俄罗斯,
在我心中,你灰色的小屋,
你风儿的高歌与低唱
好比初恋的第一缕泪珠。
让他把你诱惑和欺骗吧,
你不会失败,不会沉沦,
只有忧虑才会给你
美丽的面颊覆上愁云。
另一位象征主义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了长诗《世纪末》(1891),这是一部总共十章的组诗,在题为《祖国》的最后一章中同样也出现了忧伤的语词:
祖国啊,我依然爱着你——在异国他乡
愛得比我以前任何时候都热烈、痴狂
千年森林中波澜壮阔的林涛轰响
以及小俄罗斯沉思曲轻轻的忧伤
俄罗斯象征主义第一浪潮的代表人物巴尔蒙特以追求乐感和明朗的意象而著称。即便如此,诗人享有盛名的代表作题目就是《苦闷的小舟》,该诗中的月亮形象更是“一脸忧伤”。巴尔蒙特的抒情诗《无言》(1900)中,对祖国的热恋也一如勃洛克和梅列日科夫斯基般忧思悱恻:
俄罗斯自然风光温柔疲倦,
隐藏着忧伤,暗含着悲痛,
广漠无言的痛苦难以消解,
似伸展的远方寒冷的高空。
巴尔蒙特在首段就写到了俄罗斯大自然无声的痛楚与暗含的悲伤,在诗的结尾处长歌当哭,反复吟咏“哭泣的忧郁的心灵”。
诚然,象征主义者不仅是对俄罗斯祖国忧心忡忡,生活中忧郁的情绪也时常涌现,如巴尔蒙特的《孤独》(1890):请相信我,人们不会/完全理解你的心灵!/你的心灵充满忧伤—— /就像装满水的陶罐;以及《芦苇》(1895)中的“忧伤的月亮竟默默不语”。
象征主义女诗人吉皮乌斯的短诗《千篇一律》(1895)开篇便是苦闷情绪的渲染:在傍晚孑然一身的时分/感到愁闷感到疲倦的时辰/一个人踱着步,跌跌撞撞……
还有老象征主义诗人、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无关风月的哲学思考也摆脱不了忧郁的思绪:尘世生活意识的噩梦你将/摒弃,怀着爱恋与忧伤。
阿克梅派一方面继承了象征主义的精神探索,另一方面又追求消解象征主义神秘的抽象,致力于返璞归真地描绘生活细节,刻画真实的忧郁与悲伤。阿克梅派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具有本质性的纯净,近乎完全接近音乐的诗行里透露沉默的伤感:当可爱的艺术家/在玻璃布卷上描摹/耽于转瞬即逝的力量/却遗忘了悲伤的凋零。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未来派诗人较少使用忧郁的词汇,这与他们的审美取向密切相关。未来派宣称要同一切文学传统决裂,主张进行文学形式的试验,他们做法乖戾,大量运用粗俗的词语和自造的文法不通的词语与句法,表达语义错位。未来派的狂飙带来了消极的文学效果。
被誉为最具俄罗斯气派的诗人是叶赛宁,他的抒情诗以“蔚蓝色的柔情”和对“木头罗斯”的坚守赢得几乎所有俄罗斯人的钟爱。在叶赛宁早期描写自然的诗中忧郁的意象就显现出来:四周一片灰暗的浓云/仿佛带着深深的愁闷/向着远方飘去……(1910);秋雨的水滴啊/你们把多少苦涩/飘洒在人们满怀愁绪的心上……(1912);我重又一人留下/无人抚慰/我心里忧伤……(1913)
叶赛宁不仅自己心中常常满怀伤感,也为母亲担忧。在脍炙人口的《致母亲的信》(1924)中,诗人祈求老妈妈:你就忘掉自己的不安吧/可不要为我深深地忧伤/别总穿着破旧的短袄/走到大路上去翘首怅望。
在《苏维埃罗斯》(1924)一诗中,叶赛宁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却俨然成了“不知来自何方的忧郁旅人”:忧愁的喜讯——无人分享。但他仍然愿意为祖国歌唱,因为诗人相信,“谎言与忧伤终将消逝如烟”。
同样是在1924年,刚及而立之年的叶赛宁写下包含哲理,略带哀伤但旷达、深沉的诗句:阳光下花楸果实已经熟透/枯黄的青草还会有生机/就好像树叶悄然飘落地上/说出我心中忧伤和愁绪。翌年夏日,离世半年前,诗人感悟到:生活是忧伤迷人的幻觉/所以它这般强劲有力/甚至能用那粗暴的手/书写决定命运的文契。
三、忧郁的抒情语篇
语词构建了诗歌,但是语言的魅力又常常在于言外之力。对白银时代诗歌而言,很多忧郁的语境可以不依赖直接使用忧郁或者伤感的词汇,而是通过整个语篇建构起忧伤的语境。叶赛宁的抒情诗往往通篇弥散着忧愁:
我不悔恨、呼唤和哭泣,
一切会消逝,如白苹果树的烟花,
金秋的衰色笼照着我,
我再也不会有芳春的年华。(1921)
叶赛宁对青春逝去的无奈与对俄罗斯文化的深深眷恋营造出浓浓的慨叹愁绪。
阿赫玛托娃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女诗人本该多愁善感,然而她在诗作中很少使用忧郁、忧愁一类的词汇,只是在早期的皇村生活中有过“坐在永恒的小溪上,少女永远忧愁绵绵”这样愉快的忧思。事实上,阿赫玛托娃的忧郁更加静谧深沉,虽然没有外显语词的直接张力,却隐含在润物无声的静态描写之中。她不喜欢直白地倾述,而是委婉地忧郁到心碎:
我宠爱映在窗上的光,
它笔直,纤细,浅淡。
今天我从清早就缄默,
而心——分成了两半。
长诗的意指往往是通过全篇的格式塔才能构建完整的语境,所以有时忧郁之情内隐于全部语篇,只在结尾等关键处有总结性的暗示。在阿赫玛托娃的长诗《安魂曲》(1934-1963)的结尾,没有诅咒与谩骂,而是代之以的缓缓的倾诉,女诗人已经不是在讲述自己儿子受前夫古米廖夫牽连入狱的个人悲剧,而是在记录一个时代的痛苦与忧伤,从而更具高尚且宽容的道德:
就让那泪水般融化的雪,
从不动的青铜眼上流淌,
就让监狱的鸽子在远方哀鸣,
轮船在涅瓦河上静静地远航。
四、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见,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色彩纷呈,不同的流派与不同的审美交相辉映,但是俄罗斯民族的忧郁心理却始终浸润其中,反复吟咏,独具魅力。
忧郁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基因。汪介之认为,俄罗斯文学与艺术的这种忧郁与悲凉的情调和底色,根源于俄罗斯民族生活在其中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更为其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苦难体验和忧患意识所决定,它造成了这个民族的文学与艺术特有的厚重感和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
忧郁也是白银时代的历史阵痛。其时俄罗斯整个国家、社会面临历史转型的痛苦抉择,思想的迷茫与探索导致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文化价值的忧虑和不安。
综上所述,忧郁情结滥觞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在文化复兴的语境感悟中又获得了诗学审美的青睐,成为白银时代俄罗斯诗歌独特的韵律。
参考文献:
[1]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汪介之.忧郁与悲凉:俄罗斯文学与艺术的共同底色[J].广东社会科学,2018,(04).
[3]周启超主编.白银时代诗歌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作者简介:
朱劲松,男,汉族,吉林长春人,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