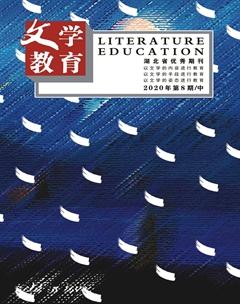作为非典型江南的香椿树街:苏童对话语霸权的消解
内容摘要: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是苏童两个地标性小说系列之一,由52篇短篇小说和部分中、长篇小说构成,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与此同时,“香椿树街”还展现了“江南”符号并未包含的阴暗、暴力、机械的元素。这些元素也正是苏童对传统“江南”的反击。总体而言,文本世界的创造以及江南符号的新书写体现了苏童对历史多元解读的倾向,也彰显出苏童对话语霸权的抵制。
关键词:苏童 香椿树街 江南 话语霸权
苏童是当代文学中难以绕开的一位作家。自1983年发表作品以来,他笔耕不缀,创作出《妻妾成群》、《红粉》、《米》等一批优秀作品,一般被划分为红粉系列如《红粉》、《妻妾成群》等;历史题材系列《我的帝王生涯》等;枫杨树乡系列如《米》、《罂粟之家》等以及香椿树街系列。其中短篇小说多集中在枫杨树乡系列和香椿树街系列。
一.香椿树街的空间
自1983年创作《桑园留念》以来,苏童不断创作出以“香椿树街”为背景的小说,开始构建一条“香椿树街”。一篇短篇小说只能独立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且只能深入表达某一种思想。但当很多篇小说连缀成一个系列时,其容量和内涵往往可以媲美与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经过多年耕耘,苏童笔下以“香椿树”为背景的小说(包括7篇中篇小说和3篇长篇小说)多达62篇。这一系列小说具有相当庞大的内容,而且打破了长篇小说的整体性,具有开放性。这使作者可以更自由的运用叙事手法,也使文本有了更多样的阐释空间。
“香椿树街”系列的不同作品之间除了地理标志“香椿树街”一致,人物也具有相关性,即部分人物会在不同作品中屡次出现。如绍兴奶奶出现在《伞》《七三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白雪猪头》《桥上的疯妈妈》等作品;锦红出现在《城北地带》和《伞》中;小拐和红旗在《刺青时代》和《城北地带》都有出场;还有王德基、达生、三霸、莫医生等人。但是这些名字相同的人所经历的事件在不同作品中却不一定一致。比如锦红在《城北地带》中以夭折告终,而在《伞》中则与施虐者有了新的交集。除了出现在不同小说的同名人,还有部分名字不同,但在不同小说有着同类属性或同类气质的人物。像《桑园留念》中出现的女孩丹玉,《像天使一样美丽》中出现的珠珠和小媛、《水鬼》中出现的邓家女孩,她们的行为都让人捉摸不定,想法也令人难窥究竟,始終萦绕着青春的忧郁气息。总之,“香椿树街”中的人与事呈现出零散、碎片、却独立的特征。他们并不由统一的意识支配,而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①,即他们都是相互独立的主体,同时他们又在“香椿树系列”中平等交流。
系列中人物重复出现,与之相关的事件也因为交流而在不同视角下重复出现。从不同人物的角度出发,同一起事件在不同层面可以完全不同。《哭泣的耳朵》和《伞》中都出现了强占幼女的事件。《伞》从上帝视角强调了事件的发生场,细致叙述主人公的悲惨命运。而《哭泣的耳朵》中,主人公的弟弟成为叙述者,从旁观者的角度“一蹦一跳”地提起这件事。叙事学家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谈到:“一件事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再发生或者重复,‘重复事实上是思想构筑。”②读者在很难确定信任哪个叙述者的同时也建构了自己的观点——通过综合不同文本客观梳理整起事件及其影响。
平等对话与重复带来了“香椿树街”系列的开放性或者说未完成性。它不再局限于长篇小说对人物成长性的描摹,而是挖掘不同时空下同一人物的多元可能。这种开放性及其背后的碎片化、零散化也是对宏大叙事整体性的解构。这使得苏童无论何时都可以在“香椿树街”的世界里继续添砖加瓦——“我的短篇小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但是我有意识地保留了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这两个‘地名,是有点机械的,本能的,似乎是一次次的自我灌溉,拾掇自己的园子,写一篇好的,可以忘了一篇不满意的,就像种一棵新的树去掩盖另一棵丑陋的枯树,我想让自己的园子有生机,还要好看,没有别的途径,唯有不停地劳作。”③时间的流逝不会停止,而人生命的有限,因此历史的尽头永远难以触及。但开放的“香椿树街”系列却可以因为其未完成性而达到某种永恒。
二.香椿树与江南
苏童自称笔名的含义是“苏州的童忠贵”④,童忠贵是其本名,苏州是其故里。以他青少年时期成长的苏州街道为蓝本的“香椿树街”也带着些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的气息。即便忽视作为蓝本的苏州街道,“香椿树街”系列的字里行间也显现出南方的特有自然景象。比如梅雨和青石板——“时断时续的黄梅雨落在外面的青石板路面上,空气潮湿而凝重,酱园的地板上每天都是湿漉漉的,洇满了顾客的泥脚印和水渍。”⑤又如阁楼、河水之类和江南水乡紧密联系的景观。这些叙述使读者可以迅速将背景定位至南方。
但是除去大量的与江南有关的意象,苏童同时也突出了一些反古典江南印象的意象。他曾提到“南方通常会被理解为一种刻板印象。比如大家说到江南,马上会想到一座小桥一条船,这个是让人非常倒胃口的,对于南方的机械符号式的描画。而且它很甜腻、很恶心,我一直认为这样对南方的描述不光是庸俗,还是让人反胃的。甚至是对南方的一种不公平。”⑥所以,他承认对南方的书写是对“南方被轻浮地定性为“小桥流水”之后的一次极大的反叛行为”⑦。在场景上,他构建了基建式地标铁路和化肥厂,这与传统江南婉约精致的景象几无关联,而和工业化后环境糟糕的现代城市画面紧密联系。在人物塑造与审美上,不同于多才风流,细腻委婉的传统江南印象,“香椿树街”里的人们固然心思细腻,但也思虑过重,常常拘泥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人们的鱼》中,柳月芳因为自家官势衰微门可罗雀而邻居张慧琴的生意蒸蒸日上,产生出一种尴尬、羡慕还不愿意承认的复杂心理,最终这种心理被张慧琴的大方体谅所化解,体现出苏童对那种敏感纤细的心理状态的不认同。
不过苏童在对传统“江南”这一固定符号进行颠覆的同时,也间接深化了江南的某些印象。潮湿、阴暗、拘泥细节、神经质的敏感多疑实际上也是多雨柔情、细腻婉转等传统江南印象的另一种表达。此外,苏童给“江南”增加了一些新的印象。铁路、化肥厂等现代建筑显然可以看作是物质现代性的表征,这正和江南地区开埠以来迅猛发展是吻合的。或许在苏童看来,“江南”一如香椿,虽是春天的使者,却因其特有之味令人爱恨交织,有着不断被开发新意义的可能。
三.对话语霸权的抵制
历史是时空结合的产物,由于时间的不可逆,在人类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人们往往只能把握当时所能够认识的历史的某些方面。而在苏童的笔下,“香椿树系列”中的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是该篇中的主人公碎片化的某一记忆。不同文本中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同一条街上,但是他们每个人对历史的经历、体验、记忆都是非常不同的。这使得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点的共时性碎片相组合,造就了一种庞杂宏大的文本现象,显示出不同时期的不同角度的“香椿树街”。并且这一系列中,主人公们经历的不同事件的每一次上演和经历的相同事件的每一次重复都对历史的确定性造成了怀疑和重新解读,甚至使得整个“香椿树街”的历史变得扑朔迷离,打破了传统历史确定性叙述的话语霸权。正如马友平认为的那样,新历史主义下的“历史作为叙事”坚守了“边缘化的叙事态势”,提出“边缘化叙事策略本身即具有‘非中心的疏离功能,使处于中心的话语露出破综,历史的话语霸权被消解”⑧。
另一方面,“香椿树街”一旦与现实相对应,就会发现“江南”这一文化符号的多面性。“江南”从地理标志,转化为历史文化符号,成为一种固有的文化象征,是古往今来无数人所建构的结果,这一结果显然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然性。但是,对“江南”的解释的唯一性必然会导致故步自封。于是在苏童的笔下,“香椿树街”不再等同于烟柳画桥,不再是文人骚客的陈旧墨迹,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多元体,它有少年的斗争也有邻里的暗讽。以此为代表的“江南”因而有了阴暗的一面,也有了新的成分。“江南”是历史的,但是不是绝对的,它应该是可以被又爱又恨的,而不是一定要一味的被追捧。这种对“江南”的新解也是一种对固有观念的挑战。
在对话语霸权的抵制过程中,苏童完成了对固定符号的消解,和对新的文化观念的重建,这和当下作家的追求显然是一致的,也是多元文化历史背景下作家的走向之一。
参考文献
[1]苏童.短篇小说编年[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0.
[2]巴赫金,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三联书店,1988.
[3]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 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04.
[4]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08.
[5]韦伊.苏童小说的空间叙事[D].华侨大学,2018.
[6]兰奂铮.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成长主题研究[D].河南大学,2018.
[7]梁海.“纸上的南方”——论苏童小说的空间叙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57(05):145-153+207.
[8]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苏童小说创作特征论[J].文艺争鸣,2007(10):137-143.
[9]吴舒婷.论苏童小说的差異性重复[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2):251-256.
注 释
①巴赫金,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②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1.
③苏童,叶迟:苏童 香椿树与枫杨树,小说选刊.2018.05.
④苏童:我们仍在人性的黑洞里探索,凤凰网读书.2013.08.06.
⑤苏童:另一种妇女生活·苏童文集·末代爱情,南京:南京文艺出版社.1994.330.
⑥苏童:我们仍在人性的黑洞里探索,凤凰网读书.2013.08.06.
⑦苏童:我们仍在人性的黑洞里探索,凤凰网读书.2013.08.06.
⑧马友平:《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文化审视》,《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作者介绍:秦阿香,广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