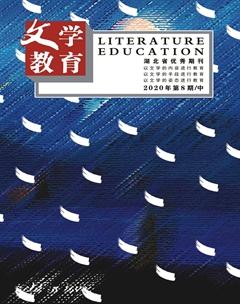论鲁迅的文学主张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刘中慧
内容摘要:鲁迅先生对萧红的创作影响颇深,萧红更是在创作实践中一直贯彻着鲁迅先生的文学主张。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创作题材上,萧红延续了鲁迅的“不必趋时”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在创作方向上,萧红继承了鲁迅的“为人生”和“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创作目的;在内容和体裁上,更是坚持了鲁迅先生“重视乡土色彩”和“创造新形式”的特点。然而,萧红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主张并不是一味模仿,而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继承并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鲁迅的文学主张 萧红创作 “不必趋时” “为人生” “创造新形式”
王孟白教授曾这样评价萧红:“呼兰河畔草青青,天南地北早闻名。女儿原有英雄气,文采偏从鲁迅风”(北方论坛,1982年第1期);孙犁说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钱理群曾言:“和现代文学的宗师最为相知的竟是最年轻的萧红”,这些话都十分恰当的概括了鲁迅先生对萧红创作的影响及萧红与鲁迅先生的师承关系。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鲁迅作品中思想内容的深刻忧愤,艺术形式的不拘一格,使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萧红是读着鲁迅的作品进行文学创作的,因而一直被鲁迅先生的文学主张所深深影响,在文学创作的这条道路上,她更是始终如一地将这些文学主张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准则。
一.创作题材的选取
在创作题材的选取上,萧红与鲁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不必趋时”
1935年,《生死场》的出版,使得萧红声名大噪。但作为前期作品的《生死场》,在结构安排上确实有些散乱,作品的前十章还在描述“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愚昧人民,后六章却笔尖猛转,直接叙述愚民们突然觉醒,有了强烈的反抗意识,纷纷走上反抗道路。这不免让读者有些不明所以。胡风在读后记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然而,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的短处或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1]”其实,胡风此处的表述并不是十分准确,让读者“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的原因并非是萧红“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究其原因,在于作家对所写题材并不熟悉,因而才会有牵强、生硬之感。同一时期的作品如《看风筝》等也有类似缺点。萧红也渐渐意识到自己对于题材的驾驭上的困惑,因而在与鲁迅先生的第一封通信中讨论的便是取材问题,鲁迅在回信中说:“不必要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2]”鲁迅强调作家创作时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写自己能写好的东西。这个观点与1931年,在关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鲁迅曾明确指出的:“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观点相一致。萧红认真领会了鲁迅的指点,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创作有了显著的进步。《呼兰河传》出版后,作品选取的题材,成了人们贬低作品的共同口实,有人认为萧红“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只能“在往昔的记忆里搜寻写作的素材”,更有人直言:萧红“走下坡路了。”然而,事实上,萧红有着自己明确的题材选取及创作意图,她的创作更是符合一切艺术家的创作规律。“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的。(《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七月》第15期》)”可见,在创作题材的选取上,萧红和鲁迅先生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即“不必趋时”,只需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或者是“起着思恋情绪”的题材。只因为此,《呼兰河传》才能在今天的文学史中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2.“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
在谈到自己作品的取材时,鲁迅曾表示:“多采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3]”,因而,鲁迅笔下的“阿Q”是被社会迫害、只能以“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的可笑者形象;祥林嫂是被封建等级观念迫害致死的“下等人”形象,他们都是这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萧红曾谈到过自己对于鲁迅小说的理解:“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和他们一起受罪。(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萧红对鲁迅的小说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她钦佩于鲁迅先生对于题材的深刻认识,因此在作品人物的选材上,也保持着与鲁迅一致的步调。在《生死场》中,萧红选取了东北大地上那些“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人们,他们过着和动物一般愚昧的生活,没有自我觉醒的意识,有的只是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也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她饱受着地主阶级的迫害,最后惨死于家中。他们都是这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然而更病态的不在于他们的身体,而在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呼兰河传》中的人们就是对这种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的集中反映。作品中,萧红着重揭示人们愚昧、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作者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写了这座小城的“盛举”:跳大神、唱戏、娘娘庙会等一系列风俗活动。这些客观的描述都表现了封建风俗对于人的毒害,其中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的形象更是栩栩如生,他们的悲惨经历也似乎仍历历在目。在萧红的众多作品中,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也“取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但须提到一点,萧红在人物的选材上,并非一味的照搬或模仿鲁迅的文学主张,她是在理解鲁迅的文学主张的基础上再结合自己的所求“为我所用”,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具有着深刻的国民性弱点,而萧红塑造的“有二伯”形象虽有着与阿Q相似的弱点,但其又很善良,这样使得人物更有人情味,从而更能引起读者的同情。
二.创作方向的确立
1.“为人生”
鲁迅先生在谈到创作目的时,曾言:“说到为什么要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4]”,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鲁迅也表达过自己的文学观:作家应该“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鲁迅注重强调文艺的真实性,指出作家要正视现实和人生,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萧红在创作方向上就师承了鲁迅的文学主张,小说《王阿嫂的死》中,萧红为的是中国劳动妇女痛苦的人生。作品中王阿嫂的丈夫被活活烧死,王阿嫂自己也被踢得流产而死。而当她死后,她的女儿却仍在坟前担忧和哭诉:“我还要回到张地主家去挨打吗?”一句话,将残忍的社会现实表现的淋漓尽致:受地主压迫并不是短暂的事实,底层劳动人民奴隶般的劳作,是代代相传,周而复始的。一方面,萧红在为底层劳动妇女不公的命运鸣不平,另一方面,作家又迫切希望此种黑暗的社会现状能够有所改变。在《生死场》中,“她的创作视野已经扩展到整个‘中国的人生[5]”在生死场中,前期的人们愚昧、麻木:“在乡村,人们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曾描述过他们的生存状态:“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了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然而在作品中,人们愚昧的精神状态并不是一贯如此的,后六章中,人们的意识突然觉醒,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鲁迅在《〈生死场〉序》中这样评价该作品:“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對于死的挣扎,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可见,鲁迅先生充分肯定了萧红“为人生”的创作方向。
2.“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目的时曾明确表示:“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性”的思考,当他在日本看到中国人对杀害自己同胞的行为而面无表情时,他意识到“我们的第一要义,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接着,鲁迅弃医从文,决心要以“文艺”为工具,揭示国民弱点,改造国民精神。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鲁迅表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指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他的小说中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都反映了“国民性”:奴性、懦弱、精神胜利法等。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巨大,萧红也深受其影响。1938年,在一次抗战文艺界的座谈会上,萧红说:“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与鲁迅的创作主张何其相似。在萧红笔下,《生死场》中关于对女性生产的描绘,让读者了解到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生存和生产的不易,揭示出“病苦”,读者便发现了当时社会中女性的弱势地位,从而引起人们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达到“疗救”的效果。萧红的后期作品《呼兰河传》中更是做到了“揭出病苦”:“翻开萧红的后期代表作品《呼兰河传》,这分明是一幅画满了灵魂的图画,所以‘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点沉重下来。这沉重来自呼兰河的人:他们可怜又可笑;既懒惰又勤奋;苟且且顽强;迷信、愚昧、残忍但又那样仁慈和善良。这沉重还来自于呼兰河的事:怪诞、奇异,然而又是那样平淡、自然、合乎情理;在这种人、事中,呼兰河的生活:声色喧嚣多彩却又显得寂寞、苍凉。[7]”萧红用细腻的笔勾勒出国民的灵魂,她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生活,而是整个的社会风俗,表现出她对国民性的反思。
三.创作特色的体现
1.体裁上:“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鲁迅认为:“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论睁了眼看)”,鲁迅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大胆,常被众人所称道,更是被誉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在这方面,萧红更是深受鲁迅先生影响。钱理群曾说:“鲁迅与萧红在艺术上都具有一种不受羁绊地自由创造的特质,他们不为成规所拘,总是努力地寻求与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形式[8]”萧红的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当有人说她写的小说并不像小说时,她直言:“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科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可见,在创新文学新形式方面,萧红视鲁迅为榜样。当别人质疑她的小说形式时,她不仅用鲁迅先生的小说加以辩护,还对传统的小说形式表示质疑,她认为小说的体裁不应被条条框框所拘束,她认为,有多少作者,就应该多少种形式的小说。她的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塑造,若以传统眼光去评判,那么她的小说肯定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胡风在《生死场》的后序中也曾指出萧红小说创作中的两个不足:“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第二,在人物的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胡风是站在传统小说的立场上对萧红的小说进行评判的,因而他将萧红的亮点都视为缺点,然而萧红不仅没有改正这个缺点,反而在后期作品中将其发扬光大了。在后期作品《呼兰河传》、《小城三月》中,全文仍没有完整的故事和人物,然而风格自由,随意,其中的情调更是独树一帜。正是这独特的小说形式,成就了后来的“萧红体”,也为后来的“诗化小说”、“小说散文化”开创了先河。
2.内容上:重视乡土色彩
鲁迅非常重视文学作品中的乡土色彩,其笔下的《祝福》、《故乡》。《社戏》等都能让读者感受到浙江农村的风俗面貌以及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土人情。鲁迅曾说:“现在在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他还表示:现在的文学“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到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力。(致陈烟桥,1934.4.19)”正是因为对乡土色彩的重视,鲁迅才被萧红的反映“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的作品所打动,才会不遗余力地帮其出版。而萧红在创作中也是一直秉承着鲁迅的创作主张,其后期代表作品《呼兰河传》就是一部杰出的保持着乡土色彩的佳作,茅盾在《呼兰河传》的序中曾评价其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更有学者表示:“它成功地反映了东北农村世代相传的民间风俗。这里有春夏秋冬四时的山川景色,有人们生老病死的法规,有婚丧嫁娶的习俗,有年节祭祀的礼仪。[9]”值得一提的是,在乡土小说中,萧红并没有对农民的苦难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而是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萧红因其作品中的“乡土色彩”,而渐渐“打出到世界上去”,直到今日,《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仍在美国和日本广为流传,也得到如葛浩文等国外学者的关注。
在鲁迅和萧红的乡土小说中,除了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外,其乡土小说中还有“自传体”性质,即在描绘故乡山水之间能隐约寻找到作家本人的身影。这种“自传体”形式并非直接表现自我,有学者认为:“在处理自我与创作的关系上,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隐匿自我……二是宣泄自我或表现自我……三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如鲁迅、沈从文、萧红、孙犁等,这些作家在从事创作时,往往不隐匿自我,也不宣泄自我,因此其创作既冷静又热烈,既写实又抒情,既再现又表现。[10]”正是对这种创作方式的灵活运用,鲁迅和萧红的作品才显得别有意味。鲁迅的《一件小事》、《故乡》等,萧红的《商市街》、《家族以外的人》等都是此类小说,正是因为有“自传体”性质成分,才会使小说中的乡土色彩更加真挚、感人,令人印象深刻。
总之,萧红在创作上深受鲁迅先生影响,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秉承着鲁迅的文学主张。在创作题材上,萧红延续了鲁迅的“不必趋时”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在创作方向上,萧红继承了鲁迅的“為人生”和“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创作目的;在内容和体裁上,更是坚持了鲁迅先生“重视乡土色彩”和“创造新形式”的特点。但萧红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主张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将其结合于自身的情况,在继承中发展,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小说风格。正因为此,萧红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才会一直屹立不倒。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全集[M]//《生死场》读后记.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300.
[2]鲁迅.致萧军[M]//鲁迅书信集.卷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8.
[3][4][6]鲁迅.南腔北调集[M]//我怎样做起小说来.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
[5][9]陈世澄.试论鲁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原载《萧红研究》丛书第四辑,《北方论丛》编辑部编,1983年内部发行.
[7]贺常颖.从《呼兰河传》看鲁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四期.
[8]钱理群.精神的炼狱[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221.
[10]单元.论萧红对鲁迅小说艺术创新精神的回应[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5(04):70-73.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