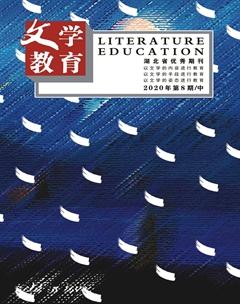严歌苓小说《太平洋探戈》中的种族观
内容摘要:《太平洋探戈》是于2014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作者严歌苓以其瑰丽的文笔徜徉于太平洋两岸,勾连起毛丫与罗杰两位主人公冲破束缚、追寻内心、向往自由的故事,中国的毛丫与澳大利亚的罗杰,其成长经历分别为两条叙事主线,最终交汇于美国,文中罗杰的困境则是由他对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所导致。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揭示小说中种族刻板印象的幻灭之由,并指出所谓单一的种族品质亦即是人性共通之处。
关键词:《太平洋探戈》 严歌苓 种族观
《太平洋探戈》中的两条叙事主线分别从中国的毛丫和澳大利亚的罗杰展开,他们的成长经历亦是叙事线逐渐发展靠近并交汇的过程。随毛丫的成长经历一同构建起的还有坚韧、隐忍、专注的品质特征,这种特质也是另一条叙事线上少年罗杰为之所吸引并推动其故事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澳大利亚,十五岁的罗杰在观看亚洲驯虎女郎表演时,观察到她那因专注而散发出的独特个性气质,并被其深深吸引,从而将这误认为专属于亚洲的种族特征,视为内心深处的追寻,并将这种追寻付诸于婚姻,在与一名华裔女性的婚姻挫折过后,方才意识到,这种独特的个性魅力是人性共有的特质,属于每一个专注自己的内心真正偏爱的事业,并为之付出、沉浸其中的人,并非属于某一族群。
一
小说开篇,二十四岁的毛丫在大洋彼岸著名的三号街上摆摊做买卖,这里都是她的同类——卖的不是身外之物而是自己的本事,她卖的是一身精湛的杂技,毛丫的技艺本属于中国国内高规格的舞台,观众也都是精挑细选的,但在这条步行街上,多是看热闹的人,没人通晓其中的门道。毛丫是毛师傅从火车上捡的,所幸,她遇到了善良淳朴,天命之年无子嗣傍身的毛师傅和毛师娘,将毛丫当亲生女儿般抚养。夫妻二人和杂技打了一辈子交道,当然,这一切在毛师娘眼里不过都是“没出息的饭”,她千方百计阻拦毛丫练功,但均以失败告终。之后毛丫在毛师娘的教学下练功。正是这种倔劲,让日后的毛丫冲破一切阻挠,心无旁骛地表演着最爱的杂技。此时,罗杰的叙事线在澳大利亚展开。罗杰的生活平静中溢出点庸俗,成长于悉尼小镇的农场主家庭,十五年的成长岁月中放眼望去都是年复一年的收获与播种,单调平和的成长环境也同时塑造了他单纯执着的性格。他执着于自己那一幅幅妙手偶成的画作,平凡生活中唯一一点不安就是对画作仅剩的那点少年无助的期待。他想要逃离,却没有方向;他本会心无旁骛地画下去,画农庄上来来往往的陌生面孔,假如没有那场马戏,没有碰见那个驯虎的亚洲女人。也许是他基因里携带的某个片段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喚醒,促使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而不是让道听途说的二手经验建构起自己对别处初始的想象,或者说正是这真假参半模糊不清的想象才让他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向往。马戏团的亚洲女人像是从东方走来的一个神话,过着吉普赛人一样的流浪生活,骨子里却是东方女性的含蓄内敛,娇小的身躯仿佛驻藏着无尽的能量,在猛虎面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永远都在展示与奉献,面对马戏时的专注与柔情,纯粹得不像个真人。当罗杰为追随神秘的驯虎女郎而走出小镇时,此刻的毛丫正为逃脱亲生父母的掌控规划苦练杂技,最终的演出成功是对亲生父母抛弃她、后又试图规划、掌控她人生的一次报复行动。
罗杰将他对亚洲女性单一的想象付诸了实践。和一个拜金的华裔女子失败婚姻使二十四岁的罗杰意识到,让他难忘的,在内心深处推助他苦苦追寻的,并非他所想象的亚洲女性独特品质,而是那一小撮能沉浸于心灵自给自足从而淡然了无所求的个体,他自己也曾是这样的人,从童年起便将画画视为精神依托,但之后沿着错误的方向所做的努力使他离绘画越来越远。在他心里划开一道难以愈合口子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到处散发着异质的灵魂,这个灵魂给他展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可以做个精神上的吉普赛人,世俗中的畸零人。近乎人生十分之一的光阴足以让他少年时单薄的印象变为想象并持续发酵,发酵的幻影在他心里给亚洲人都蒙上一层薄纱,阻碍着他像了解其他种族那样去了解亚洲人,对亚洲女性的理解不过还停留在十五岁短暂的邂逅。对婚姻过高的期待让他心生幻灭,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华裔妻子阿翠都将种种冲突归结为种族文化的不同,许久后罗杰才意识到这种不合适与种族无关,问题症结在于心灵上能否真正契合,但幻灭的同时也迎来了真正的成长。
二
作为一名常年旅居海外的作家,严歌苓的这部中篇更像从自身经历出发,以尝试打破西方人对东方女性或是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文中的叙事者“我”以一个他们共同朋友的身份向读者讲述了毛丫与罗杰的故事,而“我”的视角也正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说的局外人的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可以同时行走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这种(流亡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1]70,小说中作者刻画的毛丫正是这样一个追寻自由的角色,无论是对抗着社会潮流坚持练杂技还是留在美国以表演杂技谋生,高超的技艺给了她足够的自由度选择自己的人生。严歌苓曾戏称自己是“文学的游牧民族”,并且认为“审视和反思一种文化,赏析或批评一种社会状态、生活状态,不被这个社会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卷进去,最好是拉开距离,身处边缘。”[2]作为一个作家,这种双重视角就是让她“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1]70,从两种不同的经验观念出发,并以此为养料,从而探索出属于自己特有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1]71。罗杰在澳洲与华裔女子阿翠的婚姻亦可看成是对未知的好奇与对自由的渴望,只不过他对亚洲女性的这种好奇更像是猎奇。亚洲驯虎女郎留给他的印象过于神秘而美好,他想象着阿翠身上也必然有着同样的隐忍与含蓄,婚姻是他对此一探究竟的合理借口,而距离的消失也让他逐渐看清事情的真相本质,并且意识到“驯虎女郎留下的记忆是略带创伤性的”[3]54,这种创伤亦是长久以来自我建构观念的崩塌。
路易斯·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附着在一定机制上的,对个体具有构造作用的生产活动”[4]771,并通过“质询”的方式,借助家庭、教育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控个体,从而将个人转变为意识形态主体。对亚裔的种族刻板印象也正是这样停留在罗杰观念中,这种刻板印象本质与种族偏见并无二致,只是借助了优良品质的外衣才显得不那么尖锐。少年时的罗杰曾觉得成年澳洲人对亚洲女性的戏谑言语是“堕落”的体现,却不曾意识到他自己保有的观点同样是建立在不平等的注视之上。“人们通常会注意那些能够巩固他们心中刻板印象的案例,而忽略或忽视那些不符合刻板印象的案例。”[5]71少年时期的短暂相遇后,驯虎女郎的形象一直为罗杰所难忘,一切和亚洲有关的事物都能激起他的回忆,就算婚后也时不时暗暗地拿阿翠与她做比较,仿佛是在印证自己的看法正确与否,当逐渐发现阿翠是全然不同的一个亚洲女性时,他对女性的幻灭开始了,也是个体内心微观意识形态幻灭的开端,这也正符合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主体的看法:“有足够的敏锐接受统治者的教导,也就有足够的意识质疑这些教导。”[6]46
当罗杰意识到亚洲女驯虎师的魅力与种族无关,而是“她那心灵的自给自足使她那么淡然”[3]53时,他选择拿起画笔,按下婚姻的暂停键去往美国,以找回在两年婚姻中迷失的自我。罗杰的了然是顿悟式的,从他走出小镇农场再到走出婚姻,根本动力都是为了“偷享他自己那点乐子”[3]103——绘画,并非此前一直认为的问题根源——种族文化。这和另一端离开父母家,走出国门的毛丫目的相同,如她所言:“一个人要是爱自己正做的,它对他就不再是件活儿了。它就是个乐子。”[3]116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基于权利话语的东西方文化形象建构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认为“东方”并非真实存在,对东方的各种刻板印象与想象都是西方进行新殖民主义文化控制是一种手段。这种扁平化、单一化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也在不经意中使西方人将亚裔为代表的东方群体看作是异于自身的存在,视为陌生的他者。而事实上,无论东方西方,其内部都有著诸多共同的相似特征,都是多元的,长期处于变化之中。东方人和西方人,除外表的差异,在作为“人”这种生物个体方面,都有着对自由的向往精神与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
三
理想与现实的交汇发生在罗杰与毛丫在餐馆中的第一次见面,专注于能充盈内心的工作,品尝成就所带来的瞬间快感,是人类共有的品质追求,紧紧包裹于自我内心的禀赋只是借助了种族的外壳得以凸显,人们对自由的向往是超越种族、超越地域的,而作者也正是借助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打破以罗杰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人刻板的种族印象。
参考文献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2]严歌苓:我是“文学游牧民族”
[3]严歌苓:《太平洋探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4]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5]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族群关系》,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6]Eagleton, Terry.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91.
(作者介绍:查伟懿,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