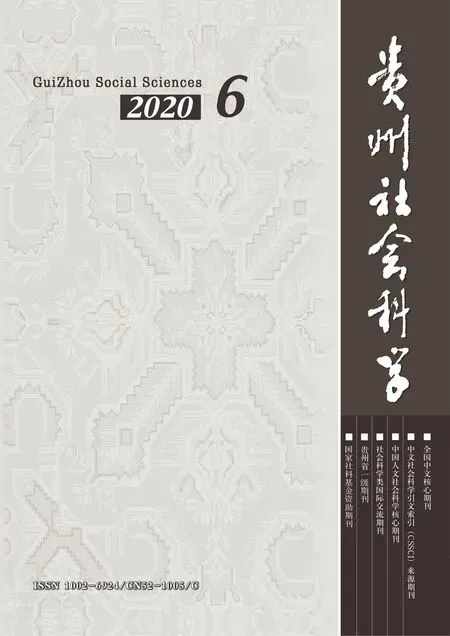“神话即古史”
——以“刑天”“夏耕”为中心的夏史求证
柴克东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一、引论:从“古史即神话”到“神话即古史”的研究范式转向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在帝制时代末期的中国本土学者如姚际恒、崔述等人就曾掀起过一场针对今文经学的疑古思潮。1903年,“神话”一词由日本泊入中国,在经历了“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两大反传统思潮的激荡之后,最终与疑古思潮汇聚,催生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史学运动,这就是由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首倡的“古史辨”运动。随着胡适“东周以上无信史”口号的提出,“古史即神话”开始颠覆两千多年来的“古史即信史”传统,成为古史研究的新典范。
从学术史自身进行考量,“古史辨”运动在中国史学史上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陈其泰先生所言:“‘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1]14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神话”一词在传入中国时概念界定不够清晰,与之相关的研究理论也远远谈不上成熟,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古史辨派过于夸大神话虚构和古史叙事之间的区别。对于他们而言,古史似乎是被古人发明出来的,并且这种发明随着时间的积累越发显得扑朔迷离。
事实上,古史辨派对于神话与古史之关系的看法是建立在几个值得怀疑的具有内在矛盾的观点上。首先,作为过去的古史与作为对此古史之叙事的神话之间的矛盾。承认神话与古史之间存在距离,并不意味着神话叙事是虚构的。对于像恩斯特·卡希尔这样的哲学家而言,真正的神话实际上出自某种不依赖虚构的东西,某种在形式和实质方面都与虚构相对立的东西。[2]6究其原因,就在于神话思维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神圣因素使得任何虚构都成为对神灵的亵渎。对古人而言,神话可能比历史本身还要真实。其次,是时间与叙事之间的矛盾。“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是顾颉刚先生最为人所熟知的学说,其中心思想可概述为“古史的上限愈后愈长,古史的人物愈放愈大”。[3]换言之,历史叙事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距离古史真相愈来愈远。但按照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观点,时间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时间,仅仅是就其依照叙事的方式组织起来而言的;同样,叙事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就其描绘了时间经验的特征而言的。利科著名的历史叙事三阶段理论指出,任何叙事都包含预构、构造和重构三个模拟成分,这些模拟成分可以通过周期性运动创造一种叙述与现实之间的类比或形而上关系。[4]43据此,神话叙事之所以能够表征遥远的古史,其方式就好比比喻中的一个词语能够代表另一个词语的含义。
总之,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割裂了古史与神话之间的内在联系,对重建古史系统造成一定障碍。严格说来,“古史即神话”是对古史的一种人为遮蔽。古人之所以迟迟没有提出“神话”概念,是因为几千年来的人们本来就生活在神话中。历史用神话的方式讲述,是历史本身的要求。
文学人类学派倡导从“古史即神话”到“神话即古史”的研究范式转向,是基于中国本土神话学理论的逐渐成熟以及考古发掘所积累的大量物质遗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兴起的“神话热”思潮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为重建古史系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材料,而要解读这些材料,必须要掌握相关的神话理论。有鉴于此,文学人类学派积极倡导神话与考古的结合。夏史研究历来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共同关注,也是重建古史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所有被认为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址中均没有发现像殷墟遗址那样的文字记载,因此关于夏文化的研究始终难以达成共识。本文尝试以《山海经》中的“刑天”和“夏耕之尸”为中心,结合文学人类学派的“四重证据法”及大、小传统理论,对“神话即古史”的具体内涵进行阐释。
二、“刑天”与“夏耕之尸”的断首之谜
《山海经》叙述战争的一大特色,是突出表现战争双方首领之间的激烈冲突。《海外西经》和《大荒西经》中的“刑天”和“夏耕之尸”神话,其真实内涵可能与商革夏命有关,其文曰:“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5]191-192“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5]273
人类自古以来就对头颅赋予了特别的神圣意味。《释名》谓“头,独也,处体高而独尊也”,《春秋元命苞》谓“头者精明之主”。这种视头颅为精气之所居的思想,实际上源自一种更为古老的观念,即认为头颅为生命力之源泉。叶舒宪先生认为周人始祖后稷的“稷”字,其原始意义即为长有大头的象征生命力之源的谷神。[6]将谷穗的成熟饱满和人首的发育关联在一起,即为神话思维之典型特征。但由此导致的可怕结果是,用人首来祭谷、祭田的习俗开始出现于农业文明中。生活在我国云南南部的西盟佤族素有猎头习俗,直至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这里还出现过用人首祭谷以求丰收的骇人事件。佤族人认为:“头颅是神明和灵魂的居所。……它是灵魂和生命的象征,因而是可能向神提供的最珍贵的奉献;它贯注了人体所有的一切神秘,因而是神灵的化身。”[7]这一对佤族人头颅崇拜之深层信仰的理论提炼,将古老神话中被遮蔽的历史信息再一次激活。这启示我们,《山海经》作者之所以特别强调刑天、夏耕被断首的命运,其深层意蕴可能与头颅的特别神圣性有关。
对于受神话思维支配的古人来说,头颅既为神明和灵魂所居之处,所以欲消灭一个人,必从消灭他的头颅开始;同理,在战争中欲彻底征服敌方部族,最具震慑力的战术是首先消灭其首领。(1)卜辞恒见“多首”一词,其用法与“多君”“多正”“多长”相同,饶宗颐先生认为即“魁帅”之意。详见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卷四)》,《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居住在头颅中的神明并不会因头颅的脱离人体而消失,因此在战争中对于敌方首领及其头颅的处理往往会通过一种宗教手段。据《逸周书·克殷》,牧野之战,纣王自知大势已去,遂登鹿台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又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8]
在商纣王和二妻均已死去的情况下,周武王仍分别以“黄钺”和“玄钺”斩下他们的头颅,再悬之于太白旗和小白旗。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使用武器和旗帜的颜色,显然与这些颜色的神话内涵及其所象征的身份等级有关(2)“玄”“黄”二色,其原始意义与某种神话观念有关。叶舒宪先生认为玄黄二色之神圣性始于史前时期的先民对于玄玉和黄玉的尊崇。“玄”本指黑色,代表苍天(夜空)的颜色,“黄”代表大地的颜色,“天玄地黄”观念的形成,即是对此二色之神圣性的明确解读。详见叶舒宪:《玄黄赤白——古玉色价值谱系的大传统底蕴》,载《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世俘》对商纣王及其二妻之头颅的处理有更加具体的记载:“维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庙。……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首或入,燎于周庙。”[9]
陈梦家先生早已指出,《世俘》所载周武王用商纣王及其二妻之首燎祭于周庙之事,可通过康王时期的小盂鼎铭文(《集成》2839)得以证实。[10]可惜陈先生对此燎祭之深层内涵并没有进行解释。事实上,这篇铭文为西周荐俘献首或礼之实录,从中颇可证孔子“周因于殷礼”说法之不妄。
根据卜辞,商人在俘获方国首领后,会以之祭祀祖妣。辞例如下:
(1)□亥卜,羌二方白(伯)其用于祖丁父甲。(《合》26925)
(2)用危方甶于妣庚,王宾。(《合》28092)
辞例(1)是卜问是否用羌族的两位方伯祭祀祖丁、祖甲;辞例(2)的“甶”字,据《说文》为“鬼头”之意,故该辞为商王亲自贞卜是否用危方首领祭祀妣庚。祭祀仪式之后,商人还可能砍下这些方伯的头颅,在上面铸刻铭文。胡厚宣先生就曾识别出十一片刻有铭文的方伯头骨。[11]
对比《世俘》和小盂鼎铭文,可知周人的荐俘献首或礼完全本自商人。据小盂鼎铭文,此次盂与鬼方之间的战争规模空间,所俘获首或、虏、牛、马、车、玉等战利品数量为西周铜器铭文所仅见。但铭文重点记录的是在周庙举行的燎伐鬼方三首领,以褅祀周先王之事。从仪式之隆盛程度而言,似不亚于周武王克商后的燎祭仪式。盂对鬼方之战,几同于灭国。
总之,战争结束后在宗庙内举行隆重的荐俘献首或礼,是商周时期通行的宗教礼仪。仪式中除了向祖先报告胜利成果外,最为隆重的环节,是用敌方首领的头颅来祭祀祖先神灵。如前文所述,头颅为人的灵魂和神明所居之处,物理地砍伐并不能令其消散,是故必须采用宗教或巫术手段方能彻底令其消亡。商纣王及鬼方三首领的头颅之所以特别尊贵,就在于它们是部族至高权力和至上神所居之处。用先砍伐、后燎祭的手段处理这些头颅,是为了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完全征服其所代表的部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刑天和夏耕之尸的断首之谜解析如下:第一:在古人的观念中,头颅是生命力之源,是灵魂和神明的居所。断首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而不能令其灵魂和神明消散。刑天和夏耕在断首后仍能执干戚,操戈盾立,是先民用神话想象的方式将这种观念形象化;第二:人间的战争同时也是天上神灵之间的战争。在宗庙中用敌人首领的头颅燎祭祖先,是用厌胜之术彻底征服居住于这些头颅中的神明,以防止对本部族成员及祖先神灵构成潜在威胁。刑天被帝断首,意味着商人不仅在世俗的战争中取得了对夏人的胜利,而且其至上神帝同时也战胜了夏人的至上神天;第三:燎祭之后对头颅进行沉埋,是处理敌人头颅的最后一道程序。刑天的头颅被葬于常羊之山,夏耕的头颅被葬于章山,其中包含有商人在用夏人首领之头颅祭祀祖先后将之沉埋的历史信息。
三、“断首”与“革命”:商人抑夏与周人尊夏
如果上文对“刑天”“夏耕之尸”断首之谜的解说不误,则至少说明在《山海经》的成书时期,商革夏命的历史的确以神话方式流传着。这里使用“革命”一词,仅仅因为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革”之本义为鸟兽去毛之皮,其引申义“变革”“革除”的出现要晚至西周末期。“命”“令”二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写法相同,义亦相通。《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又云“令,发号也”。丁佛言认为甲骨文“令”字的上部像屋宇形,故令之本义为“朝庙受命者,恭承之义,象鄙恭也”[12]。白川静持论与丁氏相似,谓“‘令’形示头戴深深的礼帽、跪受神托之人”[13]。卜辞恒见“帝令”,说明令之本义确与至上神的神示有关。
事实上,“革命”乃“革天命”之省称。“天命”不见于卜辞。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集成》6104)有“肆文王受兹大令”之语,与《康诰》“天乃大命文王”、《诗·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句法相同,为“天命”意义之首见。此后如大盂鼎(《集成》2837)、询簋(《集成》4342)、毛公鼎(《集成》28413)等铭文均有文武膺受天命之说。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天命思想形成于西周时期。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有待商榷。周初文献虽盛称天命,但周人并没有将此思想视为自己的发明。西周中期的遂公盨铭文有“天命禹敷土”的记载,说明周人相信早在大禹治水时期就已经有了天命思想。
对周人而言,传说中夏的立国者大禹与周的立国者姬昌都曾接受过来自上天的神示。换言之,周人和夏人有着共同的至上神天神崇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商人信仰的至上神只有帝。殷墟卜辞既没有表示天命的词汇,所有的“天”字也不表示天神。对于这种现象,过去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在不考虑夏人的情况下,周人对天的信仰实际上脱胎于商人对帝的信仰;商周的至上神崇拜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过在商人则称之曰“帝”,在周人则称之曰“天”。时至今日,这一说法显然需要修正。我们的依据是:首先,由刑天神话可知,《山海经》的作者对于天和帝之间的敌对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二者之间不存在派生关系;其次,1977年发现的周原甲骨文中有“□告于天,甶亡咎”[14]的占辞,其句式与何尊铭文“隹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句式相同,这两处“天”明显指代天神,足以证明甲骨文“天”字的确有表示天神的意思。因此我们的解释是:天神和帝是同时并行的源自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至上神。天神崇拜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夏文化、先周文化及其相邻的文化均有此信仰;帝崇拜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先商文化是持有此信仰的主要族群。殷墟卜辞中之所以不见天神、天命观念,是因为商汤灭夏之后,对夏人的至上神及其作为天命接受者的历史采取了遮蔽和贬抑的态度。此外,《史记》中还有武乙射天、宋康王射天等商王及其后裔戮辱天神的事迹。而周人之所以在强调天、天命的同时,又保留商人的帝崇拜,是因为周人一方面要向西部地区的同盟者声明文王作为天命接受者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还要拉拢和安抚子姓的商人贵族,以稳定其在东部地区新建立的统治政权。
总之,“断首”和“革命”实为一事而两说。前者是东方系商人后裔对夏人及其至上神的一种贬抑,后者则是周人对商汤灭夏这一历史的抽象化表述。
四、“有夏”与“西邑”:文字小传统对夏文化的延续与遮蔽
按照文学人类学派的观点,小传统对大传统既有延续的一面,又有严重遮蔽的一面。所谓延续,是指小传统的一切文化基因均源自大传统;所谓遮蔽,是指小传统的文字符号对大传统文化具有筛选、过滤或加工改造的功能。[5]98-109以上文所讨论的“商人抑夏”和“周人尊夏”为例,商人由抑夏而在卜辞中拒绝保留有关天、天命的信息,并运用神话加工方式将夏人的至上神天神及其部落首领塑造成狼狈的失败者形象;以“有夏”自称的周人,则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延续了天、天命信仰,并对商汤灭夏的历史进行委婉地抽象化叙事,以此突出文王作为天命接受者的合法性。由此现象,启发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是:古文字学家在卜辞中苦苦求索而不得的“夏”字,是否与天神、天命一样遭受了被遮蔽和贬抑的结局?周人自称“有夏”,是出自文化和信仰的传承,还是别有用心的杜撰?
(一)周人自称“有夏”考
周人自称“有夏”,最早见诸《尚书》。《康诰》曰“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曰“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以下以《康诰》为例,对周人自称“有夏”的动机进行分析。
《康诰》中“区夏”的不同解释较多,皆由“区”字的纷歧而来。旧说多释为“区域”,后有释为“中”,释为“崎岖”,释为“虚”,释为“大”,释为“别”等等。[15]1305—1306按诸卜辞,当以“区域”说为妥。卜辞“區”字凡6见,释为地名或“区域”则通,释为他意则于辞意不符,如以下辞例:
(3)贞:王其狩区?(《合》685)

第(3)辞的“区”为地名,故该辞是在贞问王是否要在此地狩猎。第(4)(5)两辞中的“区”字,明显为区域意。和弜是卜辞中常见的商王室附属族群,据此可知,在部族名称后接“区”以表示特定区域,是商代既有的用法。《康诰》中“区夏”一词,也当作如是解。刘起釪先生指出,不言“夏区”而言“区夏”,是古代词汇的一个表现形式。《荀子·大略》“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文选·东京赋》“目察区陬”,“区盖”“区陬”用法与“区夏”同,[15]1306因此“区夏”即为“夏族所在的区域”。
再来看“用肇造我区夏”中的“肇”字。古今学者都将“肇”字释为“始”,无人提出疑义,所以这句话就被理解成“开始建造我华夏地区”。但如果从这句话出现的语境来体会周公的意图,那么将“肇”字释为“始”将显得轩轾难通:“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衹衹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尚书·康诰》)
在《康诰》中,周公追述文王创业的经过可分为三个阶段:修德以肇造区夏,联友邦以修西土,受天命以殪戎殷。区夏为夏族所居之区域,已见上文。西土即周族所居之陕西故地,《左传·昭公九年》曰:“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戎殷之“戎”字,有释为“大”者,有释为“伐”者,实际上此处当取“戎狄”之“戎”义(详后文)。由此观之,区夏、西土、戎殷分别指称夏、周、商三族所居之地而言。若将“肇”字释为“始”义,则夏族之建造必非始于文王。笔者认为,“肇”字,此处当释为“恭承”或“绍继”之义,“用肇造我区夏”,即“用文王美好的德行,继续建造夏族之区域”,如此则周公的追述从恭承夏族之遗业,到扩大西土之范围,最后一举克商,层层推进,逻辑清晰。
总之,《康诰》以周公追述文王“用肇造我区夏”的事迹,将周人延续夏文化的意图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周公还特别使用了一个具有贬义的“戎”字来形容殷族。《说文》谓“戎,兵也。从戈从甲”,徐中舒先生解释说“古戎族善用戈盾,故称之为戎”[16]。对周人而言,用暴力手段推翻夏族而占据中原位置的殷族无异于戎人。刑天、夏耕之尸神话中的断首情节说明殷人的确有尚武传统。周人既以有夏自称,就必须代替商人而重新占据此“中国”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武王在推翻商人政权后要迫切地在伊洛之间建立都城,实因此地为“有夏之居”,是“天命”之象征。反过来对商人而言,要想彻底摧毁夏人的王权统治,就必须将夏人从此中原之地驱逐出去。《夏本纪》曰“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尚书·仲虺之诰》曰“成汤伐桀,放于南巢”,鸣条、南巢之地究在何处,迄无定论。但通过刑天舞干戚、夏耕操戈盾立的情节,可推知商人对夏族的征服并不彻底,夏族的神灵及其后裔还在时时威胁于商人。(3)笔者曾对小屯南地甲骨中出现的方国数目进行过统计,发现武乙、文丁时期受征伐的方国至少有14个,分别是方、召方、竹、土方、商、夷方、井方、轡方、羌方、龙方、蝉方、絴方、大方、北方。这14个方国除北方位于殷都以北、商丘位于殷都东南外,其余12个方国都是在殷都以西沿黄河分布。这些方国不乏夏的后裔及其追随者。而笃信鬼神的商人必将此种忧患表现于卜辞中,这一信息可能就隐藏在一个名为“西邑”的地名中。
(二)“西邑”考
卜辞中的“西邑”见于以下辞例:
(6)贞:于西邑?(《合》7863)
(7)西邑害?(《合》7864)


(9)贞:燎于西邑?(《合》615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有一篇《尹诰》的竹书,其中“隹尹既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17]一句,与《礼记·缁衣》“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以及《尚书·太甲》“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所记略同。三处引文均提到伊尹和一个名为“西邑夏”的地方,李学勤先生认为此“西邑夏”与卜辞中出现的“西邑”为同一地名,均指夏而言。[18]台湾的蔡哲茂先生利用传世文献和卜辞进行比较,指出卜辞中的西邑就是夏,而且是夏最早的王都。[19]
卜辞不见“北邑”“南邑”“东邑”,而只有“西邑”,这就足见西邑在殷商时期确指某个特定区域。在传世文献中,西邑夏与伊尹往往同时出现,上引第(8)辞也将西邑与黄尹对贞,而黄尹已被证实就是帮助商汤灭夏的伊尹,(4)卜辞中“黄尹”为“伊尹”之说,王国维、郭沫若、商承祚、唐兰、陈梦家、岛邦男均有论述,详见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濮茅左、顾伟良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60—468页。这就进一步证明西邑和西邑夏确为同一地名,二者与夏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商王为何要将夏称为西邑?蔡先生引刘桓先生的观点,认为夏朝后期政治中心开始向西转移,西部地区由此被称为夏。这一说法,实有进一步商榷之余地。
笔者认为,《尹诰》《太甲》《缁衣》三篇文献都是站在商人立场来追述商汤灭夏的丰功伟绩,其意义与《康诰》中周公追述文王创业的事迹相同,所以“西邑夏”的称谓与“戎殷”的称谓类似,都含有对前代政权的一种贬抑。只不过《尹诰》等三篇文献的出现已晚至战国时期,距离商汤灭夏相去甚远,而此时即使是商人的后裔也开始使用“夏”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如“夏耕”)。但在武丁时代,“夏”还和“天”“天命”一样,是一个象征前代至高神权的神圣词汇,商人是绝不可能在卜辞中使用这些词汇的。那为什么要用“西邑”来代称“夏”呢?这也许可以从“戎殷” “戎狄”“荆楚”“淮夷”这些称谓中找到答案。窃以为“戎”“荆”“淮”这些前缀是用来表征“殷”“狄”“楚”“夷”等这些部族的发源地。《左传·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对楚灵王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是故荆楚之得名,实因楚人发迹自荆山。以此类推,西邑夏之得名,也当是因为夏部族发源自西邑的缘故。
既然西邑为夏之发源地,那么其地望必定位于殷墟西部地区。蔡茂哲先生认为“夏王朝的故地可能还是主要由琮(崇)侯控制,其地应在伊、洛地区。琮(崇)侯可能是夏裔,犹如周灭商后,封殷之后于宋一样,是一种安抚笼络、便于统治的方式。其后琮(崇)侯为周所灭,夏之后裔只剩‘杞、缯犹在’。”[19]笔者赞同蔡先生的观点。《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云:“鲧封于崇。”《周本纪》正义引皇甫谧云崇“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又《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云“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崇伯又称鲧伯,故崇、鲧通假。甲骨文无崇字而有鲧字,当做地名,卜辞显示商王经常出现在此地,第四期卜辞中出现了“鲧伯”《南明》472),伯是商王所分封的一个地方首领,因此鲧伯就是鲧地伯一级的首领。
如西邑为夏之发源地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西邑就是鲧地,也就是文献所记的崇地。商汤灭夏后将夏之后裔迁徙至其发源地西邑,于是西邑再一次成为夏人的栖身之所。生活在西邑的夏人后裔在武丁至武乙时期迫于商王室强大的压力,开始积极向商王室靠拢,由此得到封伯之赐。对商王室而言,由于和西邑建立了正式的同盟关系,于是“鲧”开始取代“西邑”这一含有贬义的称谓。因此,西邑、西邑夏、崇、鲧异名而同地,均指建立夏王朝的首领鲧禹的发源之地。
又据《史记·殷本纪》,纣王无道,醢九侯,脯鄂侯,西伯闻而叹之。崇侯虎告之以纣,于是纣王囚西伯于羑里。据此可知崇侯在殷商晚期已经成为商王室监督西方诸族的一支重要力量。《诗经·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等到文王图“翦商”大业时,位于秦晋之间的崇就成为文王东进的第一个障碍,故先伐之。那么,在秦晋之间是否存在一个被西伯所消灭的崇伯鲧之国的?
1985年至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西安东郊21公里处的灞河北岸老牛坡村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共计发掘面积为5000平方米。[20]1-2从地理位置而言,老牛坡位于陕西渭水盆地东部,是古代关中东出潼关,南去丹淅和江汉地区的咽喉要冲,这与文献所记位于秦、晋之间为崇国的地望相符,所以李学勤先生在老牛坡遗址发掘不久之后就指出,就历史地理而言,老牛坡很可能属于崇国。[21]
综上所述,“有夏”和“西邑”异名而实质,是商周之前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王权的夏王朝的代称。(5)需要做出区分的是,“夏”的地域范围要远远大于“西邑”,夏是源自西邑的部族建立的政权的称谓,西邑则是这一部族的发源地;“西邑夏”是商汤灭夏后对安置在西邑的夏人后裔的称谓;西邑又称谓“鲧”或“崇”,是因为夏人的始祖崇伯鲧曾受封于此地。《方言》第一云:“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李元昊将自己的国号定为“大夏”,除了宣示自己乃圣人之后外,大和夏连称还有一种夸饰的意味。笔者颇疑“大夏”或由“天夏”而来,甲骨文“天”字和“大”字写法十分接近。天本来就含有大义,商人虽然排斥“天”的天神之意,但却保留了大义,如“天邑商”(《合》36535)就是大邑商。周人由尊夏而延续了天、天命、夏等词汇的神圣内涵,商人由抑夏而用用大、西邑等词汇遮蔽、掩盖了这些词汇的神圣性。由此看来,孔子时代流行的“春秋”笔法,早在商和西周的史官那里就已见端倪。
五、余论
今天的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于夏史的研究依然遵循着新旧两种思维模式。旧思维模式认为要证明夏的存在,只有通过文字证据;新思维模式则认为夏的存在不必仰仗文字证据,通过考古实物同样可以得到求证。
事实上,正如某些研究所显示的,甲骨文的诞生是商人的占卜传统在商代中晚期理性化的结果,[22]其原始功能仅仅是作为传达祖先神示的一种工具,使用范围非常有限。所以希望通过寻找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来证实夏朝存在的方法,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退一步说,即使夏朝时期已经形成了文字,那也是与商代甲骨文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字体系。因为就甲骨文在商人生活中占有绝对崇高的神圣地位而言,商人是不可能使用前代的文字与自己的祖先神灵进行沟通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字在求证夏史的过程中无用武之地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倡导神话即历史的研究范式转向,首先就是利用古老的文献记载来回溯到文字诞生以前的大传统时代。夏代的特殊性在于,它正处在文字诞生的前夜。尽管商人的甲骨文和周人的铜器铭文大都是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与祖先神灵沟通的媒介,但在数量极其有限的记载中,我们还是捕捉到了关于夏代的一些蛛丝马迹,文字的神圣性又使得这些额外的馈赠显得无比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