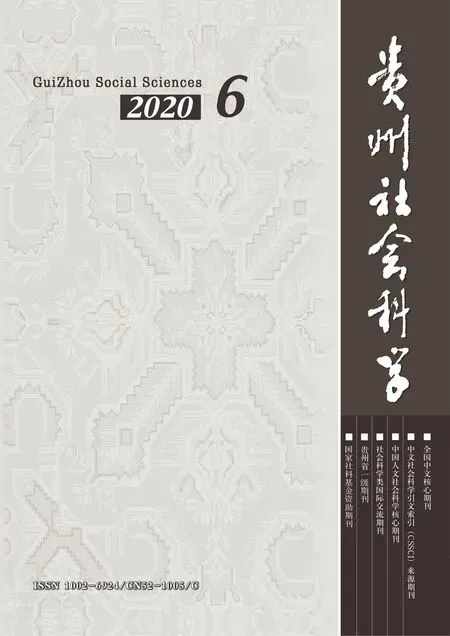“结丝”何以“织史”>
——早期中国桑蚕丝帛神话的编码与解码
公维军
(江苏大学,江苏 镇江 212013)
丝帛作为包括绫、罗、绸、缎、绢等在内的整个桑蚕丝织品总称,上古时期曾与美玉并称神话信仰之“精”,即所谓“玉帛为二精”,因而丝绸作为“丝绸之路”(亦称“玉帛之路”)通道上维系中西贸易不可替代的主导物品之一,其起源神圣意涵、货币流通作用等都是同为“精物”的美玉以外的其他物品难以企及的。由此观之,无论言及早期中国桑蚕丝帛神话的起源还是流动,其自身皆内蕴有一套完整的原生性编码,而文化大传统视域下的神圣思维观念既是主宰这些编码符号的基本原则,又是无法绕过的解码关键。
一、桑林圣所:桑、蚕、丝、帛神话叙事链的文化基因场
时至今日,能够表征人类群体“文化本性”但尚未完全被发掘的文化基因,正在凭依其更显理性的认知与阐释新视角,为文学人类学在大传统视域下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表达路径。应当明确的是,“文化基因的存在形式应该是一系列的文化编码,它不一定是生物基因的双螺旋体的编码排列,不一定具有如生物基因那样准确的复制功能及自我复制的原始动能,重要的是,要在这样的认识中深刻理解文化及其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借喻生物基因的自我复制功能来想象性地‘类比’文化基因”[1]。就华夏文明之桑、蚕、丝、帛神话而言,需要诉诸神话现象表层充分解码那些潜隐在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神话编码。鉴于充足的桑叶为蚕提供着食物来源,进而才有蚕吐丝作茧、人类缫丝织帛的前后相继行为发生,这就使得桑林成为探寻完整神话叙事链文化基因的首选圣所,人类的“结丝织史”神话观也正是基于此类特定的文化场域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西方语境下的神桑故事得以流传于今,能够反映出古希腊罗马神话的活态传承更多需要仰赖史诗和悲剧的基本事实。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神话偏重“实用理性”,巫术意味浓厚。从比较神话学视角看,中国古代的桑林不只是蚕桑生产的原料供应地,更是先民举行重大巫术活动的神圣场所,基于“实用理性”观念分析,可以将其归纳为三类:一是王者巫觋在桑林中举行盛大的祭天求雨活动,以消弭时灾;二是桑林之域男女欢合,祀高媒神,以达成求子之愿;三是攀登扶桑神树升天,以实现天地神人沟通之效。
尽管诸如《管子》《墨子》《荀子》《淮南子》等早期经典中显见商汤桑林祷雨的记载,但其中故事叙述最完整者当属《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翦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2]商汤将自身置于桑林神圣场域之中祭天求雨,意图以神桑之树作中介物进而沟通天帝神鬼、庇佑臣民的行为,以今人视角看似荒诞无稽,但“愈是野蛮粗野的似若不可信的,倒愈是近于真实”[3],这恰恰契合商汤“祭师王”的神圣巫觋角色。
就桑树而言,人们采摘桑叶之后,它们能够很快再次生长出来,成为旺盛生命力的不竭象征,因此,桑林一度成为男女幽合、祭祀高媒的场所。观“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墨子·明鬼下》)便可知,桑林并非唯一场所,古时的祖泽、齐社、云梦泽等也都具有此类属性。在先民的思维观念中,男女在桑林之所交合能够得到高媒神的恩赐,参与到生命的奥秘以及宇宙的生殖力之中,如此一来,受孕生育的目的才能实现。
如果从中国考古发现中寻觅高媒神踪迹,或可溯及新石器时代晚期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多件素有“东方维纳斯”美誉的女性小塑像,“双乳凸起,双臂收拢贴于腹前,腹部微隆,背部向内凹进,背两侧有弧形线条。此人像塑件具明显女性特征。人像通体压磨光滑,主体部分未见着有服饰。”[4]显然,此类裸体女性塑像是红山文化先民普遍信奉的女神形象,隆起的乳房、前凸的腹部、肥大的双臀,加之双手贴靠腹部的抚摸举动,这些显性特征无一不在刻意表现女性的孕育之态,而这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裸体圆雕女神像特征极为相似,由此反映出的生殖崇拜观念与祭祀高媒行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成汤祷雨与高媒之祀外,扶桑神话也是中国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扶桑是华夏神话中象征太阳神的生命之树,据《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该神树生长在东海中的汤谷之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袁珂案:汤谷,或作旸谷。[5]而《淮南子·天文训》载:“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此处之“日”即传说中的太阳神鸟,它们仅仅是飞行过程中经过扶桑,浴于咸池,真正的起飞地是旸谷。但扶桑神树绝非凭空想象出来的意象,在先民的神话思维中,大树正是古代巫觋贯通天地的主要依凭手段之一,其原型当源自现实生活中的繁茂之桑。
从考古学证据看,扶桑形象体现得更为明显。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8株青铜神树,其中二号祭祀坑出土的Ⅰ号神树通高3.96米,树干残高3.59米,由底座、树干和神龙三部分组成。穹窿形底座构拟出三座神山相连意象,饰有太阳纹和云气纹;树干直立于底座之上,共分三层九枝,每枝之上均有一扬两垂三枚花果,九只神鸟立于扬果之上;树干旁侧一条游龙蜿蜒而下,造型诡谲怪异。目前学术界更倾向于将该神树解读为扶桑,神树之上所铸九只立鸟当是“拂于扶桑”的太阳神鸟,符合扶桑“上有十日”的显著特征,此处缺失的一只或许原来铸立于神树顶端,后损毁遗失,但更有可能是铸造者的刻意表现,毕竟比较神话学视域下需要一只太阳神鸟在天上值班。神树能够真实再现古蜀先民的太阳崇拜观念,而楚地巫觋能够依凭扶桑之树实现“通天”之举,从而沟通天地神俗两界,祈请神灵降临世间庇佑子民。自上而下绕树游弋的神龙,或许是巫觋攀登扶桑升天的驾乘,由此更增添了通天、通神、通灵的神圣氛围。
事实上,在文、史、哲等人文划分的学科界限逐渐被打破以后,神话编码的文化功能意义才能够得以鲜活再现。列维-斯特劳斯早已注意到,“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将它构想为神话的一种延续而绝非与神话完全分离的历史,那么,在我们心智之中萦回不去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鸿沟,还是有可能被冲破的”。[6]无论是成汤祷雨、敬祀高媒,还是借扶桑神树实现天地沟通,在桑林所举行的神圣礼仪活动中,公共参与的不可抗拒感足以使个体借助于他人的在场而感觉仪式的完整性。随着场域中神秘力量的增强,逐渐建构起一种更高的神圣秩序让先民倍感诸神光辉的笼罩,而桑林作为桑、蚕、丝、帛整个神话叙事链文化基因表述的首要环节与神圣场所,直接影响着后续以蚕为神观念的深度想象。
二、蚕为龙精:破译“蚕理”的神圣密码

荀子借五泰(即五帝)占验直接点明蚕所具有的神秘性特征:一是“冬伏夏游”,冬天具有休眠性状,同蝉、蛇、熊一样属于先民心目中生命周期循环往复的蛰虫或蛰兽,寓意生命的死而再生;二是“食桑吐丝”,神力可见一斑,这种身具“特异”功能的神物潜含着超自然的无穷生命力;三是“三俯三起”,此可视作蚕生命变化的绝佳写照,自飞蛾产卵,首变“蚁蚕”,次吐丝结茧,再缫丝成帛,“事乃大已”。可以说,“蚕卵—蚁蚕—熟蚕—食桑—吐丝—结茧—成蛾”的整个生命形态变化过程,就是蚕“屡化如神”的完美幻化旅程,可视作宇宙生命循环无穷变化的典范,所承载的神话观念就是生命的变与不变,在某种意义上讲,商代的蚕神崇拜可谓与此同源。

此外,先民对于蚕神话化表现的认识更是同华夏文明中最具代表性与象征性的图腾动物——龙紧密联系在一起,“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蠾,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9]827蚕、龙两种神性动物都是时令性动物,区别在于蚕是现实生活中触手可及且肉眼可观的实体动物,而龙则是神话想象中不见首尾但无所不能的幻化动物。如此一来,上天入渊的龙与“屡化如神”的蚕完全能够实现形体上的置换,神龙变小即可化为蚕蠾,而东汉郑玄在为“禁原蚕者”(《周礼·夏官·马质》)所作注曰“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再蚕者,为伤马与’”。[10]可见,“蚕为龙精”的神圣性表述意在阐明一个基本事实:蚕是龙的精缩之物!
远古之时,初民将遵从时令季节变化视作男耕女织活动的关键所在,郑氏所引《蚕书》也是基于此进行解释。龙自不待说,古人将“春分登天,秋分潜渊”的神龙视作时令之神的化身,这与蚕“冬伏夏游”“夏生恶暑”的季节性特点相同,所以《蚕书》特别指出待大火星(即辰星)出现,方为浴蚕种的最佳时机,等到蚕宝将要出生时再次浴种,但因蚕、马同属于东方苍龙七宿中的房星(即天驷星),“蚕马同气”而“物莫能两大”,即通常情况下桑蚕业兴旺之年,往往容易损耗马匹的元气而致使养马业受损,所以禁止一年之内生产两季蚕茧。上古时代,人们对于先蚕(蚕神)概念中的神格意识非常强烈,有学者曾将春天始蚕的时令性行为进一步引申,“既行祭于上天主育之神,又享祀于人间育蚕之母,从而在天地神人之间获得一种精神与信息的沟通,以期来行为的最佳功效”[11],在先蚕与房星的对应关系中是否兼具生育之寓义,大可暂留探讨余地。但当时广为流传的“禁原蚕”礼俗禁忌,却能在蚕、龙二物身上有效彰显初民神话思维中的时令性特点。
无论是郑玄引注“蚕为龙精”的东汉,还是荀子阐述“蚕理”、管子描述“龙化蚕蠾”的战国,抑或更早将蚕神祭祀以卜辞形式刻于甲骨之上的殷商,虽然这些时期已经将蚕神信仰的神话思维以文字形式记录保留下来,但从先于文字和外于文字记载的文化大传统视角审视,显然其观念渊源需大大向前追溯,甚至一直远至有玉蚕实物、蚕形图像等第四重证据出土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在比红山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的淮河流域蚌埠双墩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从出土陶器中发现了大量刻符,其中,蚕是先民重点强调的动物形象之一。这些描摹蚕的刻画符号虽然看似抽象,但在陶胚表面留下的刻道却异常清楚,故而蚕的形象生动逼真,例如标本86T0820③:2是一件底径8厘米、矮圈足底完整且微凹的陶碗,“外底部刻有蚕形与相对多弧线形构成组合形符号,似表示一条横卧的蚕正在昂首吐丝结茧”。[12]该刻符将蚕的形象、蚕吐丝结茧的形象同时表现出来,而这种组合形象的重要价值就在于直观再现了先民对蚕具备的非凡神性的神话式理解,以及对其吐丝结茧现象的神话式想象。
1991年,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北区M2009中出土了一件造型别致的玉龙蚕,白玉蚕躯阴线刻画八个腹节,昂首张口,菱目圆珠,头部有角,一只飞鸟立于蚕部,或许是有意衬托其在天地间自由置换的形态,形象栩栩如生。在先民的意识形态中,龙小即化为蚕蠾,制作者通过玉龙蚕这一物的叙事,既将蚕与龙的屈曲之躯、昂首之态表现得活灵活现,又将先民对于二者生命幻化的神话观念表露无遗。作为生命之神的化身、时令之神的代表,这件龙蚕合体、神话与现实切换自如的罕见玉器,是目前已知最早代表龙与蚕关系的出土实物,完全称得上是“蚕为龙精”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展示中华民族玉文化、蚕文化、龙文化彼此交融的考古典例。“蚕为龙精”的神话表述,正是先民基于切身利益,祈请蚕神降神力以佑护桑茂蚕丰的特定表达。先民将龙、蚕两种神性动物与通灵之玉完美结合在一起,是希望能够以此表达心中祈求蚕神、龙神庇佑的信仰观念。
三、蚕鸮于钺:死而再生的神话隐喻
毋庸置疑,蚕在整个华夏先民的桑、蚕、丝、帛神话叙事链中处在最关键的环节,桑林圣所为其提供了维系生命与神力的动力之源,神蚕吐丝的神秘行为被先民视作蚕神恩赐生命能量于己的施恩方式,人们又将缫丝织造的帛回报神灵,因为也唯有“精物”之帛才能与神明所赐蚕丝能够在生命能量上真正实现转换。“在人对神的表示方面,玉器和丝绸的物理特性都足以代表‘明洁’的虔敬和庄重,遂能成为首屈一指的‘显圣物’……国家祭祀活动的第一要务是圣王对待神明的虔诚专一态度,第二要务就是玉帛所代表的献给神的珍贵祭品”[13],和美玉一样,丝帛亦充当起神人沟通必须的物质中介角色。如此一来,便可以解释后世帝王展示与象征权力的圣旨为何一定选用上好蚕丝,藏、蒙两族同胞又为何选用优质蚕丝织成的哈达进行礼佛与迎客,当然更能够解释早期国家祭祀礼仪的核心物质紧紧围绕着玉帛的所以然问题。
“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9]634美玉、黄金、天马三种“外来之物”,皆源自异域或异国,而帛为东方的“原生之物”,依照贵远贱近原则,比较容易解释这种现象。同样,对于缺乏丝绸的西亚、欧洲而言,东来的丝帛会被他们视为比黄金、天马更为珍贵之物,甚至还会被文化传播接受方进一步神话化,这从《大唐西域记》描述的瞿萨旦那王通过远嫁本国的唐朝公主私带蚕种的“东帛西输”故事,便可一目了然:“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14]
瞿萨旦那国为此备礼奉迎,后以制度形式保护桑蚕,并且为先蚕专建伽蓝,以虔诚举措求得蚕神佑护。更有意思的是,这则“蚕种西传”的神奇故事竟能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丹丹乌里克唐代佛教遗址中发现的木板画内容实现相互印证,被命名为《传丝公主》的彩色木版画还原再现了“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的生动场景。
从比较神话学视角分析,美玉、黄金、天马、丝帛这四种物质原本并没有排序上的先后之分,它们最初都是先被神话化,然后才具有了宝贵的价值,换言之,是神话观念驱动了这些资源的意义生成。再观《管子·山权数》:“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筴之者也。”[9]1309假如布帛在齐桓公时代被视为无价值的通俗之物,那么统治者为何会给予每位“蚕医”一斤黄金、八石粮食甚至免于兵役的奖赏,还要将此事定为国家层面的理财之策呢?显然,对古籍文献中的文字记载刻意进行单线条地解读已不合时宜,必然会造成阐释的片面化甚至于误读,也就无法更准确地去挖掘文本背后隐藏的大传统知识。
事实上,丝帛所获得的神秘生命能量是与蚕的死而再生神话隐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期典籍中以“币帛”“束帛”“布帛”“缯帛”“缦帛”等行祭祀或馈赠之礼,都是仪式参与者意在通过作为祭品或礼品的丝绸实现自我的圣化,“为自己创造一个超越凡人的状态,创造一个也许可以被比作古代社会仪式结果的结果”[15]115,毕竟先民普遍希望能够在神圣的祭祀场域中获得神助。丝帛这种特殊的物质材料之所以被赋予超自然的生命力,归根结底源于帛为蚕所化生的因果联系,正是先民神话观念中蚕“屡化为神”的死而再生特征,才促使着丝帛生命之精的循环流转。因此,祭祀仪式中的献帛祭神、馈赠仪式中的丝帛赏赐与回报,都是伴随着“物”的转移实现“精”(即生命力)的流转之体现。
1993-1998年,考古人员在江苏金坛西岗三星村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特殊的珍贵石钺,钺色灰白,上窄下宽,顶部弧平,中部厚实,双面凿孔,木制钺柄已朽烂无存。从侧视钺饰观之,其呈现为一种动物形象,躯体呈屈曲之状,高高昂起的脑袋,圆圆的眼睛,细密的对足,再加上遍布身体两侧的圆圈纹。事实上,这些全部符合蚕的典型性特征,其中圆圈纹所象征的正是蚕用于呼吸的气门,将其解读为蚕应更合乎情理。而将石钺镦饰部分的动物形象释读为鸮(即猫头鹰)已渐成学界共识,一双又大又圆的漩涡眼、眼睛周围刻画的变化旋转的刻纹与钩喙等显性特征,均能为鸮面镦饰提供阐释效力充足的证据。上古之时,钺同西方的权杖一样,象征着王者专享的威仪与权力,所以这件石钺的神圣性不容小觑,精美的钺饰、镦饰皆为此提供着有力佐证。
这件蚕、鸮、钺三位一体的仪式工具究竟蕴含着何种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呢?答案需要到蚕、鸮神话中去找寻,毕竟二者潜含着相同的神话隐喻。蚕是一种具有休眠性特征的蛰虫,在先民朴素的经验观察中,其生命变化节奏与季节时令相符合,所以此类循环性的冬眠蛰伏现象普遍被视作神灵的死而再生。不仅如此,“据新石器时代宗教神话的通则,大凡具有再生特征的神灵都被归结为女神——母神一类”[16],在先民看来,母体才是生命再生产的承担者。根据神话类比原则,蚕的吐丝结茧、破茧成蛾如同母体孕育后代一样,这就被神话思维理解为体现蚕女神神力的复活或者再生,而流传后世的嫘祖始蚕、蚕神马头娘、蚕花娘娘、蚕丝仙姑等神话传说中也能够反映出再生蚕女神的化身痕迹。
鸮被视为死而再生女神已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中西史前神话想象中都存在并延续着将鸮视为死而再生女神的文化基因。先民将蚕、鸮与象征神圣王权的钺结合在一起,将蚕鸮神话的死而再生隐喻呈现得淋漓尽致。石钺之上特意装饰蚕饰、鸮饰,当然有王者专司蚕桑之事,亲祀蚕神以求蚕业旺达之意,但其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意义依然是获得神灵的认同,进而求取神灵赐予的生命能量,而这“对于所有的古代社会来说,对精神灵性的认同是在死亡和一次新的再生中表现出来的”[15]111,这种生命力与人类学者广为关注的波利尼西亚人信奉的“马纳”、新西兰毛利人信奉的“豪”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皆是信奉或追求一种神力、“精魂”。
四、小结:大传统视域下桑蚕丝帛神话的编码序列还原
结构主义神话学认为,物质文化象征性的编码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丝帛能够在华夏文明中受到特殊礼遇,充分表明其编码与再编码的神化过程以及历史序列得以清晰呈现。从史前陶蚕刻符、玉蚕,到商周卧蚕纹龙形玉佩、玉龙蚕,再到汉代的丝缕玉衣、帛画,均可视为一级编码即物与图像表现神话编码,这种原型编码形式将桑、蚕、丝、帛结合为一个整体,使整条神话叙事链得以传承延续;待甲骨文、金文、帛书、简牍这些地下出土文字中出现“桑”“蚕”“丝”“帛”等字形时,二级编码打通了书写小传统的门径,蚕神信仰观念、丝帛的死而再生意义亦变得更加抽象化;“玉帛为二精”“化干戈为玉帛”“蚕为龙精”等载于古籍原典中的书面文字,则统归三级编码,这些文本编码不得不仰赖大传统视域下的物与图像叙事才能阐明背后的意涵。而后世围绕桑、蚕、丝、帛神话展开的一系列文本创作,均可视为帛的“N级编码”。由此可知,欲还原“结丝知史”的神话编码序列,就必须从小传统回归大传统,有效发挥一级编码的文化文本阐释力,进而“以空间维度为视角,结合时间维度,建立起多维交织的立体时空”[17]。
显然,源自史前文化大传统的神话思维,是华夏文明起源的观念驱动要素,也是文化文本符号编码需要遵循的模式与动力。虽然我们透过早期经典文本尚能观察到一些属于经济范畴内的丝绸贸易现象,但是当求助于一级编码的阐释效应时,就必然发现需要重新激活与桑蚕丝帛神话起源有关的想象与象征,此时丝帛就会变为神圣之物,具有了“显圣物”特质。而“因为神圣之物本身就是一种与起源的联结,它们作为个人和群体的起源,体现于自己在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中所占的位置上”[18],所以“物精”之帛就会进入权力的宗教领域,发挥出重要的社会——宗教作用,进而获得更大的符号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