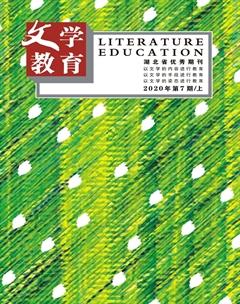批评的力度与温度
王彪

批评是一项基于知识与理性而进行判断的科学活动,但这并不能让其脱身于批评对象与批评家的个人体验,成为一门完全独立客观的创造性事业。批评何在与批评何为是每个批评家都要躬身自省的问题。作为70后批评家中的佼佼者,周新民教授用他二十余年的批评实践回答着这些问题,彰显了学院派批评的力度与温度。在周教授那里,力度即是在文学史视野中藉借理论洞见与逻辑思辨所作出的学理分析;温度则是带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批评中“人学”的尺度、对“文学性”的重视以及谦逊真诚的对话姿态。他以当代小说为对象的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小说文本的学理批评;与小说家的对话批评;小说理论批评史的谱系建构。这其中皆可见其力度与温度兼容的批评特色。
一
“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批评家的创造性活动”[1],因此对批评家生命体验的追踪是理解其批评的一把钥匙。周教授1972年生,湖北浠水人。他与陈沆、陈曾寿、闻一多、徐复观等近现代浠水人物一同分享着这里蔚然成风的文教氛围,也领受了险山胜水滋养出的那种耿直倔强的文化性格。从乡镇的农家子弟到地方师范学校的文艺青年,再到省城武汉攻读硕士、博士、博士后,他的人生之路走得并不容易,却也踏踏实实有迹可循。那种倔强勤恳、不服输、不断突破自我的奋斗精神尤其让人印象深刻。我想这种甘坐冷板凳的定力与永不自满的求知欲是人文学者所应有的基本品质。正有赖于这种孜孜不懈的精神支撑,他才廿年一日地在批评领域披荆斩棘、不断开拓;也正是这艰难旅途中对世事人生的深切体验才让其对文学多一份感受力,给批评增了几分厚重感。
周教授专业的学术训练始于文艺学。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文艺方法、观念更新重塑的时期,在经济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后现代各色文艺思想蜂拥而入。当时因未上理想学校而陷入苦闷的周教授在偶然接受现代美学的洗礼后便沉浸其中。从最初对克罗齐、苏珊·朗格等的零散阅读到就读研究生后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研习,周教授在文艺学上所受的影响与专业训练长达十年。这种专注理论的学术训练不仅提升了他对事物观察的思辨力与洞穿力,也逐渐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影响着其后来文学批评的视野与理路:“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这种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吸引了我去阅读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观察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我所写的文学批评论文,基本上有着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痕迹。”[2]当然理论的“片面深刻”与“观念演绎”等特质也给他之后的批评带来不少困扰。
於可训先生曾说:“新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原本是学文艺学的,后来到我门下‘被迫转向现当代文学,就像当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样,虽然吃了一些苦头,但也颇见成效。”[3]吃的苦头和所见成效是事实,而“被迫”则是先生常有的幽默戏说了。其实周教授的转向是结合自身专业背景的主动为之。早在1998年秋冬之际,确定要考博的他对中国当代文论界走马观花的引介西方理论,缺乏思考与创造性而陷入的“失语症”产生怀疑。与其做西方文论的“二道贩子”,不如“用西方学术资源解决中国本土的文学问题”。于是便决心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受西方后现代影响的新时期文学上。翌年,他便考入武汉大学追随著名学者於可训先生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如果说硕士期间的系统研习为其打下坚实的理论素养,那博士期间的艰难“改造”则使其获得了文学史视野。从早期的《论后现代写作的合理性》(2000)到这一时期的批评实践,我们明显看出那种简单的理论演绎与阐释的退潮,史学的视野与文学的特质在其批评中凸显。
当然最能呈现他这一时期研究特色的当然是博士论文《“人”的出场与嬗变——近20年来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2002)。该论文借助福柯话语理论与谱系学分析方法,在文学史视野与文本细读中对新时期小说中“人的话语”的重生、发展与演变作学理性整体考察,呈现出社会历史变革中“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背后的动态过程与复杂面目。在这项研究中周教授的理论素养与谱系学研究方法都在文学史视野中得到整合,文本细读的功力也日见精纯。也正是在这项研究中周教授将“人学”在文艺理论及文学史的视野中整合,成为其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尺度。“文学是人学”,对文学进行阐释、解读的文学批评当然不能忽视人的维度。此后周教授也一直秉持“人学”尺度对作品作学理性反思,诸如《个人历史性维度的书写——王安忆近期小说中的“个人”》(2003)、《生命意识的逃逸——苏童小说中历史与个人关系》(2004)、《圣天门口:对激进主义文化的多维反思》(2007)、《自然:人类的自我救赎——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2007)等等,都是从个体的生命意识、道德尺度、自然尺度来反思在历史、革命、自然中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於可训先生才称周教授为“以‘人学为本的批评家”。
另一面,他也意识到文学批评并不是简单的理论或观念的演绎,批评对象的本质属性才是批评家更应该关注的。文学得以自立在于其“文学性”,因此小说的文体形式成为其批评的着力点。其实早在硕士之前他就特别关注西方的形式主义理论,胡亚敏教授的《叙事学》更是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隐秘茎蔓结出的第一个果实便是《由“角色”向“叙述者”的偏移——“十七年”第一人称叙事小说论》(2001)。此文虽借力叙事学理论但走的却是经验实证的路子,通过对十七年小说叙事角色類型的归纳总结探索小说的审美变迁与形式背后的话语内涵。博士毕业后周教授从《论先锋小说叙事模式的形式化》(2003)到《近二十年长篇小说乡村现代性叙事规范的拆解》(2013)再到《重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2017)形式批评之路愈加宽广精深,走向更高层次的融合。以《重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为例,从概念的辨析到文学史谱系的追踪,从作品本质的归纳到叙事形式的考察,周教授做到了在纵横交织、古今转换的维度中对作品的综合考察,堪称文学批评的典范之作。
二
从2003年最早对王安忆的访谈算起,周教授至今已对四十余位——涵盖50后、60后、70后三代的作家、批评家——做过对话访谈。这些访谈的成果先后集中刊载在《小说评论》(2003-2007,“小说家档案”栏目)、《芳草》(2012-2016,“六〇后作家访谈录”栏目)、《长江文艺评论》(2016-2017)、《文学教育》(2019至今,“每月一家”栏目)。这些对话访谈文章除结集为《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一书外,还被收录到他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中。在《当代小说批评的维度》里,周教授还特意将访谈以“对话诗学”为名,列入其小说批评的“四维”之一。由此可见对话访谈在其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与特别意义。
这种重要首先体现在对话中理性与情感的糅合,为批评赋予直抵人心的温度。周教授曾说:“文学的重要价值是对心灵的慰藉。文学就得观照人生,就得直接和人的心灵面对面”[4]。文学是柔软心灵之间的对话,文学批评也并非全然的理性分析。它也有对文本的感受,对作家心事的关照与解读,需要和作家面对面的敞开心扉。或许批评家在对话提纲的准备中的确凝聚着其深思熟虑的学识理性,但当“面对面、心对心、性情对性情的直接交谈”(刘醒龙语)中除了你来我往的理性交锋,总有一些性情的感染、一些怦然的心动。这种会然于心是理解作家的绝佳途径,也为文学批评增添魅力。周教授的访谈对话多能做到在理性交锋与感性体认的互动中“对受访者的深入阐释和理解”(於可训语)。
其次,对话批评的直接目的是在批评家与作家的沟通合作中建构个人的文学史。这种作家的“个人史”涵盖着社会时代背景的关注、创作道路的回溯、重要作品的理解以及艺术观念的嬗变,是宏大文学史具体而微的缩影。随着周教授对当代作家有选择的持续关注,越来越多有着独特经验与文学价值的“个人史”被梳理,这对集体文学史无疑起着丰富与调整的作用。如果这种努力能为此后的文学史追认,那当然是批评家的荣耀。但周教授在对话批评中所体认到的“对话诗学”更为重要,因为它关乎“批评”的根底与尊严。批评的本质不是自说自话的独白,而是基于常识与逻辑理性的对话。批评家不仅要和文学文本对话,还要和文学史、作家、读者、批评同行以及自我对话。周教授的一段自述颇能道出“对话”之于其批评的意义,可引作注脚:
“文学批评实质上是自我主体的批评家和对象主体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由于文学批评的主体是富有生命的批评家,他要表达的是自我的精神世界。而文学文本还是世界与人生的价值、意义的符号性存在,在文学文本“沉淀”着有关人生的精神意蕴。因此文学批评活动应该是超越了任何功利的,而是人类、宇宙的精神现象的交流与对话。而文学批评的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审美交流、对话,才是文学批评的根本出路。”[5]
三
周教授又是勤于自省、善于反思的,他时常对自己发出“批评何在?”的反问。我们知道,就像在文学史的链条上才能给作家作品准确地判断与定位,也只有在批评史的视域中批评家方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因此,与其说他对小说理论批评的关注是学术转向,不如说这是其建构自身批评身份的必要补充与自觉拓展。不过,当我们回想到他从文艺理论转向文学批评的初衷时,就有理由相信这“自觉”中隐隐有着重构中国式文学批评及文艺理论话语谱系的远大图景。他90年代末正有感中国文论界的炫奇与无力才转向经验实证的批评实践的。而凭借着批评实践对历史与现场、创作与理论、传统与新变的敏锐把握与长期积淀,周教授又有旧业重操之迹象,这不能说不是个战略性迂回。
其实周教授对小说理论批评史的关注是有迹可循的。早年文艺理论的专业素养为其埋下伏笔,而对新时期小说文体形式的着重则是直接触发。中国新时期小说对形式的关注始于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与小说的影响。因此,梳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衍变是周教授从事形式批评的基本前提与题中之义。在《走向形式——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小说理论批评》(2006)、《文学现代性的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2007)、《新时期中国式形式批评的创建》(2009)等论文中,周教授正是通过历史的溯源,呈现出文体观念演变的内在理路,为文体批评提供参照维度。
随着资料的丰富与视野的拓深,周教授对理论批评史的研究渐成规模。《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研究》(2011,长江文艺出版社)是以地域视角反观中国当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而《中国新时期小说理论资料汇编》(2014,武汉大学出版社)则是从时间维度巡礼新时期小说理论承续与新变。周教授对湖北文艺理论批评家们的精审定位,对新时期小说理论文献的爬梳与择取,都向学界展示了其重构批评话语的“史家情怀”以及与之匹配的学术胆识与实证精神。尤其是后者,周教授虽然只对资料做了简单的择取与编年,“但就是这样一种客观中立的叙述立场,却能让读者在纷繁芜杂的历史资料中,一窥批评理论的演变轨迹”[6]。实际来说,以上二著只是周教授深入研究的基础。这种对理论批评有效的清理与汲取激发着周教授以历史、全局的眼光提出更富建设性的命题:建构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理论批评话语体系。近年来的《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2016)、《建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小说理论》(2019)、《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多维社会功利性价值》(2019)都显示了其在这方面的努力。
从概念辨析、资料汇编到轨迹梳理、谱系重构,周教授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是稳扎稳打令人信服的。这项融合理论素养、史学情怀与学术创见的研究工作不仅为其自身的批评厘定位置、确立方向,也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提出新的愿景。我们期待周教授在此方面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周新民:《学院批评的出路》,《湖北日报》2012年7月21日。
[2]周新民:《当代小说批评的維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代前言,第2页。
[3]周新民:《“人”的出场与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序,第2页。
[4]明海英:《追求文学批评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记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新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17日。
[5]周新民:《学院批评的出路》,《湖北日报》2012年7月21日。
[6]叶立文:《学院批评与史家情怀——记湖北大学周新民教授》,《湖北日报》2014年5月10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