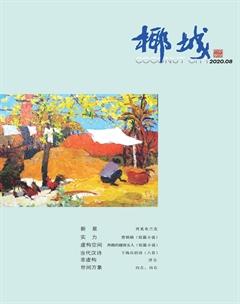时间到,我们该说再见了
郭亮
写完《再见布兰克》的那天,天气不好。好也没用,时间不对,出不了远门。
我一直觉得做什么事情就应该配什么时间。比如该学习的时候用力学,该恋爱的时候凶猛爱,该说再见的时候,就说再见。
布兰克是我给小说里的自己取的名字,其实就是black。再见布兰克,就是再见黑色。黑色是年轻时的肤色。逻辑很简单——再见,年轻时的黑皮肤。
到这里,疑问就出来了:为什么要和黑皮肤说再见?为什么是年轻时的黑皮肤?整篇小说就在解答这两个疑问中展开。前半段解答的是第一个问题:皮肤变白了,得了白癜风,所以再见黑皮肤。后半段解答的是第二个问题:年轻时以黑为丑,千方百计想要变白,啼笑皆非。终于变白,且是不可逆的白,却高兴不起来了。
这里面是该死的隐喻:我们总想得到的东西,真的得到了,便傻眼了。
当然并非万事皆如此,所以才说这个隐喻该死。它偏偏在我的小说里应验了。我相信真实的世界里,这种隐喻是小概率事件,所以我们依旧心存侥幸地对自己拥有的好东西视而不见,需要用这个隐喻来敲打自己:看看,多痛苦,还不好好活着。
人活着,总要敬畏一些东西。敬畏了,才变得有礼貌,心里踏实。我年轻时也有凶猛的时候,确切地说是大多数时候都很凶猛,凶猛的代价是事后自己会很难过。后来我发现,当我敬畏与理解一件事、一个人的时候,我反而变得特别舒服。
这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小技巧。
小说里要讲的核心可能也在于此:一个人被该死的隐喻砸中之后,与其丧着脸痛苦地回忆自己做错了什么,真的不如接受算了。因为自己一定是做错了什么啊,这还用去想吗?结果已经不可逆了,用高僧的话来讲就俩字:放下。
时间到,就说再见。岁数到,就对青春挥手作别。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时间。
这也是我写小说的动机:我写过很多年的商业评论、给企业写品牌传记,但心里一直认为自己最该写的还是小说。35岁开始写小说,如今写了整一年,还有的是时间。
我把小说的基础看得很重,就是生活的阅历、知识的密度、语言的可能性等等,同时我把表达的方式看得很轻,我认为优秀的作品得让人第一眼就读得下去,所以我习惯在小说的第一句话上费很多工夫,有时候睡前不小心想到一个句子,这一夜可能就睡不成了。我顺着往下想,想着想着就天亮了。
这样做不利于身体健康,但符合我的原则:时间到,该做那件事了。我又不是每晚都这么干,之所以这晚想到了,说明我该想了。
另外一点就是幽默。优秀的作品能把幽默运用得就好像这东西的老家就是这篇小说,贾平凹的很多小说里都充满了逗趣段子,我在读他的作品之前甚至听过很多次这些段子。时间放得长一点,作品本身的生命力当然比这些段子更强韧,所以段子比作品流行也不是什么坏事。而且幽默和滑稽不是一回事,幽默是狡黠与敏锐的体现,滑稽不是。幽默有门槛,滑稽没有。
我庆幸自己想要幽默的时候能编出幽默,我为这一点感到高人一等,真的。摘两段这篇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段子(这家伙怎么能写得这么好):
为了变得白一些,我试过不少方法……比如尽量减少外出曝晒,有兄弟邀我去踢球,我说不去,晒黑了就养不白了。那兄弟愣了三秒钟,疑惑地问我,晒黑了为什么会养不白?
她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班里个子最矮的那个女生眉来眼去,还说她是你見过的最美的女孩……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的意思是,你是怎么得到的这种谣言?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也未能免俗地抒了一下情。那几个情节来自我的真实生活:当时奶奶脑梗卧床,小说里写的是等疫情结束,回乡奔丧。就在杨黎编辑通知我这篇小说将会刊用的次日,我收到了奶奶病逝的消息。
小说与我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它来自我过去的生活,包括那些虚构出来的情节。一篇小说完成之后,意味着一段生活落幕,另一段生活开启。
感谢杨黎编辑,让我有机会把作品通过《椰城》送到更多的朋友面前,我不怕你失望,因为我相信编辑的眼光,也相信我的……好了不吹了,时间到,我们该说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