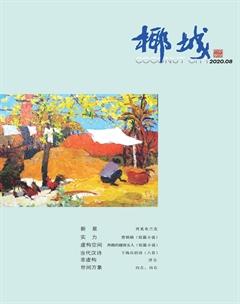再见布兰克
郭亮
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写一些可悲又可笑的人。
我这人年轻时有过很多外号,没一个好听的。除了“布兰克”。就连唯一好听的“布兰克”,也是black的音译,黑不溜秋。
古龙说,一个人的名字或许会词不达意,外号绝对不会错。我恨古龙。
那天,英语老师进来的时候,我悄悄对同桌说,老师真黑啊。那厮当场反水,向老师打小报告,阿亮说你真黑。老师笑了笑,笑的时候必是在思考应对之策。然后他说,阿亮也很黑,布兰克。一屋子小混蛋哈哈大笑,告密者被我狠狠地捶了一顿,还是无法阻止布兰克声名远扬。
中学六年,不少人都以为我姓布。真的,我的好兄弟而今在机关上班,时至今日他手机通讯录里给我的备注还是“布兰克”。
17岁读大学,女同学私底下说我又黑又瘦。你也清楚,背后的议论如果被当事人得知,无非两个后果。其中之一是深以为然并痛改前非,我就是这么做的。
为了变得白一些,我试过不少方法。比如用一种日本产的药妆抹脸,名叫雪肌精。再比如尽量减少外出曝晒,有兄弟邀我去踢球,我说不去,晒黑了就养不白了。那兄弟愣了三秒钟,疑惑地问我,晒黑了为什么会养不白?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四年以后我大学毕业终有所成。所有人都说,布兰克你可真白。
至于另一个后果,反唇相讥。我没得讥,总不能讥讽那女生说,你瞧你,又白又胖……搁从前那会儿,这不算损人的话。
搁现在,就不是什么好话了。今天流行健身房里撸出来的那种身材,以及带点儿焦糖色的皮肤。再瞧瞧我,又白又胖。都说风水轮流转,转到我头上,不是风就是水,唯独没风水。
我的白之所以叫人更加苦恼,是因为它白得不匀。
30岁结婚,婚后没多久发现腰间有一毛钱钢镚儿大小的白色圆斑。一开始没当回事,后来一毛钱变一块钱,就有点儿讨厌了。我老婆说,你这个是白癜风。
我的笑容凝固了,我说你的乌鸦嘴别咒我啊。跑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看了一眼就说,白癜风。
我老婆的笑容也凝固了,她就是从那天起讨厌乌鸦的。白癜风和乌鸦有点神秘的关联,二者都与诅咒有关。乌鸦是不祥之兆,白癜风是难言之隐。哦不对,这货不隐。人们看见白癜风都避而远之,齐刷刷变得颇有教养。
另外,得了白癜风就很难痊愈了。远的有迈克尔·杰克逊,近的有冯小刚。人家什么社会地位?什么资源调动力?就这也治不了,更别提普通人了。
看来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不是制度,而是疾病。
我不信命,又跑了两家皮肤科很牛的部队医院。其中一家让我做了伍德灯检测。一位年轻的医生带我进了一个小黑屋,拿一架镜头上镶了莹白光环的单反相机贴着患处咔嚓一顿拍。
拍完之后问我,别的部位还有吗?我心想这是治病救人就别遮遮掩掩了,便开始脱裤子。医生问我,你干嘛?我说会阴部位也有(为什么我会知道?我老婆告诉我的)。他赶紧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
我有些沮丧,医生怎么搞得跟普通人一样讳疾忌医?我还不知道,更沮丧的事情还在后面呐。
片刻之后,医生说,从照片可看到边缘光滑的白斑,确诊是白癜风无疑。
自我记事起,得过最大的病是高三那年冬天的病毒性疱疹,挂了一星期点滴。痊愈后参加模拟考,考了个全班第三。同学们都说,这兄弟真拼,拼得住了一星期医院,皇天不负有心人啊。
我打赌,不少人那会儿肯定都想住院。
白癜风比病毒性疱疹还厉害吗?医生给了我鼓励,她说,小伙子你看你漂漂亮亮的,一定要坚持治疗,内服外用。内服的药,我们有专门配制的草药,外用的呢,有药膏,如果再配合紫外线照射治疗,效果会更好。
我问她,怎么照射?她说一个疗程半个月,每天来照一会儿。我心想,我来一趟医院少说要三个小时,每天却只照一会儿……此时她语重心长地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心情愉快。
一想到每天都要忍受长达六个小时的拥挤交通,我的心情怎么也愉快不起来。
只好开了药,回家吃吃抹抹先看一下效果。
草药我已经记不起配方里都有什么了,只记得是那种分装好的中药冲剂颗粒,一长串小袋子,就跟便携装海飞丝洗发水一样。每次要喝之前,就取出一串,一袋一袋撕下摞成一沓,用剪刀齐齐剪开封口,一并翻倒在碗中。有的袋子里颗粒较大,还需用手拍打以确保没有遗珠。顆粒有黑有黄,散发着苦与甜的气味。浇入热水,搅拌融化之后,变成了酸与辣的气味。稍微放凉,一口饮下,最终呈现出酸甜苦辣的混合味道。感觉喝下这碗药,就能从武大郎变成武松,威风凛凛,十分正点。
外用的药膏,名字我记得真真儿的,卤米松。仿佛法国的某个电影导演,或者瑞士的。总之就是那片儿的。
就这么治了好几个疗程,啥效果都没有。
我又换了一家医院。医生是个老者,看着很有经验,他也给我开了药。我一看,金水宝胶囊。
拿到药以后翻看说明书,原来这玩意儿最大的功效是活血补肾……这哪儿跟哪儿啊?
另外还有一包类似草籽的黑色颗粒,护士嘱托我用高度白酒泡起来,用的时候涂一些,去太阳底下晒三分钟,直到患处皮肤微微发红即可。最后再抹上卤米松。
那药酒乌漆麻黑,揭开盖子便有浓香传出。我带了一小瓶放在单位,早上来了就喷一些在腰上。一个女同事是出了名的鼻子尖,更要命的是嘴不严。一进屋就皱起鼻子咻咻地猛闻半天,然后像发现了天大的丑闻逢人便问:你是不是吃了香米糕?要不就是玫瑰饼……
一年多以后,有了变化。腰上那一块钱大小的斑点,边缘开始内收,钱上也有了小黑点。医生说,这是要好了。
我内心波澜不惊,看来白癜风没比病毒性疱疹厉害到哪儿去,这不也治好了吗?
我老婆对乌鸦的感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不再讳莫如深了。
那段时间,我开始健身,决定追赶潮流的步伐。我的目标是变得像17岁一样,又黑又瘦的布兰克。
健身是会上瘾的。一开始我只是希望变得瘦一些,时日一久,初心就变了。我希望变得大一些,这是健身圈儿里的黑话,指的是肌肉纤维变粗变大。肩膀叫虎头肩,还要外翻。胸部要又厚又宽,且分为上中下胸三个部位,每个部位都要单独训练。腰部叫公狗腰,又细又紧,显得整个上半身呈倒三角形。
要实现这些,光练还不够,关键是吃。吃什么呢?高蛋白,低碳水。
蛋白粉、鸡胸肉、牛腱子,咣咣猛吃。我最喜欢的拉面、汉堡、碳酸饮料,坚决杜绝。
就这么吃了一阵子,别说还真出了点儿形状,大家都说我练得不赖。有什么重大的工作——搬个柜子啦、拎两桶水啦,都归我了。
与此同时,腰上原本已黑化的白斑又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手指关节也变白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暗示健身、吃蛋白粉与白癜风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而是我实在搞不懂白癜风的病因是什么。
以最朴素的想法来看,要治疗一种病,第一步就是搞清楚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对吧?
然而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个事实——没有人说得清白癜风的病因究竟是什么,包括医生。
有的医生说要少吃海鲜、辣椒等刺激性的发物。“发物”好像是传统医学里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如今是否还合乎时宜。有的医生说,少吃不等于完全杜绝,事实上海鲜富含蛋白质,蛋白质摄入之后会让皮肤变黑;辣椒可以刺激血液循环,可以帮助巩固皮肤色素。有的医生说,含有维生素C比如西红柿、橙子等有酸味的东西会让皮肤变白,要少吃。有的医生却说,也不尽然,可以吃。有的医生说不能晒太阳,有的医生却推荐紫外线照射治疗……
很显然,关于白癜风的病因,本身也存在争议。那么,治疗方法自然也南辕北辙。
不仅如此,人类身上绝大多数疾病,全都搞不清楚病因。
这不是胡说。我外公二十年前得了贲门癌,做了手术,又活了两年。二十年之后,我外婆得了一模一样的病,这回没做手术,活了一年多。
贲门癌是食管与胃连接处的病变。我问过一位挂号费500元的知名专家,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对方支支吾吾,说饮食习惯啦、家族病史啦、生活环境啦等等,都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疾病。
都有可能——就是不清楚的意思。
这时我又想起那个扛着照相机拒绝给我拍摄会阴部位的年轻医生,当时我还纳闷医生怎么跟普通人一般,毫无崇高之感?现在看来,在许多疾病面前,医生也只是普通人。
这么说并不是贬低医生,我觉得这属于实事求是。
如今,我以白癜风患者的身份说这话,更有十足的底气。因为我孤立无援,医生束手无策。
白癜风这玩意儿不痛不痒,不会要人的命,可它就像一块狗皮膏药贴在身上,大概率洗不掉,很讨厌!
从这个角度来说,白癜风也是一种不治之症——虽然不致命,可也不治愈。如果有人能发明根治白癜风的药,诺贝爾医学奖必须给人家。这人卖药都能卖得比马云还有钱,我一定不仇视这样的富豪。
我倒腾着这些朴素的认知,万念俱灰。
这时,一个网站进入我的眼帘——等会儿,怎么像广告软文?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植入网站广告了?我也以为……
我不提网站的名字,我们这些白癜风病友,在网站上将白癜风唤作白白,病友彼此之间也互称“白白”。
这是我将近四十岁的生命里,又一个新的外号。倒是比我年轻时的外号有萌感。
白白们教会了我不少东西,甚至说得偏激一点,他们比医生教给我的更多。比如照光,对于面积较小的白癜风,买一台便携式的紫外线照射仪,其实完全可以自己在家照。
我买了。花了一千三百多块,不贵。我记得很清楚,买完不久,我的女儿出生了。
那时她和她妈妈在里屋睡觉,我在客厅里照光。照光的过程我给大家讲一下,很有仪式感。
那台仪器由一个底座和一支手持灯管构成。底座大小恰如半块红砖,重量也差不多。手持灯管有点像机场安检员拿的那个金属检测仪。
插上电,打开总电源,按下底座上的照射开关,“嘀”的一声,灯管亮了。底座上的液晶屏开始倒计时,默认四分钟。将灯管贴近患处,照射三十秒到一分钟,千万不要超过一分钟。
由于患处的形状并不能与灯管严丝合缝,我想了一些保护措施。取一张抽纸,对折再对折,折角撕掉再展开,纸巾中间就有了一个洞。将这张纸巾覆盖在患处,洞正好能露出白斑。尔后将灯管按在纸巾上,如此一来,被晒黑的就只有洞里的患处了,不会黑及无辜的其他皮肤。
照光的时候,男人的智商就是这么高。
每隔三十秒,我就按下暂停键,又是“嘀”的一声。如此反复,把腰间与手指关节都照一遍,大概能听见七八次尖锐的“嘀”声。
我老婆气咻咻地从里屋出来质问我,为什么在孩子睡觉的时候嘀个不停?
为了减少“嘀嘀”声,我把照光时间拉长到一分钟。照完之后心满意足地去洗澡了。
洗着洗着,腰间隐隐作痛。低头一看,患处的那枚一元钢镚儿已由莹白变得暗红。
次日起床,居然起了一个黄澄澄的水泡。老婆说,你这是晒伤了,别照那么久啊。
自从有了紫外线照射仪,我的生活一眼就能照到头,不是在照光就是准备去照光。
看来我是喜欢上了这台照射仪,可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却也别无他法。
挣扎还是要挣扎一下的。于是我开始努力回忆前半生的细密往事,希望从中找出让我变白的根本原因。或者,有哪些事情能让我回归“布兰克”。
还是从我的同桌说起。他很黑,我现在怀疑当初排座位是按照肤色来的。
他的成绩本来很好,这么说你肯定猜到了,后来他堕落了。据说是父母离婚,他受到了影响。
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读了大学,认识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女同学。这女生长得好,成绩也好,给我的感觉是家庭也很好。所以我跟女同学约了一起上晚自习,习间,我与她讨论起一个名叫谌烟的女诗人自杀事件。
我说,谌烟是单亲家庭,心理必定有阴影,这是她轻生的根源。女同学没有任何迟疑就说,我也是单亲家庭,我的心理没有任何阴影。
这叫人如何反驳?后来我就没怎么跟她接触了。联想到我的同桌,看来父母离异对孩子的影响被刻意地高估了。
同桌的堕落,说到底是他自甘堕落。
我没有怪他的意思,也毫无惋惜。他依旧是一个博闻强识的人。他对我说,迈克尔·杰克逊是漂白的。我才知道,迈克尔·杰克逊以前是黑人,我一直以为他是白人呢。
同桌堕落后,不再认真听课,却能出口成章。某天上课,他拿着眼镜腿挖鼻孔,看上去很爽。下课铃一响,立刻脱口而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便一溜烟儿跑到操场踢球去了。
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的成绩排在全班倒数第五。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学期开始的时候,他是排在正数第五的。
他决心东山再起,于是留了一级。
如今想来真是幼稚,难道留了一级就能比学弟学妹们更高明吗?年龄压制又不等于成绩领先。
不过,他终于认真起来了,不再玩世不恭。
他认真地组织了一个足球队,他自己踢边后卫。那会儿法国世界杯刚刚过去,以罗伯特·卡洛斯为代表的踢法非常流行,就是你以为他是边后卫,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冲在前场,比前锋还前锋。
同桌深刻贯彻这一踢法,导致他的球队输得很惨。
更惨的是,有一回他和另一个很黑的同学在街上逛,一个混混远远地叫了一声黑鬼,他就发飙了。动手之后,他不是混混的对手,被打得鼻青脸肿,住了院。那混混说叫的不是他,而是他身边那个很黑的同学。那同学外号就叫黑鬼。
唉,想起这些往事,我还是很怀念同桌,毕竟近墨者黑。倘若我一直跟他在一起,也许就不会得白癜风了。
说起踢球,我也是足球狂人,小有名气。校园里常踢球的那二十几个人都知道我,并且知道我最喜欢做的假动作是反向踩单车。背身拿球在边路突破的时候我就会做这个动作。
有一次踢比赛,我刚一拿球,对方球员就大喊,他要反了,他要反了。喊得我心惊胆战,从此再也不敢做这个动作了。
那个大喊的球员比我们低一级,又黑又壮,每次都被我过得干干净净,但每次他都要挑战自己。我怀疑他初中三年唯一的乐趣就是防守我,然后被我过掉。
我的同桌留级之后正好跟他一队,有一次跟我吐槽,黑壮学弟背地里对我的评价是五个字,就知道盘缠。
我刚开始没听懂,盘缠不是路费吗?后来才知道,那学弟的意思是盘带。由此判断,此人是一个学渣。
看来同桌的球队惨败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幻想自己是罗伯特·卡洛斯。
我读高中以后,同桌还在初中,他留级了嘛。高中和初中位于同一幢教学楼,却像是隔了一座山。我们有了身份上的区别,便逐渐不来往了。
高中生的生活,是另一种生活。我比初中时代明显地感受到了更加强烈的危机感。
一些心理与生理都已成熟的同学总是愁眉苦脸地谈论着未来,好像再过三年大部分人都要去乡下筛灰,未来只属于那些考上大学的人。
我每次听他们说这种话,都暗自好笑。直到高三那年,我忽然觉醒了。我的父母彻底下岗了,他们没有了任何收入,看来我要准备好去乡下筛灰了。
不,我不想去筛灰。石灰粉粘在身上,就变得灰白了。可能这是潜意识里不想变白的一个征兆。
最終我还是没有去筛灰,真应该感谢父母下岗。此事激发了我的斗志,我开始发愤图强,每晚研究数学题到深夜,解题成功后手舞足蹈。外面马路上的歌舞厅小姐发出清脆的笑声,我便想起了闻鸡起舞的典故。
邻居家里的小姐姐比我高一级,打扮得花枝招展,有时候还喷了很香的香水。我们刚做邻居的时候她还是初中生,我在巷子里拿着小棍子幻想自己是楚留香上下舞动,每回都能被她撞见。她便香香地路过,留下一个深不可测的笑容,仿佛她才是真的楚留香,我只是个山寨版的。
上了高中之后,楚留香姐姐变得神出鬼没,再也见不到她的笑容了。我也无比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确实不是楚留香,哪有楚留香闻起来臭烘烘的?
要说高中与初中的唯一通道,还是足球。每晚自习前我们都要去踢一会儿足球,踢完了出一身汗,紧接着进教室上晚自习。三个小时的晚自习,也是三个小时的人肉烘干机。
汗湿的衣服捂在身上,全凭童子功发热将其烘干。下了晚自习到家换下衣服,浑身红扑扑、馊乎乎的。也许这是导致白癜风的原因之一。可惜我布兰克名声在外,当时只以为这叫黑里透着红。
班里有个女生,是正宗的黑里透着红。她个子一米七,是我们班第二高的女生,腿长得不像话,笑起来露出满嘴白牙,配上黑里透红的脸颊,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奇怪的是,我一直忘不了她。我们高中三年一共也没说过几句话,却好像洞悉彼此的一切。
后来,终于有机会跟她彻夜长谈。(当时她与我一样经过大学四年的保养已变得周身雪白,像艾尔莎公主。)这才知道不是我的主观感觉,她真的洞悉我的整个高中三年。她说那次病毒性疱疹过后,我回到班里,她一个要好的女同学跟我打招呼,我居然爱答不理。我回忆起来,真的有这回事,我当时只以为那女生在和别人打招呼。
这么微小的细节都没能逃过她的耳目,更别提那些明目张胆的暧昧了。
她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班里个子最矮的那个女生眉来眼去,还说她是你见过的最美的女孩。我刚吃进去一口饭,噗地一口老饭喷在桌上。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的意思是,你是怎么得到的这种谣言?
她哈哈大笑,说那个女生亲口说的。我追悔莫及,这是典型的遇人不淑啊。如此浮夸的情话,是我憋了许久才说出口的,却不料转身就被当作笑料卖给了他人。人心险恶,莫过于此。
她又说,另一个女生,你还送给人家一个装满细沙的小瓶子,里面藏着一张情书。结果人家看完就还给你了,你的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哈哈哈哈哈。
我惊呆了,因为这是真的。
高中时期的爱情,看来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这种曝光于白日之下的爱情也许会导致人变白,或者变绿也说不定。
只有老师假装不知道学生在谈恋爱或试图谈恋爱。
老师假装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考了第一名。
这天晚上,老师把我叫出门外,悄悄地问我家里的情况怎么样,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的心中涌过一阵暖流,来自老师的关怀让我倍感温暖。
出于对这种温暖的回报,我虚荣地告诉老师我家情况很好,父亲是单位的干部。全然没有提及此时父母正在离家百十公里外的村子里挨家挨户地在外墙上刷广告赚辛苦钱。
这件事被当作高考成功的小插曲很快掩藏在时光的尘网中,再打开的时候我气得耳朵冒烟。
原来老师的问询并非关怀,而是另有目的。按照规定,高考第一名可以获得一笔两万元的助学金。在我吹完自己家境殷实之后,这笔钱就被老师心安理得地挪作他用了。
他把钱给了高考第二名,那位同学来自单亲家庭,(怎么又是单亲家庭,单亲家庭与我尘缘未了吗?)两万元可以帮助他付清四年的大学学费。
我气愤的不是这两万块钱给了一个真正需要它的人(尽管我也很需要),而是这位老师给了我一顿社会的毒打,讓我明白话里有话的道理。
从此我变得小心翼翼,听话听音,生怕再次与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擦肩而过。
到了大学里,我为赚钱做过不少兼职,甚至因此而变得不学无术。(当然,我不太确定,是因为做兼职导致不学无术,还是其他原因,姑且这么说吧。)
我做过的那些兼职,都很苦。
我先是去了学校周围的那些小商店,一家家问过去,问人家要不要导购。结果可想而知,谁也不会花钱雇一个来自乡下的大学新生去做导购。导购,顾名思义,是要诱导别人购物的。
我又去了一家夜店(夜店名字很土,叫“放飞心情”),与我谈话的是一个外地口音的男子,穿着不合身的西服,我惊叹于宇宙中心五道口居然会有这么土的夜店男,关键是他说的话更土。他说,你要想赚钱,可以去发展女生来当吧妹,你拿抽成……我那会儿是穷,可又不傻,这种诓骗女学生的老套路,亏他说得出口。
假期来临的时候,我加入了一家快递公司。那是将近二十年前了,快递业方兴未艾,我有幸成为中国快递行业最早的一批从业者。老板和我竟是老乡,得知这一信息后我喜出望外,和他说起了家乡话,但他显然不太适应,并未搭腔。他拿过我的免冠照,仔细地贴在入职表上,又要过我的银行卡号,喜滋滋地说每个月末会把本月的工资打进卡里。
我的第一单业务是将一份文件从北四环送往首都机场。我用高德地图查了一下,全程三十公里。开车走高速需要半小时,骑车的话,要两个半小时。
很不幸,我当时只有一辆五十块钱买来的二手自行车。
我就这么虎虎地上路了,丝毫没有考虑自己能不能成功。我顺着路,一路向北。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夏日正午的阳光就让我有些吃不消了。很难想象我连踢球都不踢了,居然为了送快递顶着毒日拼命骑行。
妈的,没钱真是害死人。
更要命的是,我迷路了。问了好多人,机场怎么走。大家无一例外地觉得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那个年代是不会有人骑车跨越几十公里去机场的,更何况他们也没骑过,怎么会知道。
这可是我的第一单业务啊,仅此一单的提成就有两块钱。老板跟我说过,因为路比较远,所以提成比较高。
我在路边用公用电话给老板打电话,他一接电话就急了,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送到?这么慢还叫什么快递?你赶紧回来吧。
我只好又骑了一个小时返回公司。老板在路边等着我,他全副武装,穿着防晒服,表情焦急,甚至没来得及责骂我。他扯过那份文件,虎虎地就骑走了。
后来每当我收到新的快递,总是下意识地想知道这家快递公司的老板是不是山西人,是不是我的那个老乡。因为我从此再也没脸见他。
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求职方向,结合自己的特长,最后还是决定庸俗地成为一名家教。做家教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必风吹日晒,这样就不会晒黑了。
这正合我意。千算万算,不如天算。聘请我的这个家庭,距离我的学校有好几十站地。如果坐公交,一来一回就要十块钱。相当于我每次的家教费就要从三十元缩水成二十元了。
我一咬牙,还是骑车去吧。就这么坚持了一个学期,赚了五百元。(不是每天都去,只有周末去一次,当时的家庭很少有财力可以负担每天都去的家教。)我仔细算了算账,平均一个月能赚……一百来块。
虽然我很穷,可我毕竟是个大学生,算得出这个账不划算。再一看镜子里,好不容易白了一星期,到周末就重新晒成了乌鸡,下个星期不得不再阴回去,更不划算了。
艰苦曲折又毫无意义的兼职生涯,直到大学毕业之后终于结束了。我再想兼职也没条件了,我已经不是大学生了,还兼什么职。
好在此时,众所周知,我也不是布兰克了。此后,我过了差不多五年白白净净的岁月。
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得意的一段日子,既没有口耳相传的布兰克肤色,也没有国宝般死皮赖脸的黑白交错。最妙的是,青春还在。如此看来,让我心满意足的青春,只跟了我五年。
娘诶,真是气死我了。
青春里最叫人生气的是我没有趁着人烟稀少走遍名山大川,而躲在乡间陋室苟且偷生,直到乡间也变得人潮涌动。
我害怕拥挤,偏偏我所到之处都是拥挤。
拥挤的城市里,乌烟瘴气,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雾霾最严重的日子里,我不得不拨开云雾单刀赴会,只为找到后半生的伴侣。这种鲁莽的行为注定了我无法身心健康。
那些在爱情中未能善终的伴侣们,纷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评语。比如:“你这个混蛋,见鬼去吧。”“你不要我了吗?你还是不是男人?”“我和家里人说了,他们不同意,请原谅他们的庸俗。”“我当时真想拿一把菜刀砍死你。”“我不是同意做你的女朋友了吗?怎么不联系了?”“我知道你就是玩玩儿罢了,什么爱不起,都是借口。”
“你还挺自恋的,blank不是读布兰克吗?”“不不不,布兰克是black。blank应该读布兰恩克。我并不自恋,只不过布兰克是我最清楚的一个英语单词,你不懂。”
在回忆这场布兰克还是布兰恩克的争吵中,真正的布兰克时代已离我越来越远。在某个充满雾霾或者下着大雨的深夜里,终于寂寞地熄灭了。
我最终还是没能抓住布兰克的蛛丝马迹。白白开始暴发,手指关节的白斑未消,拳峰再添新白。腰间的白斑已从一毛钱、一块钱大小,扩大到了一颗鸡蛋大小。一颗鸡蛋确实不止一块钱,看来白斑和大城市房子一样,升值了。
更令人不安的是,作为最后的底线,我的脸上也出现了白白。两片嘴唇率先发难,然后是人中靠近鼻孔处。
紫外线照射仪的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从最初只需负责腰间与手指关节,发展到如今的面部操作。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家电使用频率最高?毫无疑问,就是这台紫外线照射仪。
照臉可不是小事,我不能再用一张纸巾糊弄了。我找来一只洁白的口罩,中间剪开圆孔。戴在脸上,正好露出嘴唇。人中部位呢?照完了嘴唇,将口罩上移,圆孔的边缘压着鼻尖,就可以照到人中了。
照射仪的“嘀”从最初的七八声,到如今每次照光都要十来声。默认的四分钟根本不够用,至少需要两个来回才能照完。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时间或许还会延长。
呜呼,脸破,则城破。城破,则山河不再。
这意味着我往后要背负着白白直面他人而生活了,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生活将持续多少年?
我的奶奶,一生率性而活,到今年已经八十岁。现在,她正躺在生活了几乎整整一辈子的那个村子里,她还没有死去。医生说,多年糖尿病以及血脂过高引发的脑梗,可以动手术,但也凶多吉少。就差直说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可悲的是,这位老太太已经啥都吃不了了,靠输液维持着最后的生命体征。
她正等待着死亡。而我在等待疫情结束,随时回去参加她的葬礼。同时不可避免地给家人展示新添的白白。上次离家的时候,我还能稍加掩饰,如今已掩无可掩。除非我找一位穆斯林朋友或者江湖女侠,借用她们的黑色或白色面纱。
与奶奶的岁数相比,我刚走过了一半的路。
这剩下的一半,由于白癜风的到访,居然比从前那一半更难。
纵然生不如死,我也不会去死。全世界还没听说有人因为白癜风自杀……如果有,那也太傻了。不是说这个人傻,而是别人会觉得这个人傻。
我是个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所以,我不会因为白白去死。(这句话怎么听都是一个完美的矛盾。)
我老婆说:“全白了也挺好看。”我眼睛瞪得像铜铃,仿佛再次被她死死地命中了后半生的皮肤颜色。这可真是个宝藏老婆啊。
全白了也挺好看……让我想起了那个同桌的话:“迈克尔·杰克逊是漂白的。”这话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目的是炫耀课本之外的知识点。只有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我记得他最后一次炫耀时,正值我们俩偷偷爬到教学楼楼顶上。落日余晖洒在平展的铺了黑色油毡布的顶面,活像一个鱼塘。我和同桌躺在地上,全然不顾有些蜇人的余温。
他指着天边的一溜儿彩云说,你看像什么?我说,像一群羊。他说,太没新意了。要我说啊,像一丛染成猩红色的阴毛。我惊叹于他的想象力,又再细瞧了一阵儿,我对他说,真他妈像。
我们俩笑成一团。笑过了,又像失去了什么。可笑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俩。沉默的空气里充满了忧伤,他没忍住放了一个短促的响屁。饶是如此,也未能打破那种坚固的忧伤气氛。我们又强忍着忧伤了几分钟,起身下了楼顶,回到教室上晚自习去了。
如今看来,他恰如当时的我,懂个屁。
屁都不懂的年轻岁月里,布兰克与那些年轻人在厚如黑巧的夜色中分道扬镳,又与黑夜融为一体。
属于他们的时代一去不返,而我的女儿正在一天天长大。
凡是见过我女儿的人都说这个小东西真可爱。她不是那种公认的漂亮孩子,但真的很可爱。我生平头一次恍然大悟,可爱是比漂亮更让成年人感到纯净的特质。
当一个人说某个小孩可爱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小孩不漂亮,另一种是这个小孩确实可爱。两种可能都与漂亮无关,但你能分辨其中的区别。
我给女儿起了很多名字,都有美好的寓意,且不落俗套。比如“叶离”(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无喧”(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蔓如”(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再晨”(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漫兮”(路漫漫其修远兮)。
后来一个都没用上,因为老婆在每个名字里都挑出了刺。比如叶离,她说会离婚,还是夜里离的。比如再晨,她说再沉就二百斤了。
现在想想,这些都已是两年前的事儿了。我在朋友圈里翻了好久才翻到这条,当时可是在万千古诗词里精挑细选出来的。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你要问我时间什么时候过得最快?我想想。应该是:当我参与上一代的死亡,旁观下一代的成长,以及亲历这一代的慌张。
说到这一代,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黑色的同桌,就像我再也见不到布兰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