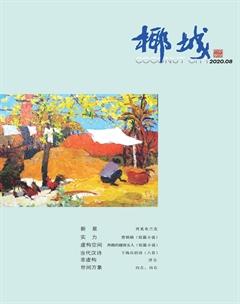背锅锅(短篇小说)
朱敏

时隔三十多年,我又一次见到了背锅锅,暮色的人群中,他面朝着街道,双手各攥着一把串好了肉的铁钎子。在他面前,是一个一米多长的黑色铁质烤炉,里面冒出紫色的火焰,他把铁钎子均匀地铺在烤炉上,随手从旁边抓起一把调料来回撒在肉串上,那个动作如此熟练,如同每年春天,他在打理好的地里撒菠菜种子。火焰在调料的刺激下,轰然窜出来,连带着冒出一股青烟,他敏捷地向后一躲,然后抓起一半铁钎子,迅速压在另一半上面,使之受料均匀,然后放下,又拿起另一半,做着相同的动作,一看就是个熟练的烤肉师傅。
要不是母亲提前指给我看,估计从他身边走过,我也认不出他来,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母亲远远的就叫了他一声“舅舅”,他抬头,在人群中搜索着声音的来源,然后就看到了我们,脸上露出一种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羞赧的笑——这笑我太熟悉了,看到这笑,我才真正认出他来。显然,他没认出我,只顾着和母亲寒暄,问母亲干啥去,最近好着没。母亲转身把我拉到他面前,用一种明显提高了的语调对他说,这是芳芳,你不认识了吗?我对着他笑,有种不自然的陌生感。他仔细打量着我,我也更近地观察着他,他好像没怎么老,脸色红润,棱角分明,额头上的抬头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深。片刻之后,他对着我惊呼,这是芳芳啊,我都没认出来,估计走在大街上都不认识了。我留意他的背,竟然好像直了很多,像一棵努力生长的白杨树,和当初留在印象中的佝偻的样子一点都不像。他冲着身后的烧烤店喊人,让我们先进店里坐。这是他侄子开的店,他在店里当烧烤师傅,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看着他老成持重的动作,听着他稳健的说话的语气,我暗暗猜想着这些年他的生活境况应该不错,否则从他脸上怎么一点都看不到沧桑和悲凉。
说这样的话不是我有意诅咒他,在我有限的生命旅程里,他真的是少数几个我觉得不幸的人。
他刚到我家的时候才二十出头,留着小平头,穿一件蓝的确良布衫,黑裤子,老布鞋,喜欢笑,见了谁都是羞赧地报以一笑,对了,就和刚才的笑一样,只是后面的笑稍稍平静了些。我下午放学回家,进了屋,母亲让我喊人,叫“舅爷爷”,看着他那么年轻,怎么就成了爷爷辈,我勉强喊了一声,把书包丢在床上,上桌吃饭。他是来我家喂兔子的,我家开着种兔场,里面有几千只从世界各地来的兔子,加利福尼亚兔、新西兰兔、墨西哥兔,还有长毛兔。父亲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来自八个国家的兔子的照片,我们常常好奇地打量,然后去养兔子的场子里对照着看,看它们和照片中的兔子是否一样。那时候交通还很闭塞,我长到十岁,都没离开过县城,用我贫乏干枯的想象力,怎么也想不出那些兔子是怎么飘洋过海来到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县城的。
家里已经有了四个工人,一个男的,三个女的,都是二十出头大小,也都是父亲或母亲的亲戚,我们喊这个“哥哥”,喊那个“姐姐”,有的辈分大,我们就叫“孃孃”。这下好了,又来了一个爷爷辈。
吃饭前我以为他和别人没什么区别,吃完饭,当他站起来帮着母亲收拾碗筷时,我才发现了他的异样,他的后背高高拱起来,像一口锅背在背上,他的前腔向内凹进去,他的下巴向里收着,整体看去,就像一个直立行走的乌龟。我呆呆地看着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奇怪的人。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驼背,别人驼背可能只是轻微的,但他却驼得太严重,几乎弯成了90度。母亲用眼神暗示我的不礼貌,他也感觉到我目光中的诧异,他急忙端着一摞空碗出去,像只受伤的小兽,再也没进来。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整排,一间挨着一间,一共八间。最前面的两间是男宿舍,但其中一间成了仓库,第三间是父亲的办公室,第四第五间是女宿舍,第六间我和妹妹住,第七第八两间打通了,父母住,里面还放着沙发、茶几、柜子,有客人来的时候,就请到这里坐。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屋,围着一张大桌子,热热闹闹地吃。夏天吃面的时候,我们喜欢端着碗在外面吃,凉快,也畅快,冬天挤在一起还好,夏天太热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都成了发热的源头。吃完饭从母亲屋里出来,我迫不及待想要打听那个驼背的舅爷爷的情况,直接钻进三个女工人的房间。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她们一个叫红红,是母亲的远方表妹,在家里排行老大,底下六个妹妹,最小的一个是弟弟。刚上到初一,父亲就不让念书了,要逼着嫁人,后来听说我们家开了种兔场,需要喂兔子的工人,她母亲走了二十多里路来我家,找母亲说情,母亲看红红模样俊俏,就留下了。她是我家的第一个工人,干三年了。还有一个叫小英,是母亲另一个远方表妹的女儿,圆脸庞,大眼睛,俏鼻梁,像个古典美人。第三个叫雪雪,是外公的亲弟弟的女儿,是从固原来的,长相一般,但血缘最近,所以母亲对她非常客气,有什么活,都叫红红和小英干,迫不得己才会喊她。三个女孩中,红红最善良,常常帮我们洗衣服做饭;小英最天真,像个娃娃,常常和我们跳皮筋、玩羊拐;雪雪最不一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文青,她自己住一间宿舍,窗前有张桌子,不干活的时候她就坐在桌前发呆,还唱歌,唱《外婆的澎湖湾》,唱《乡间的小路上》。好几次,我还看见她记日记,写完了就锁在抽屉里,不准我们碰。
这三个人中,我们最喜欢小英,因为她能陪我们玩,然后是红红,她不仅干活勤快,还会讲故事,最后才是雪雪。不,其实我们不喜欢雪雪,她在某些方面太硬了,常常让我们害怕。比如她说话,从来不笑,板着脸,像个冷血的机器人;比如她的屋子,门永远关着,不敲半天门,她都不给我们开;她每次回家,也不给我们带好吃的,反而要拿走母亲的许多旧衣服。因此,当碰到打问消息的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红红。
红红正在屋里洗锅,我偷偷地溜进去,生怕被母亲看到。我问她那个驼背的舅爷爷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来了,红红的一双手在水盆里不停地搅动,把一只只油腻的碗清洗出白瓷的质地。但是她的回答讓我失望,她说她也不知道,只听母亲说,那个驼背的舅爷爷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昨晌午就出发了,结果走错了路,等找到我家,都半夜了,看大门锁着锁也不知道喊人,整整在外面冻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早上父亲骑着摩托车出去给兔子买饲料才发现了他。因为这,父亲还不想留他,说他太老实了,可能不太会干活。我很奇怪,我们出门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没看见他呢,可能他在供销社大门边上躲风呢。我们住的院子前面是供销社,后面是种兔场,共用一个大门。是那种蓝色的铁栏杆的门,供销社每天八点才上班,后面有仓库,里面装着各种货物,仓库门口堆着化肥。供销社下班的时候,我们都把大门锁上,怕有人偷化肥。我和妹妹上学都拿着钥匙,挂在脖子上,走路的时候像只小鸽子一样,扑棱棱在胸口上跳。
冬天早上上学早,估计我们出门的时候彼此没看见,要么就是他睡着了。
因为他的到来,我一天的好奇心都在他身上。下午放学,迫不及待往家跑,想看看他是不是被父亲使回家了。刚跑进院子,就看见他了,他蹲在那里,拿着一块湿抹布给父亲擦摩托车。因为蹲着,驼背更明显了,整个人就像缩在那口锅里,他抬起头,看见我回来,又是冲我羞赧地一笑,然后嗡着声音说,芳芳回来了。我点了点头,像见了怪物一样向屋子里跑去,跑远了又回头看他,他还蹲在那里,认真地擦着摩托车的轱辘。
说实话,也就他会给父亲擦摩托车,我们都不擦,觉得麻烦,尤其是冬天,冻得手都拿不出来,何况还要握一块湿抹布。我隐隐觉得他在讨好父亲,以一种谦卑的、任劳任怨的姿势博得父亲的欢心,然后心满意足地把他留下。晚上找了个机会,我终于打问到他的名字,叫李学明,很普通的名字,上面还有个姐姐和哥哥,都成家了,姐姐嫁到外县,哥哥和父母分开过,家里地少,本來就不够吃喝,母亲还爱抽烟、爱打牌,弄得他们常常一年四季借债。这不,冬闲了,李学明在家实在窝不住,这才跑来找母亲。他母亲和外婆的母亲是姊妹,虽不是亲的,但一直走动,所以没断了这点亲戚情分。相对于他的名字,我更好奇他是怎么驼背的,但没人理我。可是,从那以后,只要我写作业不坐端正,母亲就指着我骂,迟早也成个背锅锅。
我问母亲什么是背锅锅,母亲用手指着外面,说,就像李学明那样。我这才知道,原来驼背叫背锅锅,好形象的叫法。
李学明和早来的小伙子小李住在一起,他是父亲的远房亲戚。小李长得很帅,浓眉大眼,说话顺溜,办事利索,他是在红红之后来的,先是和红红喂兔子,后来小英和雪雪来了,就彻底把他从喂兔子的行列里解放了,帮着父亲跑腿办事,三天拉一次饲料,分别从不同的地方把油饼、大豆、玉米、鱼粉等拉回来,然后用粉碎机把油饼、大豆、玉米磨碎,按比例掺匀,用麻袋装起来,红红她们喂兔子的时候再倒在槽里,用水拌湿,装在桶里,去喂兔子。因为这个原因,小李成了种兔场最自由的人,每天骑个自行车飞出飞进,红红、小英和雪雪如果想买什么东西,也找他带买。李学明来了之后,为了好区分,大家叫小李还是小李,叫李学明大李,其实李学明并不比小李年龄大,相反还小几个月,但因为辈分高、长相老,所以大家也就这样叫了。
按说场里并不缺人,喂兔子的人够了,买饲料、粉饲料的人也有,平白无故多一个人不仅多一张嘴,还等于多了一个负担。父亲一想到月底要发工资,年底还要给供销社上缴承包费,就很恼火,一直想把李学明辞掉。母亲再三阻拦,倒也不是多看重亲戚情谊,而是怕李学明的妈来闹。听母亲说,那是个不好惹的人,嘴皮子薄,骂人不喘气,能说会道,死的能说成活的,活的能说死,大家都叫她窑婆子,这在我贫乏的词汇量里,应该是最毒的骂人的话了。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对李学明说,要试用他一个月,如果干得不好,就回家,李学明听了点点头,一脸的真诚。每天大清早起来扫院子,抽水,往外面倒垃圾,给兔子间消毒、铲粪,什么活都干。刚开始,小李听说李学明要和他住一屋,还有点不高兴,觉得李学明是个土包子,也不识人眼色,妨碍了他的个人空间。后来有一天,饲料拉回来,轮到粉豆饼了,李学明跑过来帮他,他才尝到了甜头,立马热情地教李学明怎么操作粉碎机,怎么加料,怎么装袋。说实话,粉饲料真是个苦差事,粉碎机一开,轰隆隆的,整个屋子都在抖,而且豆饼沫到处乱飞,即便戴上口罩,也能把人呛死。每次粉完饲料出来,小李就像刚从面缸里捞出来的一样,整个一灰面人,头发灰白色,衣服灰白色,鞋子灰白色,用手一拍打,整个人都在往外冒灰,像一颗爆炸的微型原子弹。现在李学明代替他受这苦了,他能不高兴吗?
我和李学明之间一直刻意地保持着距离,并不像亲近其他工人那样亲近他,或者说,我对他有着一种恐惧,他的背,总是令我想起故事里的妖魔鬼怪。
三个女孩对他都很客气,客气得有一点生疏,像一层漂浮的灰尘,轻轻浮于表面。她们都觉得他干不长,最多十天半个月,肯定被父亲辞掉。但是结果令人意外,几天之后,我发现如同小李一般,大家都在慢慢转变对他的看法和态度。先是红红夸李学明聪明,喂兔子的时候知道把门全部打开,一勺一勺地舀完饲料之后再一次关上,节省了很多时间。之前大家都怕门开着兔子会跳出笼子,但是李学明说,兔子和鸡不一样,胆小,在笼子里待惯了就不会随便出来。小英和雪雪试了试,发现真是那样。然后小英也开始隔三岔五地找李学明,因为她管理的兔子间有几个兔笼的木栅栏被兔子咬断了,兔子老是往下跳,看来这属于那种胆大的兔子。李学明知道后,去外面的树林折了几根树枝,削去皮,劈成两半,重新钉在上面,兔子再也没跑出来过。只有雪雪没咋找过他,甚至正眼都没瞧过他。李学明也不在意,见雪雪提水,帮忙拉水管子,见雪雪半夜起来给刚生完兔子的母兔喂奶,他就帮着开灯。母亲说,他是一个眼里有活的人。他不爱说话,吃饭的时候只低头吃自己碗里的,偶尔夹一两筷子菜,不像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还叨叨叨说个没完没了。晚上,大家都在母亲屋里看电视连续剧,他不看,自己在屋里待着,什么也不做。他在我眼里,变得越来越奇怪,也越来越神秘。
他终于熬过父亲的考察期,勉强被留了下来。
为此,父亲还专门给大家开了个会,要大家民主表决,要不要留下李学明。我偷偷趴在外面窗台上看,红红举了手,小英举了手,小李犹豫了一下,也举了手,只有雪雪无动于衷,一脸冷漠。我没把详细情况告诉李学明,只提前父亲一步告诉他,他被留下了。当时他正在给厨房门口的土院子铺水泥,蹲在那里,身边是一桶和好的水泥,左手拿着一把铁锹头,右手拿着一把攠矛子(抹水泥的工具),端一锹头水泥倒在地上,然后用攠矛子一下一下仔细地抹平整。院子已经铺了三分之一,他一边铺,一边缓缓地往后退,像个攻占地盘的土将军。
当我说出我偷听来的消息,以为他至少会激动一下,但没有,他很平静地报以一笑,继续低下头干活,好像留不留对他无所谓一样。
真是个怪人。
他的怪还表现在穿衣服上。干活的工人每人都有一身工作服,外加一件白大褂。白大褂是进兔子间穿的,平时干活就穿工作服。因为每天都要干活,大家几乎都是一月一洗,只有李学明,每天都洗工作服。白大褂永远白净,用蓝色劳动布做成的工作服永远亮崭崭,哪怕是粉完饲料,工作服已经看不出颜色,第二天你再看他身上,又是蓝盈盈一片。
幸好家里的水都是从地下用水泵抽的,不然勤俭持家的母亲该多心疼。李学明洗衣服也不用洗衣粉,自己买了一块胰子,我看了看,就是肥皂,长长的,像一块土黄色的砖头。他把衣服铺平在搓板上,然后拿胰子在上面来回抹,衣服上滋出黄色的膏物,他放下胰子,双手握着衣服在搓板上搓,一会功夫就搓出一股又一股黑水,用清水淘洗,然后再抹胰子,反反复复,直到洗出白沫来他才罢休。
母亲拿他羞三个女孩,说李学明一个男人洗衣服都胜过她们三个女人洗的。
渐渐地,先是我家的床单被套到了李学明的洗衣盆里,然后是父亲的衣服、母亲的衣服、我和妹妹的衣服,他成了我家额外的洗衣工。有一次,他给母亲洗衣服,母亲忘了把胸罩挑出来,他竟然也默不作声地洗了。
父亲知道了,一边责怪母亲,一边说李学明真是个老实疙瘩。
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他老实,后来的一件事让我发现,其实他并不是。
有一天下午,我蹲在院子里和狗玩。我家的狗是只土狗,全身白,我们都叫它大白。它特别温顺,谁都喜欢它。但是来了外人,它却又叫得很凶,眼神里露出愤怒的、被侵犯的神情,拽得铁链子哗啦啦响。平时上学,每天进进出出都要摸它一下,它明明是已经当过狗妈妈的狗,却每次都表现得很乖巧,倒像是我的孩子。我蹲在大白跟前,用手握着它的前爪,摇摇晃晃,好像在握手。大白既不反抗,也不躲避,任由我抓着,像是一对好朋友。李学明当时就在旁边,从三轮车上往下卸饲料。本来是两个人的活,但小李把饲料拉回来后就骑着车出去了,说是有事,李学明也不计较,就一个人在那扛麻袋。院子里很安静,除了我和大白说话的声音、李学明背着麻袋走路时微微的喘气声,空气仿佛都凝滞了。就在这时,母亲突然喊我:芳芳!吃饭了!
我正玩得起兴,母亲的话就像耳边风一样轻轻地刮过去了。我和大白握手握烦了,又开始挠它的脖子,它的脖颈处特别柔软,毛也非常顺滑,我突然想试试狗会不会痒痒,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挠着,还连声叫着“挠痒痒,挠痒痒”,好像在期待着它会突然笑出来一样。大白也很享受,把头伸在我怀里,听任我给它挠痒痒。
母亲又扯着嗓子喊:芳芳!吃饭了!
一连喊了几遍,母亲喊毛了,提高音量又喊了一遍。
我还是没动。毫无预示的,李学明突然开口说话:
芳芳哎,吃饭来!
啥饭?
豆豆饭。
一揭锅,屎蛋蛋……
这几句话被李学明绘声绘色地演绎出来,一下把我逗笑了,我笑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大白向前追了两步,用舌头舔我,我一边躲大白,一边回头朝他说:你再说一遍!
他走到三轮车前,弓腰,双手各抓住一包麻袋的两个角,使劲甩起来,稳稳地落在肩膀上,一晃一摇地走向身后的仓库。因为麻袋的重量,他的背好像更驼了,简直是半弯着腰走路。我追在他后面喊他,再说一遍么,舅爷爷,我刚才没听清,可他已经不理我了。再从仓库出来,他已经恢复了平时的样子,一脸平静,好像刚才说那段话的人不是他。
但是,下次吃饭,再碰到母亲喊我,只要身边没人,他又一唱一和的:
芳芳哎,吃饭来!
啥饭?
豆豆饭。
一揭锅,屎蛋蛋……
我又气又笑,追著打他,他却只轻轻一摆肩,就把我闪了个空。
转正后,李学明干活更卖力了。父亲打算把屋后的一大片荒地开垦出来种麦子种菜,李学明成了主要劳力,这可都是吃苦受累的活。拿镰刀先把荒草割掉,然后烧草根,完了用铁锹挖一遍,把土里的草根都拣掉,然后平田、打埂,一块一块分好,等着下种。忙完这些,一个冬天又过去了。
数九之后,天越来越冷,供销社主任来找父亲,说是想找一个帮他们夜里值班的人。按规定,他们应该自己值班,一人一周,但冬天太冷,下班后回家吃完饭再骑车到供销社值班,就有些叫苦连天,好多人都不愿意。供销社主任姓康,五十多岁,中等个头,衣服穿得很整洁,但如果仔细看,他的袜子是破的,就在脚后跟,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看不见,一坐下,裤子提起来,就露出一个大豁口,而且不是一只,而是一对。这个秘密也不是我最早发现的,是李学明。有一次康主任来找父亲下象棋,他翘着二郎腿,一抖一抖的,两个破洞都露出来,李学明偷偷指给我看,我笑得哈哈的,又说给母亲,却遭到母亲的一顿呵斥,说我不学好。
康主任提出给值班的人一个月一百块钱补贴,一百块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一包金驼烟才五毛钱。这样的好差事当然很吸引人,小李知道了,当着康主任的面就提出他要干,康主任看父亲的脸色,父亲没点头,康主任就很识趣地先走了。康主任一走,小李又对父亲提出想值班的事,父亲让他先去拌饲料,马上该喂兔子了,随后再说。小李也没多想,总觉得这种事非他莫属,场子里就三个男人,他、父亲和李学明。父亲肯定不会为了一百块钱去睡在小小的值班室,说出去让人笑话。李学明是个榆木疙瘩,用母亲的话说,磙子碾上去连个屁都碾不出来,这样的人,父亲和康主任怎么放心把供销社的值班室交到他手里呢。八字还没一撇呢,小李就自我感觉良好,把这件以为板上钉钉的事告诉了三个姑娘,三人都夸他机灵,会办事,还让他吃完饭买油炸蚕豆请客。
晚上看电视时,小李不光买来了油炸蚕豆,还买了瓜子和大大泡泡糖,一人一个,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嚼啊嚼,嚼得没有香味了,然后把泡泡糖裹在舌头上,对着那层薄薄的白色糖衣使劲一吹,一个白色的泡泡就慢慢鼓起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只听得“啪”一声,泡泡破了,糊我们一脸。小李洋洋得意,父亲去隔壁乡政府喝酒去了,只等着他回来,然后把这件美差交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只睡睡觉,每月比其他人多挣一百了。
父亲一直喝到半夜才回来,我们等不住都睡了,母亲早早躺在床上打呼噜,小李却固执地坐着等,电视上都是雪花了,他才不甘心地回了自己的屋子。等他回去后,他才发现李学明没回来,他仔细回想了一下,发现今天夜里李学明压根就没和我们一起看电视。吃过晚饭,好像就没再看见。他有些疑惑,李学明做事一板一眼,每天啥时间干啥都是固定的,比如早上起来先扫院子,然后洗漱,中午要抽水,晚上吃完饭看新闻联播,看完之后跟着大家一起看电视连续剧,十一点准时睡觉。可是今天他人呢?
就在他疑惑得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又发现了异样——李学明床上的铺盖不见了,只剩下一条褥子孤零零在那里,床单、被子和枕头都不见了。他暗叫一声不好,急忙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往值班室跑。值班室和种兔场隔着一道门,出了院子,远远的就看见值班室的灯还亮着。他往跟前走,趴在窗户上朝里面看,什么也看不见,他咚咚咚敲门,门从里面打开,李学明站在他面前。
小李像是受了莫大的侮辱,瞪着铜铃一般的牛眼睛问李学明,你怎么在这?
李学明一脸无辜:厂长让我来的。
小李:看你老老实实的,想不到还会背地里玩阴的。
李学明涨红了脸:我没有,晚上吃完饭,厂长让我来帮着值班的。
小李:……那厂长咋说的,是长期的,还是就今天?
李学明:没说。
小李又瞪着李学明,不知道是在分辨他话里的真假,还是在猜父亲的意思。
值班这件事最終被李学明占了先机,虽然父亲说为了公平起见,让他俩轮流值班,但是小李却觉得伤了面子。他一直觉得自己比李学明强一百倍,家里会算账,出去能办事,长相还出众,从他身上简直挑不出毛病。忍了三天之后,小李提出辞职,他以为父亲和母亲肯定会挽留,毕竟十个李学明也抵不上一个他。但是,父亲当时就同意了,还让母亲提前给他结算工资,一句挽留的话都没说。小李悻悻地走了,李学明帮他收拾铺盖,他一把夺过去,恶狠狠地说,不要假惺惺,我不稀罕。
小李走了,最难过的是那三个姑娘。她们总觉得小李是个不错的选择,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和小李的未来,小李和她们也时时打成一片,隔三岔五给她们买点瓜子泡泡糖,虽然每个人分的都一样,但大家心里都甜滋滋的。这下小李走了,她们的爱情梦也破灭了,为此,她们和李学明也疏远起来,除了干活,多一句话也不愿意说。我和李学明却渐渐熟悉起来。下午写完作业,我就偷偷跑到值班室,和李学明一起看电视。和他看自在,想看哪个台看哪个台,不像在家里,我想看动画片,母亲要看电视剧,父亲要看动物世界,小孩一点都没有选择权。李学明不一样,他总是让着我,想看哪个看哪个,从来不和我抢台。他也不催我睡觉,想看到啥时候看到啥时候,看完了他就送我到后院睡觉。他还给我讲故事,鬼故事居多,还叮嘱我晚上不要梳头,不要照镜子,说这样容易招来女鬼。走近他才发现,他的心里竟然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我们什么都聊,但从来不提他的驼背,而且我对他弯着的背也不那么在意了,好像他和我们没什么区别。
过了不久,又发生一件事,李学明的妈来了。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窑婆子。她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瘦小个头,头发整齐地在脑后挽了一个髻,额头搽了头油,锃亮锃亮的。她穿了一件黑色的布衫,斜开襟,黑裤子,整个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她坐在母亲屋里说话,整个院子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哎呀,你不知道,一大家子都是我一个人养活,你那个姨爷爷啥都不操心,现在学明在你这里多少还能挣点,算是给家里减轻了点负担。我给他说了,让他放心,他挣的钱除了开春买化肥、买种子,剩下的我都给存上,留着给他娶媳妇……
李学明已经在我家干了一年半了,之前每个月发工资他都一分不少地拿回家,他妈也没咋来过,这次还没到月底发工资呢,她咋就提前来了呢。等她拿着钱心满意足地离开,母亲才说是耍钱耍输了,要债的堵在家里,等不到月底了,只好跑来领李学明的工资。怎么会有这样的妈,我替李学明打抱不平,又被母亲呵斥,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晚上和李学明一起看电视,我试探着问他生不生气,他一脸坦然,有啥好气的,儿子咋能嫌弃自己的妈呢?
那她也不应该拿着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耍赌呀!
她一辈子就爱耍个赌,有啥办法。
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一副不急不躁的样子,我也无话可说了。有了再一,就有再二再三再四,上次开了个头,李学明的妈几乎每月都来我家一趟,好的时候可以挺到发工资那天,大多数时候都会提前来。父亲母亲也见怪不怪,每次来都如数把钱给她,因为惹不起。私底下,父亲也和李学明谈话,说他太软弱,不懂反抗,把钱都给母亲输掉了,以后咋办呢。李学明一脸憨笑,他说他不着急。
二十三四不着急,二十五六不着急,二十七八总该着急了吧。李学明不急,父亲和母亲也急了。眼看着红红出嫁了,小英出嫁了,那个冷若冰霜的雪雪也出嫁了,家里打光棍的只剩下李学明了。
父亲知道家里的三个姑娘都看不上李学明,除了老实能吃苦,他一点优点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个背锅锅,别的不说,以后咋一起出门呢。还有他那个爱赌钱的妈,这些都成了李学明娶媳妇的巨大障碍。
母亲到处托人给他说亲,但只要看一眼本人,姑娘们都退避三舍。即便是条件最不好的姑娘、带着孩子的寡妇,竟然都在看过李学明本人之后摇头。父亲气得骂娘,他妈的,这些女人都瞎了眼吗?找男人就要找这样老实的男人,光看模样,能吃还是能喝?
李学明成了我家干的时间最长的工人,我们一出去,就有人打问说,你家是不是有个背锅锅?我回家给母亲说,母亲让我们别理,可是我知道,母亲比谁都更着急李学明的婚事。了解的人都知道是因为他的背锅锅,不了解的人都说是父亲母亲苛责李学明,故意让他找不到对象,好在我家当长工。李学明对此却无动于衷,每天该喂兔子喂兔子,该粉饲料粉饲料,该下地干活下地干活,任劳任怨,各种活计从不挑三拣四。
当他在我家干满十年时,父亲终于给他说了一门亲,对方姑娘就在我家隔壁的村子,没妈,只有一个老爹和哥哥,哥哥结了婚,嫂子厉害,处处刁难小姑子,在家实在待不住了,只好想着嫁人。姑娘叫五嘎,刚满十八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却因为家庭环境逼迫,只能选择李学明。第一次两人见面,五嘎都没抬头,因此并不知道李学明是背锅锅,父亲也安顿李学明一直坐着,别站起来,还特意把相亲时间定在晚上。从姑娘迫不及待想嫁人的眼神里,已经看出她身后的那个家是火海,时时刻刻在折磨着她。因此,第一次见面之后,姑娘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这门亲事。父亲趁热打铁,第二天就让母亲带着五嘎去买三金首饰和衣服。五嘎到了街上,眼睛都亮了,一件接一件试着,一件接一件买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像夕阳的余晖一般落在她的脸上,一整天都闪着金色的光芒。第二天,他们就举办了婚礼,简单得像是随便画了一笔潦草的画。入夜之后,所有人都惴惴不安,生怕姑娘会在深夜的寂静里发出绝望的、上当受骗的、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可是,没有,一整夜他们的新房都很安静。
早上起床,大家特意看五嘎的表情,从她那张水灵灵的脸上,竟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失望、悲伤、委屈,甚至痛苦。她很平静,像一棵向日葵一样平静。李学明也是,和往常一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扫院子,然后洗漱,准备喂兔子的饲料。中午吃过饭,五嘎来我们屋里聊天,她看着我写作业,那时我已经高三,准备高考,每天忙得焦头烂额。她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写作业,还用手轻轻地抚摸我的课本。我问她上到几年级,她说忘了,只记得上到她妈死了的那个秋天。她给我讲她嫂子如何虐待她,如何当着她爹的面把满满一碗汤面扣在她头上,汤汤水水把她盖了。我之前还觉得五嘎嫁给李学明是吃亏了,下嫁了,听她说了好多事之后又觉得五嘎是幸运的,找到了李学明这样的好人,起码他不会亏待他,不会打骂她。那天买衣服,我亲耳听到李学明对母亲说,尽量买,看上就买,买多少都行。
李学明结婚了,李学明的妈不乐意了,因为她不能再全部把李学明的工资拿走了。李学明第一次顶撞母亲,让她给他留点钱,说要和五嘎过日子。老窑婆子急了,在我们家闹了好多次,还骂五嘎,李学明一气之下带着五嘎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好像他从来不曾在我家出现过,只有母亲洗衣服的时候才会说,要是学明在就好了。开春种地,父亲也说,要是学明在就好了。夜里我想听鬼故事,我也说,要是舅爷爷在就好了。李学明走了,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李学明的背锅锅也是因为他妈,他刚生下六个月,他妈为了耍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用根绳子绑在炕角,孩子太小,老是搉着坐,时间久了,脊椎变形,就成了个背锅锅。我在心里骂着,这个可恨的老窑婆子,太坏了。
我考上大学后,父亲上交了种兔场,我们搬家到街上,开始了新生活。之后的二十年,我们好像过得很忙碌。我们终于彻底忘了李学明,他再也没出现在我们面前。偶尔碰到以前的熟人,站在大街上叙旧,他们忽然问一句,哎,你家以前那个背锅锅呢,现在过得咋样了,那可是个好人。只有经过别人的提醒,我们才会拉出一些有关李学明的回忆。
这次遇见李学明是个意外。暑假回老家,我带母亲出去吃饭,往一条新开的街道上走,母亲突然指着一个烤肉的男人對我说,你看那是谁?!
我看了又看,却始终没认出他来。他的背锅锅小多了,不仔细看,甚至不能发现他是驼背。我想起他频繁相亲的日子,为了治疗他的驼背,他夜里睡觉,在脊背下面偷偷垫两块砖头,硬是坚持睡了好几年。现在的他,看上去有些笔直,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难道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在砖头上睡觉吗?不敢相信。
和他重逢的那个晚上,他特意给我们烤了羊肉串、羊腰子、金针菇、酸菜豆腐、韭菜、烤鱼,桌子都快摆不下了,他才微笑着停下来。几十年过去,他并不显老,反而有些意气风发的意味。母亲打问五嘎,他一脸淡然地笑。过了两年,给我生了个儿子,她哥又把她接走了,重新给她找了个人家,可是过了几年过不下去,又离了。现在儿子当兵复员,又把他妈接来和我们一起过……现在好了。
我听着他慢慢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多艰难岁月,在他嘴里好像都变得云淡风轻。活了这么多年,我也知道人世苍凉,可是又有谁知道他为了尝到生活的那点甜,又咽下了多少难以下咽的苦呢。唉,我的背锅锅舅爷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