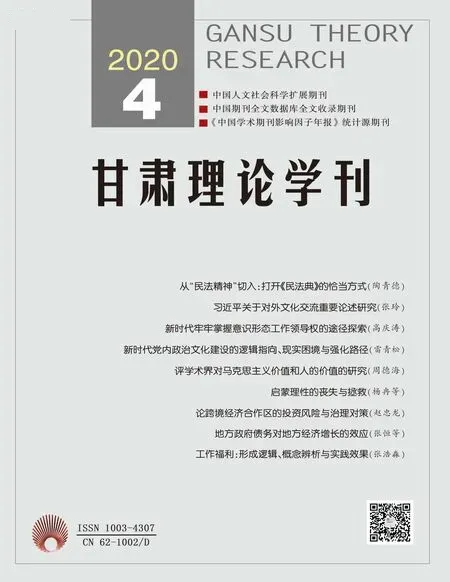工作福利:形成逻辑、概念辨析与实践效果
张浩淼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64)
1990年代起,欧美许多国家对原有的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救助进行了改革,引入了工作福利,旨在平衡权利和义务,促使受助者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以消除福利依赖。工作福利的形成与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改革密切相关,工作福利自提出之日起,就存在较多争议。这一方面体现在学术界对工作福利缺乏统一的概念界定,工作福利和与其相关的“激活”以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概念界限不甚清楚;另一方面,关于工作福利的实践效果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工作福利可以改变受助者消极与依赖的文化基因,可以明显降低受助人数并减轻救助负担[1],但不少研究认为工作福利是对济贫法时代“强制劳动”的回归,其结果是将福利依赖转化为了低薪工作,制造了在职贫困[2]。
本文旨在梳理与回顾工作福利的形成逻辑,对工作福利的概念进行探讨与辨析,尤其是厘清其与“激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区别和联系,并对工作福利的实践效果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工作福利的形成逻辑:背景、原因与推动力
工作福利(workfare)最早出现于美国,1960年代尼克松政府时期“工作福利”一词首次进入公共话语领域。1970和1980年代,美国在关于福利的讨论中,“工作福利”一词屡见不鲜,用来指那些针对福利领取者的各种就业项目[3]21。1996年,克林顿政府实施了激进的福利改革,出台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将救助制度从“资格机制”改为“工作优先”模式,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福利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对救助采取时间限制并强制提出工作要求以促使受助者尽快就业,还伴随一系列的奖惩措施。
美国工作福利的形成和快速发展使英国、澳大利亚等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纷纷效仿,比如,英国在1980年代早期开始使用“工作福利”的概念,把原有针对青年群体的公共就业计划称为工作福利项目[3]24。1997年,布莱尔政府提出了系统的工作福利政策,通过设立求职者津贴替代原有的失业救助,要求失业者必须积极寻找工作才能领取津贴,还通过各类“新政”计划促使青年、长期失业者和单身父母等参与劳动力市场,把工作福利计划推向了福利改革的最前沿。在英、美等自由福利国家工作福利项目风靡之后,德、法等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也开始相仿相效,于1990年代末期引入工作福利的理念和路径,比如,2002年德国的“哈茨改革”就是对原有救助制度的彻底变革,要求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必须承担工作义务。此外,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即以慷慨的福利供给著称的北欧,也在发生“悄悄的革命”,其在社会救助中逐步构建起以地方化、市场化和突出个人义务为特征的工作福利,使工作福利成为北欧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比如,丹麦1998年颁布的“激活”法案弱化了收入保护原则,强调了工作义务和福利领取的关联,正式引入工作福利的原则[5]。由上可见,工作福利最早在美国形成,之后在英国等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普及,最后扩展至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回顾工作福利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以下三点重要逻辑和规律:
第一,福利国家的危机和改革是工作福利形成的总体背景。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向国民提供慷慨的福利待遇,福利国家得以形成并快速发展,这对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好景不长,1970年代末,受石油危机和全球化加速的影响,欧美经济出现滞涨,沉重的福利负担既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也使劳动力价格偏高,企业竞争力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患上了所谓的“福利病”,福利国家遭遇了整体危机。为了应对和化解危机,“积极福利国家”“社会投资国家”“发展型社会政策”等理论和概念应运而生,强调改变传统福利国家以权利为基础提供消极福利的方式,转向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提供积极的福利,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与市场的结合,变事后补救为事前干预。在福利国家改革与重建的总体背景下,工作福利出现并逐步成为主导,它为福利领取者强制增加了义务,以促使其重返劳动力市场,体现出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以及与市场的联结,这顺应了福利国家改革的大趋势,是福利国家危机与改革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有学者断言欧美的“制度型福利国家”已经逐渐被“工作福利型国家”所取代[6]46-47。
第二,福利依赖问题是工作福利形成的直接原因。福利国家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慷慨的福利待遇,保障了公民的社会权利,但是在福利国家建设中出现的福利膨胀,使贫困治理的问题日益暴露[7]。福利国家的贫困者领取救助后,不愿积极寻找工作,因为贫困者普遍缺乏技能,即使找到工作,工资收入并不比救助待遇高,这会导致受助者长期依靠救助生活,损害受助者的工作伦理,由此引发福利依赖问题。比如,在美国,1960年贫困家庭中近2/3的户主有工作,到1991年这一比例已降到1/10[8],且大部分受助者是单身母亲,她们这种福利依赖的态度和行为不仅使自身落入“贫困陷阱”,还对其子女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了福利依赖的代际传递[9]。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宣称要“终结我们所知道的福利”,1996年《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法案》出台,该法案增加了对福利领取者的工作要求、限制了福利领取时间并实施了严格的制裁措施,是典型的工作福利政策。由此可见,工作福利对受助者提出了强制性的工作要求,通过各种方式激励、重塑及培养受助者的工作伦理,使其尽快进入劳动力市场,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福利依赖问题。
第三,国家间学习是工作福利得以普及的重要推动力。所谓国家间学习,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的改革信息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策选择带去影响的一种模仿或学习过程,是一国的制度与政策被他国借鉴的现象,许多学者还把这种现象称为政策转移、政策模仿等,但国家间学习是关于政策借鉴的总体概念[10]。工作福利最早在美国出现,1996年克林顿政府实施了激进的福利改革,使工作福利在美国成为主流政策,这标志着现代福利国家对受助者的社会保护导向发生了本质变化,受助者需要主动投身劳动力市场而不再只是被动地领取福利。美国的工作福利首先在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被广泛地学习与借鉴,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1997年开始实施“从福利到工作”的政策实践;之后,以德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和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也开始模仿并实施了工作福利,如德国2002年的“哈茨改革”和瑞典2000年的“激活保证计划”均是典型的工作福利计划,以促进受助者重返劳动力市场。由上可见,国家间学习推动了工作福利在福利国家的扩展与普及。
二、工作福利的概念辨析:工作福利、“激活”政策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根据美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第18版)的定义,工作福利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在接受救助时应当提供相应劳动,以这一要求为条件的福利项目,为了与现金救助相区别,曾被称为工作救济,如今,此政策通常被称为工作福利[11]。工作福利从严格意义上看,具有地域性含义,指的是美国的福利改革措施,强调的是受助者的义务和责任,要求受助者通过工作来换取救助,侧重于“工作优先”原则,重点在于工作要求、制裁和领取现金救助的时间限制,带有强制性、惩罚性和消极性的特点[12]5。然而,随着工作福利政策在欧洲和其他福利国家的扩展与普及,以及“工作福利”一词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普遍使用,工作福利概念的外延开始拓展,除了“工作优先”的消极性措施外,一些积极的措施,如培训、教育、儿童照料等也在一些情况下被视为工作福利的组成部分[12]7,这就导致了工作福利概念的模糊化,尤其是容易与“激活”政策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产生混淆,因此,有必要对工作福利、“激活”政策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区分和辨别。
“激活”政策是指促使受助者和失业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工作导向型福利措施的总和,这类“激活”措施可大致分为两类,即积极型(人力资本发展型)措施和消极型(劳动力市场关联型)措施,顾名思义,前者主要是促进受助者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提高人力资本以使其能够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而后者则是通过快速就业的方式强制受助者接受任何工作以脱离社会救助[13]。由此可见,工作福利对应的是消极型“激活”措施,也就是说,工作福利从严格和本源的意义上讲,只是试图使受助者进入工作状态,并没有把提升受助者的技能水平和人力资本作为政策设计的目标,正如美国工作福利政策实施中一名监督者所言,“你不需要通过教育来获得就业,为了就业你只需要去工作”[14]。
工作福利即消极型“激活”政策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市场型工作福利和工作创造型工作福利。市场型工作福利强调增加低工资的就业岗位并促使福利依赖群体,如长期失业者、单身父母以及病残群体,尽快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接受那些低工资的就业岗位。市场型工作福利旨在使福利依赖群体更可雇,尤其是运用财政政策去补贴低工资就业,当福利依赖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会获得相应的在职补贴,这有助于增加其就业的动力,但是,市场型工作福利对福利依赖群体没有教育和培训承诺[3]32。1980年代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逐步采取了市场型工作福利,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美国的工作福利强调福利依赖群体在一定时间内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否则会面临惩罚,进入市场后由于工资较低,政府实施了低收入工薪家庭的工作收入课税扣除政策(EITC),向实现就业的低收入受助家庭提供额外补贴。工作创造型工作福利是兜底的政策工具,对于那些无法在私营与公共部门获得就业的就业困难群体,需要通过工作创造型工作福利使他们为了救助待遇而工作。救助管理机构在常规劳动力市场外创造“工作测试”活动来检测受助者为了保持待遇而愿意工作的意愿,当然,工作创造型工作福利存在一些固有缺陷,这限制了其应用范围,这类政策必须是“额外的”,以避免与现有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就业产生竞争,相应工作必须置于政府的控制监督之下,这意味着这类工作具有非生产性或象征性的特点,这类工作不能给接受者带来技能的提升甚至会产生污名化效应,也就是说,工作创造型工作福利是一种“人造性”就业,其效用有限。然而,对一些长期失业者而言,其对就业的期待度很低,他们不会把这类工作项目当成惩罚,反而非常乐于接受,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面对非生产性劳动力的膨胀,并不得不对这些就业最困难群体承担直接责任,因此,工作创造型工作福利可能导致参与者不会去市场中寻找有酬就业,尤其是在他们认为其可获得的工资很低的情况下[3]34。1990年代后,许多OECD国家实施了工作创造型工作福利,由政府提供捡拾垃圾、清扫街道等公共就业岗位。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概念最早于1950年代出现在瑞典,是瑞典充分就业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波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发挥了劳动力动员的作用,加速了劳动者从传统就业部门转向现代就业部门,它强调的是使劳动者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就业转向高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注重的是工资政策、人力资本生成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联结关系[15]121。1960年代中后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逐步发展转型,迈入第二波阶段,尤其是1973年后,当石油危机导致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发生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它脱离了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联系,范围开始缩减,主要包括公共就业服务的扩展、教育与培训政策以及公共部门的就业创造。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普遍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目标定位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普遍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是改善国家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劳动者技能提升战略的一部分,并把技能生成与劳动力市场动员和流动性联结起来。普遍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需要依靠其他劳动力市场机制如工资谈判等才能取得成效,还需要政策制定者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劳动力市场分割,尤其是避免低工资部门的产生,OECD国家中采取这种政策的寥寥无几,只有瑞典和其他少数北欧国家采用[15]123。目标定位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OECD国家则比比皆是,主要聚焦于劳动力市场中的特殊群体,如青年、中老年劳动者、长期失业者及其他弱势群体,政策包括对上述目标群体的不同程度的承诺,如教育、培训和公共就业岗位的创造,一般而言,针对青年群体会提供较为慷慨的政策服务,试图使其接受主流培训和教育以提升人力资本,短期课程主要针对长期失业群体以破除其失业状态,让其尽快就业[3]35。由此可见,目标定位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应“激活”政策中的积极型措施,旨在提升特定就业困难群体的人力资本,而无论哪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严格意义上的工作福利都没有交集,因为工作福利并不关注参与者人力资本与能力的提升。
总的来看,工作福利、“激活”政策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关系如表1所示。严格意义上的工作福利概念是通过强制性和惩罚性措施要求参加者以工作换救助,并没有教育和培训的承诺,对应的是消极型“激活”措施,其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之间泾渭分明,但是随着工作福利政策的扩散和工作福利概念外延的拓展,一些情况下,工作福利与“激活”的概念接近,而积极型“激活”措施对应目标定位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这才导致某些情况下工作福利可能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产生关联。

表1 工作福利、“激活”政策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关系与特征
注:笔者根据Jörg Michael Dostal的分类整理改编。Jörg Michael Dostal,The workfare illusion: re-examining the concept and British case [J].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2007,42(1).
三、工作福利的实践效果:福利依赖的降低与在职贫困的出现
工作福利是为应对福利依赖问题而出现的,旨在促使受助者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就业实现自立并摆脱对救助的依赖。因此,考察工作福利的实践效果可以从其是否有效地应对了福利依赖问题入手。关于福利依赖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基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偏于主观的概念界定,即认为福利依赖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一种流行于底层阶级( underclass)的“依赖文化”,受助者宁可依赖救助生活也不愿寻找工作;二是偏向客观的事实描述,即家庭需要长期依靠救助金生活,关于“长期”如何界定,在不同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定义。由此,衡量工作福利的实践效果,一方面可以考察工作福利是否改变了受助者消极的主观态度,另一方面可以考察工作福利是否降低了受助者依赖救助金生活的时间,即受助者是否可以通过就业逐步摆脱救助。
工作福利的出现意味着受助者不再仅是被同情的弱势群体和单纯的权利享受者,而是必须承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义务,不能再依赖救助生活。关于工作福利实践的研究表明,从主观方面看,工作福利确实提高了受助者个人的工作努力水平,改变了其以往的消极态度,形成了责任与义务观念[5],工作福利参加者对工作抱有积极态度,尽管其知道救助的重要性,但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有酬就业来脱离救助,赢得自尊和尊重,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16];从客观方面看,工作福利降低了受助者人数,提高了受助者的就业率,比较有效地降低了受助者对救助的依赖[4]。以美国为例,1996年通过福利改革全面实施工作福利后,从1996年8月到1999年3月受助人口显著下降了40%,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的一项报告表明:从1996年到1998年接受救助人口下降的1/3是实施福利改革所取得的,全面采取工作福利是这一时期广泛并持续的受助人口下降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福利改革后受助者的就业率在短期内不断上升,1998年美国受助者的就业率达到23%,而1992年只有7%,1997年也只有13%,其中单亲母亲作为救助对象的主体,就业率增加尤其明显[17]。但是,工作福利在较为有效地降低福利依赖的同时,并没有明显地降低贫困率,受助者由于缺乏教育和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有限,就业岗位不稳定且工资偏低,此外,“对工作必须接受”的条件限制会对工作质量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出现“以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为代价的廉价劳动力供给的扩张”,造成在职贫困群体[4]。例如,美国的研究发现,部分前受助对象工作后的收入仍难以达到贫困线,属于工作穷人,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75%的前受助对象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特拉华、明尼苏达、俄勒冈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与佛罗里达州彭沙科拉城的政府工作示范计划参与者的平均收入仅为官方贫困线的2/3[11]。
事实上,关于“激活”政策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促进受助者就业脱贫方面,积极型“激活”措施的效果明显且长期,消极型“激活”措施只有短期效果或效果不明显[13]355。也就是说,从长远看,为了减少福利依赖并促进受助者通过就业自立,重视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积极型“激活”措施比单纯地强制受助者进入低级劳动力市场的消极型“激活”措施更为有效[18]502。由此,对应着消极型“激活”措施的工作福利,在降低受助者人数方面显示出短期效果,从长期看却难以使受助者脱贫并容易导致在职贫困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工作福利从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众多国家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福利主义转向工作福利主义已成为当今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工作福利在严格意义上属于消极型“激活”措施,秉承“工作优先”原则,通过强制性与惩罚性措施力图使受助者尽快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对教育和培训的承诺,很难使受助者提升就业能力和积累人力资本。在实践中,工作福利通过强制性和惩罚性措施确实改变了受助者消极依赖的态度,减少了受助者人数,较为有效地降低了福利依赖,但却制造了在职贫困和工作穷人,难以真正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在国家向贫困者提供救助的情况下,工作福利能否取得成功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与整个反贫困政策体系特别是就业支持政策的完善与否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缺乏有效的反贫困与就业支持政策,受助者的能力贫困问题与合适的就业岗位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19],那么工作福利的实践效果必然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