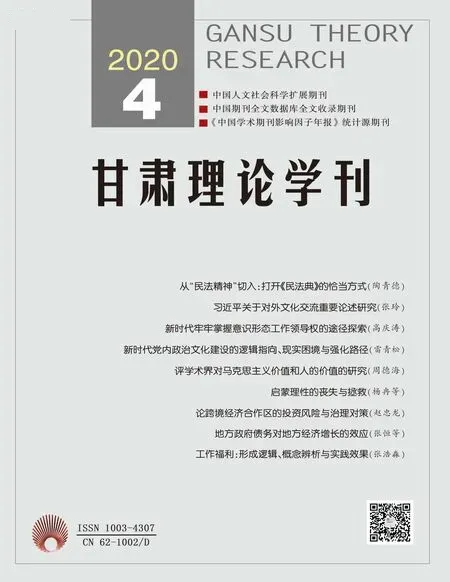论伤害原则的两种解读
冯秀岐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伤害原则是《论自由》中的核心原则,也是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密尔对伤害原则的正式陈述是:“人类之所以有正当理由干涉其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不管是出自个人还是集体地,唯一的目的是自我保护。也就是说,施用权力于文明社会中任一成员而违背其意志且不失正当,其唯一的目的是防止伤害他人。”[1]223也就是说,在密尔看来,干涉个体自由的唯一正当理由是防止伤害他人。但是,防止伤害他人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防止行为者的行为伤害他人,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它仅仅干涉(1)对他人会造成或已造成伤害的行为。第二种是防止他人受到伤害,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它除了干涉(1)外,还干涉(2)并未对他人造成伤害但干涉之便可防止他人遭受伤害的行为。
对防止伤害他人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导致研究者们对伤害原则有两种不同的解读。这两种解读与对防止伤害他人的两种理解相对应。第一种解读认为,仅仅当行为者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时,伤害原则才允许干涉行为者的自由。这是一种狭义的解读,可称之为有害的行为阻止原则(harmful conduct-prevention principle),布朗采取这种解读[2]135。另一种解读认为,即便行为者的行为根本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只要干涉行为者的自由能阻止他人遭受伤害,伤害原则就允许干涉行为者的自由。这是一种广义的解读,可称之为一般的伤害阻止原则(general harm-prevention principle),莱昂斯采取这种解读[3]5-6。
二者的区别在于,狭义的解读要求被干涉者的行为本身必须是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而广义的解读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它认为只要干涉一个人的自由可以阻止他人遭受伤害,就可以干涉这个人的自由。很明显,广义的解读可以包含狭义的解读,且比狭义的解读允许干涉的范围更广,因而也就对人的自由有更多的限制。
本文将考察这两种解读的合理性,论文主体分为四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分析《论自由》中分别支持两种解读的文本证据,并指出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是支持广义的解读的核心证据。因此,我将对这两种要求的探讨作为讨论两种解读的合理性的重点。在第二部分,我将相对明确地界定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并将重点区分狭义和广义的合作的要求。在第三部分,我将考察研究者们提出的第一种方案:通过解释密尔对两种要求的看法来加强狭义的解读的合理性。在第四部分,我将考察第二种方案:尝试采用广义的解读解释两种要求。最后我将简要总结全文。
一
研究者们对伤害原则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且广义的解读包含狭义的解读。那么,《论自由》中有文本证据支持狭义或广义的解读吗?
明确支持狭义解读的文本证据很多,散布于密尔对伤害原则的表述与论证当中。首先,在初次表述原则时,密尔写道:“人类之所以有正当理由干涉其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不管是出自个人还是集体地,唯一的目的是自我保护。”[1]223这里所谓的“自我保护”,应理解为保护自己不受他人行为的伤害,因此,这句话可理解为:干涉他人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保护自己免于遭受他人行为造成的伤害。这种说法是支持狭义的解读的。其次,在表述伤害原则的段落中,密尔写了这样一句话:“要使强迫成为正当,必须是所要对他加以阻止的行为将会对他人产生祸害。”[1]224很明显,这也是在指出只有当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时才能加以阻止,因此是支持狭义的解读的。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如“只要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伤害我们的同胞”[1]226和“由于对他人利益的伤害或者可能伤害”[1]292等。
文本中也存在支持广义的解读的证据。例如,在正式陈述伤害原则时,密尔写道:“施用权力于文明社会中任一成员而违背其意志且不失正当,其唯一的目的是防止伤害他人。”[1]223正如之前分析过的,“防止伤害他人”的方式,除了包括干涉(1)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还包括(2)并未对他人造成伤害但干涉之便可防止他人遭受伤害的行为。狭义的解读只能包括(1),而广义的解读可以包括(1)和(2)。因此,这正式陈述可算作支持广义的解读的证据。
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证据似乎支持广义的解读。它是密尔表述伤害原则允许干涉的行为的一段话:“我要力争说,这样一些利益是享有权威来令个人自发性屈从于外来控制的,当然只是在每人涉及他人利益的那部分行动上。假如有人做出了一个有害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一桩初看就要处罚他的事件,可以用法律来办,或者当法律惩罚不能妥善适用时,可以用普遍的谴责。还有许多积极性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要强迫他去做,也算是正当:例如到一个法庭上去作证;又如在共同的防卫当中,或者为他享受其保护的社会之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联合工作当中,担负他的公平份额;还有特定的个人仁慈行为,例如去救一个人的生命,或挺身保护遭受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总之,凡明显是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1]224-225
在这段话中,密尔似乎区分了伤害原则允许干涉的两大类行为。第一类是有害于他人的行动。第二类是积极性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有人将第二类行为中的例子分为两类,分别称作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cooperation and good Samaritan requirements)[3]4。合作的要求包括去法庭上作证和服兵役等;乐善好施的要求包括救一个人的生命和挺身保护遭受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等。
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似乎超出了狭义的解读允许干涉的范围,因而偏向于支持广义的解读。举例来说,当一个人力所能及,却不救人或不挺身保护遭受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按照乐善好施的要求,就可以对其进行道德谴责或法律处罚。但是,狭义的解读禁止在一个人的行为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干涉其自由。因此,假使这个人的行为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狭义的解读会反对谴责或处罚这个人。因此,在不去救助者的行为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前提下,狭义的解读不允许乐善好施的要求。
广义的解读允许乐善好施的要求。在广义的解读看来,允许干涉不救人者的行为,其理由不在于不救人者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在于干涉其行为将阻止他人遭受伤害。对于其他乐善好施的要求,也是如此。因此,这就能很好地解释密尔所说的:“还有特定的个人仁慈行为,例如去救一个人的生命,或挺身保护遭受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1]225所以说这段表述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的文本似乎支持对伤害原则做广义的解读。
由上述讨论可知,《论自由》中有文本证据分别支持对伤害原则的狭义和广义的解读,其中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是支持广义的解读的核心证据。因此,对这两种要求的探讨构成了讨论两种解读的重点。考虑到《论自由》中有诸多文本支持狭义的解读,有研究者想通过澄清和解释密尔对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的看法,来加强狭义的解读的合理性;也有研究者认为狭义的解读无法处理两种要求,于是尝试采用广义的解读。
二
讨论上述两种方案时,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狭义或广义的解读能否充分解释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因此,先对两种要求进行相对明确的界定是有必要的。
来看乐善好施的要求。所谓乐善好施的要求,通常可以理解为:当有人被伤害或处在危险之中,如果行为者救助他就能使之免于伤害,且自身不会遭受严重损失,那就可以要求行为者实施救助。鉴于密尔未明确界定伤害原则允许的乐善好施的要求的内容,我将乐善好施的要求限定在他所举的例子之内,即救一个人的生命和挺身保护遭受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
乐善好施的要求比较简单,合作的要求相对复杂。在《论自由》的核心段落中,密尔两次表述合作的要求。在第一章初次表述伤害原则时,密尔写道,一个人要在“为他享受其保护的社会之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联合工作当中,担负他的公平份额”[1]225。在第四章复述伤害原则时,密尔写道:“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份额。”[1]276
对于这两次表述的关系,进而对合作的要求的内容,研究者们存在争议。布朗认为,两次表述虽然很相似但有重要的差别[2]145-146。在第一章的表述中,密尔说的是“社会之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联合工作”;而在第四章的表述中,密尔强调的是,“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的工作。任何联合工作既包括“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的方面,又包括促进利益的方面,其范围更大。
莱昂斯认为,密尔也会认同促进利益与阻止伤害有差别,但莱昂斯对两次表述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3]13-14。莱昂斯认为,在第一章中,密尔只是在一般性地陈述合作的要求,而后面的表述才能代表他真实的想法。例如,在第四章总结伤害原则允许干涉的行为时,密尔写的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份额”[1]276。在这句话中,密尔将合作的要求限定在“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的工作。因此,莱昂斯认为,密尔是依据阻止伤害界定合作的要求的。理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密尔所举的例子,例如到一个法庭上去作证和在共同的防卫当中担负自己的公平份额。另一方面来自上段中对两次表述的关系的理解,即后面旨在防止伤害的表述才代表密尔对合作的要求的真实想法。尽管未明确指出,但布朗认为密尔是依据阻止伤害和促进利益界定合作的要求的。
由上述讨论可知,密尔对合作的要求的不同表述使得界定它变得困难。然而,如果不能相对明确地界定合作的要求,就无法充分讨论狭义或广义的解读能否完全允许它。所以,为了便于讨论,我将以狭义的合作的要求指称密尔所举的例子,即到法庭上去作证和在共同的防卫当中担负自己的公平份额;以广义的合作的要求指称依据阻止伤害和促进利益来界定的合作的要求,即布朗所理解的“为他享受其保护的社会之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联合工作当中,担负他的公平份额”[1]225;以合作的要求指称狭义和广义两种合作的要求,或泛指合作的要求。
三
界定完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后,我们来考察第一种方案:狭义的解读能充分解释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
之前的讨论表明,狭义的解读不允许乐善好施的要求。但是,这个论断是有条件的,它要求不去救助者的行为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这种有条件性为狭义的解读允许乐善好施和合作的要求留下了可能,也有证据表明密尔尝试依据这种可能为狭义的解读允许两种要求辩护。
在区分了“有害于他人的行动”和“许多积极性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之后,密尔试着解释这种区分:“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动贻害于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而贻害于他人,在任一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都是正当的。”[1]225有人认为,密尔这句话意在给出区分伤害原则允许干涉的两大类行为的标准,即行动和不行动[4]256。具体来说,这句话是想说明:“有害于他人的行动”和不做“许多积极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都属于伤害他人的行为,即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两者的不同只在于,前者是因行动而对他人造成伤害,后者是因不行动而对他人造成伤害。
如果上述理解成立,就为狭义的解读允许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留下了可能。理由在于,如果未完成两种要求属于因不行动而对他人造成伤害,伤害原则允许它们就是为了防止被干涉者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这正符合狭义的解读。因此,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将未完成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视为对他人造成伤害呢?或者说,因不行动而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说法能否充分解释两种要求呢?
先来看合作的要求。布朗认为,将一个人没有担负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的任务中自己的份额视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这个观点容易得到辩护。但将一个人没有在“为他享受其保护的社会之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联合工作当中,担负他的公平份额”视为对他人造成了伤害,这个更强的观点得不到辩护。理由在于,维护社会之利益所必需的联合工作范围更广,其中包括乡村建设等问题。一个人未完成这类广义的合作的要求,不能说他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因而狭义的解读不能允许这类广义的合作的要求[2]145-146。因此,根据布朗的观点,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因不行动而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说法能解释狭义的合作的要求,但不能解释广义的合作的要求。
再来看乐善好施的要求。布朗指出,至少存在一些情况,尽管一个人未完成乐善好施的要求,也不能说是他造成了伤害[2]145。例如,当我不去救助被第三方推入水中的人时,尽管我未完成乐善好施的要求,但造成伤害的是第三方而不是我。因此,密尔将未完成乐善好施的要求视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做法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因不行动而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说法不能充分解释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换言之,没有充足的理由将未完成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视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这是否意味着狭义的解读不能充分解释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未必,伯格尝试为密尔辩护。
伯格认为密尔有如下观点[4]123-278:只有为了防止一个人伤害他人的权利,才可以干涉他的自由;权利是由正义的规则界定的,而正义的规则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正义的规则保护安全利益。为了讨论的需要,首先,我将结合密尔的正义理论说明正义的规则如何保护安全利益,从而引入体系性利益的说法(以便随后讨论合作的要求)。其次,我将概述权利与正义的规则、功利主义之间的关系。最后,我将分析将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纳入个人权利之中的做法,从而考察狭义的解读的合理性。
首先,正义的规则如何保护安全利益?伯格指出,密尔对正义的解释的核心在于宣称正义的规则保护安全,理由在于两点[4]148-149。第一,正义的规则禁止人们相互伤害,它们以社会强制的方式参与到对伤害的社会性保护当中。第二,正义的规则界定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规制着人们的行为,使它们变得一致;行为的一致使得个人的行为构成社会正义体系的部分,也能更好地保护人们的安全。
伯格认为,第二点表明对权利的认可创造了新利益,即体系性利益。体系性利益源自体系自身的存在,每个参与到体系中的人都在维护体系中具有的利益。创造权利体系使得几乎所有对权利的侵犯都有其不合功利之处。伯格认为也存在潜在的体系性利益。基于不断计算的各种不确定,建立强制性规则体系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而有其合功利之处。这两种体系性利益的存在加强了认真对待权利的功利主义基础。
因此,这就涉及到,对于密尔而言,权利与正义的规则、功利主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首先,权利是由正义的规则界定的。依据密尔的正义理论,一个人具有权利的充要条件是[4]131-133:当且仅当存在或应当存在要求社会保护一个人对X的运用、享受或拥有的得到认可的正义规则时,这个人才对X具有权利。其次,正义的规则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密尔指出:“为什么社会应当保护某个人拥有某种东西?那么我能给出的理由就唯有社会功利。”[5]55结合密尔的权利观念和功利原则,可知当且仅当得到认可的规则保护它们符合普遍的社会利益时,一个人才能对某些行为模式或对待宣称有权利。
那么,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是否属于正义的规则所要求的呢?即它们是否属于个人的权利呢?假使它们属于个人的权利,又能否基于功利主义而为之辩护呢?
先来看合作的要求。密尔提及过各种正义的规则,其中他对合作的看法,对于讨论合作的要求很有价值,伯格关注到了这点[4]147-153。伯格指出,人们需要合作,因为有些重要的事情只有通过参与其中的多数人的协作性努力才能完成。合作促进两种利益,一是合作产生的物品中的利益,二是潜在的体系性利益。为了保障这些利益,人们需要遵守合作的义务。如果有人不遵守合作的义务,合作将是不稳定的。因此,就需要确立强制性规则来使人们遵守合作的义务,这些强制性的规则确立了人们服从的义务,而遵守它们就是在维护体系性利益,从而是合功利的。
伯格相信,将对合作的分析与密尔的权利理论结合,便能发现人们服从的义务对应于他人的权利。合作源于并促进体系性利益,有时应以社会强制的方式保护体系性利益。正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密尔对权利的分析使得他相信每个合作者对他人的表现具有权利。这种对应,使得服从的义务具有了公平的义务的重要特征。
是否存在公平的义务?研究者们对此充满争议。我并不展开相关的讨论,只是想提出:在对公平的义务的功利主义辩护充满争议的情况下,将合作的要求纳入个人权利之中的功利主义辩护能否成功?同样会充满争议。
伯格认为,密尔试图将合作的要求纳入个人权利之中,如果一个人未完成合作的要求,那么他就伤害了他人的权利。因此,密尔将未完成合作的要求视为对他人造成伤害是没有问题的。但正如伯格所言,尽管密尔承认人们在合作事业中有相应的义务,但他没有讨论这些义务的恰当限度,或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具有或不具有它们[4]292-295。从而,对于密尔而言,能纳入权利之中的合作的要求包括哪些,能完全包含广义的合作的要求吗?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我们便无法确认狭义的解读能否充分解释广义的合作的要求。
再来看乐善好施的要求。伯格认为,可以依据救助权来解释乐善好施的要求。伯格指出,在特定情况下,人们在他人的救助中具有巨大的利益,乃至于要确立规则以使利益得到保障,这使得人们享有了救助权。因此,如果一个人不去防止祸害以满足乐善好施的要求,就是伤害他人的救助权[4]123-278。
在我看来,伯格的解决方法的要点在于将乐善好施的要求纳入他人的救助权之中。只要一个人未完成这些要求,那么他就伤害了他人的权利。因此,伯格认为,密尔将未完成乐善好施的要求视为对他人造成伤害是没有问题的。但正如对将合作的要求纳入个人权利之中的功利主义辩护充满争议,将乐善好施的要求纳入个人权利之中的功利主义辩护仍有待考察。
最后,简要概括伯格对密尔的辩护:密尔试图将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纳入个人权利之中,如果一个人未完成这些要求,那么他就伤害了他人的权利,于是便能依据因不行动而对他人造成伤害来解释两种要求,因此便增强了狭义的解读的合理性。
但正如上述讨论所展现的,这种做法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能纳入权利之中的合作的要求包括哪些,能完全包含广义的合作的要求吗?第二,将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纳入个人权利之中的功利主义辩护能否成功?考虑到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故不能得出结论说对伤害原则的狭义的解读完全成立。
四
第一种方案没有成功,我们来考察第二种方案:广义的解读能充分解释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吗?
如前所述,密尔对伤害原则的正式陈述可支持广义的解读。除此之外,密尔在表述伤害原则允许干涉的行为时的一段话似乎支持广义的解读。在这段话中,密尔似乎区分了伤害原则允许干涉的两大类行为:有害于他人的行动;积极性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
密尔在解释这种区分时写道:“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动贻害于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而贻害于他人,在任一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都是正当的。当然,要在后一种情况下施行强制,比在前一种情况下需要更加慎重。一个人做了祸害他人的事,要他为此负责,这是规则;至于他不去防止祸害,要他为此负责,那比较说来就是例外了。然而,有许多足够明显和足够重大的情况足以证明那例外之正当。”[1]225如前所述,布朗认为密尔这段话旨在说明,“有害于他人的行动”和不做“许多积极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都属于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
莱昂斯不同意布朗的看法。他指出,密尔承认造成伤害的行为和未能阻止伤害他人的行为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是布朗忽略的[3]9-11。理由在于,密尔明确写道:“一个人做了祸害他人的事,要他为此负责,这是规则;至于他不去防止祸害,要他为此负责,那比较说来就是例外了。然而,有许多足够明显和足够重大的情况足以证明那例外之正当。”[1]225莱昂斯指出,在给出这个区分的同时,密尔似乎也指出,伤害原则不仅允许干涉造成伤害的行为,也允许干涉未能阻止伤害他人的行为。
莱昂斯认为,总体而言,整个这段话提供的证据是模棱两可的。密尔最初对因不行动而贻害的评论表明他对例子的性质有些困惑,好像他希望将干涉限制在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之中。然而,密尔随后明确地扩展了干涉的范围,使之不限于造成伤害的行为,也能包括未能阻止伤害他人的行为,而这正是乐善好施的例子要求的。
很明显,如果造成伤害的行为和未能阻止伤害他人的行为的区分成立,且伤害原则允许干涉未能阻止伤害他人的行为,那么这无疑是支持广义的解读的。
伯格不认同莱昂斯的理解[4]225-226。伯格认为,密尔在祸害和不去防止祸害之间只做了词汇上的区分,他并没有说不去防止祸害不属于贻害。相反,密尔将不去防止祸害视为因不行动而贻害。做了祸害涉及积极的行为,而不去防止祸害涉及疏忽,但关键是这两种说法都明确被密尔归属于贻害。所以,伯格认为,这段话支持布朗的理解,而不是莱昂斯所说的是模棱两可的。
在对这段话的理解上,总体而言,我认为莱昂斯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布朗和伯格的观点尽管存在一些不明确之处但却是正确的。密尔区分了“有害于他人的行动”和“许多积极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但更为重要的是,密尔并不严肃对待这个区分。确切地说,密尔提及这个区分,只是为了说明伤害他人可以有因行动和不行动两种方式。密尔不严肃对待这个区分,是因为对于伤害原则而言,重要的是行为是否伤害他人,至于是因行动还是不行动而伤害他人,这一点并不重要。所以,基于上述理由,密尔只是在需要区分因行动和不行动而伤害他人时,才会提及这个区分;在其他时候,密尔并不重视这个区分,也因此他一般会采用笼统的表达乃至以前者来包含二者。
例如,在《论自由》的第四章中,密尔写道:“对他人有损害的行动就需要有完全不同的对待了。侵犯他人的权利;……甚至自私地不肯保护他人免遭损害——这些都是道德谴责的恰当对象,在严重的情况中也可成为道德报复和道德惩罚的对象。”[1]279在这段话中,密尔将“自私地不肯保护他人免遭损害”归属到“对他人有损害的行动”中。
同样的,在第四章中,在列举完伤害原则允许干涉的行为类别后,密尔总结道:“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1]276在这句话中,密尔将所有伤害原则允许干涉的行为归结为“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行为,实质上就没有严肃对待这个区分。
总之,密尔区分了“有害于他人的行动”和“许多积极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但并不严肃对待这个区分。在这个问题上,布朗和伯格的理解是正确的,而莱昂斯的理解是错误的。但是,即便莱昂斯对这段话的理解是错误的,仍至少有两点理由支持我们继续考察广义的解读。一是密尔对伤害原则的正式陈述可作广义的解读。二是狭义的解读并未完全成立。因此,我们不妨沿着莱昂斯的思路,来探讨广义的解读能否充分解释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
之前已经证明,广义的解读能充分解释乐善好施的要求。广义的解读允许干涉不乐善好施者的行为,其理由不在于他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在于干涉其行为将阻止他人遭受伤害。那么,广义的解读能否充分解释合作的要求呢?
如前所述,对合作的要求的不同理解使广义的解读解释它时更复杂。莱昂斯认为,广义的解读能充分解释狭义的合作的要求,即密尔所举的合作的要求的例子,如出庭作证[3]6-8。他指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依据阻止伤害解释出庭作证:为了建构有效的社会规则系统,就需要法庭来处理争论。要想维持它的良性运转,法庭就要对人们提出要求,出庭作证便是要求之一。在法庭提出的要求自身能依据阻止伤害而得到辩护的情况下,出庭作证作为要求的一部分,便可以依据阻止伤害而得到解释。据此,莱昂斯认为广义的解读能充分解释狭义的合作的要求。
广义的解读能充分解释广义的合作的要求吗?莱昂斯的回答是:视情况而定。举例来说,乡村建设属于广义的合作的要求,但广义的解读不能解释它。理由在于,乡村建设通常是为生活困苦的人提供更舒适和便捷的条件,而不是为阻止伤害,因而不能依据阻止伤害来解释它。
因此,莱昂斯认为,广义的解读能充分解释乐善好施和狭义的合作的要求,但是不能充分解释广义的合作的要求。然而,如果广义的解读都不能充分解释广义的合作的要求,那么是否存在伤害原则之外的限制自由的理由呢?布朗认为密尔支持道德的强制执行,并借此来解释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但莱昂斯和伯格认为布朗的做法不成功。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遗憾的是只能搁置了。
以上考察了对伤害原则狭义和广义两种解读的合理性。《论自由》中明确支持狭义的解读的文本证据很多,而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是支持广义的解读的核心证据。于是,我分析了研究者们提出的两种解决方案:通过解释密尔对两种要求的看法来加强狭义的解读的合理性;尝试采用广义的解读解释两种要求。但前者因未解决两个问题而失败:一是能否将广义的合作的要求纳入个人权利;二是将两种要求纳入个人权利的功利主义辩护能否成功。而后者不能获得《论自由》的文本证据的充分支持,也因未能充分解释广义的合作的要求而失败。因此,两种解读均未完全成立。
——读《论自由》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