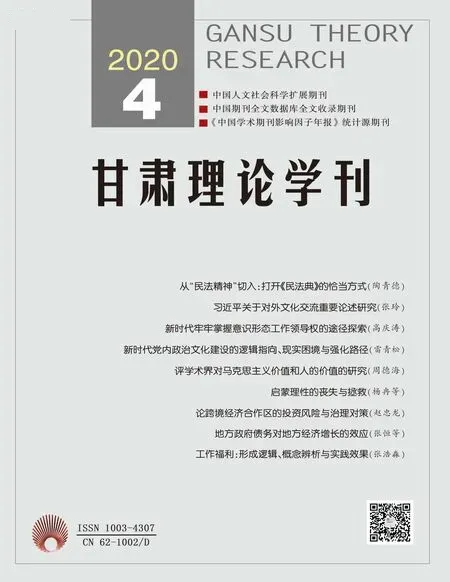论村落共同体:地方共同体想象的形成及其问题
张宗帅,邓小燕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文学系,北京 102488;2.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一、“村落共同体”概念的形成
近年来,在中国乡村研究中,“村落共同体”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应用。随着“村落共同体”这一概念被不断不加选择地加以运用,其所带来的问题性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因此对“村落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产生背景及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辨析和重新想象显得十分必要。“村落共同体”概念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张力:对“村落共同体”概念的建构,出于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及城市化的回应。波兰尼、鲍曼等现代社会理论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力量不断地瓦解和冲击着传统的农村社会,“市场力量对农村、农民的冲击根本上就是对共同体的冲击”[1],随着城市化、资本下乡及跨国农业对本土农业的冲击越来越强烈,传统的农村社会经受着痛苦的瓦解。城市生活的孤独和陌生化也使得人们对传统乡村寄托了乌托邦的想象,从而使得“村落共同体”这一具有田园色彩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讨论的视野中来,“村落共同体”成为与“社会”(城市)相对照的存在。在中国的农村研究中,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构建的“共同体”与“社会”这对处于社会历史发展演变历史形态(同一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概念逐渐转化为农村社会生活与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对立(同一历史时间中的不同地理空间)。
“共同体”这一概念来自1887年滕尼斯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共同体”一词来自德语gemeinschaft(英译为community),在中文中译作“共同体”或“社区”,这个词有集体、共同、公有、共同体、社区的含义,而与“共同体”(gemeinschaft)相对照的“社会”(gesellschaft)一词则有社会、社团、联合体的含义,是利益计算和理性选择的结果。“共同体”具有自然、有机性、地域性、自治的特性,体现了人们的自然的本质意志,是基于情感与信任的结合,是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它强调的是人们的共享道德感及其激发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与地方感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是建立在边界尤其是地理边界上的,是地方性的,因此“共同体”与“地方”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后来人也往往将“地方”与“共同体”并置;而与之相对的“社会”则更强调它的社会性、人的理性建造和选择性,是一个相对于具有自然性的共同体的人造之物,是人类社会理性计算不断发展的产物,是非地方的。“共同体”与“社会”是两种抽象的理想类型,韦伯认为共同体和社会是连续、混合地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是具有连续性的演变过程,而不是完全对立的。中国学者毛丹也指出,作为“共同体”“社区”的村落的状态受到国家力量、市场力量的影响,村落共同体要保持活力,就要突破边界,通过建立社区外的联系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得到发展。“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处于与外界的互动和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由此可见,“共同体”概念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存在较大的“想象性”和“建构性”,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简单的对立和水火不容的,而是一种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的复杂交叉关系。
从“共同体”“社区”的路径对中国村落进行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1919年,葛学溥指导学生在广州凤凰村进行调查;1935年,吴文藻领军的燕京学派,其门下的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以村落为中心,对乡民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式观察[2]46。这一类研究开启了中国农村“共同体”“社区”研究的先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类研究虽然被战火所中断(被迁移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如魁阁学派),但关于华北地区的“社区”“共同体”研究继续由日本学者进行:日本满铁株式会社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惯性调查,1940—1950年代,日本学者以满铁在1940年代进行的《中国农村惯性调查》为依据,围绕着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这一问题展开了论战[3]。这场论战分成了两派:以平野义太郎、清水盛光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存在村落共同体,小山正明、丹乔二等人以南宋江南圩田的修筑为例,认为这种村民共同修筑圩田的合作形成了佃农的村落共同体。认为中国农村存在共同体的日本学者,将村落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关系主体,把村庄看作村民自治的,而将国家的力量看作外来的因素。以戒能通孝、福武直等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中国华北、华中的村落不存在像日本村落那样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原因在于,中国北方的村落以及村民的土地没有明确的村庄边界,一个行政村往往由几个自然村组成,并且由于北方村落内部缺少大的宗族,村落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联合,村落中存在的合作是一种消极的生活互助关系,地主、中农、贫农之间存在着分离。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后来的村松祐次、古岛和雄、河地重藏等日本学者。到了1980年代,日本学者滨岛敦俊通过进行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结合性研究指出,江南三角洲不存在小山正明和丹乔二所说的由“圩”形成的村落共同体。日本学者对中国村落共同体问题的关注有日本学界自己的历史语境,如后来的日本学者旗田巍指出,主张中国存在村落共同体的学者,其背后受到大亚洲主义观念的支配,企图寻找中日农村的共同性来为侵略行为张目,而主张中国不存在村落共同体的学者则是受到“脱亚入欧”观念的影响。在对日本学者所引发的“村落共同体”概念进行分析和讨论时,应对这一语境进行辨析,从而建立在中国语境中讨论这一概念时所应具有的明晰性。
二、村落共同体与地方士绅
地方士绅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构建村落共同体的想象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学界“乡绅土地所有论”便体现了地方士绅与村落共同体的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日本学界持“乡绅土地所有论”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地方士绅是相对于中央的、封建化的半独立权力。但是这一论点没有考虑到地方乡绅的权力是通过科举考试经中央权力授予的,国家通过对科举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得“绅士同国家的关系有双重性质,既支撑着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4]5。张仲礼指出,中央权力通过对成为士绅成员资格的制度控制——科举制度,实现了对士绅的控制,即中央权力可以授予同样也可以收回给予士绅的权力。科举取士不仅是中央权力对士绅身份的承认,同时在考试内容上通过儒家思想中“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实现了对士绅的价值引导。罗志田指出,士绅承担着“天道”和“天理”这一类超越地方的伦理价值,使得地方士绅获得了一种“天下”视角,士绅与中央(天下)关联在一起,即“天下士”,这样一来地方士绅就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的一面,把对中央利益的关切纳入进来,成为国家利益的隐性代表。地方势力与大一统国家政权之间建立了一种“虚实兼具又不可或缺的关系”[5]47,绅与官(国家的代表)、士(道的代表)联系在一起。地方士绅虽然身处地方,但在思想和情感上有与中央、儒家伦理密切联系的一面。
从权力获得的方式上来看,地方士绅作为地方权力集团,其权力是中央权力授予的,而不是通过与中央权力的对抗获得的,这种权力来源使得地方士绅即便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力(甚至与中央权力进行对抗),但这种自治和对抗的力量也是十分有限的,甚至这种自治和对抗本身也是中央权力的一部分。如罗志田所指出的,“我们不必总是关注地方与国家对立甚至对峙的一面,还要看到其互补的一面”[5]60。南宋以后废除了乡官,官止于州县,这一系列措施体现出中央对地方的放权,是中央权力有意识地建构出的一个非官方的地方社会。在这个非官方的地方社会中,以往的研究已经指出地方士绅在地方事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这种重要作用是在中央权力有意识地默许下实施的,并且这种地方权力的运用往往在中央权力的监视之中,萧公权曾指出,“尽管地方人士被广泛用于辅助控制,但官府仍然很小心地注意对他们的监视”[6]351,官府对士绅以“礼法绳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中央权力对地方豪强势力的压制和掌控,如清初,强势的中央权力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对江南地方士绅进行了打压,乡绅的力量衰弱下去,直到清中期以后才有所抬头。
地方士绅与中央权力是一体两面,与中央权力互补,而不是半独立的权力集团,地方士绅与地方民众也并不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近世以来,科举考试门槛降低、教育普及、捐纳入士等因素导致地方士人群体数量膨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士绅阶层在实际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上与科举所引导和预期的儒家理想价值和行为方面产生了分离,儒家经典所倡导的“天下”“天道”不再成为地方士绅阶层的精神理想,地方士绅阶层的精神面貌走向世俗化。如陈宝良所指出的那样,明代中叶以后,士风趋坏,地方士绅横行乡里,形同无赖[7]388。中央帝国的后期,不论明清,都出现了既对抗中央权力又与民争利的地方劣绅。顾炎武在《生员论》中也指出了这种现象,地方缙绅侵夺田产、奴役乡民的情况不仅时有发生,而且出现了地方士绅公开藐视凌辱地方官员、官弱绅强的局面。当地方士绅阶层对中央权力都缺乏认可的时候,很难指望这一阶层成为平民阶层利益的维护者。地方士绅对官方权力的对抗,如拖欠赋税,并不必然导向对平民阶层利益的维护,地方士绅阶层并不是代表地方平民反抗中央权力,而只是维护自身阶层的世俗利益,甚至是为侵犯平民阶层的利益扫清中央权力这个障碍。这种地方士绅权力的扩张及其对平民阶层利益的侵害,往往在中央权力出现危机的时候显得更为突出,从明崇祯末到清初,江南地区的“奴变”就反映了地方士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如学者范金民所指出的那样,明代后期,中央控制力衰落,江南士绅在乡居的地方成为地方邪恶势力[8]53,“地方士绅与衙役勾结,对乡民滥征赋税”[4]5。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地方士绅经常与政府官吏勾结,干预司法、侵占平民田产和利益,“在讼师、衙役等群体中,基层士人武断乡曲、欺压百姓的行为更加常见”[9]146,这些地方士绅不仅不是地方秩序的维护者,反而成为地方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地方豪绅不仅不是地方水利设施的建设者,反而成为与民夺利的破坏者,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主要由中央政府进行财力支持,在大规模的灾后救济和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上,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中央权力,而不是地方士绅。学者冯贤亮也指出,“《清实录》与《清会典事例》中屡屡言及州县地方每有兴举,只要于地方绅士不便者,就会出现格而不行的状态”[10]351,可见地方士绅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并不是如以往研究中所强调的那种积极的面向。滨岛敦俊指出,明嘉靖以后,随着商业发展,乡居地主移居城市,乡居地主维持乡村社会稳定的体制开始瓦解(这一体制在南宋的时候并没有建立,直到明朝才开始建立),同一圩岸内的地主与佃户、佃户与佃户之间缺乏合作,圩岸的修筑不是依靠村民之间的合作,而是要依靠中央权力的介入才能完成[11]51。尤其在基层的乡村社会发生灾荒动荡的危机时刻,中央权力的存在及其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央的权力可以借此时机长驱直入到乡村社会[12]64,通过外部权力来保护乡民的利益,如赵旭东指出的那样,中央权力通过在乡村危机时刻渗透到乡村,并通过秩序的恢复体现出中央帝国权力的存在,这样就自然颠覆了村落共同体、地方社会的自在性和封闭性。
综上,对士绅在地方社会中作用的强调无疑彰显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并不存在中央与地方明显而尖锐的对立。中央对地方的“放任”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意在“使国家与民相忘,不必时时向老百姓提醒‘国家’的存在”[13]。乡村虽然在地理上远离中央,但是一直处于中央的视野和权力触角之内。赵旭东指出,中央权力更多以象征性的“天威”存在,中央权力对乡村的控制和影响突出体现在危机时刻,通过打击地方豪族对乡民的欺压,象征性地表彰、惩罚等道德手段来施展权力。这种中央权力的施展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对地方治理的全面控制力。
三、村落共同体与地方自治
“村落共同体”概念的构建与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存在着重要的联系。清末民初,地方士绅的势力开始增强,地方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与中央权力的全面衰弱有密切关系,并且这次与以往中央权力衰落所导致的地方士绅势力增强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次地方士绅势力扩大的形势中加入了一种新的思想因素——近代尤其是西方1848年革命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清末新政中的“地方自治”更多是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现代民族国家治理观念影响后的产物,地方自治首先需要现代民族国家的授权,对地方自治的主张,呼应着国家大一统的需要,目的是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全面治理标准[14]398。面对着王朝危机、西方文明冲击和民族爱国情绪,地方精英通过“发现”乡土社会来拯救民族国家,“从乡土社会出发来恢复、实践整体秩序”[15]8。地方社会被认为是与国家机能同型的,在整体秩序出现危机的时候,独立性的地域被视为恢复秩序的方法,要进行国家建设,必须先进行地方自治。而要实现地方自治,则必须从最小的单位——乡村开始,以村落自治为起点不断向外扩展,村落共同体成为地方自治的起点和最小单位。这一思路被以米迪刚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派所实践,在乡建派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目的里,建设乡村是为了“从最小的基层单位出发建设国家”[14]413。从世界范围来看,乡建运动并不为中国所特有,而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它是与各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乡建派受到丹麦等国的社区建设运动的很大影响,乡建派对于改造乡村的热情,也折射出世界各国在建设民族国家上的努力。地方精英认为,只有从乡村建设和地方建设开始,才能逐步由村向镇、县、省一直到国家进行同心圆状的扩展,最终恢复国家整体秩序。这种现代地方自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与中央权力的关系。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及乡绅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在严格意义上不是这种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诉求下的地方自治,而“村落共同体”概念及对地方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自治性的强调则是用这种现代地方自治的眼光看待传统社会的结果。不能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与传统地方士绅所发挥作用的地方社会画等号,因为在这种现代地方自治的情势中,地方士绅已经不是传统的地方士绅,地方社会也不是传统的地方社会,中央“天下”也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
要实现乡村自治,就要有明确的乡村边界(乡村边界对应着国家疆界),就要在村民中培育“团体”(群体、国家)意识,这不就是日本学者所“发现”的或“未发现”的村落共同体吗?非此不能“脱亚入欧”。但这种乡村和地方自治的实践具有很强的外来性,是由上而下所推行的非地方的地方化,这种地方和乡村自治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同时支撑这种从最基本单位入手来改造国家的思路的思想观念是“有机体”概念,国家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乡村便是有机体上的一个同源同构的切片,并且是迫切需要用西方文明进行改造的切片。国家、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相应地村庄便是一个共同体。乡村建设实验,目的在于通过在一个地方实验的成功进而推广到全国。某一村庄成为整个中国的缩影。由此可以看出,地方自治话语的产生与现代民族国家及国家意识的形成密切相关,这使得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具有很大的发明性和想象性。在现代地方自治这样一种视角中,传统地方士绅及其所活动的地方社会的独立性和自足性被夸大了,并且在这种对地方自治的想象中构建了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对立,“地方精英进入以地方自治为主的政治话语中,强化了相对于中央的离心力”[15]11。吊诡的是,地方自治话语兴起的原因和目的都在于建立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这种动力参与想象出村落共同体、地方士绅与地方社会的独立性,但这种想象又反过来建构了国家与地方的对立,以及地方内部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和对立在传统的中央权力和地方社会中并没有如此凸显。
这种对于中国地方社会尤其乡村是一个自治性共同体的想象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6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学在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逐步转向地方史和“内部取向”的区域研究,专注于对某一地方区域的基层社会历史的描述分析[16]104,这一研究转向受到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的影响,提出了“中国中心说”(柯文)、“过密化”理论(也译为“内卷化”,黄宗智)、“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等理论术语,强调地方基层社会的独立性和多元性,而非同一性和整体性。在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中,突出的代表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就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国家权力深入到自治性的地方乡村社会,导致了乡绅的劣化和乡村社会生态的破产。杜赞奇在中国传统农村基层政权与现代民族国家权力之间设置起二元对立的关系。美国学者施坚雅在1964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也认为,中国农民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但这个自给自足的社区不是村落,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17]40。施坚雅引申了美国农村社会学家雷德菲尔德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民的各项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如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以基层市场社区而非村庄作为组织单位,这样中国的每个基层市场都构成了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小传统,中国社会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小传统构成的。虽然施坚雅将视角从村落扩展到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村落作为自足的共同体的想象,将共同体拓展到基层市场,但他还是沿袭着“在农村底层存在着某种经济、文化上能够自给自足的自发性社群机制”的研究思路,这种研究思路将地方社会和地方社群看作是一个以自身为存在目的而存在的自治共同体,“外来的政治力量如欲以强力构建社群,必然遭到抗拒,乃至失败”[18]。杨庆堃、舒尔曼等学者都遵循了这种研究思路。
陈耀煌指出,“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到了1990年代前夕,愈益贬低外来的国家的影响,并同时逐渐抬高既存的地方因素”,这一研究趋势到了1990年代以后日益发展为将国家与农村社会二元对立起来,其中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弱者的武器”概念成为这一趋势的重要理论话语。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村庄中的“小农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传统农村存在着共同利益和集体福利保障机制,是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团结起来抵御外来危机,尤其是反抗自上而下的中央权力。“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理论在后来的相关研究著作如李怀印《华北村治》、高王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和运用。这种地方社会自治性的村落共同体想象,设置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关系,而这种对立关系是非历史的,它给乡村涂上一层浪漫的田园色彩。针对这种具有田园和理想色彩的共同体想象,舒尔茨和波普金等人以“理性小农”为理论工具和框架对其进行了批评。波普金等人指出,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农民并不是为了维护村庄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展开行动,而是谋求“个人福利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19]33。村庄中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在村落内部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往往需要引入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来进行干预,村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不断地与村庄外部的环境进行力量的互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正如雷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一个农民社区的文化却并非是独立自主的;它只是它所附着于其上的那个文明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层次。既然农民社会只不过是附属于一个大社会的‘一半’,因此农民的文化就只能是‘半个文化’。”[20]93农民的这半个文化,自然不具有独立性。如果把乡土地方看作小传统,中央权力代表大传统,虽然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长期以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这就自然打破了对村落共同体的想象以及那种预设的地方与中央的对立。这种预设的对立无疑是一种理论的想象,它忽视了乡村社会更复杂真实的社会关系,妨碍我们想象一种新的地方社会关系,因此,对“村落共同体”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的清理和重新想象变得十分重要。
四、村落共同体想象引发的问题
关于地方社会是一个自治性共同体的想象还有它更为吊诡的一面,即这种对地方自治的幻想中不仅设置着地方与中央的对立,还同时矛盾地隐含着“乡村=国家”的共同体想象。这种吊诡之处突出地体现在近年来盛极一时的“中国在某庄”类型的非虚构写作中,这一类写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试图通过对一个村庄的书写来折射整个中国,这一企图通过这一系列书的书名便可窥一斑,如《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国在梁庄》等等,这一类写作试图“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21]16。这种心态其来有自,最早出现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1899年出版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明恩溥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22]1,这种认知心态也使得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人类学家都一直把乡村社会作为在中国进行人类学研究的重心,如荷兰学者高延的《中国宗教系统》、美国学者葛学溥的《华南农村生活》等,以及中国学者费孝通、杨懋春、林耀华等人进行的乡村社会人类学调查,其中尤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最为典型。《乡土中国》第一次成功地将地方性的乡土与中国对等起来。但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内部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这种试图通过对一村的把握扩展到整个国家的想象模式,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破碎性。人类学者利奇就曾对此提出质疑——“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况中国国情?”[21]325费孝通在1990年代曾专门针对利奇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这一时期的费孝通试图用“类型”和“模式”的概念来修正他在《乡土中国》中所进行的以熟悉一个小村落来显微出整个中国的尝试。费孝通指出,“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社会文化,不应当不看到它的限度”[21]332。费孝通已经意识到其中的限度并提出要从微型研究中走出去,但费孝通的这种修正和对限度的意识并没有引起后来的农村研究者和乡土书写者的足够注意。后来者沉迷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所构建的想象模式,对费孝通所构建的尝试性话语实体化、理想化,对其乡土温情的情感认同不作历史分析和判断,对“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等概念,不加辨析地进行公理化的运用,使得《乡土中国》在为后人提供一套想象乡土的工具的同时,也成为摆脱不去的蝉蜕。并且这一思路正暗合了乡建派的方法——乡村建设实验,目的在于一地实验的成功进而推而广之到全国,某一村庄成为整个中国的缩影。这样,在对村落共同体的想象中就笼罩着一种国家主义的话语,对于村落共同体的想象成为一种国家叙事的隐喻,而乡村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被忽视,这种想象模式无疑限制了对乡村的进一步思考和观察。
对“村落共同体”概念的清理,第一,要破除国家与乡村基层社会的二元对立想象。这种二元对立想象,将乡村想象成不受国家干预的封闭自足的有机体,在这个自足的有机体中过分夸大了乡村精英(强人、能人、新乡绅)在乡村基层社会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弱化了数量更为庞大的普通农民群体被国家所赋予的平等发展权、政治话语权,使得精英俘获、宗族势力、特权力量在乡村滋生,强化了乡村内部精英与非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不平等性,阻碍了中央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的信息畅通和利益联结,使乡村基层空间趋于封闭性,为乡村社会矛盾的发生和乡村治理埋下了隐患。要避免这种二元对立的想象,就要从国家层面增加村民以组织团体方式获得表达自身权利与利益诉求的渠道,如国家支持农民群体以自愿原则按照法律成立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如“各种专业组织、技术组织、市场中介组织以及各种服务乡村和三农发展的社会组织”[23],通过农村合作组织建立广大农民群体与外部社会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交流互动机制,打破农村基层空间的封闭性,从而弱化村庄能人、强人在乡村基层空间中的权威及其对村庄权力的垄断,保护更广大农民群体的权利。第二,在打破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疏通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联系机制的同时,更要避免将农村社会与国家发展主义话语等同起来的共同体想象。这种想象将乡村小共同体与“封闭”“落后”“蒙昧”联系起来,将大共同体(城市、国家、世界)与“文明”“开放”“自由”联系起来,构成了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落后的二元论。将乡村发展、乡村治理与生产主义的农业等同起来,将乡村看作一个单一的进行农业生产、积累粮食和劳动力的经济空间,忽视了乡村基层空间的多元主义面向,尤其是乡村在文化层面的价值和独特性。要避免这种想象,就要以乡村的“去问题化”作为前提,立足于人的情感需求,将乡村看作一个人与自然万物亲密协作的充满熟悉感的人文地理空间,这一空间能够为现代人提供城市空间所不能提供的归属感、亲切感和安全感,为重新调整人与物的情感关系、化解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提供可能性,成为一个与现代城市空间平等互补的基层空间,从而重新确定乡村在现代文明中的坐标,开辟出乡村基层空间在生态文明和人文关怀中的多种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