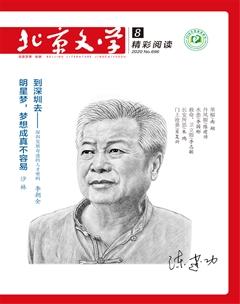亡灵追
1
你听过见过闪婚、闪离,但“闪亡”你一定没听过没见过。我就是一个“闪亡”遗孀。人生一场,电光乍闪,另一半已没在黑暗中。
小半年,就把一个新娘变新寡。
“小董,你真不懂?”
他们都这样问我对我说,我是真的不懂,还是假装不懂?其实,他们都不懂我,他们只关心我的未来,只关心世俗、身体,这样就简单多了。在他们看来,身体离开了这个俗世,那就一切都完了。
问题是我觉得还没完呢。半夜我被自己这个问题吓坏了。我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小董?”
他们以为我被从天而降的悲恸打蒙了,但他们不知道我并不想知道他——我丈夫,怎么死的,而是想知道他怎么活过来的。最后的结局有什么好奇的,那个日子不是单数,就是双数。
是的,我懂,小董懂,谢谢你们的关心,你们不是想让我埋葬悲伤,趁早再嫁吗?埋葬?哈哈,比埋葬更彻底、更干净,一把火烧掉,化作一缕轻烟,升天了,多爽快、多清静。对不起,地很贵,我没什么可以埋葬的。
小董开始把着方向盘,加满92号汽油,奔上追亡灵的路上。
2
那是哪洪荒之年的事儿了——哈哈,鹏树呀,从圆明园那边出来,晃在北京城里就一堆废墟——不骗你,他就用一堆废墟印满汗衫,还海晏河清,那种被走动的废墟埋葬,直想号的感觉,你有过吗?对不起,我不喜欢你,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居然找得到我,把我过去挖出来,那是祖坟,那是一种暴尸的感觉,让往事倒抽一口冷气。你知道吗?我不喜欢。过去是一根肋骨的话,你现在不远万里,来抽出来,这不叫我二次坍塌吗?我不喜欢你,真的不喜欢你!——你喝茶。
小董死死盯着她的眼睛,像盯着死藤缠绵的亡灵——她不想记住她的名字,这不重要。
小董掂起茶杯,花茶,轻轻一啜,落杯时,挂香熏鼻。
那年我年方十八,像你现在一样——我不是奉承你,我干吗要奉承你,像你现在这样年轻,我知道你不止十八,现如今什么易容术没有呢?这超棒,世界变得越来越真实起来啦,本来就是嘛,想要什么,就能真实地得到,实现谎言,不是越来越棒了吗?你别看我满脸沧桑——屁,谁说的,爱你一脸沧桑,我才不厚着一脸沧桑来等你傍呢!哈哈,我年方十八那花样年华,比你漂亮,信吗?你了解女人什么才叫漂亮吗?我想你不懂,你是鹏树最后一个女人,也只能是屠宰场的,他灵魂关闭了——不,升天了。对不起,我本来都忘了,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找上门来,赶来我这儿,让我变得更歹毒的。对不起。我原谅一切,宽恕过往。
小董给她续茶,琥珀色的茶水,小溪般淙淙流淌。
其实也没什么说的——要说的太多了,你明白吗?噢,不介意我抽支烟吧?对不起,我不是这样的——嗯,那年一堆废墟向我飘过来,比沙尘暴可怕多了,沙尘暴轻飘飘的,没有重量。鹏树这堆废墟,又臭又重,乱七八糟又激情万丈。
哈哈,懂吗?男人就一个带坏的词:“流氓”,女人也是一个带味的字:“骚”。懂吗?谅你无知。刚才我就说我的十八岁比你漂亮,这种漂亮你懂了吗?——现在才懂的话,有点晚了,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我们”都晚了。一个老了,一个年轻就失去了。
艺术?对,艺术,就是为了耍流氓的借口——耍得好,就艺术了。别、你别插嘴,这是我的舞台,对不起,是你今天找上门来,给我的舞台,你退下、退下,对不起。让我说说艺术,或者说我的艺术。
那就先从艺术说起,这是多棒的话题啊今天!
是啊,不打艺术说起,何以说人生?哈哈,好玩吧,是这样的,鹏树这堆废墟是多么的重金属多么的辉煌,庆幸我那时出现,借十八岁的光环加持一堆废墟的回收率,人生就是变废为宝。对,这叫颓废的废,哈哈!鹏树那时多像一匹大鹏,要冲天呢!那是在酒仙桥的七棵树艺术区,穿着打扮成一堆废墟的鹏树要表演一个节目叫“窥”:两扇无形的天门,只露一条缝隙,从中可窥天地万物百兽芳草——那是鹏树用他的肢体语言对观众表达——对,我当时是观众之一,我第一次亲眼看行为艺术表演——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这是一场蓄谋已久而临场发挥的流氓行为。
我看着这个疯子般的所谓艺术家,在偌大的高挑展厅里,让他这堆长脚的废墟四处奔跳,紧张、焦虑、绝望、痛苦,他在找什么呢?他用双手抚摸虚空,打开空气,他窥见了什么,值得他惊喜的,值得他期待的,值得他沮丧的,值得他艺术地再艺术的——他踮起脚尖,芭蕾舞步,公羊一样跳到我面前,摆了一个发情绅士般请的手势。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觉得他穿着燕尾服,接上他的手,胳膊就能长出翅膀,从高挑的展廳飞向艺术的天空。
王子需要一个配角,现场的,非我莫属。他打开他的虚空,要有个实体,就是臀部,不再是空气,而是十八岁的臀部。
那时,我是一个穿着牛仔服包裙的艺校女生,我现场贡献了十八岁的臀部。我感觉自己特伟大,直到今天,你来告诉我鹏树嘎了,我也觉得那天他最后窥见我十八岁的臀部的伟大之处——懂吗?废墟之上,那代表未来,孕育大地,万物之母。
我不懂,那时候我一点不懂,我就贡献了。鹏树只是在我们共振的空气中,对着我,举起双手,在虚空中比划了一下、二下、三下,这就够了,呃,艺术到了这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比划几下子。
我为艺术贡献几秒钟臀部算什么,鹏树赢得我的尊重,他整个儿为艺术献身。我成了明星,回到学校,比校花更风光,男生追得像蚂蚁见蜜糖,他们都盯着我的臀部。但我看不上他们,我每个周末,都来七棵树,鹏树说:“你是第八棵树。”
我是来牺牲的,参与鹏树的团队,我突然乐在其中,每块骨头都咬到了艺术的部位,我与鹏树与艺术,所爱所行,像榫卯与楔子的密谋。一切都这样的妥帖和结实。都怪我的这个臀部,害得我这么早就找到了快乐、弹性的源泉。
后来我问过鹏树,怎么在林立的臀部里,相中我的?
鹏树说:“你这个道具恰好在我的缝隙里。”
我就喜欢鹏树这样,生活,就是寻找缝隙,找到了就钻进去,别错过,现场,立刻,艺术地。
你不是要一个真实的鹏树吗?找回一个真实的人,我可以参与进来,是表达我的幸运呢,还是不幸?且慢,你热一下茶,再凉一下——回忆得凉一下,再一下,别太烫了,伤不起。
鹏树,最不喜欢的就是面对他的母亲,但他又是最离不开他的母亲,这是一个想飞起来却又离不开大地的人,最崴脚的地方。
鹏树的母亲不常来,我在别人的嘴里,听说鹏树的母亲是一个单身女强人,就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角色:女企业家,在老家石家庄开有挺大的旅馆餐饮业。鹏树的母亲来北京,每回都是送钱来的。除了鹏树,我和艺术家们一看见鹏树的母亲出现,就像看见了北京烤鸭内蒙古羊肉新疆牛腿和黑龙江五常大米来了。
那时,鹏树已住在七棵树,我住在他的树林丛中,他母亲就找我这第八棵树,好像我会给她开花散叶结果。这是对的,做母亲的唯一心愿。尽管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准备要长大的女人。鹏树的母亲说,与儿子说不上一句话。她来,只为看一眼儿子。
我那时懂得羞愧就不是我了。
懂吗?十八岁,花,还没开够,轮不到果来结束花期。
鹏树这样安排我的剧情:“往我头上浇水。”
——这哪是水呀,是稀释的尿,来源我就不说了。对不起,那时年轻,鹏树也比我大不了多少,我们需要尿素比化肥多。那是一个杂花生树的幻景,最要命的是,我们营造的桃花源要与人分享,那是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儿呀!
早就混得倍儿熟的警察来文明执法了,也不执法,只是释法,一套工作程序无懈可击,法规解释得通情达理,向我们敬礼,向艺术敬礼,亲切地问我们:“怎么有一股臊味?多久没洗澡了?”
我扑哧笑了。
鹏树还是头顶一沓报纸,浑身像贴上马赛克,粘满了花花绿绿彩色黑白的新闻纸,穿上一件纸衣服,回答不了警察的问询,他的助理代答说我们只喜欢泡澡。
警察哥们儿一样问:“昨晚搓了吗?”
助理亮出胳臂,答:“瞧,这搓的,搓脱层皮儿了都。”
我们和警察都笑开了,警察像可爱的狗儿吸了吸鼻子,说这空间挺大的,就味儿太冲了。临离开时,警察对一动不动的鹏树说:“这报纸不好这样弄,今天的。”
鹏树化石一般,要融化了,我赶紧浇水。
我知道艺术就是撒谎,大家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好感觉。那些流氓呀和谐呀阳光呀块垒呀,都是媒体煽动观众对艺术的偷情。鹏树用他的身体力行艺术地告诉我,不用嘣一句话,凡艺术,都是失败的远方。
他与换上便装出来喝酒的警察“同病相怜”。警察说,妈的,我有你这老妈,就立马请艺术滚蛋!
鹏树知道警察的母亲是躺在床上的药罐子,警察是同仁堂老顾客,鹏树逢年过节给过些钱物。
看看我,再转看警察,鹏树对我说:“你是第八棵树。”
鹏树对警察说:“你是第九个铜像。”
鹏树说对了大半,后来那警察哥们儿真的浇起了铸艺玩儿,但铜的玩不起,玩铁的,听说宋庄陈列馆门口那一溜儿铁警,就是他的毕业作品。
鹏树带坏很多人啊,让大家感觉坏得这样好玩,这坏,就有点意思了——你明白吗?那天,我看了这场报纸化成纸浆的艺术录像剪辑后的成片,直想发笑。鹏树挨过来,他喜欢挨着我的臀部坐,说真是临场作戏——
我问你和我吗?
那是另一场。鹏树接着说,我想把这剪辑成两个版本,全本国外,精装本留给祖国。
只有我知道,鹏树是多么热爱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越来越不行的时候——我指的是生意,把家和财产都分了,一男两女,三份财产,优先给鹏树选。
鹏树不想为难母亲,他让两个姐姐先选,他的理由,像他用行为表达的艺术一样:以后母亲要跟姐姐过的。
当着我的面,鹏树的母亲哭了,我记得是那种孩子在大人面前的撒怀抽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那时,我跟鹏树好几年了。鹏树母亲每次来都偷偷瞄我肚子,冬天就伸手摸我肚子这一带,借口问我的羽绒服够不够厚够不够暖,拖着我逛东方新天地,一定要给我买鄂尔多斯羊毛衫。
鹏树用母亲给的那份财产,变成了两套房产一幢别墅,一套在十里堡,一套在798,还有在立水桥的一幢小别墅。
给别墅挂窗帘的时候,鹏树从后面围上来,用胡子茬扎我,说:“你丫的披着帷幕上前台,咋不致敬我这一观众?”
那是多大的天鹅绒帷幕啊,足足能包裹我们身前身后。我向鹏树这个唯一的观众打开自己以致敬,像一只粽子,把粽叶一张张褪将出去。
鹏树每次一摸到我臀部,我就要哼歌儿一样哼起来,但这次隔着帷幕,我觉得我要飞天出窗。艺术是遮挡的窗帘,鹏树说我们用行动落下窗帘。
我和鹏树就在每个套间每个房间为租客挂窗帘,为自己落窗帘。这些行为都因为不长久,从而得以留下婆娑人生,可能就是为了要等到今天,你的出现——你别皱眉头,谁又不是谁的艺术品呢?谁说我们不是不同时段共同完成一个艺术表演呢?
后来,我是看着鹏树一套接一套再一幢别墅折腾光的,我说过,我当初只是为艺术贡献几秒钟的十八岁臀部,鹏树为什么要为艺术献身,用这些房产抵押,化作他的舞台,我叫不停自己的青春,我们非常狂妄而执念,杂乱而肆意。我都不明白,这些房产不足五六年间,就全都改姓换名了。
那时,我们接到无数国际城际艺术行为表演邀约,像赶场一样动车转换空中飞人,恨不得变成三头六臂,就像我們血管里的血,只能加速奔流,不然就会血栓死去。
鹏树猖狂到用他的行为艺术变成了魔术,他的谎言三头六臂,我越来越出现幻觉,鹏树一出门,夜不归宿,千手观音就向我伸出无数玉臂,渐渐地从千手变成千面观音,蛇一样扭动欲念。我半夜惊叫而醒,一身冷汗。
我已经虚弱到皱成一床单被,鹏树不想我这样被幻觉夺命。有一天,他盯着我说:“抱歉,的确是这样,她们只是另一个器官。”
我的手臂无力地垂下床来,千手观音玉臂顿时如秋天的黄栌叶落纷纷。我只是臀部。我说:“明白了。谢谢。”
只是一瞬间,好像还没来得及卸装,艺术市场的不景气直接就是脑梗。我一觉醒来,清醒后四处找我那窗帘,我要被子,我要衣裳——我心痛并羞愧,我怎么开始的,开始恐慌的,想要那么多?幻觉有时挺好的,但要不回了。
“千金散尽还复来”。鹏树就会呻吟这句。身边只剩下我这个艺术家时,我们搬到了宋庄,离河北地界八公里。
“你后悔吗?”鹏树问我,“那些东西不会再回来了。”
还会回来吗?他这话问得我心惊胆战又万念俱灰。这房产又不是我的,房产在鹏树脱手两年不到,升值到想爬上别人的楼跳楼。鹏树的那些器官也是一个幻觉,只剩我这个臀部,我哑然失笑,心想“臀部一思考,上帝就要哭”。
“我再也不能给你什么了。”鹏树日益明显是在对我“劝离”。我父亲和兄弟都来找过鹏树,我二哥还几乎与鹏树手撕起来,三哥的啤酒瓶差点掷中鹏树那颗为艺术而生的头颅。
我与鹏树哪有离不离之说。没有了艺术,就回到现实生活吧。
你看,我老得多快。
3
从南城开车回来,一路拥堵,我全程泪流满面。为什么没有雨刷一样的泪刷呢?她叫什么名字了呢?鹏树这一路活过来,在我这儿死去,他走过的路,路边的里程碑,里程就是数字,就是一个接一个名字吗?丽泽桥堵死了,我干脆伏在方向盘上号啕大哭。
鹏树,操!
满院子的艺术家都笑炸了。
什么叫大公无私,什么叫舍己为人,什么叫脱离低级趣味,鹏树就是了!
一位山东策展人跳着臭脚告诉我:“小董,我告诉你,鹏树兄弟绝对够哥们儿,那种为艺术献身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宋庄的标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兄弟,你喝高了。”我说。
那是在小堡艺术广场南街,一个百多平方的小院子里,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家凑一起,为我和鹏树而来,或者他们本来就是隔三岔五来某个院子醉一顿的。这个我了解,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哪醉了?哪醉了?嫂子——我是该叫你嫂子,还是弟妹呢?”山东策展人摇晃地仄身过来,擎高玻璃杯,被身边的艺术家强按下身去。
一位河南的油画家凑近来,对我说:“小董你别怪山川,他和你家鹏树铁得紧。”
好像我家炕上还葛优躺着鹏树——这话中,我爱听!
我感激地朝河南油画家点点头,挪远一点,他浑身丙烯味。
“嫂子……”搁下酒杯,鹏树的铁哥们儿山川才能和我好好说话,他却不瞅着我说话了,而是四顾小院,大声问道:“你们知道我凭啥一眼就相中鹏树兄的吗?”
坐桌边的一位中年画家笑道:“我知道,不是操,就是酒!”
艺术家们哄院大笑。
“丙烯”又想凑近来安慰我,我忙礼貌地朝他点点头,一再远挪。
“操!算你瞎蒙中一半喽,是酒!”山东策展人看也不看我这个嫂子一眼,说:“我记得就是2007年夏天,妈的,喝了酒才记得清那年那场酒,来得晚了一些——我刚来宋庄,之前与鹏树兄也就是在798打过几个照面,他也落魄得与我差不离。他心好,让我找到落脚处前,先寄他籬下。那天一见面,逮着我就问吃饭了吗?我刚跳下公交车,饭在哪儿吃?他就架我到路边饭店,就在艺术东区广场那儿,看着我吃喝,只动几下筷子,陪我喝半瓶啤酒。我吃饱喝足,人像酒瓶东歪西倒的,才知道他已吃过饭——你说,这样的兄弟,我哪能不寄他篱下!”
一院的艺术家不吭声,都用酒瓶酒杯相互致敬。
我都记下了。
“还有一个‘揍——”策展人山川职业性地狠狠横扫全院艺术家一眼,问:“这一‘揍,谁出手?”
一位文弱书生般的画家站起身来,弓着虾腰,留着差不多及肩的头发。
像一幅揉碎扔进垃圾桶的瘦山水。桌中心的一条大嗓门爆嚷起来:“臭小子,你咋看就一欠揍的痒劲儿!”
“喝多了喝多了九大山人!”
“别、别、别,九叔九大山人,别跟祖国未来计较,来来来,喝一杯醒酒云雾山。”
“对对对,撤酒上茶。”艺术家们亮出胳臂胸膛,纷纷劝架,舞台上顿时台步杂沓,道具像在真空里一样浮泛,小茶杯穿插杯盆狼藉的往事,一地骨屑。
我云缭雾绕,晕乎乎的,不知道是酒醺还是茶醉,鹏树现身出来了,躲闪穿梭于艺术家之中,依然是一副意味深长的坏笑容。他壮硕的身躯怎么变得娇如女子,竟然在茶香氤氲和香烟浓罩中,缓步登上莲花宝座——那儿的观音什么时候腾空的——我被唬了一跳,感觉手背压上了一瓶丙烯,像发烧吊瓶输液,我挣不掉那种晕眩的高烧。鹏树坐上的莲花宝座,莲花花瓣喜逢甘雨,变成了尖尖儿的火焰,悄无声息地舔动蔽天的窗帘。
我忽然看见了窗帘的花款与颜色,水仙、罂粟、玉兰和郁金香,颜色是深海的蓝,鲸鲨一样赤裸着皮,“泼刺泼刺”发出金属的响声,划破一双年轻眼眸的水波。起风了,杨花柳絮从天而降——但这已是暮春了啊,我闻到了鲸鲨搁浅化腐的味道。
鹏树双手合十,朝我做了一个“噤声”的眼神。清香徐来,他说:“让我告诉你。”
那一刻,要不是手背上被压上一瓶丙烯,我真的要求大地收下我一对膝盖。
“董,那是一件鸡毛蒜皮小事儿。”鹏树发声轻如梵音,“那臭小子是驻马店人,可怜见,还喜欢捣鼓艺术,更不被人待见,不是穷到揭不开锅,而是穷到吃屎——嗬嗬,这是他行为艺术到屎了。我说呀,臭小子,你用这噱头,不臭自己,也恶心艺术啊!这臭小子咋回我的,说‘我连吃自己的屎都不行吗?我立马一愣,说行行行。我真他妈的不如他艺术。”
见我听得骇然,鹏树顿了顿,女性化的脸庞丰润起来,我似乎看见他身后的佛光——妈呀,死是这样成仙的哪,怪不得我外婆老早就对我说人人可成佛,我算是这刻才明白人老无欺言。
“臭小子屎来运转——2008年秋天一老外到宋庄,竟然大批收臭小子的画,臭小子这批画被叫作‘超灵派——画家们都叫他吃屎派,嗬嗬嗬!其实呀,是臭小子参加798一先锋画展,给人家大鼻子相中了,追来的。那是一笔美金——不,欧元结算啊!但大鼻子被拦下了,那些眼红的画家痛陈臭小子的劣迹,把他的排泄系统画贬得一文不值,抢大鼻子到自己的画室——大鼻子被各种墨迹未干的世界名画吓倒了,落荒而逃——我拦住了大鼻子,与包围大鼻子的那些艺术家们群殴一顿——我是狠狠被揍了一顿!最后大鼻子只收臭小子一张小画,臭小子就凭这不用吃屎,得了一年生活费。”
我朝腼腆地坐在艺术家们中的臭小子看去,他的被长发掩护好的小扁头,勾得更低了,桌下的狗与他亲,在啃他给的骨肉相连。
我这才明白,给鹏树送终,有一个人为什么默默长泪不止。原来是他。
突然几声响彻云霄的嗨嗨嗨,山东策展人山川说完臭小子这段吃屎和卖画的经历,说:“鹏树的仗义,就从拯救臭小子不用吃屎一年起!”
我一怔——这不是鹏树刚刚跟我说的吗?怎么变成了另一个人说的——我忙望向莲花宝座——没有鹏树呀,观音端坐,风清正气呢。
闪现,闪身,闪离,闪光。谁说不是呢?肉身沉赘,一闪念,莲花宝座也是有的——“嫂子要听吗?”忽然,丙烯在我手背稍用力了一下,我感觉自己会变成丙烯的作品,只能远观,近看的话就是另一团丙烯。
有什么不能听的呢?我惘然道,望向莲花宝座上观音的背后,一片烟雾玄虚。
臭小子拨开众人,给我续上热茶。他始终一言不发。
“对,老话说盖棺定论。”先前那位吵吵嚷嚷的九大山人九叔消了几分酒,茶一灌,身子与精气神就都有点塌了,竟伤感道:“今儿个,就当是鹏树兄弟追思会吧。”
艺术家们都点起了头。
山川恢复了策展人的派头,仰起蒜头鼻,隆重地说:“我们就是想重现一个真实的艺术家,给小董重现她的丈夫——也许这只是我们的愿望,力不从心,但我们会艰难地去共同完成这件作品。”
艺术家们都看着我再次点起了头。
“嗨,也就是那场鹏树与桂花‘毕业典礼的行为艺术。”不知道谁开的头,谁说下来,是山川还是九大山人九叔,还是丙烯或者是要一吐为快的臭小子?
这些都不重要,对于此刻的听者我来说,真的一点也不重要。我突然记起来了,那十八岁的臀部就叫“桂花”,在秋天飘香的精灵。我知道,桂花早就凋零了,过一会儿,就再次飘零,落地,入土,不再是无情物。
“桂花?桂花长得咋样,我半辈子还真没见过,但桂花这人——啧啧,有这一人,我觉得成妖了,得修多少轮回呢,最终还是还俗为人。”
“是喽,桂花是一个多骚多专的妖呀,听说十八岁就被鹏树行为艺术了。最后一场艺术表演后,她就撤了,不知道是回老家了呢,还是嫁人了?反正是不知所终。老哥们儿,醒醒神,醒醒,还记得鹏树那场行为艺术挣来了多少真金白银吗?”
“那都是留给鹏树一个人的吧?”
“鹏树不是没见过钱。”
“桂花净身出门的吗?”
“净身出门?归来仍是少女身。”
笑声,狡黠的,猥琐的,放浪的,诧异的,惊悚的,嘲讽的——这似乎是一场各画派各画种各画技的大杂烩,他们都活在、画在、狂在、开心在眼前,什么都可以的话,就会是什么都能快活的了。
我不知道自己何来这些灵堂里才配有的思考——是不是丙烯将手按压在我肩膀上,他们都怕我过于激动。问题是有什么还能让我偏激的呢?他们都把关于鹏树的事儿泼在宣纸和画布上了,我能揭一层是一层,能稀释一点是一点,反正不是赝品就得咯。
“那场狂欢,直把鹏树变成另一个鹏树。”是谁说的,是谁与谁与谁一起补充说的——鹏树,只能是鹏树!
一只茶杯,或者是酒杯,一只啤酒瓶清脆落地,只听到一声碎响。过往不受干扰。我听着呢。
“包车,鹏树没有醉,是鹏树喊的包车,请我们奔三河,那儿与燕郊交界。”
夜色的潮白河,微微泛起粉红的波浪。
“響应我们广大艺术家的时代要求,操——鹏树请我们高K一歌!这可是天大的行为艺术福利。”
“兄台,是福报。善哉。”
“花和尚!”
“别打岔——让我们回到三河,三河,那是多么美妙的艺术之乡。”
“九叔,为啥叫三河?”
“名河利河情河——三河汇成叫三河。”
“真的假的?”
“假的。”
又是一阵笑骂声。
“嫂子,我用生命向你保证,鹏树那晚只通宵号歌,像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号到歌厅小姐心里发毛,一直号到哑。”
“对,鹏树是一匹热爱艺术生命的狼。嫂子,我也用我的名誉向你保证,我出来时看见鹏树大哥跟歌厅老板娘谈笑风生——噢,在数钞票。”
“我看见鹏树大哥在砍价!”
“砍你个头!”上一个说的是一个愣头青,被九大山人用铁砂掌砍了一下头。
“庆生,有你这一说的?这不成了生米煮成熟饭,打死狗讲价了嘛!”
“那晚艺术家们才发觉自己多久没在歌厅亮喉开荤了呀!原来还有热爱大地的能力!”
“臭小子是开苞。”我听出这是九大山人九叔的大嗓门,好像是。他们已成了混声部,偏旁和部首和身体各个器官都打成了一片。
鹏树就是这样凑成的。
有个男人多好啊。这是我江河激涌的方向。歌声把河床铺宽,那些把胸脯肉垒成臀部大的大婶,三河那晚是貂蝉。
不用多说,三河的水,浪打浪。
“嫂子,鹏树这次包车三河请客,让我们愿意为他死!”谁说的,“这是多么令燕郊大地感天动地的一次壮举,不仅让艺术家回阳,还增进了京冀紧密合作与深厚友谊。”
这肯定是策展人说的。
鹏树的艺术,全行为出去了。
我信。
这是一个幸福的伤心男人。
一颗男人心不为女人伤,那该是怎样的伤?
操!艺术变成了创可贴——这又是谁说的,我挣开丙烯,抹了抹眼睛。莲花宝座上佛光掠过,有什么远去,远去了。
4
我认识鹏树的时候,鹏树已经一贫如洗,像深秋的槐树,秃了树枝,麻雀不亲,喜鹊不爱,何来大鹏?哈哈!我听说他曾经什么都有,现在什么都无。我不怕,我来自贫穷的乡下,曾经什么都没有,现在有了鹏树就什么都会有——当初我就是这样一个相信未来的乡下姑娘。我有大臀部,外婆说好生养的肥臀,外婆给我算过命,三男二女。我想我嫁给鹏树,好生与他厮守一辈子,慢慢地听他的故事,让他在被窝里,亲口告诉我,哪怕一千零一夜,也不要急,一个细节咂个嚼个两天三夜,让那些女妖淡出鸟飞走。我是落地的兔,玉兔,不是月亮的,是鹏树草窝里的。我总是心里说别急,我们得生养三男二女,一窝子大鹏小鹏。要多慢就有多慢的时光,一起孵化明天。
那天是第一天。我看见鹏树走进来——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叫鹏树。
“你这只兔头——”他指着我说,我满委屈的,委屈死了,我就是属兔的,在这间兔头粉店打工。
“新鲜吗?”
我含泪重重点了点头。
那天雨夹雪。
悄无声息的,背对着我,他用舌头与双手,像蚂蚁,不,像细菌一样,把两只兔头整个儿收拾得如此干净、雪白,舔成一件艺术品,让兔头觉得值得,觉得舒服而倍感欣慰。
他瞅着惊呆的我,说:“送你。”
这两只雪白的兔头,现在供在鹏树的骨粉盒前。
我为什么喜欢上一个老男人?别人问我,我也自问,告诉你,我是从喜欢上他的一双手开始,他把兔头吃成这样,那得多有天赋,多有耐心爱心啊!還有一个秘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鹏树,就是他像我爷爷吃蟹一样吃兔头。我爷爷吃蟹,名震四方。爷爷先把蟹盖掀开,分四大块肢解,灵巧的手指配上尖利的指甲,剔净蟹肠蟹鳃,蟹心蟹胃直接努长馋嘴巴吸溜。蟹的七手八脚都被爷爷的舌尖舔净,爪子里的每一丝蟹肉都吸进嘴里。吃净之后,一只蟹仍旧复原回来,齐须齐脚,蟹盖扣得像一顶红翎,红通通地趴在餐桌上,像七品县官跪接圣旨。
鹏树也是这样。两只雪白的兔头,让我永远温润在那个傍晚的雨夹雪。
鹏树抱我的时候,喜欢说:“好得你那不是两只兔牙,而是两只虎牙。”
“我兔子开荤。”我张开虎口,从上咬到下,咬死他,咬得他嗷嗷叫着求饶。
属兔虎牙,鹏树服了,说我吃定他了。
这“吃”(克)不好,这是我后来恍然的。当时是鹏树“吃定”了我,我跳槽了,从兔头粉店,跳到鹏树“两个人的店”打工,我的唯一条件是要做另一个人,老板娘。
鹏树像捧着兔头啃一样捧我。
我雪一样被他舔化,夹雨。
鹏树这个老板,说白了就是给我打工的,扛重工,干脏活,买菜炒菜,上场面。我这新来的女伙计,端菜送酒收拾饭桌招呼客人。鹏树豪气,常想请客,艺术家嘛,拉不下脸皮,不好意思收钱,人家要强付,就不断地往下打折,打到我当场骨折。
“由我来!”我当机立断要行使老板娘权力了。
“两个人的店”这才略有盈余。
但挨过寒冬还是不容易,我都痛恨人类为什么不会冬眠,那可以回避多少不堪啊!
鹏树的行为艺术已是孤家寡人,再也搭不起草台班子,他开始想“两个人的店”能给他的艺术行为供血。后来证明只能是间歇性输血,而且再这样依赖下去,会肾亏心虚,艺术一做血透,就离死期不远了。
我不能对着“两个人的店”见死不救,我知道鹏树对艺术,比我和他“两个人”更性命攸关。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鹏树这样认死理认领艺术的。
那个破玩意儿!鹏树说破玩意儿就破着玩呗。
鹏树说,我不懂的东西,我还认,这是天性。他要我。
我有一晚,对鹏树说:“我们明天改一改店名。”
“改一改店名?”
“嗯,只改一字。”
“哈。”鹏树来了兴头,他要看我如何表演。
我说:“把‘两个人的店,改成‘一个人的店。”
第二天, 改了店名,我就去通州健身中心上班,我是干农活长大的,十六岁去东莞工厂进车间流水线计件,我最不缺的是肌肉与力量。那些资产阶级健身教练对我苗条而丰满的身材只会“哗哗”欢叫,他们异口同声说我像某某某刚出轨的明星,特别是某些曲线。我的每一颗汗珠花一样开在他们眼里,都会反射出一朵欲望。
掌控欲望,是一件多么健身强体的事儿。
“一个人的店”说辛苦也辛苦不到鹏树哪儿,鹏树就一甩手掌柜。
我帮补“一个人的店”,下班还得回家加班帮厨。鹏树越来越觉得我明智,神通经商之道。
我暗笑。我哪有啥道道,我只知道我喜欢上一个艺术家,为之殉道。
但想不到鹏树用生命或者说肉体殉道,而且来真的,无须预演。
春天刚来,冻土正想解冻,“一个人的店”也要考虑关门了,北京的行政副中心把周边的房租推上风暴中心。鹏树可能那晚太累了,他喝酒回来,想扎在破捷达里吹一会儿暖风,吸一支烟,但他睡着了——是的,他是去谈“一个人的店”转让业务,或者是他的艺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身体结束艺术生命,不!谁在谣传鹏树自杀的,我都要跟他没完!
说一千道一万,都怪我那晚比鹏树睡得更死。第二天天麻亮,乌鸦还是喜鹊叫醒宋庄,我一摸床边,窝里冰冷得讓我打了一个冷战。
他长眠在家门口。
5
离开宋庄是傍晚,我经过艺术东区广场时,广场的蹦迪正高分音贝震翻了天。我也听说鹏树用他的艺术统领着广场蹦迪,男女老幼,童叟无欺,跟着鹏树群魔乱舞,无论舞伴高矮肥瘦,俊丑黑白,出手相邀,鹏树都欣然与她蹁跹,火辣性感的贴身舞,把屁股扭出身体,掀起广场一片喝彩和哨声。甚至有流言说广场上蹦迪的女人,都与鹏树有一腿。这当然不是指舞腿。生活中暗指的太多了,晃得我都分不出哪条是狗腿,哪条是义肢。
得承认,我生起过对鹏树的醋意和怨艾,还有天然排斥和抗拒,但这些都催长了我的好奇心,与他走近并短暂生活过,我越来越了解鹏树后,对自己却越来越不了解。这种感觉令我猝不及防,也始料不及。怎么会这样的呢?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山川酒醒时,对我说过一句重话:“小董,知道得太多好吗?我们活着只需要化妆,只有鹏树的死才是真的。”
这帮狼心狗肺的艺术家。
我回到老家。村头村尾的狗都流窜成了流浪狗,它们成群结队不是觅食就是苟合,不知道是它们意愿的还是适应的,反正它们的队伍日益壮大,分明担当起守土有责、保村卫庄的重任。
外婆说回来啦?
我说回来了。
外婆从一开始就疑惑我嫁给一个艺术家,她本能地觉得只有私塾先生才有资格懂点不是农活的事儿,过年前能写几副对联,红白喜事能胡诌几句。别的什么艺术家都是江湖骗子手,而且还不同画画啊写字啊唱戏的骗子,用另一种伎俩来当作艺术行骗的勾当。
我不敢说是用剥净两只兔头来勾引我。
当初,刚回家我就郑重地宣布,我的鹏树是一位艺术家。这太伤外婆的神性了。但这没有妨碍外婆对要做新娘的我说:“你就是一颗沾泥带土的土豆。”
“早晚得种回泥土里。”外婆说。外婆不问我这眨眼间婚姻的前因后果,她从不焦急刨走她土豆的艺术家——我本想天暖了带鹏树荣归村里。外婆不想知道得太多,像我这样,对亡灵充满无知的好奇。
外婆只是接受并敬重过往,她说,活着就是为了记着活过来的,多累啊,早晚不被累死才怪呢。
我出神地,瞅着外婆越来越弯进地面的影子。
地心吸引力是多么的慈善。让这一切慢慢地来。只是我不知道,有些人的慢慢来已经来过,像鹏树,轮到我时,已是慢慢地加速离去。
“那是到另一个地界。”外婆越来越弯进地面,弯向深处,那是灯光照不亮的地方,我家的厨房,呛满人间烟火。
我融进黑暗里,密不透光,不知道自己是睁开眼还是紧闭。黑暗就像在水里吧,沉在水底,深深的水底,厚重的掩埋。好了,鹏树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像透气的水泡,冒上藻荇覆盖的水面。我摸黑走进厨房,柴火映照中,全都在晃动,剪影般的外婆在点香拜神,火光被窗外一缕风轻拂,闪了一闪,又闪一闪——我蓦然看见神龛里的观音,闪成了鹏树,像昨天在艺术家院子里看见的一模一样。
“来,给他烧支香,好上路。”外婆的声音来自天空也来自水底。
作者简介
麦子杨,男,广西北海人,现居北京。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可口与可乐》、中短篇小说集《表妹》和诗集《众里寻他千百度》。
责任编辑 子 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