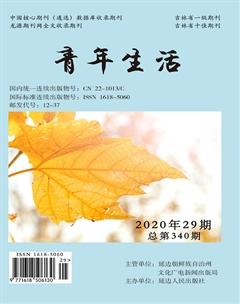网络社区“删帖”乱象的隐患与治理
摘要:在网络平台监管的实践中,因“删帖”范围模糊、网络编辑对内容违法的自主裁定权、以及多元利益等因素,网络空间内“删帖”乱象频出,“删帖”甚至成为了一些组织危机公关的常用手段。“删帖”乱象严重危害了公共利益与舆论秩序,因此法律、公民、网络平台各方面需合理打击网络删帖乱象,规范网络删帖程序,齐力打造良好的舆论生态。
关键词:删帖;危机公关;互联网治理;内容审查
“刪帖”本是一种“事后追惩”的网络秩序管控,但在多元诉求下,有偿删帖、误删等网络乱象频现。2020年6月,新浪微博因在“蒋凡”事件中“删帖”行为受到了热搜榜暂停的惩处。这些乱象导致了网民表达权受限以及网络舆论监督的缺位。[1] 在灰色网络舆情的生成路径[2]中,“删除负面报道和言论”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国内学者靖鸣等人认为删帖流程的规范化、删帖范围的边界清晰化是解决各类删帖矛盾的有效路径[3];学者田飞龙等人从法制和民主角度来探讨以“以言入罪”和“外包删帖”[4]为表现的网络管制。美国布兰代斯也曾指出:禁锢思想与想象会带来危险。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提出,传播空间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管制,而是在于怎样管制[5]。
一、“删帖”乱象的由来
网络编辑删帖的义务来源于2016年11月7日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对用户发布内容承担监管职责。而《侵权责任法》规定,若网络服务商对用户侵权言论不采取制止措施,则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商遵守行政协助或禁止侵权的义务的同时,也造成了“删帖”权的滥用。
社交媒体时代,用户的增长使发表前审核所需的人力成本急剧上升。因此,发表后追责的“删帖”机制成为网络社区内容监管的手段。但其暧昧的审查范围与模糊的审查标准往往成为 “删帖”权滥用的根源。在司法程序上,违法或侵权行为的证明,需要严格的审理。但作为言论的“法官”,网络编辑对于“违法”和“侵权”的裁决却往往发生在瞬息间。
二、 “删帖”制度的隐患
网络管理员删帖的自主裁决权为许多组织带来“合法”删帖的漏洞:只要组织声明“违法”或“侵权”,网络管理者便会倾向于删除。2012年,欧盟某机构伪造了举报人和律师身份分别向10家荷兰网络服务商投诉一项内容不合法,结果多半网络商都删除了该内容。[6]
同时,“自主裁决权”也为“有偿删帖”提供了便利。2012年“百度删帖”事件发生后,“删帖”黑产浮出水面,涉事的百度员工也以受贿罪被刑拘。据《广州日报》报道,部分网站编辑以有偿删帖为生,3·15前“生意火爆”。2015年1月,国家网信办曾联合多部门开展了“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专项整治工作。尽管整治工作成果显著,但也使得网络黑产业更加隐蔽。
三、缓解“删帖”乱象的有效路径
1. 法律:权责、范围与惩处条款进一步细化
我国现行的法律要求网络社区自行管理监督平台内容,制止一切违法言论传播。而“违法”的范围指向现行所有法律法规。据司法部网站显示,我国现有1025部法律,而包括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在内的全部法律法规性文件共有66637部。由于网络服务商需要对通过其平台传播的违法或侵权信息负有连带责任,网络编辑往往执行着极为“严苛”的删帖标准。
因此,只有在法律上,规定清晰明确的删帖“范围”与删帖“条目”,给网络平台一定的免责条件与条款,网络平台才将不再草木皆兵,一视同“删”。
2. 公民:知法不违法、权益不受侵
目前来看,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平均水平还不高。根据一份2012年的调查显示,有65%的大学生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宪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道路交通法等常识“知道一些,但不太详细”;对于与切身利益不够紧密的一些法律,例如知识产权法、仲裁法等法律知识“不甚了解”。[7] 一份2015年的农民法律意识调查表明,按东、中、西地区划分,认为“法律能够保护农民权益”的农民比例分别为47.3%、52.8%、59.2%。[8] 现实社会中,许多人因法律意识淡薄,常常未察觉到自身权益受到了侵害。根据《宪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用户的合法言论被误删后,有权申诉或采取维权手段,但真正采取维权手段的用户却不多。
3. 平台:内容应分类区别对待
网络社区内被删的言论一般分为几种:明确违反法律法规言论、涉嫌违法或侵权的言论、违反社区规则的言论。只有区别对待不同言论才能更好得维护社区规则。
对于涉嫌违法的言论或侵权言论,网络编辑都应进一步求证。平台编辑可以借鉴微信平台的“谣言治理机制”——与专业机构合作辟谣、对谣言打上标签。网络社区也可以与专业机构或人士合作进行违法认定,对于无法认定的言论,进行“涉嫌违法”的醒目标记,“标记”可作为网络平台的免责条件。
四、结 语
网络内容监管机制的漏洞、平台模糊的删帖标准,为网络舆论黑产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也为一些组织危机公关提供了一些捷径。这种止谤、妄议的“删帖”行为,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使将利益相关者陷入更大面积的舆论批评之中。缓解“删帖”乱象,应先从法律上填补“漏洞”。配合适当普法教育,帮助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辅之以更健全的网络社区言论规范。
参考文献:
[1]靖鸣,江晨.网络删帖行为及其边界[J].新闻界,2017,(7):44-53.
[2]张鸿梅.灰色网络舆情的形成、影响与应对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11-15.
[3]同[1]
[4]田飞龙.网络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技术、管制与民主[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1-80.
[5][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91.
[6]李丹丹.网络平台内容审查范围的界定[J].信息安全研究,2019,5(09):834-842.
[7]王开琼.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调查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30(07):92-95.
[8]刘金海.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研究——基于269个村3675个农民的问卷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68-74.
作者简介:雷鸣(1994-),女,汉族,山东青岛人,研究生,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