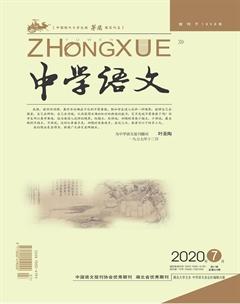叙事延宕手法在写作中的运用例谈
袁海锋
叙事是将生活言语化、故事化,它是文学写作最基础的呈现方式。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礼记·大学》)”生活如此,文学叙事亦是。从故事开启的那一刻,其结局就对整个情节发出强烈的召唤,情节也以一种无法阻遏的热情给予回应,并加速奔向故事的谜底。写作者叙事成熟的一种标志,便是对故事的有意延宕,以便情节充分展开,进而实现文学情绪的从容渗入。叙事延宕是调节写作节奏的减速器,其运用的合宜与否关系着写作的最终实现。
对于初学者而言,叙事延宕无疑是紧要而繁难的。过渡到写作教学,它自然又是“当仁不让”的教学重难点。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许多经典文学文本,其中不乏叙事延宕的成功范例。以教材选文为范本,可以为学生的叙事写作提供有效的教学路径。
一、阻遏式延宕:心有所好,但好事多磨
在叙事文本中,故事有狂奔结局的本性冲动,读者亦有窥探谜底的剧透执念。初学写作者则常应二者的诉求,不由自主地叙事“狂飙”。叙事速度加快,导致叙事时间被大量蚕食,叙事空间被极度压缩,好比整部《西游记》在孙悟空的一个筋斗里结束。叙事的文学作用除了讲述故事外,构建文学要素也是重要的目标。叙事时空的摧毁,不仅使得故事残缺,也让其它文学要素,如人物的出场、形象的清晰、关系的搭建、环境的描写等,失去立足的空间。表现在学生习作中,就是故事短小却不精悍,人物干瘪而不生动,环境空洞且无光彩,至于文学写作最为看重的情绪灌注,更是浅薄而难以动人。
成熟的写作者,或者伟大的作家,则能“忍心”搁置故事本性、读者执念的蛊惑。叙事延宕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原本顺畅的叙事路径上,制造情节阻碍,变一览无余为层峦叠嶂,变风平浪静为一波三折。犹如《西游记》中主体故事是唐僧取经,阻碍情节就是路上的妖精,二者在发展方向上是背离的。作为文学势力,阻碍情节的嵌入一方面使得读者的阅读期待受挫,叙事节奏放缓;一方面又拓展叙事的时空,让故事情节、人物、环境变得丰富复杂。当然,阻碍情节只是叙事的减速带,而不是拦路虎,作品里的阻碍情节总是会被有效地破解,也必须被破解。否则故事就只能在阻碍情节处停滞,故事自然就变成了文学的“事故”。因为阻碍情节的可破解性,在故事达成的目标上,阻碍情节可以重复运用,在这一点上,《西游记》将其运用到了极致。
阻遏式叙事延宕,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教材选文鲁迅的《社戏》。小说中,去到平桥村外祖母家的迅哥儿“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小说亦围绕这个情节进行了大量的铺张。鲁迅并未让去赵庄看戏的故事一路狂飙,而是在不断制造“阻碍情节”:“早上就叫不到船”,唯一的大船早出晚归,其余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邻村问,也没有。一层阻遏的延宕之下,外祖母的歉意、母亲的温慈借对话得以抒写,“迅哥儿”焦躁渴望的心绪借此处阻碍情节得到了映照——“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当然,这样的阻遏并不会完全阻断看戏事件的发展:晚饭后,双喜提议借八叔的航船去看夜戏。可随之的阻礙情节出现:外祖母怕一帮孩子不可靠,母亲也觉得让大人同去熬夜不合情理。类似的阻隔情节还有,比如看见渔火,却不是赵庄社戏;来到赵庄,近台却没什么空位,只能远远地看;想看铁头老生翻筋斗,却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过,一个小旦咿咿呀呀唱个不停;口渴,托桂生买豆浆,买豆浆的聋子却回去了……每一次阻碍情节的出现,除了赵庄看戏的主线叙事被延宕降速外,整个“社戏”故事的空间与时间都在无形中被拓展,延宕情节夹杂的人物、环境要素无时不在建构一个真纯质朴的乡村世界;人物“迅哥儿”跟“社戏”有关的情绪也一波三折、起伏不定地弥漫,以至最后拔高至“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这或许正与阻碍情节的合宜运用息息相关。在经典的阻遏式延宕处置中,《社戏》也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抹不去的“好戏”。
阻遏式叙事是叙事延宕的一种极常见的技巧策略,除《西游记》《社戏》外,教材选文彭荆风的《驿路梨花》、梁衡的《壶口瀑布》亦属此类。写作训练中,学生亦极易上手此法,并获得较好的表达效果。
二、取代式延宕:旁逸斜出的反客为主
预设叙事的伪主线故事,并在其间漫不经心地抛出主线情节,撬动叙事节奏变频,情节承载的情绪转向升华,也是一种叙事延宕的技巧。其中,伪主线故事虚张声势,主线情节旁逸斜出却又反客为主;叙事属性前后迥异,叙事时空因之得以极大的拓展,所以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取代式延宕。
取代式叙事延宕的写作运用,其核心在于叙事节奏的变频与情绪属性的转向。表层的主线故事只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或一组伪预设,其作用在于铺垫:一是为后文旁逸斜出的后续主线搭建必要的叙事环境,包括人物关系、故事环境等;二是在伪主线故事里酝酿一种合宜的情绪,并为主线情节的情绪转向升华准备情感基点,然后抛出承载写作意图的主线情节。所谓旁逸斜出,是指主线情节的嵌入贴切自然、不露声色,继而在平地惊雷的情节展开中实现写作地位的反客为主。从故事的整体复盘,整个叙事节奏无疑被延宕了,但是情绪抒发却是在两种情感中拨乱反正,瞬间迸发,其流露也自然更为浓烈动人。
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与朱自清的《背影》,可谓是取代式叙事延宕的典范。文中鲁迅准备了一组伪主线故事的事件,比如阿长“送福橘,索祝福”“讲长毛故事”,其中预设着不和谐的主仆关系,隐藏着一段伪核心情绪——“我”对阿长的厌弃鄙夷。朱自清则将笔力集中于一个伪主线故事——祖母丧事之后,父子同到南京,并在浦口车站送别的情节,其中预设着送别的特殊地点——有远近高低相隔的车站月台,复杂的父子情绪——因家事而产生的父子隔膜。作为主线情节,阿长送《山海经》与父亲买橘子皆是凭空发生的——“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他往车外看看了说:‘我买几个橘子去”,阿长虽是蓄意却很突然,父亲则是临时起意,这是不露声色的旁逸斜出。虽然“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全用直线凑合”,但这件“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阿长却能够做成功”,它将前文设计的伪主线故事的叙事惯性一下抹平,阿长另样的形象瞬间确立了——“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与阿长隔膜的感情也瞬间灰飞烟灭,代之以留存内心三十多年的久久怀念。父亲不期然的关爱,父亲转过身后背影蹒跚的深邃,父亲为了儿子的那份艰难,使一切的不快都在背影里暂时消散,朱自清所期待的父慈子孝留存在心间。无论现实的父亲如何,这个转过身后背影里的父亲,这个文学作品里的父亲,却是那么慈爱可亲。这两个主线情节叙事属性的改变、情绪内容的转向都是在瞬间反客为主。
与阻遏式延宕叙事中异质情节的简单对峙不同,取代式延宕叙事对带异质情节的写作空间、出场契机、写作笔法有更高的要求,可以说是叙事延宕的高级表现形式。因而,写作训练中,教师要注意其写作难度的梯度升级,以便合宜展开。
三、重启式延宕:戛然而止,再绝处逢生
为了降低叙事节奏,写作者会将先行情节推入死局,以情节骤停的方式使叙事陷入停滞。在停滞中,文本处于静态的叙事语境。此时,写作者会将大量笔墨集中于人物的心理描写,或呈现过往生活的回忆,或描述当下的生存状态,或抒发未来生活的愿景。在全新的情绪状态、迥异的叙事语境中,后继情节以新的人物关系、叙事时空、故事导向为依托,悄然重启,将故事发展、形象塑造、作品主旨顺势带入全新的境地,作品在绝处逢生,这种叙事延宕可称之为重启式延宕。情节进入死局,有二种表现:先行情节的主导人物因不可控外力而诀别式离场,由其主导的情节叙事进入空转状态,难以按照已有情形维系;主导人物因不可控力,被突然抛出先行情节构建的叙事空间、话语情境、对话关系。由此,先行情节失去主导人物而自行分解,或因与主导隔绝而失去叙事意义。重启式叙事延宕,将写作冲突由情节的事件性设计,转移到人物遭遇性安排,出现的偶然性加大,文学设计感更强,由此生成的从“戛然而止”到“绝处逢生”,文学效果更加凸显。
重啟式叙事延宕的运用多见于虚构小说,如《神雕侠侣》中杨过“断臂入剑冢”。但在写实性散文中亦见其例,如教材选文《秋天的怀念》。史铁生年纪轻轻却双腿瘫痪,脾气暴怒异常,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与方向,母亲反复劝慰鼓励,终于说服儿子某一天去北海赏菊。这是作品设置的先行情节。母亲的病亡——“她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则使得家人第二日去北海赏菊的情节设计戛然而止,陷入死局。在母亲逝世后,叙事情节处于停滞状态,在此之际,史铁生终于可以抽离于情节、抽离于生活,开始思考活着的问题。他连用两个“没想到”,写出了内心对母亲的愧疚与怀念。作者借母亲的亡故而思考生活、感悟人生,也将自己推入新的生活——“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后继情节由此绝处逢生。绝处逢生的不止是叙事情节,更有走向新生的史铁生——“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我俩一块儿,要好好活……”
重启式叙事延宕先行后继情节的设计,不仅是时间线上的推移,更有人物关系的重建、环境言语的描写、形象的再次塑造、情绪内容的升华。在短促的情节叙事里,于偶然中置入突变,于突变中停滞叙事,于停滞中刻画人物形象裂变,重启后继情节,这是比取代式叙事延宕还要苛刻的叙事技巧,是叙事延宕策略的进一步拓展升级。
叙事延宕是情节建构的有效技巧,借助教材经典选文的文学展示,既有写作价值的明确,又有方法的操作示范。教师如能将这些内容转化为教学资源,无疑会推动写作教学的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作者通联:广东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