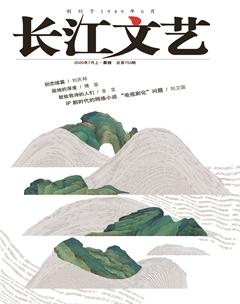一个人的村庄
张瑞明
一
城里的天,蒙着一层灰,三个月不见日头笑。路边的人步子快,口罩遮住半张脸,遇见了,谁也不理谁。一辆接一辆的车爬着走,前拥后挤迈不开步,嘀嘀哇哇乱叫,十字路口恰似马圈的围栏,绿灯亮,放走一群,红灯亮,圈住一群。
守根憋屈不行,背起行李就走。要走也没那么容易,一进地铁,就被黏住了。所幸有儿子超群引路,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好歹进了车厢。车厢更黏糊,像熬着腊八粥的锅。白面孔、黑面孔、香水味、汗腥味混杂,吸进来的气,指不定是谁出的。守根一手抓着拉环,一手护着行李,鼻子发痒,腾不开手揉,脆生生打了个喷嚏。一群人手捂嘴巴,拿眼白他。守根的行李鼓,本来就占地方,亏欠别人,这个不识时务的喷嚏,更让他不落忍,脸面通红。守根不知该向谁道歉,就低头看鞋,车底板上,有一堆鞋,乱糟糟,不知哪双是自己的。
过了六站地,守根也没捞到座位。眼瞅着一波人鱼贯而出,腾出地方,呼啦一下,又上来一波。车门像牛的嘴巴,不停反刍,也不嫌累。超群挪到空位前占座,人流一冲,又错开了。守根本就没打算坐,乡下人吃饭都蹲着,赶路何必要坐下。是超群较真,他想让父亲走得松快些,自从守根进城,就没下脚的地方。超群的家,自然是悬在半空的水泥盒子,上下左右被夹住不说,前后也打了隔断。二十多平米的房子,阳光进不来,饭味出不去,房东收租倒是挺及时。超群一家沙丁鱼般挤了四年,倒也习惯了。守根一来,格局就乱了,推让半天,守根把折叠床支到卫生间里。老爷子虽说一把年纪,也总得避讳一下儿媳,整间屋子,客厅卧室厨房连在一起,也就卫生间相对封闭。味道是差了点,守根能忍,他说从前给生产队坐场放牧,经常睡马棚。好在守根有早起的习惯,不耽误儿子一家三口早便和洗漱。
超群有孝心,想让老爹在城里养老,城里医疗条件好,有个马高镫短,好接济。儿媳人也不错,不但不使脸子,还三碟四碗变着样伺候,嘘寒问暖着实客套。豆豆伶俐可爱,扎一条朝天小辫,进出幼儿园,拉住爷爷的手,小绵羊般乖。守根有很多理由留下,也有很多理由离开。这年头没铁饭碗,小两口自从大学毕业,不是跳槽就是被炒鱿鱼,来回折腾,到现在也没个踏实着落。前几日,守根闲不住,跟着儿子去看招聘会,那阵势比乡下赶庙会闹腾多了,要是大肚子女人进去,会挤出孩子。会场里,全是白白净净的小年轻,大部分架着眼镜。儿子也白净,但成色差了点,脸面偏黄,眼镜片上,圈也偏少。守根这下明白了,为啥这么大个城市,容不下儿子这么有学问的人,原来不是肉少,而是狼多。那次招聘,儿子没找到满意的活儿,跳槽失败,只能还在那家公司干。工钱按说不低,但儿子还嫌低。也难怪,月底算账,刨去房租水电、豆豆学费、吃喝拉杂,小两口收入加一起,也剩不下几个。儿子买房的梦想,猴年马月才能实现。日子本来就紧巴,现如今又添一张嘴,守根哪能安心。
是走是留,守根难以决断,像站在十字路口,走哪边都行,走哪边都难。直到那晚,他梦到了花子,花子被黑三骑在身下,压得喘不过气。惊醒后,老泪就流下来,湿了枕头。守根钢骨,轻易不落泪,几个月前老伴离世,猫抓心般难受,也没哭。没想到,一个惊梦,却让他哭了一场。眼泪一流,守根想通了,一辈子想活个周全,还是周全不了,七十岁的人,该任性一次了。打定了回家的主意,就连豆豆都留不住,儿子无奈,大包小包买好东西,送父亲上路。一路上,父子无话,超群如过关斩将地闯干,爬公交、挤地铁、插队买票,守根屁股后面跟着,倒像他才是儿子。
爷俩背着包,在人群车流中穿梭。彼时城市还未热开锅,早高峰尚未到来,来来往往,大部分是下夜班和赶早班的人。也有像守根这样的旅客,成千上万拥向东西南北的车站,行色匆匆,一脸疲惫。折腾了一个小时,买到一张长途车票,超群看了看候车大厅的挂钟,尚需五十分钟才发车,再劝父亲一次,还来得及。超群说,爹,你真要与世隔绝?话虽简短,可分量不轻,切中守根要害。守根树杈般的手指抖了一下,车票也跟着抖了一下。候车大厅宽敞,灯火也通明,若没这些座椅,可以跑马。这么大个地方,噪音自然重,吵得守根心烦,恨不能立马进个清静地方。儿子一句话,就把吵闹声屏蔽了,守根觉得眼前空荡荡的,像进了一片冬天的林子。这吵闹中的空荡,虽是守根的错觉,却也是提前预支的未来。一旦踏上回乡的旅途,也就走向了空荡。城里的拥挤可怕,但城外的空荡更可怕,那是墓地般的死寂,守根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二
乡下的天透亮,车一上了坝,车窗外就是大片瓦蓝。那才叫天,是圆的,从高空罩下来,边沿齐刷刷挨着地。六月的草滩,还不算绿,镶进蓝色里,也新鲜亮眼。野花在坐胎,再有个把月,星星点点的金莲花就吐蕊了,那花只坝上有,金贵着呢。岔路口下了车,守根沿一条土路走。说是土路,土里长了一寸长的草,也没有车辙,不起灰尘。这种便道全县不多了,村村通工程实施后,有人烟的村庄都修了水泥路。人稠的村,建了小广场,村姑吃饱了,拿把彩扇扭臀转腰,走秧歌步。路灯彻夜亮,不怕费电,一根杆子上一块光伏板,足够一盏灯用。伏天,村民在路灯下打牌下棋嗑瓜子,算是村中一景。守根羡慕有人气的村,闲下时过去走走,总归觉得不是自己的地盘,便不大走动了。
坝上地界宽,土地按人头分,一人能分二三十亩,村与村相隔甚远,鸡犬相闻是定然不会。一袋烟工夫,守根才走了这条路一半。再往前行,路就陡起来,腰需往前弓。守根没想到,在城里住了三月,走这条路就吃力成这样。远远望见村舍,守根的腿就发软,咋住了一辈子的地方,灰塌塌像片坟地。四周也格外静,守根能听见肺里在刮风,喘气声不比城里夜晚的过车声小。从前的那些鸟呢?节骨眼上也不叫几声,驱驱这死寂。
守根摸到了那半截木桩,那是一棵枯了的榆树,被盖房的人取了腰身,做了梁柱。没想到,这一锯竟然弄疼了榆树,缓过秧子来,地下没死透的根,长出半截,高过了小儿头顶。这棵榆树,孤零零长在脑包山上,的确是惹眼,惨遭砍伐是必然。但既然能独占山头,就定有灵气,这灵气,直到树被砍伐才被发现。砍树那阵,正是走西口的年月,口里的人活不下去,就到口外找地方落戶。守根的爷爷,听说这树的灵气,就在脑包山上搭了窝棚,并在树桩上刻了四个大字,榆树根村。爷爷是坝下蔚州人,精通书画,逃荒到了坝上,落户榆树根,以给人家画炕围子为生,去世那年,村里已聚成二十几户人家。
守根自从出生,就没辨清树桩上的村名,老辈不指点,哪知道皲裂的树皮便是字。树桩年年变粗,树皮就一年比一年糙,脱落在地的,像一块块硬土。现如今,谁要说树桩上有字,定是花了眼,但榆树根村的村名,却假不了,一代代被人叫顺了嘴。树桩腰围阔到一定程度,年轮就大开,树心成了一个大洞。雨天时,洞里积了水,像一口井。守根常常在雨后把马拴到树桩上,那马就低头饮水。马不挑料,冬天饿了,溜达进林带,前蹄抛开雪层,吃腐烂的树叶。马对水却不能含糊,水要是脏了,宁可口渴,也不喝。榆树根这一带,大小淖泊有五个,相传是蒙古人的军马场所在,蒙古人从来不在淖里洗衣,为的就是让马有口干净水喝。也许是传统的缘故,一直以来,这里的人们,格外珍惜这些水淖,不在水边洗衣,伏天也没见个游泳的。水质清澈能饮,就招来大片水鸟,成了观光的好去处。尤其近几年,坝上的旅游起来了,夏季一到,京津冀一带的游客蜂拥而至。淖泊不再是淖泊,而是草原湖,一个个更名换姓,比如榆树根村东十里地的囫囵淖,因为每年有天鹅栖落,如今叫天鹅湖。
靠在树桩上歇了歇,守根走进村。房前屋后一条土路,羊肠子一样七拐八挒,前几天下过雨,低洼处一踩两脚泥。守根自从进了城,鞋帮子就干净了,如今再上土路,步子就扭来扭去。眼前的一户户人家,熟悉也陌生,三个月的时间不见,那些院墙和房舍,像是又脱了一层皮。坝上人家地盘大,院里除了盖正房仓房,还能养牛种菜。榆树根村的院落年代久,院墙多是用黄土滚的母猪墙,墙头不够一人深,不为防贼,为的是圈住自家的牲畜,也不让别家牲畜进来。院墙里面,大都种一片葵花,探出头来,秋天能打牙祭,夏天为了个好看。囫囵中另一片地里,竹竿挑着架豆,地上爬着倭瓜,蓄根的韭菜,嫩生生的大葱。土里挑个坑,点上细菜秧子,能吃上一季的黄瓜、青椒、西红柿。细菜存不住,少有人种,只图尝个鲜。也有人家种草莓、西瓜,纯属逗孩子玩,草莓豌豆大,西瓜拳头大,小满前后一场冻,秧子就蔫巴了。六月是该有生机的时候,可守根只能想想从前的样子,眼前的一户户院落,破七乱八堆着拿不走的东西,碾盘、碌碡、旧轮胎。有些院墙年久失修,已经坍塌,像老年人跑风的牙齿。一间间空房子更惨,因无人打理而垂头丧气,门窗被破砖头封住下半截,只露出眉眼透光,免得屋里发霉。守根看一眼这些房子,想起城里人的口罩,心里发灰。
绕过牛家、马家、杨家,守根眼前敞亮了。自家的院落规整,石头片子干插的院墙经雨,白刷刷的,葵花已结子,瓜豆正在拉秧。四间正房是砖包皮的,屋顶的红瓦暖心,新换的塑钢门窗锃明瓦亮。东向的两间仓房差了点,房顶是碱土抹的,蒙一层塑料布,再用旧瓦压一层胡麻节,可依然有烟火气。去年,贫困村旧房改造,只要翻盖房子,就给两万八的补贴。榆树根村,本来有二十多户,陆陆续续都把土地流转出去,外出打工走了,只剩下守根一户。守根坚持要当坐地户,领了补贴,把自家房子拾掇了一番,果然好住多了。守根本打算住到死,不曾想房子修好了,老伴突发心肌梗塞,留下他一个人。老伴生前爱干净,里里外外都利索。守根拿起笤帚心烦,放下簸箕意乱,看见啥,啥都有女人的影子,院里房外,处处揪心。村子里转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还得闷葫芦般回家受煎熬。守根实在熬煎,便给儿子打电话,也就有了城里那三个月的另一种熬煎。
三
六月后,天鹅湖的旅游就起来了,花子一定在那儿。黑三这人财迷,挣钱不要命,花子跟了他,也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三个多月不见,花子指不定瘦成啥样了。守根起了个大早,溜溜达达出了榆树根,东行十里,望见天鹅湖时,阳婆婆刚露头。晨光打进湖水,溅起金星,飞进眼球中有点发烫。守根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可他确信,只要花子在湖边,一眼就能看见。
早在大集体时,守根就是远近闻名的马倌,无论啥样的马,到他手里,准保上膘。早年间,坝上的马都是北边过来的,纯正的蒙古马。蒙古马有耐力,不吃不喝能跑几天,可身材小,劲头不足,榆树根人称之为单片子马。那时没有拖拉机,养马是为了耕地,就只能对单片子马进行改良。俄罗斯有一种大屁股马,个头大劲头足,守根在生产队放马时,经常牵着大屁股儿马,与蒙古稞马配种。榆树根这一带,有时也为民兵出坐骑,稞马也是蒙古马,儿马是另一个品种高畜马。高畜马个高腿长,跑得快。拖拉机遍地有之后,马没了用,眼见着要绝种。是旅游业救了马的命,天鹅湖周边的村庄盖起农家院之后,村人又开始养马,只为了赚游客的钱,好点的马,骑一圈要三十块。游客不懂马,只要漂亮就肯出钱骑,拍出的照片威风。现如今这一带的马,纯种的基本没有,全是改良过的,身材毛色都有差别。所有的马里边,漂亮不过个花子马。花子马也是改良马下的,毛分二色,远观以为是乳牛。
这一带的花子马中,漂亮不过花子。脊背雪白,肚底黢黑,白毛黑毛全都油亮。这匹马是驹子时,没看出好来,三岁口上开始出彩,远近的人都羡慕,说守根养了一辈子马,养出了马精。守根打理得更精心,一心要把花子养成马中赤兔,让十里八乡的人开开眼。放马有讲究,水马旱羊,马最爱吃水草,水草催膘。五更的水草最嫩,挂着露珠。放羊讲究晚出早归,羊倌出坡,小米下锅,放马就不同,讲究早出晚归。守根放马,在榆树根一带起炕最早,回家最晚。马光吃不行,会吃成大肚锅锅,必须每天遛,好马不卧,好孩子不坐。守根冬夏无常牵着花子,转遍了这一带的草滩,膝盖都走没了油,落下关节炎的毛病。马皮要经常刷,刷干净了,马才舒服。马尾不能太长,长了容易绊住后蹄,剪马尾是个细活,毛糙人一剪子下去,看着齐刷刷下来一截,一根根毛发粘着呢,不顺溜。守根剪马尾,从里面掏着剪,把里面的疙瘩全剪通,再用梳子一顺,就一根是一根。打鬃是一年一次,最看马倌的手艺,守根打鬃,用夹板夹住马鬃下剪,不光图个整齐,还要前高后低,脊梁骨留一撮长毛,为的是不挂笼套也能有个抓手。马三岁前爱得白喉,三岁后就是四号病,花子没得过,守根连只蚊虫都不让往它身上落,走站拿把马尾做的苍蝇刷子,啪啪地掸。那一年,花子起得猛了點,小肠转了筋。守根连忙牵马去八道沟。站在一道沟沿边,狠狠抽了屁股一鞭,花子嘶鸣一声,蹿起老高,越过沟坎,肠子顺过来了,马粪呼呼地出。养马这一套活儿下来,就是九年,守根把个花子养得毛光尾顺、身健体滑,牵到哪儿,哪儿叫好。
进城前夕,守根心存侥幸问儿子,城里能不能养马。儿子笑了,说人都快成蚂蚁了,还能容得下马。守根无奈,只能给花子找新主。如今种地的人,都不养马了,景区里碰运气,都说马好,一谈价,双方都摇头。守根是稀罕钱,但如今有社保医保、土地流转费、儿子给的零花钱,不至于过不下去,拿花子赚外快。守根是觉得,卖亏了,对不起这匹马。转来绕去,被黑三盯上了。黑三络腮胡子,一脸凶相,那年偷鱼时挂了花,被承包水库的保定人一弹弓伤了左眼,玻璃花眼球分外吓人。黑三扯住缰绳,掰开花子的嘴看牙口,看完呲着嘴说,这牲口是个样子货,中看不中用,魁肥人骑上去就得爬蛋。守根不答话,拽住缰绳要走。黑三不松手,依旧在说,七摇八不动,九岁拉了缝,你看这槽牙,缝有一指宽了,秋后一过,就成了面子口,谁还要?守根还是不搭理,扯过缰绳走开。转天再来天鹅湖,人人见了花子都躲着走,守根心想,也该花子命苦,就狠下心来,牵马往黑三跟前蹭。黑三从前是牲畜市场的牙子,压价自然老练。两个人做着手势过招,勾九、撇八、捏七、挠六、抓五,几个回合下来,守根就败了。守根不甘心,想当年,他也算牲畜市场里的一号,没少从蒙古人手里买牲口。守根没败给经验,败给了时间,儿子电话催得紧,让趁着他近期有工夫接站,快些动身。
三个月前卖掉花子,守根就成了杨白劳,一想起花子和黑三的模样,真有心喝半碗卤水。守根想见花子,真就远远望见了。天鹅湖边的马群里,只有一匹马是黑白花,那毛色和神态,化成灰也认得。花子通人性,经常用嘴唇滚守根的老脸,尾巴一摇一摇,那是马在笑。守根本想远远见一面就走,免得打了照面彼此难过,可一眼望去,腿就不由人,大步流星跨过去,膝盖也不疼了。花子头上扣着笼套,嘴里箍着嚼子,一根缰绳绷直,拴在铁橛上。二十步远时,花子就抬头急着往前迎,前蹄立起来,咴咴叫个不停。一旁正在揽客的黑三,瞅见是守根,像见了冤家,大声吼着,老不死的,滾一边去,牲口惊了,你赔得起吗?守根似乎没听见,三步两步跨过去,搂住了马脖子。
四
炕上地下都干净,老伴走了,庄户人的精气神不能丢。四间正房空着两间,指望儿子一家回来拾掇一下就能住。住人这两间,外屋是下厨的地方,盘着一方锅台,稳着大铁锅,蒸饭炒菜都快。无论是烧秸秆、烧牛粪,还是烧碎煤,锅台上都不落灰,一条抹布来来回回擦,把瓷砖面擦得发亮。里屋窗台连着大炕,炕帮子也是瓷砖,炕围子是一层印花塑料布,半指后的毡子铺在炕面上,上面还是一层印花塑料布,保温耐磨。炕尾整整齐齐码着被褥,炕头隔墙就是锅灶,睡人容易上火,压一溜木板,上面坐一溜花盆,君子兰、洋绣球,老伴最待见那盆平顶珠,粉白的花朵挂满枝杈,开得双眉双眼。靠北墙立着三节红柜,漆面旧了也没发黑。柜子上方,悬挂照人镜,边框插了一张全家照,去年拍的。中间坐着的,是守根和老伴,后面站着的,是超群和媳妇,豆豆斜在奶奶怀里。拍照的人喊,茄子,全家人都露牙笑。守根一直不主张拍全家照,老大、老二都夭折了,咋能拍全乎?老伴查出病,医院推了手,守根改变主意,还是拍一张好。
墙上挂着全家照,炕头养着花,按说这日子够滋润,咋缺一口人,少一匹马,就分分秒秒过不下去呢?从城里回来这才几天,守根就在这家里坐不住了,到处乱转,转到膝盖坚持不下去,才进屋上炕躺着。村里是别指望串门,家家封门闭户,粮食一搬走,连耗子都没有。好在有带不走的猫,从空房子里找寻过来,赖在守根家不走。守根数了数,大大小小十一只,活奔乱跳。守根给每只猫都起了名字,剩菜剩饭地喂,走了仨月,竟然一只没少,真不知咋活过来的。守根小时候让猫挠过,最不待见猫,现如今,村子里少了生灵,也只能将就拿它解闷。要说喜见的,还是马,尤其是朝夕相伴的花子。这些天,守根没少跑天鹅湖,去了也只能远远看看花子。不能靠近,靠近了花子就尥蹶子,连嘶带咬,连踢带蹬。那一次,竟然把个游客掀翻在地,那可是城里人,摔坏了,黑三就吃不了兜着走。好在那人是搞地质勘探的,常年在外面摸爬滚打,皮实。站起身拍拍屁股,扭了扭遮阳帽,身子骨像是没事。黑三胆大,也吓出一身冷汗,上前递烟赔不是。那人不但没讹他,反倒要再骑一次,说烈马才过瘾。这人说还想骑马,黑三才瞅见,缰绳已攥在守根手里,那牲口早不管不顾奔了旧主人。惊吓变成愤怒,黑三蹿过来,照着守根就是一巴掌。守根眼睛一黑,金星乱冒,左脸火辣辣,像抹了泡椒水。踉跄着回了家,镜子里照了照,脸面肿了起来,左眼圈发黑。守根对着照片说,老伴,我再不去看花子了,在家守你。
过了芒种,天气入伏了,这个节气屋里阴,院里暖和。守根搬个凳子坐下,抬头看天,天是真好,瓦蓝瓦蓝,要不是有棉花般的云朵,会更像倒悬着的天鹅湖。天不能老看,看久了头晕。守根低头逗猫,把鞋脱了让它们抢。鞋是布鞋,不经撕扯,再说鞋垫是老伴纳的,走针穿线刺绣一对鸳鸯。从猫嘴里抢出来穿上,猫还想玩,但守根不想了。守根想起个好去处,这节气那里一定开眼。守根走向栅栏门,觉得浑身乏力,膝盖隐隐作痛,脸也还是疼,那地方有五里地,来回就是十里,还是改天去吧。守根转回来,坐到凳子上,看天和逗猫都没了意思。人真是奇怪,刚做过的事,就八个六个不想再做,再做一次能咋的?能死?守根不信邪,接着逗猫,逗着逗着,就又想起一件事。这可是件早该干的事,守根来了精神,立马起身进了仓房。仓房里暗,刚从阳婆婆底下进来,一时看不清物件。守根定兴了片刻,摸到那口大瓷缸边。伸手往下掏,掏出一编织袋旧棉花,再掏,要找的东西就出来了。守根抱着这个流流挂挂的物件,放到院子里,猫群就围过来,用鼻子嗅,用爪子挠。守根就是要让猫们见识一下这副马鞍,这可是全套鞍子。守根一件件摆弄,对猫说,这是鞍桥,红木的;这是马颤,牛皮的;这是马镫,这个你们可咬不动,是铁铸的,硌牙。守根拿起肚带,不言语了,心里泛酸。肚带是马尾编的,结实耐用,沥汗透气,松紧自如。那是花子的尾毛,从五岁积攒到八岁才凑成这条带子。肚带编成后,花子没用过几天,就像鞍子没用过几天一样。守根从锡盟买回这副鞍子,只是觉得好马该备一套好行头,用不用搁在其外。守根养马,平时不上鞍子,马就是马,脊梁上扣个东西,总归是个累赘。
守根摆弄完马鞍放归原处,有点发困,挪动进屋里,上炕躺下。正是花开时节,炕头的花争抢着,把香味往鼻子里送。人都说,花的味道,近似女人的味道,闻着能迷乱心智。守根想在花香里做个梦,看看老伴在干啥。昏昏沉沉像是睡着了,一团浆糊,乱糟糟看不清画面,也听不懂声音,好似把所有的心烦都搅合在一起,只是一味地想哭。守根从睡意中挣脱出来,有些后怕,一个人若这样睡去,连个叫醒的人都没有。守根才七十挂零,还不到平均寿命,不想死,老伴就是真在那边,也不想急着会面。现如今,不愁吃不愁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指不定哪天又出个好政策,榆树根村又人丁兴旺起来。守根好奇,想多活几年,看看这日子到底是咋红火的。想到了日子好过,守根又来了精神,穿鞋下炕,他这就去五里外,看看那个地方。
五
白露过后,天气就有降雪的意思,守根知道身子骨憔悴,早早裹了棉衣。一夏天雨水,冲垮了房后朱老二家,把石头瓦块挑出去,就只剩一片烂泥潭。朱老二是个絕户,死了三年,两间土房面目全非。承包守根五十亩耕地的外乡人,今年改种了青玉米,收秋后没处存放。守根出了个主意,把朱老二家拾掇出来,挖个青储窖,就能放个十吨八吨。守根是喂牲口的行家,自然会倒腾青储窖。闲着也是闲着,帮着外乡人挖坑运土,一直把打碎的青玉米倒进窖里,用塑料布包好,封上土,才完工。干活这几天,膝盖竟然不疼了,身上也长了肉。外乡人要给守根算工钱,守根分文不取,说庄户人受点累怕啥。外乡人也实在,说大爷,今年雨水大,我承包榆树根这几千亩地,都种了青玉米,收成好,有的是票子。守根也知道这人赚了钱,如今种地谁不赚钱?地皮税免了不说,还给补贴,就连耕地都不用花钱,乡里统一雇了拖拉机,还安着定位仪,怕司机偷懒,耕得深度不够。赚钱是赚钱,地少了利薄,不如流转出去省事,年年干拿票子。榆树根人走的就是这个路子,把地一包,拿钱走人,到外面打工或开买卖,再挣一份钱。时间一长,不愿再回乡,村就成了空心村。依滩靠水的地方就不这样,搞生态旅游,坐地捞票子。
青储窖封了口,外乡人就走了,又把守根一个人留在村里。守根怕的就是这个,尤其白露之后,草地见黄,耕地发黑,四处没个看头。再说今年腿脚更不利索,一动身膝盖就疼,外面就是有景,也看不得。村里像个烂坟滩,没去处,只能在家窝着。一群猫都逗皮实了,见了他知道还是那一套,就卧着当观众,他自己倒像一只猫。马鞍子拿出来晒了几次,几次都想起了花子,闹心,干脆藏进大缸,不再让这东西见天日。进屋就对着后墙说话,全家人都阴着脸,说半天没人搭理。绕来转去,身子疲乏了,上炕躺倒就睡,睡死过去也认了。人上了岁数,一年不比一年,不仅没了火力,也没了心气。
记得去年芒种过后,午觉醒来,溜溜达达去了五里外自家的地,就为看一眼地里的收成。那土豆秧子的长势收敛了,已到了翻地收菜时节,心想,外乡人脸上又该开花了。去年土豆收成好,价格却低,外乡人没笑出来。包地就是这样,赔钱三年也不怕,有一年捞住,就连本带利回来了。就拿今年来说,牲畜饲料贵,青玉米自然能卖好价钱,外乡人发了。守根裹着棉衣,躺在炕上没睡着,琢磨着地里的事。想不通为啥榆树根人的肥水,流了外人田。守根和外乡人聊过,得知那人是大同市人,为了来坝上种地,把好好的工作都辞了。城里人能跑到农村,为啥农村人不能守住家呢?这人和超群同岁,正是干事的时候,人家能种田养家,为啥超群就不能。守根想到了儿子,又想起了那三个月的城里生活,虽说是挤了点,却不像现在,想合计个事,身边连个说话的都没有。究竟是挤点好,还是空点好,守根品不出来。到哪说哪的话,躺在这盘大炕上,四外走风,跟睡在野地差不多,还是挤点好。守根侧着身睡,睁眼就看见了炕头的花,天气转凉,花瓣尽落,唯那盆平顶珠挂着花朵,像烟熏了一样,粉白里透着灰雾。
霜降过后,地上了冻,手脚摸到哪里都是冰凉。守根佝偻着身子,把铁炉子从仓房搬出来,架在屋里。又从仓房找出一袋干牛粪,铲了一簸箕煤块,把火点上。冒了一阵烟,呛得他不停咳嗽。咳嗽也费力,蹲在地上大喘气。气喘匀了,守根出院把剩下的牛粪放回仓房,这天阴沉沉的,指不定啥时候下雪。天上飞来一片乌鸦,哇哇叫着,像是坟地被旋风刮起的纸灰。守根仰着头,目送最后一只乌鸦过去,心想,村北有片林带,这些鸟一定找到了家,该去看看。一直到立冬,守根也没去那片林子里看鸟,一场雪封了路,走道打滑,容易摔跟头,这把年纪,倒下就别想起来。数九天,更出不去,守在火炉边熬奶茶。想着天鹅湖冻瓷实了,花子该清闲几天了。炉子上的奶茶咕嘟咕嘟响,守根躺在炕上迷糊。墙上的钟没了电,不知啥时候停的,停就停吧,有点没点一样过日子。
这个梦清脆,能听见窗外的脚步声,咯吱咯吱,那是皮靴踩在雪上的声音。外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踢踢踏踏进来了人,咚咚地跺雪。里屋的棉门帘也掀开了,守根觉得不是梦,一咕噜爬起来。揉揉眼,看见三个人,是儿子、儿媳和豆豆!三个人穿着羽绒服,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手里拎着大包小包,脸上露出喜气。
守根哆嗦着,急着下地,一时找不到鞋在哪。儿子说,爹不用下来,我们上炕。豆豆第一个上了炕,搂住脖子说,爷爷,过年好!儿媳笑着说,这孩子,猴急着是不是想要压岁钱呢,明天才是初一。守根有点蒙,咋熬了些时奶茶,就熬出个大年三十?是啊,表停了没人理,月份牌也有日子没翻了。守根拍拍脑门,开颜一笑说,好,咱过年!
年夜饭自然是饺子,热气腾腾。哪能少了酒,斟满了杯,喝个痛快。一冬天屋里没这么热,守根解开棉袄,还要喝。儿媳说,爹少喝点,以后爷俩有的是时间喝酒。守根端起的杯悬在炕桌上方,眼瞅着儿子发愣。儿子笑着点头说,是啊爹,我们不走了,以后陪着你一起过。守根把杯放下,气呼呼地说,你们犯傻了吧?离开了城里,吃啥?喝啥?
儿子和儿媳对看一眼,笑着说,都安排好了,咱县里第三小学招教师,豆豆她妈聘上了,豆豆也正好能到三小念书,我呢,就在咱这榆树根村发展,明年咱家的地就到了租期,我想试种金莲花,这花适合坝上气候,开得漂亮,有药用价值,不仅能观赏,还能做茶,一旦能行,就把榆树根的地都包过来,往大里做。儿子一番话,让守根心里敞亮了,一杯酒又下了肚。
不知过了多久,守根迷迷糊糊醒来,发现屋里只有自己。儿子一家呢?莫非真是梦?守根不甘心,瞪大眼四处看,日历还真翻到了腊月三十,挂钟的秒针还真咔咔地走起来。分针眼见着跳进零点,窗户映入火光,院子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夹杂着欢呼声,爆开了守根的心花。那欢呼声好熟悉啊,那是孙女豆豆的叫声,过年喽!过年喽!守根一骨碌翻下地,找到鞋,套到脚上往外冲。屋门推开,一挂鞭刚好收尾。守根瞪大眼睛,清清楚楚地看见儿子一家在院子里放炮仗,一根二踢脚升到空中炸开,空荡荡的村庄瞬间被怒放的回音填满。
责任编辑 张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