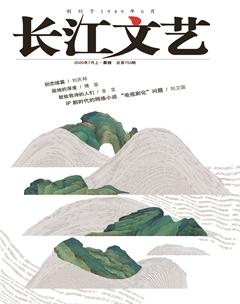喜鹊
李云

1
周菊沒有想到,胡宗平那年在柿子树下对自己说的话,会是一个不好的预兆。那话当时听来就有点不舒服,可再想想,也没什么大碍。加上跟胡宗平是第一次见面,她拽着王世成的胳膊站着,看上去关系亲密——这种时候,心里就算有点消化不良,也只能搁下,不去计较什么。不计较的同时,还得和颜悦色热情周到地跟她打招呼。
就这样,周菊便成了胡宗平来长村遇到的第一个人。不管她对周菊的印象如何,周菊倒是记住了她略带沙哑的声音。最后,又记住了她那天的打扮,她烫着拉丝头,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粗跟皮鞋。很洋气的一个女人,也很漂亮,只是漂亮得有点不着边际。有点逮不住的感觉,今天看眼睛是这样的,明天看鼻子又是那样的。
而她身边的王世成,因为隔着一头拉丝头蓬松着,俊朗的国字脸落下一层阴影,五官便像浮在雾气里,隐约、躲闪。其实躲闪的是他的眼睛,他没有想到爬了半天的路这狗啊猫啊都没有遇见一个,单单遇见了周菊。周菊刚结婚,身上喜气洋洋的,在她的喜气洋洋下面,王世成看到了自己脚上一双灰不溜秋的运动鞋——这双鞋子呵,真该好好擦洗一下了。
前两天,他就穿着这双鞋子,肩膀上扛着一蛇皮袋菌子气呼呼去了河边卖。他的背后鞭炮声阵阵,这天是周菊跟润子结婚的好日子。王世成追求过周菊,阵仗闹得还蛮大的,第一次卖完菌子,他就用卖菌子的钱给周菊买了一只洁白的奶罩回来。周菊怕羞不敢收,他就用竹竿挑着袋子将奶罩从窗口塞了进去——然后,手指放在嘴巴里吹了一个长长的口哨!但是,周菊还是听从父母的话嫁给了润子,润子跟他是一起穿着开裆裤长大的小伙伴,王世成生着闷气,便没有去喝喜酒,自顾自扛着一蛇皮袋菌子下山了。
恰逢柿子树开花。柿子花是由果绿色渐变为奶白色盛开的,意思是刚开始花是果绿色,但真正盛开了就成了奶白色。一小朵一小朵,肉肉的质感,跟女孩的脸蛋一样,很想摸摸。周菊走到柿子树下,禁不住一阵欢喜,顺手摘了一朵拿在手上仔细地瞅,王世成说她是村花的话就在耳边响起。他还说村花就是柿子花。奶白奶白的,好想摸摸呢。王世成生平机灵,就算说深情的话,也有一丝插诨打科的腔调。但是,周菊就是喜欢他这个样子,他一开腔,一抬眉毛,一扬头发,就特别快乐。不像润子,好是好,可总有点沉闷……想着,周菊就将手中的柿子花朝辫梢上的红头绳里插——而就在这时,胡宗平跟王世成上来了,站在她俊俏的背影里,沙哑的声音也从背后传来:哎呀,这花是白色的,插头发里不吉利!
长村的女孩子都是插着野花长大的,一会儿鸢尾花,一会儿桃花,一会儿紫丁香。红红纷纷紫紫蓝蓝,都欢喜。周菊转过来的脸,懵里懵懂地盯着胡宗平看了看,又去看王世成,脸突地就红了!柿子花从指间落到地上,她很疑惑,这个洋气的漂亮女人是谁呢?嘴角也就疑疑惑惑地笑了,双手落在胸前,拽着辫梢拉在指尖绕。绕来绕去间听得王世成在介绍:这是我媳妇。但他的声音很快淹没在胡宗平一味地强调戴白花到头上不吉利的声音里,便急了,将脸转过去,黑着脸对胡宗平阻止道:就你多嘴,就你知道得多,啥白花不白花,这是周菊妹子,住我们隔壁。
柿子树的西头是王世成的家,东头则是周菊跟润子的家,两户人家之间仅仅隔着一棵大柿子树。柿子树是谁种的,有人说是王世成的爷爷,也有人说是润子的爷爷,几代人过去,爷爷们也都去了地下,这段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王世成不在乎这些,手一挥,管他谁的呢,我一个人能吃多少,柿子你们打,我要是正好遇到给我吃一个就行。
按说呢,西头不成也不好嫁东头,怪就怪王世成不争气,被阿爹数落了几句“不成器”“吊儿郎当”就跑到不见人影了,有头没尾的。周菊悄悄给了他一个月,等他带媒人来提亲,可他就是没有来。再见,自己成了润子的媳妇,他也领了胡宗平回来。算是各自成了家,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大家都生活在一棵大柿子树下。
好在,两家人家之后的相处无碍,胡宗平的心思不在这里,她好吃懒做,每天呵欠连天,手指上夹着纸烟看着远处心事重重;而周菊忙忙碌碌,屋前屋后,身边围绕着叫唤的鸡群和猪崽,将日子过得朝气蓬勃。
只是,偶尔,她坐在院坝里择菜,或奶孩子,会看着柿子树想起胡宗平那句话:哎呀,这个白色的插在头上不吉利!再看柿子树,眼前就晃荡着一片绿和一片白。
之后,又是王世成的话:哎呀,你最美了,就是我们的村花,喽,像我家门口的柿子花那样奶白奶白的,没人比得过你。
2
谁知道呢,十年后,周菊的头上会戴上一朵小白花。小白花被月光打着,显得更白,仿佛一朵柿子花遗落在头上。这个时候,润子刚走,是跟着王世成去矿上打工埋在井底去世的。从矿上领骨灰回来,操办好丧事,在屋里转几圈,周菊就再也无法在空落落的家里坐下来,这才来到柿子树下坐着。
青柿子挂满了枝头。与茂密的叶片拥挤在一起。月光落在上面,形成比树干还浓的黑团覆盖着,鬼影重重,身前身后挤满了忧伤和哀悼。地上落着几粒过早夭折的小柿子,酒盅大小,脏兮兮的,身上裹满泥浆水。润子走的时候说过,等我年底回来浇院坝啊,用水泥浇,平平整整,干干净净。浇筑院坝是周菊心中所想,因为水泥院坝,晒谷子最好,再也不会有碎石子掺和进来。走一步路也干净清爽,再在院坝边种上夜茉莉栀子花,多美呀!但,终究因为手头紧,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从而一直没有浇成。
也就是说,在没有遭遇变故之前,一切都还具备着希望,还有盼头。现在呢,话还在,人呢?一大颗眼泪滚下来,周菊抑制着内心巨大的悲痛,将头埋进手掌心里,仿佛只能依偎掌心力求安定下来——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有时间开始悲伤,身子不停地打摆子。一遇到棘手的问题,她就会打摆子。好像很冷,嘴唇哆嗦着。但不能哭出来,哭声会令屋里的孩子害怕。咽口唾沫,非常艰难地将哭声咽回肚子里,头从膝盖上抬起来,手掌拨弄着沾在腮边的头发,她便泪眼闪烁地仰望着黑暗的苍穹,道:多健康多好的一个人啊,应该长寿啊!
润子出事的电话是后半夜打来的。王世成在电话里不敢多说,但是村子里跟着出去的人已经传话回来,说润子好惨啊,头都瘪了!半夜三更来电话,已经预告没啥好事情,深一脚浅一脚赶到队长家听电话,周菊就尽量将事情想到最坏,润子可能出了事故,断了腿,或,少了只胳膊,怎么也没想到人会——没……了!王世成断断续续地在电话里说:周菊呀,怪我,润子,出事了……略微停顿一下,才急切地吩咐道:你赶紧过来,到了电话我我到车站接你!周菊就这样握着话筒像电线杆杵着,身子在抖,腮帮子在抖,上牙磨着下牙,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从身体内部发出来的,空洞地哀嚎着,像有无数的凿子在凿,连胳肢窝都疼——再是冷,非常的冷!
这也是周菊第一次出远门,火车的速度太慢了,简直是慢腾腾的!世界大得出奇,人一离开村子,就会找不到了。一路上她都小心翼翼地捂着口袋,生怕接润子回来的路费丢了。
润子是被装在一只黑色拉杆箱里带回来的。出去一个活生生的人,回来是一捧骨灰!周菊捧着骨灰盒站在院坝里,有气无力地:我们……回来了。房檐下,站着两家人的老父老母,以及赶过来关心的乡邻乡亲。大家的眼睛都聚焦在她手里的骨灰盒上,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动弹。一时之间,天地之间寂静得出奇,都眼巴巴地看着,仿佛在辨别那到底是什么……
柿子树也耷拉着满树的叶片,沉重得站不起来,突然,一只小柿子从树上落下,咚一声打在地上。地,颤动了,惊动了默哀着的人们,润子的娘这才张开嘴巴爆发出一声长长的呼唤:儿啊,我的儿啊——,一把老骨头踉踉跄跄地扑了过来……
之后,便是办丧事,入棺,叩头,行礼,出殡,安抚老的小的……润子是死在外面的,骨灰不得进屋。他的骨灰盒就直接从院坝里被放进棺材。院坝上搭了一个棚子,漆黑发亮的棺材搁置在两只长凳上。棺材头上刻着一个大寿字。寿字下面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摆着糯米蒸糕和三支青烟袅袅的香。棺材底下则点着一盏长明灯。王世成的儿子陪着润子的儿子双手握着一根香、一脸瞌睡地围着棺材转。也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反正王世成关照过大鱼,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大海。后来他俩就头挨着头靠在长凳脚上打起了瞌睡。黑压压的送葬人群,走来走去,忙着哭泣,忙着做菜,忙着倒茶,忙着抽烟,忙着点炉子——初夏的夜啊,凉意丛生,也不知是谁将炉子点燃了,红汪汪的火苗子噗嗤直跳,一个没心没肺的大嫂连连嚷着:哎呀,火在笑,来客了,来客了,肯定是润子回来了!
周菊挤在人群中间,被叫着找这找那。她一脸恍惚,本能地应着,本能地配合着,耳朵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感到人们在动,手在动,嘴皮在动,漆黑的人头,白茫茫的孝衣,好像一部无声电影,世界只剩下一片白一片黑。在这黑白分明的世界里,又觉得地皮在朝下陷,一只脚就要掉进去了。焦急时刻,她看见了润子,润子也站在人堆里,在唤自己,他好像还在笑,木木的笑意里露出雪白的牙齿。但是,一个黑影晃来,遮住了他,遮住了那张木木的笑脸,周菊一急,喊着“润子”,眼一黑,身子一歪,直接晕倒在了地上。
当被掐着人中唤醒,眼睛看着对面的板凳,周菊又见润子正坐在上面搓绳子。他没事就会坐在板凳上搓绳子,下雨天不好下地干活,搓;晚上烤火手闲不住,搓。搓出的绳子绕在板凳头上,绕不下了,才会站起来,拉着绳子绕成一个绳圈放到阁楼上码着,为今后做蚕架、扎瓜棚和捆玉米秆做足了准备。
周菊想起来了,出门那晚,他就用绳子绕在自己的胸脯和肩膀上量了一圈。绳子变成尺子,铭记着自己的胸围和腰围。他说挣到了钱回来给你带件好衣裳啊!然后将绳子放进口袋带走了。估计是想等到买衣裳的时候再拿出来比划。
周菊还记得,他出门那天由于自己心慌,做事不顺手。拎包碰到一只碗落在地上,瓷碗顿时碎成两瓣。润子怕她多想,赶紧安抚着“岁(碎)岁(碎)平安、岁(碎)岁(碎)平安”。揣着那截记录着胸围和腰围的绳子出发了,周菊从他的背影里收回来的眼睛,落在柿子树上,便发现柿子树该修一修了。下面的枝叶长得太重,黑压压地罩在屋顶上,怪不得灶屋总是不够亮堂。
3
按说,这事周菊自己可以做,爬上去拿把锯子锯掉多余的枝丫就可以——你周菊是啥人,地里屋里,都是好手,用锯子扛锄头上灶头,哪样不会呢?但每次看到柿子树,她想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柿子树的树冠已经高过屋顶,枝丫一部分搭在王世成家的屋顶上,一半搭在润子家的屋顶。像一个巨人和蔼可亲地搂抱着这两间屋子,也像是柿子树在依托着这两间房顶生长。这边搭在润子家的灶屋,那另一半则遮在王世成的房间上。房间的窗户上挂着一条酒红色的丝绒帘子。这是胡宗平带来的第三样时髦东西。她蹲在窗户上挂帘子时,就隔着窗户问过周菊好不好看?周菊看一眼墨绿的柿子树,再看一眼酒红色的丝绒窗帘,一愣,又去看了一眼奶白奶白的柿子花,又看了胡宗平漂亮的脸蛋一回,待看到她还是那么漂亮,皮肤奶白奶白的,眼神就沉到湖底,嘴上笑吟吟道:红红绿绿,蛮喜庆的!
胡宗平也看看柿子树,又看看手中的帘子,哼着小曲儿慢慢悠悠地挂上了。
这天晚上,王世成就蹲在这道帘子下,默默地陪着周菊闷声不响地抽纸烟。用力吸一口,烟头就亮一下。一脸的沉重就闪现了,而背后的红丝绒帘子却成为一块黑色的幕布幽暗地垂挂着。他在等周菊哭,只有他知道,她到现在都还没有哭出来,一定憋坏了。起初不哭,是忙着处理润子的事,坐车,谈赔偿款,安抚老人小孩,再是操办丧事。现在事情都办好了,是该哭一场了。可又怕她哭,若真哭了,咋弄呢?润子依旧回不来!自己又不能帮她做点啥呢?说白了,连句安慰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也不好多说,如果說了,反而会……也就在这一刻,他决定还是尽早出去,不能留在这里给她增添负担。
因为,这事一出,即使在悲痛的葬礼上,人们还是会说出内心的猜测:哎呀,润子这一走,倒是好了王世成啊,可以跟周菊来第二春了。
对啊,周菊都给他带大了娃,早好了也说不定!
这些话太难听了,要是周菊听见如何受得了,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心有多善,别人倘若不知,我王世成是明白的。自从胡宗平走后,大鱼可好在有她呀。虽然大鱼也挺懂事的,清秀,聪明,志向远大。跟周菊也亲,一口一个婶,嘴巴甜得好似抹了蜜。跟大海住在一个房间里,情同手足。大海的性格则像润子,温暖、宽厚,踏踏实实。两个人的性格正好形成互补,就像是周菊生了两个儿子。但现在要为周菊考虑,再好也不能都丢给她,大鱼可以出去读民工子弟学校。这个决定一旦形成,王世成就重重地舒出一口气。看一眼面前的周菊,只见她的身上弥漫着厚厚一层悲伤,黑黢黢的背影孤独又可怜,好像随时会从石头上掉下来。
一根烟抽尽,烟头丢到地上。地上早已落有一大摊烟头。一包纸烟也抽完了。周菊仍旧坐着不动,露水升腾上来,空气潮湿了。她咳嗽两声,大概受了凉。王世成的心一阵抽搐,猛然站起来,朝前走两步,又停下来,退回到窗帘下。摸了一把被露水打湿的头发,艰涩道:你哭吧,哭出来好受些。
黑黢黢的背影一悸,估计没有想到他在背后。继而,长长地叹一口气,明显是强忍住眼泪在摇头,鼻音粗重地说:不哭了。哭,有啥用呢?
王世成说:憋着更难受,你不是不晓得。
黑黢黢的背影说:我晓得。
继续沉默。夜风吹拂着发丝,吹拂着柿子树的叶子,吹拂着红丝绒窗帘。萤火虫在夜空里绿莹莹地闪。又隔了一会儿,王世成道:我对不起你呀,也对不起他,这都是我的错!
润子在自己组里,那天巧得很,大家都出来了,就他慢一步压在里面了。事情的发生仅在几秒间,一个井道就塌了。事故原因矿里的领导仔细解释过,但王世成心里清楚,自己这辈子算是愧疚上了周菊——如果可以,他希望死的是自己!
虽说当初没有娶到周菊,对她嫁给润子有不服之意,可王世成知道自己还是希望大家都好好地活着。当时,润子想出来挣钱,他就劝他不要出来,他说娃读书的钱有我呢,你出來做啥?其实只是怕周菊孤单,大好的年华一个人留在家里干活太苦。润子没有听他的,坚持要出来,他说大家都出来挣到了钱,年底回去给媳妇给娃带了好看的衣裳和好玩的玩具,就觉得自己特别窝囊!王世成知道他想对周菊好,建议他在屋里养菌子,跑出来有啥好的,像我这个没媳妇的人才出来,你犯不着。润子说:正因为有媳妇,才要出来,我出来挣点回去,总是好的,那屋子今后总归要翻建吧,院坝总归要浇吧!话都这样说了,还能说啥,只巴望着平平安安忙到年一起回去过大年。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这事一出,自己和周菊,就成了一个死了男人,一个跑了老婆,可以再度续缘的人!就连胡宗平离家出走,也跟周菊扯上了关系。她们说胡宗平走周菊是见的,她知道,但她就是不去阻拦,他们就隔一棵柿子树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事让周菊浑身长嘴也解释不清。带胡宗平走的男人,先是到了自家,用三十块钱买了自己的头发后,就去了胡宗平家。当他看见胡宗平坐在院坝里梳头发就愣了好一会儿的神。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识,但见他径直朝她走了去。胡宗平的嘴巴里正含着一根烟,见到有人过来,就侧头看了一眼。男人跟她对视一眼,就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红塔山,并抽出一根含在嘴巴里,再伸手将她嘴巴里的烟头拿下来对着点。点燃的红塔山他没有自己抽,而是送到了她的嘴巴里,他自己则抽从她嘴巴里拿下来的一点点烟头。不知是嫌弃脏,还是因为被调戏,噗嗤一声,胡宗平吐掉了烟,嘴巴里还跟着骂了句什么。不想这个男人又摸出红塔山,照样点上一根,又塞进她嘴巴里,嘴皮子嚅动着,说了句什么。转眼,就看见胡宗平咯咯地笑了,带着他进屋了。
王世成在开拖拉机拉煤炭,几天回来一次,等他再回来,胡宗平跟这个男人就不见了。大鱼被周菊接到家里吃饭,王世成抹着一脸黑煤灰过来,气呼呼地蹲在地上说:这个女人跑了——穿着那双鞋子穿了。
如同来时一样,胡宗平又穿着那双保管得很好的高跟鞋跑了。王世成出去转了一圈就回来了,他说她要走,找有啥用!之后,自己就出门去了。他将大鱼委托给周菊和润子带着。关于这件事,还是润子做的主,他坐在板凳上搓着绳子,对周菊说道:一个娃是带,两个也是带,我看这事成。润子都这样说了,周菊自然用心带着。自己娃吃啥他一样吃啥,有时候只有待他更好点。
王世成偶尔会汇一笔钱回来,汇款单上写的是润子收。润子将汇款单拿给周菊,说:咱们娃有的吃,他就有的吃,这钱你去帮大鱼存着。
问题的最终结点还是落在孩子身上,他们才让人揪心啊。一咬嘴唇,周菊跟王世成道:我没怪你。你莫说了。要怪只怪我没福气,也怪润子命短。
王世成说:可我心里清楚,要是我最后一个走就好了……
周菊站起来道:不许瞎说!他都走了,让他安心吧,你应该知道他是啥人,不会怪你的。
王世成愣愣地看着她,也听到了她气呼呼的喘息,犹疑半晌,道:……那,明天早上我带大鱼出门去了,你照管好自己啊。我会给大海寄学费的。
你要带大鱼出门?那他读书咋办?周菊急了,转过来的脸,泪花亮晶晶的:你不用担心我的。我是不允许你带他出去的,他叫我婶呢!
继而,倔强道:大鱼还是给我带着吧,过继给我也行!我告诉你,王世成,你别小瞧我,我不会垮的,孩子都那么好,你怕啥呢,急啥呢?你出去可以,明天早上来陪大鱼吃好早饭你走吧。你听我一句,不要去矿上了——孩子还小,我们,我们都好好地……活着吧!
听周菊这般一说,王世成就没有主张了,唉唉地应着,眼睛落在她头上的白花儿上,心里就狠狠地骂了句:“胡宗平,你这个贱货!”转身间,又听到周菊站在屋角说道:你明天早点起来,柿子树你去修一下,不然屋顶都要被压塌了。
4
夏天过去,小孩读四年级了,得去街上读书。周菊便带着两个孩子去街上租了一间小房子陪读。房子靠近学校,三个人挤在一小间里,厨房临时搭在阳台上。即使这样小的一间,租金也很贵。现在很多家庭都这样,家里的其中一个男人和女人在外面挣钱,留下的一个就跟着陪读。周菊这样做,实则是没有办法。
婆婆自润子离世,就变了一个人,她生硬,刻薄,不容商量,站在院坝里指着柿子树说:这柿子树的一半也是我儿润子的,如今我儿不在了,就是大海的。而你还弄个野娃子在身边,用我儿的钱(事故补偿款)来养人家的娃,你的心啊太狠了,润子瞎了眼看上你,他就不该娶你——是你克死了他!
柿子已露星点橙色,开始告别青涩走向成熟,力所能及的样子。周菊盯着一只柿子看着,尽量不让眼泪流下来。
于心来说,润子走了,自己这个大儿媳妇,得替润子照顾好两个老人,尽好孝道——她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将悲伤深深地压在心底,妥善地照顾好家里,每天还去老人那边走走,仍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劳动力。可婆婆看见她,总是黑着脸,当外人看,张口闭口全是责怪:你说他突然跑出去干啥呢?你咋不出去进工厂呢?他这一年肯定犯冲,他出发的那天有没有看日子……
这些问题也是周菊要追问的问题,可是再问也没有人回答了。不久,老母亲来了。她来借钱。特意梳了头来的。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尽显威严。她来借润子的十五万赔偿款,她说自己是润子的娘,这钱得交给她保管。这个钱就当是跟你借的,等大海长大了,钱再还他。她端端地坐在堂屋中间,是如此地严厉和端庄,腰杆子直直地抻着,不容分说。
曾经,她是多么喜欢自己的呀,说自己贤惠,最会勤俭治家。逢人就夸,说了活路好,还说针线茶饭也好,模样还俊,一样不落人。然后就将柿子树下的家交给了自己打理,他们则住到堰沟边看水去了。那几年啊,是家里最得意的几年。润子的弟弟华儿书读得好,是长村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分到街上吃商品粮,铁饭碗稳稳妥妥的。老两口可算是功德圆满。大儿子留在身边,相互有个照应。小儿子的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们肯定是要住到街上去的——咱家街上总算有人了!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突然觉得扬眉吐气、事事如意。只是,没如意几天,润子就出事了……
哎呀,我的儿啊,你命苦啊,你在我身边好好地活了二十几年啊……儿啊,你在天堂听得到妈的心有多痛吗……
见周菊愣神着,老母亲忽然就将上半身朝桌子上一趴,手掌抓着桌面嚎啕大哭了起來。哭泣一阵比一阵高,一声比一声悲恸,头发乱了,散落在脸上,沾在泪水里。周菊站在边上跟着默默地流泪,心想要是也能说哭就哭就好了。可自己的眼睛哭肿了,大海会问,不能让大海每天活在痛苦中。这个孩子跟润子一样,不善于表达感情,但心里啥都明白,会暗暗心疼人。只能咬着牙尽量将日子过得祥和一些。
妈,你莫哭了,都是我没照顾好他……
老母亲依旧哭着,眼泪跟下雨一样多,很快,眼睛像个桃子红肿着。身子骨萎缩成一团,来时穿着还合身的蓝布衣,大了,空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嘴巴有气无力地哭诉着: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啊,看到我儿站在屋角,他回来了,血肉模糊的,喊我照顾好他的儿……
润子是怎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也不会不信自己的。眼见着老母亲哭累了,像一个树疙瘩搁置在椅子上,不停地咳嗽着,上气不接下气。上半身久久地弯在膝盖上起不来,周菊就走过去,拍着她的背说道:妈,我这就去给你拿存折,你莫哭了。
这十五万赔偿款还是王世成拼了命去“周旋”来的。矿里的领导一个个油头肥耳,根本不肯给,王世成说干了嘴也没有用。看着默默坐着的周菊,来来回回地踱了一阵步,他冲到周菊面前说了句“我一定要要到!”,转身便冲了出去。当周菊跟上来,他已经身上绑着雷管站在领导办公室。他高高地举着打火机说:我兄弟这么年轻就走了,丢下一家老的小的,你们做事要讲良心!不给十五万,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说着,就打燃打火机要去点导火线!
红汪汪的火苗一闪一闪,周菊的心跟着抖了,拽着王世成说:咱们不要了,回吧。
王世成一把推开他,又继续喊着:你们看见了,这么年轻的漂亮女人,成了寡妇,你们看见了,她今后怎么过!那一刻,他高大威猛,无惧生死,只有周菊知道,他在为自己赌一把,如果不给,他是真心会炸死的。他害怕今后的日子成天面对自己的孤苦伶仃。这会让他生死不如。最关键的是,他走不出润子是在他的组里出的事。好像他成心要害他一样。
当然,十五万对于长村人来说可是一笔巨款。润子的娘拿走存折后,七大姑八大姨也相继来借钱。口口声声说要去买种子,要去买煤炭,要动工造房子,一千八百随你,你现在可是咱们长村最有钱的人!周菊正在剁猪草,话声一响起,她的手就停在半空,左手狠命地捏着猪草。刚打来的猪草,绿汪汪的草汁在指间黏糊。周菊看着来人的架势是非借到不可。只好继续剁猪草。菜刀落到手指上,疼痛传来,左手的食指便被菜刀剁掉了一块肉。
有时,人们直接到地里去找她。她正在薅草,热得浑身是汗,满面通红,捏在手心里的薅锄就在来人的脚尖前薅。汗珠淌进眼睛,又涩又辣,再出来就变成泪珠儿了。整个下午她都拼命地不停歇地薅着,直到筋疲力尽地坐到地上不能再动弹了,才大口地喘出一口气。
5
只有周菊知道,当拿到十五万赔偿款的时候,王世成大哭了一场,他举着支票,开心地跑来,手舞足蹈地,说钱来了,钱来了。但是,一看见周菊,他才笑着哭了,他将支票递给周菊,又点着上面的数字证实,个十百千万……突然,他数不下去了,抱着周菊的肩膀哭道:其实我是想死的,我欠你一条命啊。周菊任他哭,知道他其实是害怕,别看那天英勇无比,也是被逼急了才这么干的。
王世成自小多波折,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去山上伐木回来,一脚踩空,人和木头一起滚到水沟里当场去世的。留下的媳妇一生也没有走出早年丧夫的悲痛,将日子过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她将身子依靠在门框上,失魂落魄地幽幽地看着远方唉声叹气,逢人就阐述自己的命苦。起初人们可怜她,会驻足听听,也陪着唉声叹气几声,再说几句深情饱满的安慰话。可时间一长,没时间管了,任她自个儿怨天怨地——没几年也走了。所以,当胡宗平失踪之后,润子发话帮带大鱼,也是善心之举。感念着这份好,也就想通了周菊不嫁自己是对的。润子家来自“五好家庭”,加上又是一个实诚人,再喜欢周菊,却从不多说啥,也没有跟自己争斗。只会在农忙季节赶过去帮衬,甚至还跟着周菊的父亲跳进猪圈掏过猪粪。所谓的身为新时代农民的优良品质他都具备,经他手种的田,收成也好。
而自己除了会说几句好听的话,就是一棵浮萍,注定一生飘荡。根本不配拥有一个好女人!他这一走,就不见人影了——他什么时候才能稳定下来呢?才能不叫人操心呢?才知道体谅别人呢?周菊的二老看着默默地替周菊着急,周菊装着不见,一声不响忙自己的。只有她自己知道,王世成那天修剪完柿子树,并没有来陪大鱼吃早饭。可王世成知道周菊憋着眼泪做了酸辣子炒腊肉,他只是站到柿子树下看了看这边很久,闻了闻菜香,默默地转身走了。他不想再见周菊,觉得自己让她受苦了。周菊似乎也知道他不会来,带着两个孩子在饭桌边等着,却没有吩咐大鱼去叫他。当听到锁门声响起,便知道他出发了。
这一走,直到快过年,才来消息。他通过邮政局找到周菊,汇了两千元钱过来。邮戳上显示的地址是江苏镇江。周菊看着汇款单,面前又站着润子:我们娃吃啥他吃啥,这个钱你去给大鱼存起来。
这时候,周菊已在街上的周大嫂餃子馆做帮厨。刚开始去做小工,打打杂,扫扫地,端端饺子,洗洗盆子啥的,但她手脚麻利,又会包一手好饺子。饺子馆老板很开心,忙不过来了就叫她一起包饺子,或进厨房打汤。这一来,她的好茶饭手艺就有机会显山露水。老板本来是一个喜欢舒服的人,见她这般便美滋滋地坐到吧台上去数票子去了,将厨房全部交给她打理。忙进忙出,忙上忙下,干净利索。事后,又发挥了腌泡菜的手艺,饺子馆可是离不开好泡菜的,由她腌制的泡菜做出的酸汤饺堪称一绝。很多食客专门为这碗酸汤饺而来。他们一进门,就直接喊道:周大嫂,来碗大份的酸汤饺。要辣要酸啊!
好嘞!马上好。周菊应着,一阵叮当响,又香又酸的酸汤味飘了出来。而她包的饺子,褶皱会变换着来,有的像鱼儿,有的像星星,小孩子特别喜欢。常闹着要去吃“小鱼儿”。饺子馆的老板不姓周,为啥叫周大嫂饺子馆,直到两年后,饺子馆老板的丈夫发财进城建房去了,一家人搬到城里住,饺子馆转给了周菊开。大家才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事,为啥不叫马大嫂饺子馆呢?老板拍着周菊的肩膀欢欢喜喜道。
周菊盘饺子馆的钱都是娘家兄弟姐妹一起给凑的,他们一边数钱一边数落着:“哪有这样的人家,儿子走了就将你撵了出来,还不管孙子!”周菊听着不回复,能将饺子馆开起来,还是很高兴的。紧接着小孩读初中了,花销大了,为了节省开支,她就一个人忙。从凌晨起来买菜,到深夜发面,好在大海跟大鱼懂事,不让她操心,上好夜课也会过来帮忙,作业多半是在饺子馆里做的。周菊看着他们,又疼又怜,眼睛落在大鱼脸上,就觉得他长得越来越像王世成了,就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欣慰地一笑。又去看大海,看着他拙笨地学着包饺子,跟润子一样,总想多心疼点自己,正在揉面的胳膊里就又增添了一股力量。对了,这是咱的希望呀!有他们一切都好!
忙忙碌碌中,一晃,孩子读高中了。高中得进城去读,周菊只得转了街上的店又跟着进城。经过一番找店,很快又盘下一个小炒店,重新开张营业周大嫂饺子馆。城里到底店多,生意并不好做,而店铺租金又高。几经周转,才在岚河边找到一间租金便宜、位置还算过得去的店铺。全靠好手艺维持。
这些话看似几句就说清了,实则有很多的难题需要处理和克服。但周菊下过决心,都经历了丧夫之痛,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和经历的呢?所以,很少愁眉不展。总以一副乐观、豁达的样子,与隔壁邻居亲亲热热地相处。有一个常年来吃饺子的杂货铺老板,他四十来岁,熟悉后,会问一些私人问题给周菊:周大嫂,你男人做啥的呀?咋从来不见他呢?
周菊正好端着一碗酸酸爽爽的饺子汤出来,看着香气扑鼻的饺子汤,她回应道:他在天堂寨呀。
天堂寨是哪里呀?
这个地方啊,在长村呢。
长村是哪里呀?
哎呀,长村在天堂寨的山腰腰上啊。那里呀,有一棵很大的柿子树。
润子的坟茔的确在天堂寨。但这个人不知道,只当真以为天堂寨里留守着她的男人在看家,那里种着一棵大柿子树,那个地方很美,人不能全都出来。但这个人投射在周菊身上的眼神非常暧昧,笑一笑,他又道:看你样子,他很疼你啊,只要说起他你眉眼里都是欢喜。
周菊一愣,是啊,多好的一个人啊!又听得男人说:他疼你是应该的,你看你多能干,性格又好,不贪小便宜。说话也俏皮。那酸汤饺么,又这么好吃。你这样的女人不疼疼谁呀!
6
如周菊所料,王世成这次走不会轻易回来。有长村人下来看病或出门等车,来店里吃饺子,看见周菊会问道:那个王世成还没有回来呀?他现在在哪里呀?
周菊微笑着摇头。对方又说:不对呀,他都为你绑过雷管,不会不告诉你的吧?周菊依旧笑着,努一下嘴,说:你的饺子汤冷了,赶紧吃啊。
嘴上虽没心没肺地笑着,但心里却更加清楚明亮。看来王世成早料到什么叫人言可畏什么叫闲言碎语!只有他人在外地,自己才能安静地过日子。为此,宁愿选择常年飘落在外也不回来。他这样做真够狠心的,他怎么可能不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呢?但是,他也只能这样做,如果他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的话……
这天,店里风尘仆仆地进来一个人。自称是跟在王世成手下跑腿的,他从车站一出来,就赶到饺子馆来解馋,好像一年半载都没有吃过饺子。一边吃一边说话。从他嘴巴里,周菊知道了些许王世成的现况。他人在南京,已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赚了些钱。跟一个大胸脯女人住在一起。那个女人是寡妇,男人早年死在矿上。王世成可怜她,收他在工地上做饭,晚上就一起睡。最后还感叹了一番:我这个哥啊,有魄力,招人喜欢。
其实,王世成跟周菊的联系现在用的是手机,非常方便,还互加了微信。有些近况,两人要是愿意说都是可以知道的。但两人并没有过多的聊天,翻开页面,只有几句淡淡的寒暄,各自说过几句天气情况,再是收到大鱼的生活费后周菊会返回去一个微笑的笑脸。当王世成问起大鱼的学习成绩,他收到后也会返回一个微笑的笑脸过来。平常,周菊也只是打开他的微信对话页面看看,再安静地关闭掉。感觉这个人很远,却又在身边,再看,还是很远。
这晚,周菊失眠了。无法入睡的同时,她听到岚河水流淌的声音是复杂的,淙淙的,哗哗的,呜呜的,遇到石头,或是弯道,会慢走,会停滞,也会激越。电视塔倒影在岚河里,葱葱郁郁的连绵起伏的山峦也倒影在河水里。河水因此绿油油蓝盈盈的。傍晚时分,一个扛着救生圈的男人带着女人和小孩去河里玩耍,他们一会儿蹲在沙滩上挖沙子,一会儿爬到石头上拍照,一会儿走到水里嬉戏,欢乐的笑声跟着河水奔跑着,哗啦啦的,又欢喜又畅快。
回想着这一家人家的幸福,周菊的嘴角不由得慢慢地打开微笑了。身体里有一个部位就开始调皮着动了一下。是的,轻微的一下,跟微风拂过河面那般,轻轻地荡开一层细细的涟漪。仿佛岚河水跑到身体里来了,它在搅和着什么,带动着什么。这情况不妙!心慌意乱地将手掌落在胸口上去压着。慢慢地,又加大了力度摁了下,再松开,再摁下一个漩涡。心慌慌的,像是一个无法填塞的黑洞。周菊只好又将手掌从胸口拿开,摸到手机拿在手上捏。后来又打开手机找到王世成的名字写道:大鱼星期五开始高考了。
隔一会儿,又补充道:你回来陪他参加高考吧,这可是人生大事啊!
半夜三更的,他可能在睡觉。周菊也不等他回复,将手机关闭睡觉。但一闭上眼睛,不禁又皱起眉头来:他真的跟那个大胸脯女人住在一起了吗?他会带她回来吗?那个女人的男人也死在矿上,多像……对呀,多像自己呀,别人不好这样比,自己是知道的,只是她长得好看吗?有多大年纪呢?
本以为听到这些心情会依旧平静,日子啊得继续朝前拼,睁开眼想的是饺子馆,闭上眼念的仍旧是饺子馆。因为饺子馆养活了自己也带大了大海和大鱼,是富有恩泽的。但,此刻,心跟着窗外的岚河水失落着,害怕着,又想到多年前胡宗平来的情景。她的样子啊还是那么清晰明了,一点也不像是消失了多年的女人。只是一开始她的心没有跟上来。
——这个人虽聪明,却闲不住,用村里人的说法就是到底不靠谱,成天牛里牛气的。暗自嘀咕一句,也算是责备了王世成一通。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下了。却是一堆乱梦。在梦里,周菊又看见了润子。他站在柿子树上,身上穿着一件胸口上印有一条蓝色的鱼的圆领衫。柿子树依旧枝叶繁茂,树大根深,柿子花一半白一半绿。他看见自己,就咧开嘴巴笑着从柿子树上跳了下来。但整个动作只看见他胸口上的鱼长上了翅膀,轻盈地一飞就飞来了,鱼嘴巴翕动着:我走了啊,投胎转世去喽。
紧跟着又划拉两下翅膀,一扇,不见了。
润子——
骤然从梦中惊醒过来,身子黏糊糊的,全身是汗。孩子们已经去了学校。看来睡过头了。他们没有叫自己,估计是想让她多睡一会儿。这俩娃啊,真叫人放心。手放在胸口,周菊唤了声“润子”,道:是呀,你安心去吧,孩子们都好着呢。
7
喜鹊叫,喜事到。
喳喳,喳喳……
站在水槽边洗碗时,周菊听到了喜鹊叫。叫声从岚河边传来。波光粼粼的河面,对岸群山环绕,绿树成黛,瞪大眼睛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找到喜鹊站立的位置。农村人最怕的鸟是乌鸦,它一叫就感觉“大事不好”。从枯树老屋头顶飞过,暗沉沉的——对了,润子走的前几天,周菊就听见乌鸦落在柿子树上叫。叫得人心惶惶的,呱呱呱,只图自己快活。
而另一种鸟叫喜鹊,这就很不一样,它在哪里叫,哪里就有喜事降临。它是吉祥的象征,周菊家的堂屋里,就张贴着一张有喜鹊的年画。它跟穿着红兜兜胖娃娃的年画连在一起,喜事连连。所谓自古画鹊兆喜的风俗不假,那年月,家里的确順利,润子跟自己结婚了,生娃了,小叔子毕业了,分配了工作,成了街上人,老人吉祥安康。
那么,现在,喜鹊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一个饺子馆,有什么喜事降临呢?莫非,莫非……周菊突然兴奋起来,莫非两个娃高考会有好成绩?是呀,如同中国所有父母一样,高兴之外,还有紧张,毕竟高考是一件大事,马虎不得。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这种即高兴又紧张的情绪里似乎还有点别的。禁不住从衣袋里摸出手机又看着王世成的回复:马上启程,等我!
他的这句回复,是很快发来的。只是周菊故意关机才没有看到。第二天早上一开机,信息就跳了出来,时间显示的是一点三十五分。这个时间跟周菊发送的时间只相差了四十秒。好似他就在等着她的召唤一样,只有得到她的召唤,他才能放下包袱回来。所以,他很高兴,还有点骄傲。从他的语气里,能感受到年轻那会儿的样子,口气很容易就牛起来。
现在交通发达,从南京回来,估计也就一天多点的时间。明天也就到了。一晃,他离开也有十来年了,山上的家早已荒废。只能让他回饺子馆坐坐——就当他是亲人吧,周菊苦涩地抿抿嘴,转身打开冰箱,想找一块腊肉准备煮,他最喜欢吃腊肉炒酸辣子了。
喳喳,喳喳,喳喳……
喜鹊叫得甚欢。被水龙头冲刷着的双手,由于常年要和面揉面包饺子,为了饺子保持原味,再冷都不用护手霜,怕护手霜的香味包进饺子,这样就很难吃了。手因此没有得到保养,很是粗糙。擦干双手,周菊在手背上抹了点猪油膏,便带上门,跟着喜鹊的叫声来到了河边。
得想想啊,他回来了该如何面对他?昨晚冲动了,咋就发了信息给他呢?大鱼是他的儿子,高考一到,电视机里天天呼喊着,哪个家长不会知道马上要高考了呢?他若真惦记他的儿子,自然会想办法回来。不回来,自然是不想回来。他不是跟那个女人,对了,说不定那个大胸脯女人不让回呢?……周菊纠结着,徒生烦恼,他回或不回这种心情都很折磨人。
更折磨人的事还在后面,她居然想他在外这些年想过自己没有?他出门这些年,除了给大鱼寄生活费,没有一句话是给自己的,他到底在想什么呢?那么多的时光,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自己也在润子的悲痛中走不出来,可昨天晚上怎么就突然明白了呢?手掌摸摸发烫的脸,怎么看都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那么这是谁呢?
岚河水蓝盈盈的,是县城唯一一条河流。它一会儿呈之字形走,一会儿像一条缎带直飞,河中央有时候是深潭,有时候则是大石头,还有长着大柳树的滩涂。水从边上走过,风从天上来,头发和衣领被吹起来。周菊蹲下,对着河水看见自己一张充满忍耐和坚守的脸,笑了——对了,他说叫自己等他,等他什么呢?怎么等呢?
喳喳,喳喳——喜鹊似乎就在对岸叫,就在那棵最大的柳树上。手搭凉棚罩在额头上,拼命地看也没有看见喜鹊的身姿。继而,又听得喜鹊在叫,喳喳,喳喳,驻足倾听,还在前方。前方是电视塔,电视塔在山顶上,每天都要看着人们睡去又醒来,万家灯火,爱恨情仇,生老病死,都在它眼里。塔尖上的黑点,便是喜鹊的窝,它落在的位置正好对着饺子馆!
仰着脑袋,听喜鹊的叫声时,周菊的手无意间落在胸口,捏着一粒纽扣把玩着。纽扣嘣一声跳出了扣眼,王世成俊朗的脸就出来了;继而,扣子又呼啦一下扣上,王世成不见了。一惊,又去抓扣子,扣子嘣一声跳出了扣眼,王世成浑身绑着雷管说话的声音就响起来了——你们做事要讲良心,像她这样一个漂亮女人就此一个人过了……
扣子被扣上,再扯开。实则只有一个动作和程序,一粒扣子带着原始的姿态突破出来,扣眼就显得徒劳无力。扣子得到释放,胸口一松,压抑的胸口一弹,被一颗纽扣喊醒了,它开始松弛,不再压抑和窒息,的确是该好好地呼吸一下岚河的风了。
当岚河水蔓延到皮肤上,从扣眼里灌进胸膛里,又顺着乳沟流淌下去,好像是站在岚河水里的石像,正在沐浴夏日的冲洗和水的抚摸。水呀,多么体贴人心啊,像一只只小手,要将每一寸皮肤都清洗一遍。清洗掉痛苦,哀怨,忧愁——让生活多一丝清朗。周菊就这样站在水里洗澡,慢慢地清洗着,顿觉肉身被水漂浮着,虚妄又真实,还有点得意忘形,与人为的不顾一切……
8
于是,从河边回来的人,身上带了一丝水汽,鬓角和发梢湿了,裤子、衣服也湿了,水滴从鞋子里挤了出来,一路跟了回来。直到看到饺子馆门口站着的好几个客人,周菊这才意识到荒唐——对了,怎么就跑到水里去洗澡了?那还是周菊么?
难为情地笑笑,难以掩饰的是几许春色,边走边摸裤子口袋找钥匙开门。只听客人在问:你这是掉到河里去了啊,你再不回来,我们还以为你跟哪个男人跑了呢!你看你,有啥想不开的呢?
也有人关心道:你总算来了,我还以为出啥事了呢,你可从来没有关过门!
那个開杂货铺的男人也在,他走出人群,急切道:这咋跑到河里去了呢——你,没事吧?
人群中还站着自己的小叔子。小叔子平日里对两个孩子的学习也有所照料和帮助,估计也是来关照小孩高考的事情的。不想却是替他的母亲来的,他叫了声嫂子,将一个信封放到周菊的手上,并告知说:我妈病了,在医院,肺癌。晚期。这个是她托我转给你的,她说该物归原主了。可惜她已经走不动了,没办法亲自来,你多包涵啊。
小叔子到底是当官人,处事不惊,再急的事都说得客客气气。一听他的话,周菊急了,急乎乎地问道:那妈住在几号病房?小叔子说:806,你要去的话找后面那幢楼。说着,关照周菊放好信封,自己则急吼吼地赶回去开会。看出他对信封的重视,周菊这才将信封举起来对着太阳照,待看到里面的那张类似存折一样的东西,心中一颤,这是润子的……
只是,现在,这张存折婆婆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客人在店里叫:周大嫂,快来一大碗酸汤饺。对,我也要一碗。
信封捏在掌心,就像抱着一块大石头。迫使身子只朝下坠,双腿发软,跟当年得到润子去世的消息一样!街上,载着小叔子的汽车正像一条黑鱼游过绿灯——与此同时,绿灯闪烁,切换成红灯。一绿一红间,周菊猛地朝屋里回应道:一大碗酸汤饺啊,好嘞,马上……就来!
但她真实想法是得赶紧去医院看病入膏肓的婆婆。生活巨大的雾气和悲喜交集又一次从四面八方涌来,打一个喷嚏,眼泪一涌而出,她知道自己就要哭出声来了!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