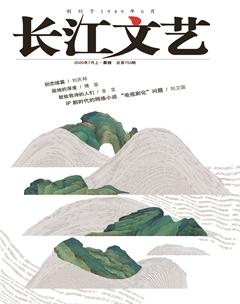我骑车去火车南站送信的那一年夏天
何大草

一
暑假的午后,我和小北都会摸到机关大院去游荡。
家属区和机关大院一墙之隔,靠最里边有两排红砖小平房,20来户人家,当头是公厕。我们进了公厕,推开百叶窗,一跳,就在大院了。
大院里有十幾幢老式小灰楼,一座水泥建的六层办公楼。万年青分割了道路,草坪交错,种满了树。如果不是造反派常开了卡车闯进来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呼口号,倒很像一个幽深的植物园,或是疗养院,清静得好。
沿东边墙根,是茂密的夹竹桃,开满了白花、红花,冷艳夺目。小北说,不能碰,有剧毒。顺夹竹桃而行,会撞上一座兀然隆起的大土堆,爬满杂草、藤蔓,顶上立着两棵石榴。是几年前挖的人防工事,闲置了,已然像古代的帝王冢。石榴结了果,红彤彤的,没有人理会,又裂了口,露出水晶般的石榴米。小北和我钻上去偷摘,惊吓了一群野鸽子,咕噜噜乱飞。还有一只兽,绿眼珠、皮毛金黄,带花斑点,嗖地蹿出来!跃上墙头,一溜烟不见了。我叫了声:“好大的猫。”小北哼了哼:“有这么大的猫?豹子。”我不信,不过,也难说啊。
露天篮球场,少有人打球,草就顶破了水泥地皮,一簇簇冒出来。篮板下老搁着一颗球,路过的人可以顺手投个篮,但这种人也很少,径直就走了,像揣了好重的心事。我和小北就捡起球练攻防,球技都不行,十投八不中,出身臭汗而已。
球场北端,是养猪场,十几个圈里拦着不同大小、毛色的猪儿,小北喜欢拿根小竹竿抽它们。我不忍,总抓把饲料朝槽子里扔,看它们欢叫。
饲养员是农村来的小伙子,我们叫他冯二哥,带了点称兄道弟的亲热。他父亲是郊区的生产队队长,专门负责给机关送蔬菜,跟行政处搞熟了,就把冯二哥弄上来做了临时工。
有一回炊事班在这儿杀猪,我们去时已在开膛了。七八个人围住案板,开膛手是个黑油油汉子,叼着烟,敞着衬衣,袖子挽得老高,露出卷曲的胸毛和汗毛。他拿刀在猪肚子里利索地切割,掏出肠子、心、肝,最后是肺。肺上有斑斑黑点,他指着黑点,得意洋洋地宣布:“这,就是肺结核。”围观者悚然一惊,个个凑近去看,轻声叹息。我也吓了一跳,小北冷笑,叽咕道:
“扯鸡巴蛋,听他吹。”
小北父亲是机关才子,外公是老派文人,他受的家庭教育,全都文质彬彬。
但,自从目睹父亲被造反派扇了耳光后,小北的脾气变坏了,胆子也变大了,他常对我说:“妈的个×!不要让人觉得我们是好欺的。”
他眼里,大人都是装神弄鬼的,且不可理喻。只有少数人,譬如他外公,还算是正常:一,毛笔字写得好;二,废话少;三,笑容多。
从六岁起,外公训练小北临《曹全碑》、《张迁碑》,今年满了13岁,又转临《颜氏家庙碑》。在我看来,他已算半个书法家,学校、家属区要写幅大标语,有时就叫他动笔,红纸、大字、墨迹酣畅,我是服气的。
我自己百无一能,只喜欢读点小说,好吹给院里的娃儿听。已读完《艳阳天》《金光大道》、家里仅藏的一部《水浒传》,以及小北家的《三国演义》。他对小说没啥兴趣,但还是把外公的《红楼梦》又给我搬运了回来。院里的大人称我小书呆子。我自忖有点呆,不过,也不是很呆。
那些漫长的下午,除了投篮、逛猪圈,我还陪小北去看大字报。机关大门内外,几面墙上都被大字报糊满了,且天天更新。内容嘛,我觉得废话、屁话多,很无聊。但小北专注于看字,津津有味。他说:“有些字,写得相当可以哦。”我说:“比起你老外公如何?”他笑道:“不好说,反正是别有一番风味嘛。”
作为对我的补偿,他也陪我去阅览室翻杂志。
阅览室是间奶油色小屋,位于小树林中的一个平台上。我们推门而入,管理员老伯在打瞌睡,瞟一眼,认得是家属小娃,也懒得管。小北耐住性子,浏览四面八方的报纸。我主要看《阿尔巴尼亚画报》,这是唯一能远眺欧洲的一个小窗口,建筑、街道,还有皮肤惨白的人,都不见得漂亮,但色彩、风味是很不相同的。翻到海滩照片时,小北恰好凑过来,指着个圆滚滚女人赞叹道:“真他妈一身好肉啊!”
二
约莫四点,进来一拨打字员、话务员,阅览室一下热闹了起来,老伯的眼珠子都亮了。她们都很年轻,发如乌云,脸颊白皙,在满是灰衣、蓝衣的机关里,她们的衬衫是粉红、嫩黄或者雪白的,好不鲜丽。
休息时间,她们来扯闲聊,阅览只是个幌子。
“小娃,让一下嘛。”她们要围拢坐,就冲我们挥挥手。我们不理睬,凭啥子。
她们相互看看,鄙夷地笑笑,勉强坐了。
“小娃,几岁了?”我们不答话。几岁?问得好笑。
“是家属娃娃哇?”也不应她,那是自然的。
“咋不上学呢?”又是废话了,你没当过学生啊?
她们的头发、脖子散发出很重的味道,像新剥开的柑橘,好闻,又略有点冲鼻子,这让我不能专注看画报。瞟了下小北,他正愣愣的,眼睛落在一个女子的身上。就是她,一直在问我们,也像是个为首的,比其她人高些,也丰满多了,鼻梁挺拔,左唇上一颗美人痣。《红楼梦》里说艳压群芳,指的就是这种女人吧。
却有个女人在望着另一处发神。
她瘦极了,瘦棱棱的,头发散散披在肩上,手里抱了个果酱瓶做的茶杯。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啥也没有,只是两墙之间的犄角。
后来,她们都推门走了。
我和小北也走了出去。
但,那瘦女子还坐在门外台阶上,慢慢喝水。她的脚边,是一棵紫薇,即俗称的痒痒树。我觉得好奇,就去抠光滑的树干,看树梢的花摇不摇,其实是利用转身之际,多看她一眼。
她被打扰了,盯了盯我,又望望树梢,但没有说话。她脸窄,鼻子细长,身子似乎还没发育够,眼神却已像活了很多年。颈子那儿,锁骨很是尖锐,顺着领口,还能隐约看见两只小乳房:乳沟中,藏了一颗痣,大如胡豆,黑亮亮的。
我心头咚一跳!正好,小北的手把我一拉。
“你脑壳发昏了?”他说。
“昏……昏个×。”我难得冒了句粗话。
“嘿嘿,你会觉得她漂亮?”他追问一句。
“……”漂亮,不好说。丑吗?好像也不是。
“用书法打个比方,她像瘦金体。”
瘦金体,我不懂,也没听说过。她乳沟中那颗痣,倒是黑得像一滴黑金。
三
大院里蝉多,傍晚前叫得最欢了,有如下暴雨。小北和我把面粉揉成小团子,拿到水龙头下不停地冲洗,炼成面筋,戳在竹竿上,就可以粘蝉了。
粘蝉很考眼力和耐心,这两样我们都不缺,总能收获十几二十只。我粘的,都给了小北,他拿回家喂鸡。他养了一只金色大公鸡,早晨叫得像军号,走路也橐橐有声,俗称九斤黄。
我汗湿透了,就撇了小北,先从5号小楼背后抄近路,去澡房冲身子。
5号小楼是两层的西洋式建筑,却又带中式坡屋顶,据说从前是一个军阀的公馆,黑砖墙上,勾出了均匀的白砖缝,我看着像医院。背后那条小路,夹在墙和灌木丛之间,湿答答的,常有人从楼上把茶水泼下来。我匆匆穿过,忽然又转了回去。
打字机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一扇窗户内,正坐着那个瘦小的女子,在操作一台老式的中文打字机。天气恶热,她穿了件肥大的短袖汗衫,更显瘦骨嶙峋了。但,散发用手帕束成了马尾,双唇紧抿,嘴角深陷,出奇的坚定。打字机十分笨重,而她灵巧地掌握着机头,在铅字盘上转动着,按下打字键的一刹那,很像是扣动狙击步枪的扳机。
蝉声焦灼,热浪一阵阵的,她却孤立于这一切之外,专注、专心,啪!啪!啪!把找准的字钉,一个个揪起来,以千钧之力,敲在滚筒的蜡纸上。
我傻乎乎地,站在窗外,看了她好久。
四
星期天,小北去了外公家,接受书法训导,并吃顿很有油水的午饭。我闲得无聊,就把已读完的《红楼梦》又翻了翻,最终还是骑了父亲的自行车,从大门进机关去逛逛。
自行车叫公车,是行政处发给干部的杂牌货,呆头呆脑、粗蛮、丑,座墩也很高,我用脚尖才能把踏板踩到底。但好处也有的,不怕摔,摔不烂。大门的值班室坐着大爷,还站了个别手枪的卫兵,一看是公车,也懒得拦,随便进。
大院的星期天,静出了荒凉。人迹是没有的,阅览室关闭了,就连猪儿也一直在昏睡,哼哼都免了。我溜达一圈,经過5号小楼,龙头一拐,就穿进背后的小路了。晓得星期天不办公,还是没忍住……每次后半夜醒来,我似乎都能听见打字机的啪啪声,遥远、悦耳,像梦的一部分。
粗蛮的公车把小路塞满了,灌木扫着轮子、护履板、我的小腿,又痒又痛……却又很舒服。经过那扇窗户时,明知没人,我仍然朝里边多看了一眼。
她正站在窗口看着我。
我差点摔下车!赶紧用力一蹬,夺路就逃了。
“喂,小娃!”她在后边喊。我把刹车猛一拧,双脚叉在了地上。
她把头探出窗户,向我招了招手。“进来一下,”她手臂伸出老长,划了一个弧,“你从那边走……”门洞在那边,这个我晓得。
小楼里阴森森的,两条走廊里,关门闭户。只有打字室还开着,一块光亮投在发暗的红漆地板上。进了屋子,我发现还有个男人,坐在打字机对面。是个中年干部,国字脸,白衬衣口袋塞着红色工作证,硬绷绷的。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不认识他,但这种人,在家属区我见多了,只是他还多了点不知哪来的自得。
吊扇转着,热浪一波一波的。
她今天也穿着白衬衣,扎进蓝色长裙里,还有一条很宽的皮带,把腰束成了一小把,像小说上所写的,盈盈一握。但,她比我想象的高许多,高了我一个头,我目光恰好落在她胸前。她胸脯几乎是平的,但也坚定地翘起了两个小乳峰;乳沟里,藏着一颗黑金似的痣,我见过。
“你帮我去送一封信,南站,找得到吗?小娃。”
我讨厌被人叫做小娃,但还是……忍了。她的声音不大,但清脆,好听,很不像从她嘴里发出的。
她退回桌前,拉开抽屉,抓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喜欢吗?”
“不喜欢,”我说。甜东西,我都不喜欢吃。
“那你喜欢吃啥呢?二天我请你。”
“我要想一下。”
“好吧。”她再拉了拉抽屉,拉到尽头,掏出信放在桌子上。不是一封,是很厚的一摞,牛皮纸信封,每封都撕开了口子,中间又用麻绳仔细捆好了,成了一块结实的砖。我刚看清收信人名叫“史小玺”,她突然把信收回去,装进一个更大、更厚的牛皮纸档案袋,并在封口打了三枚订书钉。这袋子下边印了一行红色加宽的宋体字,是单位的名称。她拿钢笔把单位拦腰连划了两下,随后写了三个大字:马援收。
她的字,像火柴棍拼成的,差得让人难过。
“你去过南站吗?有点远。”
我点点头。其实没去过,但方向是晓得的。
“到了南站,你问马援就可以了。”
“他很有名吗?”
她没回答,嘴角浮起一丝笑,像嘲笑……但也未必是。
“可是,今天是星期天啊。”
“他休息星期二。”
“我该跟他怎么说?”我把档案袋接过来。
她略略犹豫。“啥都不必说,你送信就是了。”
我纠正道:“是退信。”
她脸红了一下。她脸本是苍白的,而且很光滑,这一红,如灯笼嚓地一下,从里边点亮了,很好看。
“如果他给你回信,收不收?”
“这个……”她犹豫着,突然,打字机对面的男人厉声问:“你父亲是哪个部委的?”我差点把他给忘了。
但我没有搭理他,依然望着史小玺。我喜欢看她犹豫不决,有点为难,不知所措的样子。
那个男人生气了。“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他嗓音不算高,但已经十分不耐烦。
我把脸转过去,对着他的脸。“你是哪一个?我认不到。”
要是他发作,我就回敬他:“你算老几啊!”这是小北惯用的口气,我今天就要学学他。
他的确是被激怒了,脸气得铁青,手拧成了拳头。估计拳头里还攥满了汗水。我没害怕,就站在那儿,等着他。然而,不晓得为啥子,他居然克制了,把头扭向了窗外。
她呢,叹口气,拿手在我头上拍了下。这一拍,把我和她的距离拍近了,也拍远了,我懂的。
“去吧,”她轻轻推了推我。“想好最喜欢吃啥子,二天我请你。”
我出了门,在走廊的阴影里站了会儿。
听到她的脚步也走到了门口。她对他说,“你该放心了嘛。”
门“嘭”地一响关上了。
五
本城有三座火车站。北站是客运站,紧挨市区,闹热得很。我从这儿乘车随母亲去过广元县,天没亮进的站,已是人山人海了。
东站是货运站,小北去过,他说,乌烟瘴气、灰尘满天,去一趟,这辈子不想第二趟。
南站是做啥的,我一直没搞清。北站往南,是全城最长的一条公交线,跑16路公交车,穿过漫漫的城区,抵达南站。小北的小姨就在16路公交车做售票员,他曾陪小姨上班,去过南站。
我问他南站啥样子?
他说,“跟北站比,太他妈不同了。”
“咋个不同呢?”
“反正,你去过一趟,这辈子都忘不了。”
這太吊胃口了。我约他啥时一起去看看,他说要得嘛。但东耽搁、西耽搁,一直没成行。
这一回,我算是给自己找了个机会。
把档案袋夹在自行车后座上,我脚下猛蹬,一头闯出了机关的大门,把值班大爷和卫兵都看傻了。
北站、南站之间的大街,也是本城的中轴线,分为三段:人民北路、人民中路、人民南路。中路又叫后子门,位于明代蜀藩王府故址的后边;前边约一公里,曾伫立一堵巨大的红色照壁,后来照壁拆掉了,地名还保留了下来。
我骑过后子门、红照壁,算是出了城市的腹心,人和车都少了。不过,街道依然很宽广,种满桉树的绿化带隔开了快、慢车道,街沿上则是枝蔓铺展的梧桐,梧桐后一间间挨着小平房。临近南河,即古时候的护城河,突然闪出一座庞大的建筑物,苏联式风格,带着广场和巨大的廊柱,名为东方红大礼堂。旁边还有一座灰褐色、积木般的大宾馆,临街的庭院鲜花盛开。
这礼堂、宾馆、河上的桥,被画成简陋的线描,印在两分钱的火柴盒上,我早就看得想吐了。
过了桥,再骑过医学院门前,一环路即已在望了。路那边,建筑物已很稀疏了,且简陋、矮小,间杂了些小块的菜畦。然而,一座塔拔地而起,把人的视线一下子引向了高空!很高,比机关大院的水塔高出几十、一百倍吧。这是跳伞塔,用来训练伞兵,或者跳伞运动员。我和小北曾骑车来看跳伞,看了半天,肚子都饿瘪了,也没见半个人影子跳下来,扫兴而回。
跳伞塔,也是我骑车抵达的最南边。
我再次把车骑过去。跳伞塔在一圈低矮的围墙内,墙内的坝子很冷清。塔,就更冷了。
墙外有一个凉水摊,摆着四只玻璃杯,两杯橙红色,两杯是白水。卖凉水的是个七八岁的女娃儿,脸圆圆的,头发汗湿了,黏在宽大的额头上,手里还握了把芭蕉扇。我伸手去端白水,她指着橙色杯子对我说,“哥哥,你喝这个嘛,四分钱。”她的表情很诚恳、很期待,我心头酸了下。
我默默喝完带点糖精味的白水,摸了五分钱放在小桌上,冲她笑了笑:“不找了。”她忍了忍,没忍住,嘻嘻地笑了,张开缺了颗门牙的小嘴巴。
我问她,“南站还有好远呢?”
她说,“还有好远好远哦,我也没去过。”
六
我又骑了很久,绿化带、行道树消失了,街道逐渐变成了公路,两边是绵延的村野,小片的水稻、苞谷地,大面积的是油绿的蔬菜田。
回头,早不见跳伞塔的身影了,而路还望不到尽头。偶尔一台解放牌大货车驶过,卷起滚滚的灰尘和热浪。
太阳把柏油路面烤软了,我也快蔫了,自行车碾上去很有些吃力。不过,田野的开阔还是让人愉快的。一条灌溉渠穿过路下的隧洞,水绿得发黑,人一到这儿,凉气嗖地卷上来,舒服得发抖。
渠边一棵栗树下,坐了个戴草帽、拿竹竿的男人,在用鸡肠子钓螃蟹。
我就学了小北的口气冲他喊:“老把子!你安逸哦!”
他也不生气,还向我招了招手。
这时候,背后传来三轮车的咵咵声,我靠边让了让。但肩膀还是被人一拍,叫道:“嘿!”
居然是喂猪的冯二哥。
他赤着上身,油光光的,脖子上挂了条毛巾,不时揩把汗。三轮车里站一只绵羊、一只山羊。绵羊已经晒得萎靡了,山羊却目光炯炯,十分桀骜和愤慨。二羊之间,还塞了一只锣、一只大鼓,三根缠了红绸的木槌。
我问冯二哥,咋不上班呢?
他说,请了假的。明天他大哥结婚,要请生产队的乡亲们吃个羊肉宴。先去行政处借了锣鼓,又去双流的黄佛镇买了羊子。鸡鸭家里是有的,菜嘛满地是,要好多自己摘。
我说那咋个吃法呢?
晒场上架两口大锅,锅还是公社食堂关门扔下的。羊肉砍成大坨,一口锅红烧、一口锅清炖,其他菜算小菜。酒嘛要管够,几坛子苞谷酒、苕干酒,去年我爸就已经备好了,60度以上,保证喝得你栽跟头。
我说,好热哦,不怕热啊?
“怕啥子呢,以火攻火嘛。一两个月都没有沾荤了,妈的个×,肠子都痨惨了!”冯二哥说罢,哈哈大笑。
冯二哥平时在机关大院里,寡言寡语的,没想到他吹壳子还这么得行。
我也嘿嘿笑了,又问,喝酒吃肉还敲锣打鼓啊,又不是梁山泊。
“梁山泊算啥子。我们先把地主、富农弄起来批斗几分钟,再欢天喜地跳几分钟丰收舞,然后就——敞开肚皮整!”
那,地主富农吃不吃喝呢?
“这个不能说……”随后他环顾一圈,挤眼道,“都是本村本姓的,啥子阶级敌人哦,当然要吃嘛……悄悄吃。”说罢,又哈哈笑。我也跟着笑,好像我也是白捡了顿酒席的小地主。
你嫂子漂不漂亮呢?
他瞪了我一眼。
我赶紧声明,不说就算了。
他还是说了。“公社一枝花,铁姑娘队的队长。”
我一听“铁姑娘”,忽然想到了孙二娘,想笑,但不敢,就做出频频点头的样子。
前边有条黄泥巴岔路,插入田野中。冯二哥龙头一转,拐了上去。
“明天有空,你跟小北一起来耍嘛。”他指了指远远的一片竹林盘。“六队,姓冯,一问都晓得的,前头有家水碾房。”
我说,要得、要得。
三轮车碾上了半块砖,嘭地跳了下。锣鼓发出波波的声音,绵羊、山羊也叫了起来:
“咩……咩……”
“咩!咩!咩!”
七
和冯二哥分手后,一朵浮云飘来,把太阳遮住了。天色渐暗,还滚过一阵阵雷声,像要下暴雨。然而,雨没有下,风也没有吹,更热了,闷在蒸汽笼子里的热,蒸出黏腻腻的汗,五内焦躁。我麻木地蹬着车,怀疑永远都骑不到南站了。
公路边立了根站牌,我刹了车细看,上边好长一串站名,密密麻麻,数到最末,倒的确是火车南站。离这儿,还有一站路。
我吐口氣,伸舌头舔了舔淌到嘴角的汗水,咸死了。
顺公路向前看,大地潮水般延伸,地平线灰蒙蒙地展开,很像宽银幕电影中辽阔的画面。我看过的唯一宽银幕电影,是朝鲜的《卖花姑娘》。故事我忘了一半,但里边的歌声还记得,这会儿在脑子里响起来,混沌、迷茫、听不懂,但又深情和忧伤,很像此时此景的配乐。
再骑一会儿,地平线上冒出了一座孤零零的屋顶。
屋顶渐渐升起来,让四周田野显得十分的荒寂。屋子是深绿色的,但也很难说,天空灰暗,它也很像是灰色的,灰中掺了些灰心丧气的蓝。
八
南站是一幢小楼,在旷野中,看起比实际还要小。前边是一块小广场,落满了灰尘。右边有家小小的火柴厂、一家小旅馆,挂了两条横幅: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我心头一喜,最后用力一蹬,前边突然现出半块烂砖头,赶紧转龙头,前轮避开了,后轮却碾了上去,“嘭”地一跳,我摔下车,还滚了滚,一身灰,左边膝盖还破了皮,有血流出来。我索性坐在地上,且歇歇气。
刚好一个穿蓝工装的少妇经过,手上拎着盖了报纸的铁皮桶,低头喝一声:“小娃,跑到这儿来耍啥子?!”伸手一抓,就把我提了起来。她袖子挽得老高,浓眉大眼,皮肤被风吹黑了,黑里透红,亮亮堂堂。
我还没说话,她又从地上捡起档案袋,捏了捏,掂了掂。“‘马——援——收。是钱吗?好厚。要雇马援杀人呢,还是放火呢?”
我先是一惊,继而大为好奇。“他杀过几个人?”
少妇哈哈大笑。“几个人?他差点要了我的命。”说罢,也不还我档案袋,径直朝楼里走。我赶紧推了车跟在她屁股后边撵。
候车厅里只坐了几个带箩筐、抱着扁担的农民,冷清得像一座掏空的谷仓。
她带我走进角落的值班室,里边有个红鼻小老头,抱着印了火车头的搪瓷大茶缸,在哼样板戏。她叫声:“喂!”我以为他就是马援。然而她又叫:“马援呢?”小老头朝后边指了指。
值班室是个穿堂,我们穿出去,是一条走廊,又左拐右拐穿了几间屋子,就到了车站的另一边。是个很高、很宽大的平台,望出去,天地迷蒙,铁轨就在脚下,枕木之间铺满碎石,又冒出一簇簇荒草。稍远,停着一长列闷罐车。
铁轨很远之处,有个人影子在摇摆着。“马援在查路,快了。”少妇说罢,又指了指我推着的公车,喝道:“站客难打整,还不坐?这种破车子哪个偷。”
平台上有张桌子、两根独凳、一把长椅,一排带水槽的自来水龙头。墙根还码了堆劈柴,大小均匀,排列整齐,上边扔着一双溅了泥浆的雨靴。我刚坐下,少妇又喝道:“看你一身的灰,先去洗了嘛。热死了。”说着,拿指尖拈着衣服不住地扇风。“还是你们小娃好,短袖子、短裤子。这身工作服烦死了……幸好我里头啥子都没穿。信不信?”我脸一红,她哈哈大笑。我想到的,却是史小玺身上的痣。
少妇递给我一条毛巾,要我好生洗,不要怕洗脱一层皮。又把桶提上去,扒开旧报纸,是四根雪白的猪蹄,且是前蹄,肥胖、有弹性。她拿了把小锯片,在蹄趾之间耐心刮,又用水仔细冲,还随口跟我说:“喜不喜欢吃猪蹄?”
“喜欢啊,”我老实回答。
“喜欢清炖还是红烧呢?还有,卤起吃咋个样?晚上把锅儿放满水,端到蜂窝煤炉子上烧开,封了炉门,只留一个火眼眼,一直炖到天亮,你说有好耙和?啧啧。”
我嘴里清口水都包满了,说不出话来。她又款款而道:“你不晓得买个猪蹄子有好难。又要凭肉票,又要排长队,排拢了恐怕也卖完了……幸亏,我舅舅是肉铺子的刀儿匠,这个后门嘛,还是可以走一盘的。”
我叹口气,由衷赞叹。“你好得行哦,吃得下四根猪蹄子。”
她也叹口气,笑道:“啥子得行,我才不吃呢,炖给马援吃的。”
这个我没想到。“哦,你们是……”
“不要想歪了,他可怜……我可怜他。”
“他咋个可怜了?”
她还没回答,马援已经走到台子下边了。
他把一盏灯、一把镐先放上台子,然后朝少妇伸手“喂”了声。
少妇走过去,一抓,就把他提了上来。
九
马援满头卷发,架了一副大眼镜,跟我想象的,很是不一样。他似乎应该再强壮些、再矮一点,年龄也应该再大几岁。然而偏偏不。
他跟我握了手,诚恳道,“辛苦你跑一趟,小伙子。”他手指细长,老茧却不少,钉得我好痛,但我心头是高兴的,居然不叫我小娃。
少妇变戏法似的,端出一只大搪瓷缸、一只竹壳开水瓶,上边也都印了红色火车头。“喝茶、喝茶,看你出了好多汗。”
“谢谢师傅。”马援笑笑。
“我不是你师傅。”
“谢谢宋师傅。”
马援把茶缸揭开,飘出一股茉莉花味道。我突然觉得嗓子在冒烟,嗫嚅道,“我也想喝茶。”马援把杯子推给我,我喝了一大口,水温正好,满嘴清香,好舒服。“谢谢宋师傅,”我说。
宋师傅瞪了我一眼,把杯子推回给马援。
马援突然看到了我的膝盖,冲宋师傅叫起来:“快去把紫药水拿来!”宋师傅气哼哼地,进屋端出一只赤脚医生用的小箱箱,先拿酒精替我消了毒,再拿紫药水细涂了一遍。
马援把脸转过去,看着那一列百年不动的闷罐车。
“好了,”宋师傅说。“谢谢马哥,”我说。“你谢他啥子?”宋师傅哼了哼,揪住马援的耳朵,把他强扭了回来。“这个小娃说,要雇你去杀人?敢不敢?”
马援呵呵笑。“笑!你不怕见了血要晕头啊?”她轻声呸了一口。
那个档案袋就搁在桌子上。
马援脱了工装,里边是圆领白汗衫,胸前仍然印着红色火车头,背上湿了一大块。他在水龙头前擦了脸、胳臂,用肥皂仔细洗了手,擦干了,坐到桌前,把档案袋拿在手里,掂了掂。“好重哦,像块砖。对不对?”他问我。
“比砖重。”我说。
“是钱就好了,你天天吃猪蹄子都吃不完。”宋师傅假咳了几声。
马援把那捆信取出来,嘘了一口气。宋师傅又呸了一小口。我则夸张地笑了笑,哈哈!随后,全都安静了。
远处,响起一声汽笛声,在昏暗、浊热的空气中散开了。
他用指尖拈住细麻绳,耐心把它解开,一封信、一封信在手里过了遍,如故人重逢,掂一掂,是重了,还是轻了呢?表情专注,也像在走神,是很有所思的样子。但并没有把信抽出来,最后又把它们重叠好,在桌上齐了齐,依旧用麻绳捆成一块砖,塞进了档案袋。
我也趁机把他的字细看一番,不像是他写的,相当有力道,而又很秀丽,恐怕不比小北的外公差。
“马哥,你喜欢史小玺是不是?”
他很大方地点点头。
我就指着档案袋上的“马援收”三字,恶意地笑了笑。“字好丑。”
他脸一下烧红了,好像这是他的错。“女娃儿的字,不都这样嘛,”嗫嗫嚅嚅,理不直、气不壮。
宋师傅仰天大笑,仿佛响了串惊雷。
雷声在天边滚过,终于吹起了小风,有了一丝吝啬的凉意。但雨水还是没有落下来。
十
“小玺咋会找你送信呢?”马援颇有些不解。
“她信任我嘛。”
“信任……你们很熟吗?”
“是啊,她妹妹是我的同桌。”这个答案,我想好一阵了。
“可是……你念几年级?”
“开学念初一。”
“她就一个妹妹,比你大得多啊。”
“是堂妹。”
“堂妹,啥子名字啊?”
“史湘云。”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想笑了。
“哦,”马援先笑了。“这名字取得巧。她家的亲戚朋友,也都算书香人家啊。”
宋师傅干咳两声,冲他道:“封、资、修的毒,你中得太深了……吃的亏还少了?”
马援苦笑,摇摇头,喝了一大口茶。我把茶缸拖过去,也喝了一大口。宋師傅撇嘴说,“算啥子本事呢,男子汉拿茶出气!”说罢,端起来也是一大口。
马援突然脸一沉,拍桌道:“茶母子都喝干了,还不掺?!瓜婆娘。”
我吃了一惊。但宋师傅没吭声,提起竹壳开水瓶,把茶缸掺满了水,还冲我偷偷一笑。
妈的,女人真不可理喻。
我问马援,“马哥跟史小玺该是同学吧?”
他捋了捋卷发,表情又有点走神。“算是同学,但不同年级,我是1968届高中生,她是1966届初中生,比我小一个年级。但她妈妈是我的语文老师,常把我的作文拿回家让她读。后来,老师常邀请我去她家耍,给小玺辅导写作文。”
“我懂了。”
“懂了啥子?”
“才子佳人嘛。”
“她算佳人吗?比你的史湘云如何?”他来了兴趣,很当真。
我嘿嘿假笑,做出一副老练的样子。“她们嘛,完全是两种人。”
他伸手指着我,诚恳点点头。“说对了,小伙子,小玺的心思重,说话留一半,让你自己想,嘿嘿。不过嘛,她眼光高,又很准,看文章是没人能跟比她的……真的。”
宋师傅把茶缸朝他一推。“喝口茶。看你激动得,话都抖不伸展了。”说罢,提起一桶猪蹄进了屋里。
马援松了一口气。我略有点失望,还扭头朝屋里看了看,已是人影子都没了。
他问我,“你读过《红楼梦》?”
我说没读过,我哪读得懂。
“史湘云跟贾母啥关系?”
我说她是她的侄孙女。
“你还没看过!”
我说只胡乱翻过几下,不算。
“你作文写得咋样呢?”
老师和小北都夸我作文还可以,但我忍了忍,只说一般化。
“作文写好了,是很好耍的一件事。你要好生写。”
我自然是点头。
“那,你念的哪所中学呢?”
我说还不晓得嘛。初一只是戴帽子,还是在长发街小学混。
他也点点头。“原来是长小的,我去過,只半个巴掌大。是有点受委屈了。”
我暗骂了声:妈的!就问他读哪儿呢?
“一中,就在东马棚,离长发街很近的。小玺的家,住西马棚,是个独立的小院,有口井,一棵石榴树。她是独女,父亲比她年长四十几岁,已是个老人。而她妈妈还年轻,也是一中最漂亮的女老师。”
我就请教他,女人漂亮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不好说,譬如红楼十二钗,就是十二种很不相同的漂亮。”
那,史小玺漂亮吗?
“她啊,”马援顿了顿,很慎重地回答:“已经超出漂亮二字了。她是有味道,吸引人。”
我叹口气,若有所悟,但依然迷茫。
“不急,小伙子,你耍过一回朋友就晓得了。”马援笑笑,又把话题扯回小玺家的小院子。“那棵石榴树估计也是年过半百了,就歪在井口上,开了花,结了果,裂出一条大嘴巴,也没人摘。我去了,小玺就让我摘了吃,其实我也不喜欢。石榴米水灵、好看,但是不中吃,没肉头,干脆连核一起嚼,就成了一把渣。倒是有一回,她把西瓜裹在床单里,放到井里泡了一下午,吃起又清凉又酣畅!”说着,他咂了咂嘴巴。
那,小玺咋个评价你的作文呢?
“我有篇作文,专写一棵老槐树,用了八千字。老师打了90分,小玺说,应该打120分。老师问,为啥呢?小玺说,100分是最高的标准,而这篇作文已经超出标准了。”
我哈哈笑,略带嘲讽说,就像小玺已经超出漂亮了。
马援却坦然接受了。“是啊、是啊……小玺是很有眼光的。”
我有点不服气,就问他,八千字写一棵树,不会废话太多么?
“咋会呢。它有好多树叶对不对,你细看过没有,每片树叶都不是一样的。何况,还要开花、落叶,蜂子来采花粉,麻雀来搭窝。蚂蚁钻进树洞,挖个舒服的蚁穴,子孙繁衍,好多的故事。有一天,雷电劈下来,把半个树烧焦了。再有一天,它被斧头放倒了,锯子把树干切成一段、一段……头一回,我看到了年轮,闻到树液的味道。”他顿了顿,问我,“你闻到过没有?”
我想不起来了。就问他,很香吗?
他摇摇头。“不是香,是冲鼻子,想落眼。”
那,老师给你打120分没有呢?
“没有。但老师给我做了道菜作奖励,凉拌姜汁肚丝。是她外婆传下的厨艺,任何馆子都做不出来的。小玺说:吃了这盘肚丝,你二天要为我写一部小说。”
小玺想让你当作家?
“是啊。她呢,说自己成绩不够好,医学院考不上,当护士还是可以的,手脚利索,心肠硬,一针扎下去不会皱眉头……这个女娃子。”
我想起她打字的神情,冷漠而坚决,不由叹口气。
他也叹了一口气。“说这些,都很没意思了。我高中没毕业,高考就取消了,下农村当知青。她妈妈托了从前的学生,把她弄进了机关。”
我老气横秋地点点头,以示:我懂。
“我们还通过一阵信。我写些插秧,打谷子,赶场卖红苕,偷农民的鸡鸭,房东媳妇偷人家的汉子……她都喜欢看,也回信,但都写不满半页……言简意赅,我也是喜欢的。后来,她不再回信了。我懂,也就不写了。”
你回城好久了呢?
“刚好两个月。回来后,我没忍住,还是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我在南站上班了,打杂,啥子活路都干一点,没有技术性,但也不算苦,比乡下好多了。”
她也没回信?
“回了几行字,大意是,我们从前写的信,各自烧了吧。”
你肯定没有烧。
“我肯定不会烧。但……没想到,她也没有烧。”
他说罢,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我好容易想到一句话,可以打破这哑然,正要说,宋师傅端了个铝锅大步走出来,在桌子上一顿!
我心头一喜,猪蹄子炖好了?锅盖揭了,冒出一股股蒸汽。蒸汽散尽,露出半锅煮熟的苞谷。
这时候,一列客车慢吞吞靠了站,又慢吞吞开走了。“是去昆明的。你去过昆明吗?”马援说。我摇摇头。“火车要穿过大凉山,我就是在那儿插的队。”他又咕噜了一句。
十一
苞谷还连着壳。把壳剥开来,是一束嫩红的长须,把长须撕下来,这才是苞谷棒。苞谷籽十分饱满,乳白、浅黄,虽没石榴米娇艳,然而很可口,拿牙一咬,苞谷浆就溅在口中,十分清甜。
我啃完了一根,伸手再拿,宋师傅把我的手抓住了。“他今晚值夜班,要填肚皮。你差不多合适了,嘎?”
我略微尴尬,好在还没脸红,就瞟了眼马援。
马援很专注地啃着,一粒也不漏网。他说,“我没得事,让小伙子多啃两根嘛,那么远的路。”
我离开的时候,马援再次跟我握了手。“二天空了,又来找我耍。”
宋师傅也假笑了两声,还在我头上拍了拍。“运气好,猪蹄子管够。”
天色已经昏沉沉的,雷声隐隐,但不吹风、不落雨。我骑到那条水渠边时,一身又已汗湿了。就架了车,走到钓螃蟹人坐过的板栗树下。地上,留着堆烟屁股,一个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纸烟盒。
我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光溜溜钻进了渠水中。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