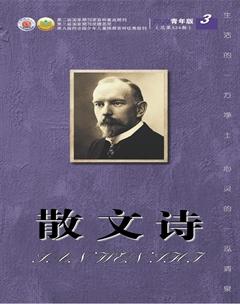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外三篇)

严彬,1981年生,湖南浏阳人。出版诗集《我不因拥有玫瑰而感到抱歉》《国王的湖》《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大师的葬礼》、小说集《宇宙公主打来电话》。参加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硕士。以诗歌《在家乡》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
《浏阳河》是中国名曲,大家都知道的。人们可能不知道有个浏阳市,但想必绝大多数成年的中国人知道浏阳河,奥地利那些素质颇高的市民也许也有人知道——因为中国最优秀的民歌演唱家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这首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也说不定。而作为就出生在浏阳河边上、在浏阳河边打滚、直到上大学才离开的浏阳人,我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在家门口听哪个唱过这首歌,小孩子没怎么见人唱过,我妈妈和我姑姑也没听她们唱过,没听满姐姐和春姑姑唱过,甚至那位最爱唱歌的红姨,我怎么也没听她唱过这首歌?但我记得,我爸爸倒是唱过几回。他一边用浏阳普通话唱着歌儿,一边拉着二胡,我听过。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以前我常常在电视上听这首歌,现在想起来,我好像就是在电视里学会了这首歌的:
浏阳河(念ho,二声),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嘞?
出了个什么人,领导我们大解放,哎噫哎噫子哟……
这也许是我的错觉。那时我们小学和中学每周各有两节音乐课,课名就叫做“唱歌课”。不像现在的孩子,人人都要学两门乐器,那时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大多除了口哨,几乎什么乐器也不会,民乐是有的,二胡,大鼓小鼓,镲,喇叭,这几样最常见,笛子、古筝等等那些则都没有。我记得小学时有过两位音乐老师,一个是彭老师,我们的校长,他会弹风琴——一种样子和声音都类似钢琴、但远没有钢琴声音丰富而动听的踏板琴,上课时他便一边坐在那里弹着风琴,一边教我们唱歌,教的歌我现在没有一首能记得起来的,这是实话。而另外一位音乐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名字我忘记了,教我们唱一些儿童歌曲,有“竹子开花——哕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星星多美丽,我们没有忘记你;高高的月儿天上挂……”,还有“池塘边,柳树下,有只迷路的小花鸭。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哭着找妈妈”, 还会“多——来——米——法——嗦——拉——细——多——”,教我们唱简谱。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唱歌课,算是音乐启蒙。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音乐方面的启蒙,便是乡下逢年过节,或者谁家办了什么事情,许愿还愿,要唱一两场戏。常见的有影子戏和花鼓戏。影子戏也就是皮影戏,是在室内演出的,搭个小小的特制的棚子,两张旧式双人床大小,乐手、唱戏的、皮影、工具箱,甚至天冷了还有火缸……都在里面摆着,乡村艺术家掌控着提线木偶般的皮影人,吹拉弹唱,一曲好戏上演;阔气一些的人家,或者事情大一些的,就唱花鼓戏。皮影戏里唱的什么,我们小孩子通常搞不大清楚,而那花鼓戏呢,咿咿呀呀之中,我们也听熟了大人们唱的那几首名曲:
什么《补锅》;什么《刘海砍樵》。
看戏当然要比在学校上唱歌课有趣多了,因为人多,热闹,到处都是花花绿绿好玩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到了那时候,大人们带我们去看戏,或者我们跟大人讲要去看戏,总能要到一两毛、三五毛钱,那样我们就可以去戏场上买东西吃。要知道,在乡下,至少在湖南浏阳镇头的乡下,在我们那些沿河的集镇和村落里,一年到頭,除了逢年过节红H喜事不说,就属赶集和唱戏两样最热闹的事情。还是那几样:人多,有各种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卖,有唱戏的,有玩杂耍的——也就是在这两个时候,大人们也愿意放自家孩子出门去玩。我爷爷很喜欢看戏,而我爸爸喜欢拉二胡,他们都偶尔会哼几句戏曲,以前我不爱听,总觉得就像那课文里鲁迅先生形容那鲁镇的大戏,“咿咿呀呀”,那台上的人啊总唱个没完,还挺吵,老生上场了,还要搬个凳子坐在那里唱上半天。但我听得多了,也学会了他们唱得最多的几段,其中就有我上面提到的两段花鼓戏,《补锅》和《刘海砍樵》。
我爷爷喜欢看戏,他就常常带着我和我弟弟到处去看戏。看戏,看的是草台班子在乡下唱的花鼓戏。花鼓戏有词有句,用长沙方言唱出一个个曲折的故事,或凄婉,或荒诞可笑,或惊心动魄,总之没有一个是平淡的。从前是自己或当地人搭台,如今富裕的村子多半已经建好了自己专门唱戏的戏台。看戏也不分远近。比如我们镇头镇,据说方圆有一百多平方公里,下面有好多个乡,乡下面还有村,村的下面还有生产队(组)。这是从前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划分,也是泱泱农业大国大多数人赖以生息的生活场景。镇头镇五乡十村,远到麻田、南门坝,近到涧口本村,临近的田坪、小河桥、西满、莲花、烟山,没有哪儿唱戏我爷爷没有去过的。有一回在烟山上头一处供奉了某个老爷(神仙)的山上大庙唱花鼓戏,我爷爷带着我去,来回足足走了三四个钟头,清早吃完早饭便动身出门,全靠两脚走路——我爷爷不会骑车,白行车和摩托车都不会;他也不搭路上的顺风车,就偏爱走路——清早出发,九点多钟才走到。快到了,远远便见那山顶修了老爷庙的山上爆竹声声,锣鼓喧天,已经开锣唱起来了。
我就是那样,跟着也学会了唱两段花鼓戏。因此我在本省上大学,零五年后来北京工作,每到同学、同事聚会,起劲了,欢快起来,他们也会让我唱几句花鼓戏。我胆子也慢慢大了,不管他们会不会,就扯着嗓子,男声女声一并自己唱了起来:
手拉风箱,呼呼的响,
火炉烧得红旺旺。
女婿来补锅,瞒了丈母娘。
操作要留意呀,当心手烧伤。
双手烧伤不要紧,怕只怕呀(怕什么——)
说不服我妈妈娘,小聪我的同志哥。
那种感觉,其实也和在北京的外地人们——安徽人唱黄梅戏、广东人唱越剧——差不多吧,大家都是聚在一起添个即兴节目,尤其是喝了些酒,便更喜欢来几段各自的地方戏、地方小曲,图个一乐,顺道又让各自回味一下自己是哪里哪里人,不要忘记了那里有什么东西。我唱《刘海砍樵》,大家都开心,很多人还能跟着学两句,因为里头那“哥呀——妻呀——夫呀”,听起来热闹中又带着一点成人之间逗趣的风味。我不唱《浏阳河》,不是因为我不会唱,而第一是因为想不起来;再有,那歌音太高,是女声,一般就不太适合男人来唱。浏阳河有九道弯,很多人也都知道,因为歌里也是那样唱的。
浏阳河在镇头流过,我们那里便可以看到两道弯。一道是在小河桥、西满仓和镇头镇上的三地交界处,由一座浏阳河大桥相连——据说桥为文革年间所造,桥上曾刻着“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我爸爸和我爷爷都去修过那座桥。另外一道弯经过鸡首洲,被那河中央的小岛鸡首洲分作两岔流出,转一个八九十度的弯弯,过了鸡首洲,又合作一处流走。这样看来,浏阳河似乎也是由西往东流的。然而说实话,我记忆中对河的流向已经不大清楚了,总觉得似乎又是由东往西,由鸡首洲流到镇头大桥的。记性出了毛病,要等我下回回家自己去看看。我不去问我爸和我弟弟,小事情,免得被笑话。
其实我也很想好好去搜集一些湖南花鼓戏的唱腔和选段,一来可以打印下来带给我爸爸看,二来也是一种难得的文艺资料,说不定哪天成了精神遗产,还要供本地和外地的学者文人们去研究。我爸爸现在年纪也大了,已经六十二岁。去年某天,他还兴高采烈打电话过来和我说,家里当时来了十几个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一起拉二胡、打鼓,一起唱歌,唱什么都有,流行歌也唱,花鼓戏也少不了。在电话里我爸爸说得好不兴奋,把自己的心脏隐疾和未完全康复的病体似乎都忘了。我听了很高兴,还听到电话里果真传来人唱戏的声音,也有乐器的声响。我家从前楼上便放着几样乐器,有手风琴、小号,还有口琴。因为我爸从前在学校做老师时,也兼过音乐课,会弹一点风琴。但他毕竟没有教过我的课,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当时的水平如何,在课上又是怎样弹着乐器,唱的又是什么歌儿。
飞机掉在鸡首洲
在我刚刚记事不久,我爷爷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坐在房间里那张竹睡椅上跟我讲故事。最近的一个故事他说,一架飞机曾经在鸡首洲上空坠毁,碎片掉了一地,还有一些落到浏阳河里,沿着河流流到下游去了。我那时候年幼,当然不晓得去问飞机为什么会在鸡首洲坠毁,我还不会用“坠毁”这个词,我就说,那只飞机落下来的东西你有没有捡到。我爷爷就说,没有,卵都没有捡到一个。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卵”是污言秽语,但不是骂人的话。我又问我爷爷,飞机落下来的时候你见到没有。我爷爷哪里见到,他坐在自己的睡椅上面,用黄豆般粗细的香火点水烟抽,抽着抽着,他就睡着了,我也困了。
我爷爷不能将那落在鸡首洲的飞机实物拿给我看,以证明他说的不是胡话。可我后来很快就知道,真有一架飞机掉在河里了,落在鸡首洲了,我那上湾里住着的异姓伯伯家里就有一个飞机轮胎,很多人都说,那飞机轮胎就是落在鸡首洲坠毁的飞机上面的一个。
他家有飞机轮胎这件事情也是我爷爷告诉我的,但他没有带我去亲眼看。他领着我去伯伯家吃生日饭或是拜年时,他就和伯伯、伯母在伯伯家那一半红砖头一半泥砖的房子一楼坐着抽烟聊天,我则和伯伯家的孩子爬到有木楼梯连着的楼上去玩。那楼呢,不像我们现在一般家里的楼房,它没有窗户,一个人如若站起来几乎就能碰到上面盖了青瓦的屋顶,老鼠啊,土蛇啊,蜈蚣啊、千脚虫啊,各种虫子,就在这加盖了人造楼板的楼上跑来跑去,比人还欢腾。那楼当然一点也不洋气,是中国式的,一般是不能摆一张床住人的。它就是一个放杂物的地方,样子呢,倒有一点像外国楼房最顶层的阁楼,也很矮,高度是从屋脊处往屋檐倾斜而变得低矮。我熟悉这样的房子,因为那时我家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也是一层半高:一层是两间卧室、一间堂屋,后面有厨房、柴房、洗澡间,再往后面还有牛圈和猪圈,有厕所,厕所连着屋,却是建在外面,刮风的时候风从屁股上面遛过,免不了一阵冷清。我家是这样的房子,我伯伯家、叔叔家、叔公家……他们全都是这样的房子,只有一家年纪稍长一些的叔公家很早就有了全红砖盖的房子,房子前面栽着两棵大树,一棵是桂花树,一棵是柿子树。那位年长叔公呢,很早就在镇上的税务局上班,可能还是一个领导,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有好的工作,没有一个在家里作田种水稻的。这些我都熟悉,如果要我说,还可以说上很久,因为我记得从我家老屋到一里路以外吴猛进家每一家房子的样子和他们各自每间屋子里都是做什么的,我们躲猫猫会躲遍每一个角落,而有时候我们还做些别的。
在我那位上湾里住着的伯伯家老屋的二楼,我和他家的孩子一起坐在一个直径足足有一个小孩那么长的黑色橡胶轮胎上玩。很显然,当我看到那个巨型轮胎的第一眼起,我就相信那是一架飞机的轮胎。
我们在飞机轮胎边上趴着跳着,孩子中有一男两女,大一些的女孩和我是同班同学,还蛮要好,因为我们也是亲戚。她长得比我高大,年龄也比我要大一点,有时候还会帮我去教训欺负我的同班同学(我从不去惹高年级的同学,总是离那些个子高的人远远的)。她名叫淑玲,至于姓,我先不告诉你。淑玲好像是我们班上第三高的女同学,最高的是一位运动员,脸蛋白净而小巧,样子就像我们家里墙上挂着的明星海报中的关之琳,很好看——至于另外一位,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人的,只是不大记得了。在我看来,淑玲是一个很好的姐姐,她帮助我,有她在我周围我常常觉得很踏实。我们一起在轮胎边玩的时候,她也不会恶作剧,不像另外一位和我一般大小的弟弟那样,喜欢突然跳起来又坐回轮胎上面,把我们几个人都吓得弹落到地上。等我见到别人在浏阳河里游泳以后,也很希望暑假时能借伯伯家的飞机轮胎出来去河里洗冷水澡。那一定很好玩了。
可我爷爷和我爸爸妈妈都不让我和我弟弟去洗冷水澡。
他们都说,河里有水猴子,亲眼见过,水猴子喜欢拖着小孩子的腿往水底去,那样你们就没命啦!我听了当然害怕。我弟弟那時还小,他还不知道怕。可我怕归怕,已经偷偷跟着别人——还有我邻居一位叔叔——就在河边岸上一个大水塘里学会了打刨湫(音,浏阳镇头方言。一种最简单的游泳方法,样子类似狗爬式,但在水里一次游动的时间不如狗爬式的游法)和铩妹子(音,浏阳镇头方言,指潜水)。我偷偷出去洗冷水澡当然被家里人知道过,我妈妈就拿着杉树那带刺的枝条抽打我还光着的脚。那杉树条一般是我妈妈叫我弟弟去屋门口那棵杉树底下捡来的落到地上已经风干成金黄色或黄褐色的刺条,打在脚上很疼,还会有血点。我妈妈就那样打我,为的是让我长记性,不要小小年纪就去浏阳河里游泳,生怕掉到河里淹死了。
要说浏阳河,直到我上大学为止,那些年几乎是每年或每隔一两年,都会听到有孩子掉到河里淹死的消息。我们听了那死人的消息,心里害怕,但也说不上难过。一年一年那些据说附近淹死在浏阳河里的孩子们,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伙伴。我也没有想过他们是否碰到过水猴子,是不是被水猴子拖到河底下去了。
水猴子,就是他们心中的水鬼。
水鬼的故事
尽管我妈妈还有我爷爷每年都会用水猴子来警告和恐吓我们不要去河边玩水,但却没有人证明过水猴子真的存在。我的意思是,没有人拍着胸脯说他见过水猴子,我爷爷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可他们一年到头都会提起它,夏天怕你去浏阳河里洗冷水澡浸(淹)死了,秋天怕你在河边玩水滑到河里去,冬天怕你到结了冰的河面上去试着溜冰而冰破了你掉到水里,春天还怕你在河边离岸不远的李子树上摘李子吃,结果你一不小心掉下来滚到河里去了。
人是很脆弱的,乡里人不怎么讲科学,一个人病死了,可能到临死前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是得了什么病,死得糊里糊涂。可我们那里的人把命是看得很重的。人们为了好好活着,一生中不晓得做了多少事情。土地庙一年到头都有香火,有人病了就会去求老爷(方言,指的是土地神一类的本地神灵,有自己的小庙)保佑祛病消灾,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就有人去庙里老爷前面烧香磕头放鞭炮,求老爷保佑自己和全家都没病没痛,能走鸿运。你可以说他们是怕死的,尤其是老一辈的人。我曾看到几个老人在那里聊天,他们说着说着,说起以前的事,说自己年纪大了,老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上来了,他们伸出自己的手,有人瘦得皮包骨了,暗红色细细的血管就在皮下面,有人就抹眼泪哭起来了。说到底,还是怕死啊,怕自己死了一切就都空了,怕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曾孙女们过不好,还操心那些从前的小恩小怨,与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人从此再不能有瓜葛。所以我妈妈、我爷爷、我的同宗邻居们看到我们出去玩,就再三叮嘱我们,要我们不要去河边玩,不要被水猴子拖到水里面去了:他们还会威胁, “不听话看我回来不打死你”。虽然他们都喜欢骂小孩子为“化生子”(方言,主要是指一个人年轻时死了,不得好死,据说死后皮肉也不能腐烂,就在世上游走。骇人的意象),谁也不希望自己家里的小孩不清不白死在外面,到头来用一个撮箕装着,埋到一个小坟下面。我们当然也答应着, “好的,妈妈,我知道啦”。我们就结伴走了。
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觉,有很多次我一个人从家里出来,经过那条只有一尺来宽的泥巴小路,路的两边都是我爷爷的菜地和我爸爸的苗木地,我顺着小路往西走出一百米,下一个小坡,从那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由两块石板铺成的石板桥上经过,就看到一只水猴子坐在桥下常年都有流水的小小的水坝上面。我心里既害怕又兴奋,不晓得是真正的错觉还是别的什么。
现在我可以回忆并试着好好描述一下:
就算它是那只我见到的水鬼吧。现在我已经称它为鬼,而不是水猴子,其实是减少了它的神秘性的。因为就算在我们那里,人们信鬼、怕鬼,将很多事情和一个鬼联系在一起,可谁也没有真正见到过鬼,至少是不能证明的。所以我在这里将它写为水鬼,当然看上去好懂一点,不像水猴子,仿佛是一种活生生的喜欢恶作剧或真吃人的神秘生物(事实上是真有,这个以后可能会写到)。水猴子让孩子们感到恐惧。水鬼呢,就像一个不必当真的故事。
我见那水鬼就像一个小孩般大小,或者我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死掉的小孩,坐在浅浅的水上,面对着前面水青色的浏阳河。它也没有说话,没有发出声音——我仿佛至少见过它两次,其中有一次,它从水上跳回水里,不见了——我相信我是见到过它了,它一动也不动,像个小孩那样坐在那里,让我回想起来也有些伤感。我只看了它一眼,就不敢正眼看它第二次。我的心里那么害怕,因为我妈妈和我爷爷都说过,水猴子要把人拖到水里去淹死。所以我想,即便那只水鬼不是一只有着人类恶意的鬼,它那祖先的记忆、父辈传授给它的生存的习惯,也总令它要坐在水边恐吓我这样的小孩的,它会在水里悄悄伸出两只长着爪子的手,将哪个孩子在河里晃动的脚抓住,将那最倒霉的没有听大人话的孩子拖到水下,拖到长着水草、沉没了人的遗留物的水底去。水鬼以此为生,它们也需要吃东西。
我斜着眼睛加快脚步走过了那座桥,经过了那丛我熟悉的枸杞。我沿着土坡小跑到前面去,就在那前面,我爷爷正在不远处的菜地里忙碌。
他从河里挑水上来,和他从家里挑来的一担粪勾兑,再将那稀释了的粪水浇到菜地里去。我和我弟弟也就是吃这些菜还有秋天的稻米长大的。
一丛枸杞
那丛枸杞不知是何年何月,因为何故在那水边岸上长起来的。它就靠在一条宽到一米多的唆(音Jun,四声,浏阳镇头方言,指的是一种溪流)边,在浏阳河的入口处,旁边是一些别的野草,都不怎么起眼,只有那丛枸杞,高也不过尺余。回想起来,它一年中大约一半的时候挂着小小的叶子,好像也开花。花是什么样子?好像小小的五角星,是淡紫色的。它分成很多单独的枝条,从潮湿的土里长出来,每株都长出自己小小的枝条,枝条上长出河里最小的小鱼般大小簇生的叶子。它的枝叶看上去就像垂柳,只是缩小版的垂柳,没有那种风中的轻盈。
我记得每年发洪水的季节,以及其他能捕鱼的季节,都会看到它的生机。
浏阳河的水大多是在四五月间开始时常上涨,六七月间而常有洪水。洪水来了,河水是浊黄色,带着拔掉的大树、各种能浮起来的活物和人T制品,也带来大鱼,将原来的河岸淹没,河边的柳树和樟树有时只剩下一半的枝干,另外一半,甚至有六七米、八九米高的,都淹没在洪水中扩大的河面里去了。低矮的树则什么也不剩下,河边的小路成为鱼和虾的过道,它们还要凭运气或古老的技艺逃脱人类渔网的捕捞。那丛枸杞当然也就消失不见。只是不必担心,等到洪水退去,雨水冲洗掉灌木和野草身上的泥,它又好好地出現在那里了,仿佛从未经历过什么。这些野生在自然里的东西生命力那般强盛,即便柔弱的草,纤细的枸杞枝,也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活路,总要尽力好好地长下去,今年长出新叶,今年开花,今年又结果。听说枸杞最早发现于亚欧大陆土耳其的古老城市吕底亚,而在中国两千年前的《诗经》中,也有对它的记载。当然,我想枸杞的生命可能远比人类要久远也说不定,因为它们进化缓慢。枸杞早已入药,又可以食用,是炖煮肉类的好作料,令汤汁微微甜美。如今的人们被现代精神和自己制造的压力驱使,脑力和精力使用过度,而又少体力活动,少运动,不像从前的农民,都是自然生息。上班族喜好以枸杞泡水喝,可以滋补脾胃,补充续亏的肾气,又说这是进入中年的标志,也是早衰的笑谈。
我也免不了如此,终日头疼脑昏,也常携带着保温杯,杯子里泡着六颗枸杞,并且是朋友送我的宁夏枸杞,粒大,红润,有些透明。
我的朋友李医生说,这算是上号的枸杞。
而我印象中竟从没有从浏阳河边那丛枸杞上采摘过枸杞回去,没用食用过它。大约我和我的伙伴们只把它当作河边的一株野生植物,和野草、蒲公英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秋天去摘河边桑树上的桑葚,尝到桑葚的甜,而不知那丛枸杞的甜。而它也是单独的,我从没有在熟悉的浏阳河边见过另外一丛枸杞,所以如今觉得它的出现是神奇的,和我读到过的关于古希腊爱神的故事有些相似:它们也许都是没有父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爱神的一种传说,说它是最古老的神,是天地肇始之初就有的。那丛枸杞没有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就像我在河边只见过一处地方长有好看的彼岸花。彼岸花开得太过鲜艳,太过好看,我们依照老人的嘱托,认为它可能是一种毒物,用美丽的颜色招惹人,也用它去警告那些有经验的人少去碰它。枸杞没有更多的防备,除了它枝上有的小小的软软的刺——而那刺,也终归是它对自己的保护,是造物主赐予它的吧。
在一首小小的诗里,我书写过那丛在我成年以后数次回忆起来的枸杞,我觉得它是可爱又好看的。
每年每次回去,我多半也要去河边看看它是否还在那里。
它当然就在那里,比我的记忆还要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