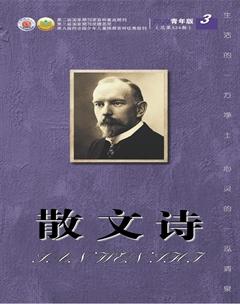我熟悉失眠犹如熟悉汉语的语法
安文

九月
九月,房门幽寂、紧锁,
胸腔的蜻蜓近乎静止地颤动。
每天例行买菜,偶尔鸽子的几声咕哝也会俘获我,
虚弱的兵士见不得号手的头颅昂起,
这会使他的忧容更加苍白。
如是鸽群低掠过他,携来几粒家乡成熟的谷物,
他拖着扭伤的脚踝飞奔起来,
压皱的稿纸渴望重披雨水的清泽。
苏俄女诗人也同为俘虏,
积雪在她心上结疤,小白鞋的尺寸无人丈量,
诗这点儿才貌只够她病重十九天,
第二十天她将起身称量整个世界,
第二十一天她患上的熱症就使我寒颤不止,
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不能解救我,
爱人的胴体更使我沦陷。天明,
忧悒的热毛巾擦拭我额角的鬈发,
拧干,铺展,转身开门,
小区的楼群如彤红的珊瑚林一般
在金光下摇曳透明的藻叶,
涅瓦河的飞练游弋于回忆录的每个词句,
彼得堡在女诗人的泪水中消逝。
猝然,幼儿园传来鲸歌将我带回
母亲逐渐隆起的腹部,顽劣的书童挑开帏帘的一角,
向尘世的牢房匆忙一瞥,
塞壬的歌吟恰似朱鹮的啼痕。
一切事物的真实皆不可妄言,
除非手风琴的簧管吹奏,
蝴蝶的性属惹花蕊犯愁。
我熟悉失眠犹如熟悉汉语的语法
我熟悉失眠犹如熟悉汉语的语法,
熟悉石英表闪着荧光的指针,
熟悉酒气与浑话如秋晨的大雾
漂浮在乡村筵席的悲欣之下,
隐去犁铧,谷堆,虚掩的房门,
结婚登记簿,盖房的欠条,
孩子酒窝如蜜的证件照……
浸酒的软木塞味满屋子都是,
黑暗递给我一把哽咽的剪刀,
花园向我敞露道路,
我手植那些我偏爱的花种,
一落地硬土路便成芳径。
跫声响在左边的窗口那侧,
午夜正萌动于鼾声的田野,
我清醒着却像高烧般昏厥,
无数朵花的萼片随风舞动,
水声滴答如治愈我的药粉,
花园此时却肆虐如暴风雨,
它从我的眉额游走而下,
践踏我的面颊,像天鹅伏地前
高吟的安魂曲一般勒紧脖颈
……一阵失聪,凋敝,空茫
……我像一阵胸腔外的心跳,
一个木柄折断的鹤嘴锄,
我只把我的喙往泥水里扎。
霞光再暗一些就是雪的毛绒
霞光再暗一些就是雪的毛绒,
窗玻璃映出一个女人的侧脸,
下一页火车开入隧道,
夜色如同凄冷的岩壁阻断我意识的全部幻想。
空气中弥漫的扎人的寒意,
像指间的烟蒂熄灭多时了。
骑行回家,巷子口另一个有些臃肿、呆滞的跛脚女人
也好些天没再出摊,代她的
又一个女人同样是一个普通的
中年妇女,凌晨时分还有
类似的小商贩在电影院附近
等待这一天最后几块钱的收入。
街道如一包空荡的烟盒,
我的肺里满是灼痛的焦油。
冰封的呼兰河依稀飘来盂兰盆节点着的河灯,
雪白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只堪回忆的身躯。
一列载走我的女人的火车仍在平原的腹地穿行,
弯月是一条手织的围巾,
河灯浸了水是晕散的弯月,
爱人和被爱永远被误解,
真理散发着千万缕不同的体味,
北国和雪国是同一处收信地址,
既然大雪终要落下,不如一齐献给孩童,
故事的开篇不假外求。
秋
遭受过春的旖旎与夏季排浪般的流火,
秋的旷野静穆地铺展,笔尖粗且钝,
像一叶笨桨触及你的肌肤只荡起
毅纹的三两片温情的絮语。
平林的尽头是新月下扛锄的农人,
他们走至岔路口,咧出烟熏的黄牙
进行一天中关于收获的简短寒暄。
遥遥地,妻儿分工,不同的声部
轮番叫喊,他们相继走入各自的村庄。
贴秋膘也是寡淡食谱上罕有的胜景。
但,北风毕竟寒凛而至,孩子们
单鞋里的脚趾宛如一块块通红的烙铁,
院孔照常流水,而墙外的水洼
无数条冰凌的游蛇吞吐雪候的讯息。
苦冬并不能使一个贫穷的家庭破产,
秋的王宫灿烂且边界遥远,
秋哦,让我举起亮晶晶的手杖,
遥遥地,比划我的唇语——难以诉说。
携一本琼美卡随想录走失在纽约街头的大雪之中
携一本琼美卡随想录走失在纽约街头的大雪之中,
甚至来不及揖别木铎而有心的头戴绅士帽的江南著者。
摩登浪漫的中古且身世悲辛的一道身影如一张雪毯
掩住我沉湎于诗国的灵魂,它的眉目潋作剑鞘,
它的欢畅是第十个缪斯,它的忧郁是肖邦的仆从。
渺茫。我踱出屋门,秋夜阒静,铃虫远遁,
秋的脉搏一瞬息沁黄了我银杏叶的心脏。
我上前然后蹲踞,微凉的手心升腾一束火焰,
火光映亮凤仙抑或长春花的仪容——
我髡彼两髦实维我仪的万物的仪容——
青椒和小葱搭话深羡交缠生津的仪容一
窗子下,芸娘为我刺绣的仪容一
仓庚从跟趾跃到头梢啄尽鹿角的梅朵。
大海看清了我
我从未在某处长廊往返走动
往返。风一般来到低洼的尽头
风。吹斜早春的细雨拂落
紫薇花纯色的头巾。我憋足了力气不停地
转动蜂鸟绣眼鸟百灵鸟
头顶上冠羽般的桅帆
我逆转了风的流向浮在峭立的崖顶
我的双脚还未生根眼眸已经湿润了
大海看清了我。
假如
我信手把口琴反向噙着,腾出
一排音孔正好供这些游荡的热风
盲目地出入:我听见雷声才从
迷离中睁眼——昏暝的时辰已经降临。
我身处的这片小树林杳无人迹,
繁茂的椴树和齐腰的苦楝
拦阻我继续前行,褚桃是我儿时常见的树木,我们在
南阳城郊的一个村庄重逢。
似有养蜂人曾在此劳作,
广袤的七月,浴火的七月,芝麻生长的七月,
养蜂人遵守自然的谕旨,转场,转场,
昏暝彻底沦为黑暗,大江潮涌,大海如镜,
妖冶的花朵一层层打开它的叶瓣,
花蜜金黄,如热泪,无声地渗入劳动者的心。
假如此刻有一只鸟雀
从村庄的一间屋顶,掠过我失神的一瞬——
一枚小小的,糖纸似的羽毛飘至脚背。假如把
时间延后一万年你我仍旧相爱,
某个少年捉蝴蝶扑入这片树林
……一枚小小的羽毛搭在两块形似脚背的化石之间。
我想象永恒的生活
那是四季之外的生活。那个早晨
我的网领毛衣刚套进脖颈,
我正欲走到窗口,男孩女孩们
春风一样跑动的声响涌入耳畔。
一阵短暂的耳鸣。
细听:海豚游弋,黄莺啾鸣,
琴弦由粗到细地振动。
他们凑近我的房子又如云般远去,
他们中间穿梭着我的儿子,女儿,
或许还躲藏着知青年纪的父亲,
母亲。“亲爱的妻子,或许我们
相爱就在此刻。”说过这句话
风雪又紧了几分。这里不是
嘉庆年间的苏州,不是瓦尔泽
散步的十月,不是俄国女诗人
在鞑靼共和国发霉的居所,
这里每一片树叶饮足了雨水也会
像出巡的公主一般抬起她窈窕的叶尖。
我在这里不写一首诗。
我偶爾出门,
这是怎样的一个花园,一首乐谱?
这是怎样的一条大河,一垄庄稼?
这是怎样的一轮新月让我瘫倒在地?
我可能一生都找不到回来的路。
当我推开发霉的房门,
桌沿是否压着一封信?
一封永远不用拆读的信。
这是我想象的永恒的生活,
这是四季之外的生活,正如
一位用德文或俄语写作的诗人
陷入绝境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