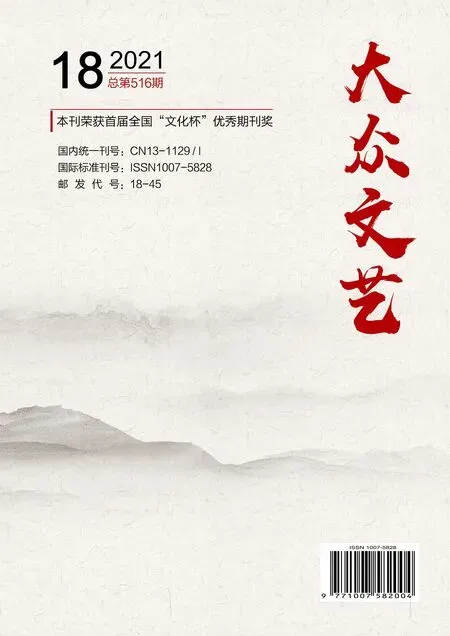日语学习中媒介语作为内部言语的使用研究
周 成 林 燕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宁波 315300)
一、引言
虽然媒介语和内部言语经常出现在日语的学习和运用中,但很少有学习者认识并了解这方面相关内容。通过本研究,希望能使日语学习者了解日语教育中媒介语及内部言语的相关定义,明确自己的学习方法的进行方式,以及有怎样的长处和短处,了解需要如何进行改善。日语教育者以此研究为参考,可更明确日语学习者在此方面可能遇到怎样的困难,更好地因材施教。
二、外语学习中的媒介语与内部言语
外语学习中目的语是除母语之外的习得的对象语言,在这里特指日语学习者所学习的日语。外语学习中为了学习者理解掌握目的语,使用学习者的母语或者非目的语的其他语言作为媒介语。以国内日语课堂为例,教师在对汉语母语学习者的日语教学中,指示或说明语法时使用的汉语就是媒介语,而日语就是我们学习的目标语言即目的语。并且,外语学习不只有学习语言知识掌握语言材料的语言学习,还有对于言语的学习。言语可以分为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内部言语以生物电信号作为载体,用于思维。而外部言语又可以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1]言语学习是一个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互相转换过程,侧重的是学习和掌握对语言的运用。[2]此文不对语言和言语之间存在的区别做深入学理辨析,而侧重学习者在言语学习过程中媒介语作为内部言语这一情况的探究与分析。
内部言语存在于语言运用的方方面面。在日语学习过程中,在对日语相关的语音文字进行输入与输出时,脑中是将其转换为我们所熟知的汉语(媒介语作为内部言语);还是对其不进行中文转换,如同以日语为母语的日本人,直接用日语为内部言语在脑中进行内部思考。本研究将视点转向学习者,因母语非日语的学习者将日语作为目的语学习的过程中,是通过媒介语学习和掌握目的语的,故以母语作为媒介语时,必然会受到母语的介入(母语迁移)。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提升,由于思维习惯的不同,部分学习者通过省略媒介语作为内部言语学习目的语这一步骤,以求更快地达到理解学习内容的目的。[3]单从内部言语步骤来看语言学习输入输出时使用媒介语的后者要比不使用媒介语的前者多一个目的语与媒介语相互转换的过程。
三、目的语输入及输出时的内部言语
言语学习的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在输入阶段主要通过听觉和视觉在大脑内部形成电信号,而这种电信号就是内部言语,通过看到或听到一些目的语的单词与句子在大脑内理解分析并进行记忆储存。此时不同的学习者主要分为:看到或听到目的语相关的单词句子时,脑内的内部言语保留为目的语并直接进行图像与场景的转化。另外一种情况,同样看到这些单词或句子,内部言语先转换为媒介语再理解成图像或场景。这两种情况还可能同时存在,并且媒介语有所不同。熟练程度对媒介语是否参与内部言语也有一定关系。对相关内容熟练程度较低时,在对输入内容所表达的意思及其背景知识充分地了解和掌握之前,媒介语将会介入内部言语。如,アップル(输入源)→apple/苹果(内部言语)而后被理解并记忆。在输入语言为以日语片假名表现的外来词时,学习者在多数情况下会先将其转换为相对应的借用语,再通过母语对借用语理解并转化。日语中高级学习者在对内容熟练程度高时,对意思及背景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省略部分媒介语的参与,省略对应借用语或省略母语转换,或两种媒介语都省略。
在语言学习输出时,用目的语在内部形成腹稿后直接写出或说出,另一种则是运用媒介语作腹稿在内部翻译成外语后写出或说出。言语学习的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在输出阶段大脑内部先形成电信号,产生后再说出或写出目的语相关语句,这种情况也就是常说的“打腹稿”;而另外一种内部言语边产生边输出的情况,常说的“想到什么说(写)什么”。根据目的语发言或写作的场合不同,较为正式的场合学习者多采用前者,如日语即兴演讲,作文答题等;较为随意时,多以后者的形式发生,如与日本朋友对话,写日语随笔等。同时学习者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在较为随意的场合下也会采用前者,也就是学习者经常遇到的“不好意思开口说外语”。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当学习者们为了表达问候这一目标时,一些学习者会先将这一目标转换为作为媒介语的内部声音“大家好”,再将“大家”和“好”分别翻译转化为“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最后进行组合并输出;或省略媒介语作为内部声音,以目的语“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直接作为要输出的对象,“不打腹稿”的情况也是这种情况的内部言语的直接外化。内部言语起对输出语言的整理和补充作用,运用媒介语时更注重“整理”功能,通过“整理”,使输出的内容更符合内部言语所已经整理好的意思;以目的语直接作为内部言语时更注重“补充”功能,通过“补充”关键语句使输出的语言合乎输出目标。
四、不同类型内部言语在学习中的利弊
在外语教育中,将是否通过媒介语教学的两种不同方法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有研究者认为是否运用媒介语各有长处和短处,认为只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反而效率低下。[4]在实际学习应用中,在课堂教学中,外教课作为直接法教学较为具有代表性,外教课较为注重快速反应,即内部言语整理时间相对较短。在此主要探讨对象为中高级日语学习者。在进行教学时,因为学习者的内部言语因人而异,此时如果没有以目的语作为内部言语听讲时,脑内是以媒介语作为理解和记忆的内部声音。教师如果使用直接法不通过媒介语进行解释说明的情况下,学习者所接受到的是支离破碎的媒介语,需要重新对媒介语进行构建。[5]当这些媒介语不足以形成能够理解记忆的体系时,大脑的活跃程度将会降低,这时通过直接法进行学习输入的目的语很可能被大脑归类为白噪音,让人昏昏欲睡。这也是初学者阶段要求外教充分调动课堂积极性,不要求学习深度,鼓励教学道具的使用,偏重课堂兴趣培养[6]的原因。这样的学习者,如果在目的语输入时加上媒介语的补充,给学习者一个脑内媒介语的对照反馈,学习者将更容易接受。对象如果是语言学习输入时是以目的语作为内部言语的学习者们,并且外教课所教授内容的背景知识是学习者在初学者阶段已充分掌握的情况下,理解效率和准确程度将会明显高于前者,也就无须媒介语的额外补充。但在教学内容较为深奥,学习者并没有了解过的情况下,将省略较多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图像场景的词句,无论理解正确与否,很可能已经形成一副依据自己理解的画面与场景,而导致内容意义偏差。
而在传统外语教学中,本国教师的母语与学习者相同,多采用间接法将母语作为媒介语进行授课。教师使用目的语的时间相对较少,但内部言语整理时间较长。[7]当教师介绍一个日语语法时,会先以媒介语介绍单词意思,使用情况,再通过例句以及例句解释去分析语法。以简单语法“は…です。”与“は…ではない”举例,学习者若以媒介语作为内部言语进行课堂学习,那么首先接收的是“是...”与“不是...”,然后推举出“这是猫”和“这不是猫”如何表达,最后再以提供的“は…です。”与“は…ではない”去整理得到“これは猫です。”“これは猫ではない。”汉语母语者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初学者阶段,多数学习者能且只能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语法的学习。而当学习者们进入中高级水平时,可以有选择性地省略媒介语转化为目的语的过程,由“は…です。”与“は…ではない”以内部言语直接补充为“これは猫です。”“これは猫ではない。”来掌握和记忆。此时教师再以媒介语作补充,学习者很可能无法将自己已形成的画面与场景与媒介语相联系,从而将该媒介语作为目的语重新进行再一次的理解,两次理解对照才能判断正误,会做很多无用功,甚至导致分心。而如果是直接法以目的语做补充说明的话,不需要转换语言,可以直接在先前理解上修饰补充,将能够达到更好地效果。
外语学习中的“影子跟读法”和“回音法”的目的在于输入,以听到目的语,不进行意义分析通过口头言语对目的语进行复述。这两种方法都是目的语直接作为脑内言语,媒介语在过程中都不参与,只是外化语言的过程有所不同。“回音法”目的语作为内部言语后,目的语在内部言语过程中先整理,再外化为口头语言;“影子跟读法”则是省略整理过程,内部言语边形成边输出。总之在使用这两种方法时,媒介语不作为内部言语。另外在进行日翻中口译时情况也较为特殊,由于日翻中口译本质上是一个媒介语输出过程,媒介语参与内部声音过程时就对目的语进行了转变,输出时以目的语输出只需要对转化完的媒介语进行记忆并在口头言语上重复。而如若内部声音为目的语,对未转化的目的语进行记忆,则会在口头语言过程中将目的语转换为媒介语,这个过程将占用大量时间,且在转化过程中,可能会丢掉很多细节记忆,从而使翻译过程十分困难。
五、结论与建议
外语学习过程中,母语必定会作为媒介语参与到语言学习中。学习者在对所学内容的熟练程度及背景知识加深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向由媒介语参与内部言语或目的语直接作为内部言语的两种学习方式的其中一种。两种学习方式在不同的教学方式下各有利弊,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会促使这种学习方法发生改变,学习效率也会有所不同。两种方法并非不可共存,而是一种选择所形成的习惯。学习者最好同时掌握这两种学习方法,能够在教师采用不同教学方法时灵活应对,不被其中一种方法所牵制。对自身进行一定的反思,多渠道多方法的学习日语,充分利用两种学习方法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