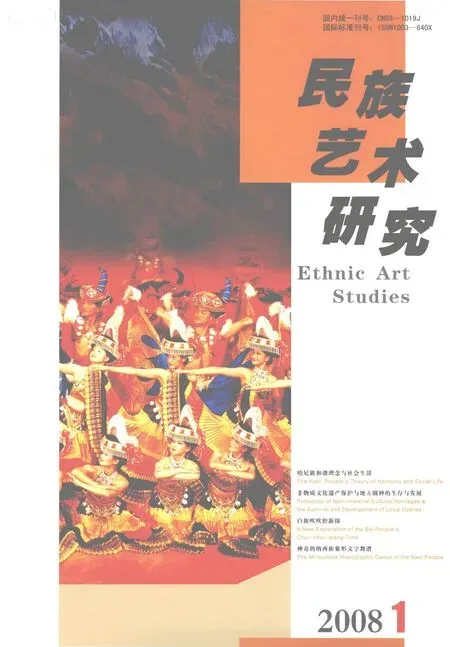从场所到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转变
王秀伟,延书宁
2007年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146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初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良好开端和文化生态保护的良性格局。2019年3月正式施行的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申报、设立与管理的基本理念和要求,对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保护区内作为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存在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是在相对漫长的时间中逐渐形成的,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建设则是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和开展的,而且该过程集中体现为人为主导的建构过程。外部力量的介入、主观性的构建、标签化的设计必将对原本处于自然状态的生产生活空间产生影响甚至冲击。在被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前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空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因参与其中的各类主体及相互间关系网络的变化导致了资本结构和空间属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增加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的资本积累、激发了原住民非遗保护与权力斗争的活力,另一方面因外部主体的介入打破了原住民社会关系的平衡以及文化空间转型与原真性之间悖论的出现。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从物理空间下的原住民寄托身心的场所到文化空间中各类主体权力斗争的场域,反映出关系性与斗争性视角下空间结构的转变。这种渐进式的转变贯穿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从设立到建设的全过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从单一生活场所到复杂生产场域的空间转变轨迹是怎样的?转变过程中多主体介入又是如何引发斗争关系的增强,并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产生双重影响的?文本从本体论角度进行阐释。
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构成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在 《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基于空间本体论建构了一个三元一体的社会理论框架,提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三种不同的空间关系。①杨芬、丁杨:《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探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10期,第183-187页。三种空间形成从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立体空间体系。其中,空间实践特指发生实践活动的物理空间,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分别指涉概念化的主体空间和人格化的精神空间。据此,我们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结构分解为物理空间、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三个维度。
物理空间,顾名思义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物理载体,明确标识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空间构造。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物理空间一般根据行政区划和文化地理单元来划分,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物理空间划定在福建省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的行政区域内,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物理空间按照古徽州的文化地理范围,囊括了安徽省黄山市全境、绩溪县和江西省婺源县。对物理空间的考察应着眼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空间辐射范围以及空间内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三个方面。从而有助于洞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客观环境、空间坐标和分布区域。物理空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承载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基本空间信息,虽然空间范围多是主观划定的结果,但空间位置、空间环境等信息基本上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的物理空间看作社会实践活动所发生的客观场所及其所处的周围环境。
生活空间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原住民栖息、生活的场所,是居民生活方式和生活情景的承载空间。生活空间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可知可感的空间形态,由人们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场景所营造、连缀而成。在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前的较长时间内,区域内居民的生活状态因较少受到外界因素干扰,生活空间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状态。该空间内原住民间的社会关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进行着内部调整与自适应,从而整体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在这种较为朴素的社会氛围和相对简单的社会关系中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发展最初多是在生活化的场景中进行表现、展示和传播的。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生活方式、生活习性的相同或相近,区域内的生活场景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因此,同一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形成和发展中多表现为集中分布、内容同质和源于生活的特征。此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托的生活空间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践活动发生的场所,其本质是居于其中的人们寄托身心的空间。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景因受外部因素介入的影响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但生活于其中的原住民因长期形成的惯习和生活形态一时难以改变,因此主观实践活动作用于客观物理空间的行为方式也难以完全消解。生活空间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寄托身心、维持各方关系平衡的场所将长期存续,构成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重要空间维度。
文化空间指依托物理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行文化生产、展示、传播、消费等精神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空间。相对于物理空间与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并非是可视化的实体空间,而是象征性的空间形态,即列斐伏尔所指的表征空间。在文化空间中,“人们以精神符号为介质,通过精神生产实践,对空间进行叙事、想象、隐喻、塑造等,赋予空间以文化内涵,建设成为符号化的文化表征空间。”①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语境中,文化空间特指文化遗产保留场景与 “漂浮其上的精神文化”②朱宁嘉:《文化空间复兴与再生可能的研究》,《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5年第21辑,第369-381页。相结合的空间。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空间的适用对象逐渐超出文化遗产的范围,指向人类学意义上更宽泛的空间概念,即由于人类活动而产生文化意义的精神空间。由此,文化空间可理解为基于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等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据此产生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流动的空间场域。文化空间充斥着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本质上是文化活动的关系场域。
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构成中,物理空间、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是三个由表及里、虚实结合的空间层次。物理空间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空间,决定了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地理坐标、空间边界和周围环境,是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依托的载体。生活空间内嵌于物理空间中,是生活场景在物理空间的填充。文化空间作为象征性空间是生活空间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延伸,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内核空间。从物理空间到生活空间再到文化空间的递进式演化轨迹,反映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的空间向度由自然状态下的客观场所向人文视角下的关系场域的转变。
二、从场所到场域的空间转变
20世纪60年代,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 (Norberg-Schulz)在讨论建筑本质时提出 “场所”的概念。他指出场所是空间的物质构成与由于人类的活动而被赋予的精神与情感意义共同构成的整体。从中可洞悉,场所不同于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蕴含着精神和情感意义的地方。在舒尔茨看来,场所 “是人们通过与建筑环境的反复作用和复杂联系后,在记忆和情感中形成的概念——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建筑、特定的人群相互积极作用并以有意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整体。”③郭红、莫鑫:《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理论评析》,《四川建筑》2004年第5期,第15-16页。据此,可以将场所看作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相结合的有意义的空间整体,它反映了在某一特定空间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所处的周边环境。场所的概念更多地体现为实体空间之外有精神价值和情感意义的“内容”。场所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当地民众 “存在的立足点”,它由物理空间下的空间范围、自然环境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当地民众获得的场所感和由此产生的场所精神构成。在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前,当地民众长期生活于其中,伴随着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的养成,民众之间特有的精神与情感不断生成、积累,成为场所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场所也自然成为民众寄托身心的处所,成为生活空间的集中呈现。
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实践社会学体系的核心概念,指 “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架构,这些位置客观上是由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的分配结构中实际或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所决定的。”①P.Bourdieu and J.D.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45.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体系中,将场域视为结构化的场所。位于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拥有一定的资本,并在惯习的引导下调整场域内的权力关系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个体惯习的养成与资本的获得往往是作为外在环境的场域内在化的过程。简单而言,场域是社会中具有独立性的、结构化的圈层。在该圈层中,各参与主体间因惯习相同或相近、资本类型和数量的迥异,形成了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位置关系,并在各主体间不断进行着争夺资本的斗争。因此,不同资本拥有方位置关系的复杂性、相互斗争关系的持续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场域的基本特征。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定后,在其运行机制下,因为众多的参与主体间存在不同的资本结构和位置关系,这就决定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作为一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独立圈层,斗争性将始终存在。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也成为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
(一)寄托身心的场所
根据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文化生态保护区 “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②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12/t20181225_836660.html?keywords,2018-12-25。拥有数量丰富且作为当地生产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区域被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基本条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和发展的空间。在被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前,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融入、适应周围环境而逐渐孕育、发展起来并进行了代际传承。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民众的空间参与,不仅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事象和实践,而且产生了厚重的地方认同感与归属感。地理空间与产生于其中的精神内涵紧密融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情感深处难以割舍的 “故土”。在民众与空间的互动中,地理空间也由此获得鲜明的场所精神,成为人们寄托身心的场所。
以六盘山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六盘山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和军事战略要塞,同时也位于我国传统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界处③陶雨芳:《六盘山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53-157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当地民众世代生活于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并形成层次丰富的空间结构。包括六盘山与泾河、清水河山水交错的物理空间,跨越陕甘宁三省的大六盘山文化圈以及大山沟峁中村落与城镇的生活空间,在这些空间中的互动过程中,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和交流碰撞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成果,如农民、商贩、马帮等下层劳动人民创造的山歌 “花儿”。由此,六盘山地区成为当地民众心灵与身体在场的文化空间,产生特有的地方精神文化与浓厚的归属感。如民歌唱词 “上了高山嘛一道梁,我有心面对高山喊着唱”中充分流露出当地民众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文化空间内精神家园的依恋。这也使得六盘山地区带有了特有的场所精神烙印。例如,提起六盘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人们往往会想到粗犷、直白、纯朴的民风和多民族交融、乡土性强的文化事象等。
(二)权力斗争的场域
某一空间范围被列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就不再仅仅是当地民众生活实践的场所,而更多地具备了公共属性,逐渐成为参与其中的各方基于资本与惯习进行角力的场域。当孕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被贴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标签时,政府、学者、企业、媒体等社会主体开始不同程度地关注并介入其中。虽然不同主体的关注点与介入方式不同,但结果都势必导致原有空间内主体结构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变,并进而引致空间属性的转变。即在各类社会主体携带不同的资本与惯习进入的情况下,该空间由民众寄托身心的空间场所渐次转向充满复杂关系与斗争的场域。在此过程中,不同主体拥有的资本与惯习不同,在介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对场域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以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清江中下游,分布有山歌、南曲和撒叶儿嗬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制定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旨在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所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形成集中连片的文化保护空间①徐琴:《生活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向——基于长阳县非遗保护实践的思考》,《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03-109页。。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当地民众文化自觉的推动下建立,从最初资丘乡民自发保护与建设的原真性文化场所逐渐转变为多种社会力量汇聚的场域。各级政府介入其中,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政府部门除积极运用政策工具激励、扶持外,还直接组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整体发展②赵军、曾婉珍、刘光菊:《场域视野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资丘经验》,《三峡论坛》2014年第5期,第24-28页。。包括电视台、报纸、网络媒体在内的媒体通过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事宜的连续报道,增加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位于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的曝光度,同时使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图景更多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学者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其保护对象的研究将外界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察视角引向深入,同时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注入了新的文化资本。政府、媒体、学者等社会力量拥有不同的资本结构和资本量能。在介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时,他们之间不免会产生利益的交叉与冲突,进而导致基于资本结构和势能的权力斗争。政府部门掌握着相对充足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在介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时因具有更高的资本势能和较大的影响力,从而通过发挥这种影响取代当地民众掌握建构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话语权。例如,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对保护区内的非遗传承人进行职称评定、制定有针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策划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庆活动等,增强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运行中的话语权。
(三)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转变轨迹
被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作为载体的文化空间由原住民寄托身心的生活场所逐渐转变为一个充满复杂关系的权力斗争场域。文化空间转变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多种社会力量的介入与相互作用,转变轨迹主要体现为文化空间内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斗争性的增强。
1.社会关系复杂化
场域在本质上是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架构。所以,从场域的视角考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需要审视文化空间内社会关系的变化。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空间的转变首先表现为参与主体由少到多所引发的文化空间内的社会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
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前以场所形式存在的文化空间内的文化参与主体主要是当地原住民。他们几乎世代生活在相似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惯习与获得的文化资本并无较大差别。虽然个体之间存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差异,但作为一个群体总体差别较小。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资丘文化站原站长田玉成作为文化能人,在当地具有相对高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过程中也相应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在审美取向、文化品位、经济资本等方面与其他当地民众整体趋同。原住民文化资本与惯习的相似性使得文化空间中不同主体之间所形成的关系较为简单,不同主体在文化创造与保护方面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例如,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六盘山及周边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当地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歌 “花儿”就是该地区民众在共同生活、交流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2.空间斗争性加强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转变轨迹还体现为所在文化空间内主体间斗争性的增强。进入新空间内的各主体为保持或提高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需要进行争夺资本的斗争。因此,斗争性是作为场域的文化空间最鲜明的特点。随着文化空间内社会关系趋于复杂,因各主体资本和惯习不同而引致的斗争性也必定逐渐加强。
空间内斗争关系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介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主体之间以及新进入主体与原有主体之间围绕权力关系进行的斗争将更加激烈。学者、政府、媒体等社会力量进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总是试图进入一个更高的位置,从而获得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其位置的高低往往由拥有不同资本和惯习的主体通过斗争决定。政府部门拥有相对充足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并且具有通过制定规划、财政拨款、实施奖惩等方式进行管理的行为惯习。因此,政府介入后,容易成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领导者,原本属于原住民的主导权转移到政府部门。2018年出台的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作出了规定,强调了地方政府的作用,对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地民众的权利、责任与利益则粗略带过,仅规定 “管理机构要尊重当地居民意愿”①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12/t20181225_836660.html?keywords。。学者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本以及金融等机构持有的高位的经济资本都使得各自在场域的斗争中胜过当地居民而获得更高的话语权。此外,新介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主体之间也存在权力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带有经济资本的各类社会力量与政府部门、学者之间就开发方向、建设内容之间的话语权的争夺。如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商业化问题存在的分歧和争论。
其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原有主体之间受到新介入主体的冲击导致合作关系的转变。作为场所的文化空间本是原住民生产生活的立足地。原住民作为最重要的主体,相互间主要表现为合作共享的关系。被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逐渐转变为场域的文化空间就不再仅仅是原住民生活休憩的空间,面向全社会的广泛的公共性和展示性在不断增强。在社会注意力有限的前提下,原住民之间为获得展示或被保护的机会出现和滋生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关系。如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地方政府采取对民间艺人评定职称的制度,分为大师、艺人和中级艺人三个等级②赵军、曾婉珍、刘光菊:《场域视野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资丘经验》,《三峡论坛》2014年第5期,第24-28。,每个等级获得不同的保护与激励措施。在这种激励措施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的艺人原有的合作关系悄然改变,相互间的竞争关系不断增强。
三、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空间转变的双重影响
文化空间从自然形成的文化圈层到被纳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范围的转变轨迹体现出文化空间从场所到场域的转变。多类主体介入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斗争关系的增强,既是转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现象也是转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立足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所依托的文化空间来看,这种转变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潜在的危机。
(一)空间转变的积极影响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所处文化空间转变的起因在于外界各类主体的介入。各类主体所携带的优势资本的加入,使得文化空间内的资本积累不断丰富。具体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等社会力量的介入,使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经济资本的存量与流量均得到增加,有助于为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社会媒体、文化学者的介入,则能够提升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从而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同时,吸附更多的社会资本。此外,政府部门制定的保护、传承措施能够帮助原住民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助力其更好地投入文化实践与创造活动中,有利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 “活态”传承。
从寄托身心的生产生活场所到充满权力斗争的复杂关系场域,文化空间的转变在充实文化空间内资本的同时,也激发了原住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活力。一方面,文化空间的转变激发了原住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使当地民众意识到他们世代相传的文化实践与事象所面临的危机以及保护的重要性,进而激励其主动投身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另一方面,文化空间的转变促使原住民在权力斗争中的能力得到提升。在外部主体纷纷介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刺激下,原住民获得难得的提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机会,意识到自身作为保护和传承主体应有的地位与权利,从而更好地参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虽然外部主体的介入导致原住民在场域斗争中权力的削弱,但必须看到相对于原住民选择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忽视传统文化事象与实践活动,或任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断传承和自然消亡现象,从场所到场域的文化空间转变对激发原住民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与能力是有益的。
(二)空间转变潜在的危机
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保护原生态文化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塑造公共语境下被观赏的对象。其保护对象本身通常是已经脱离了原生态生活环境的客体,即是在非本真性的状态下进行的塑造和展示。在保护过程中,为了迎合观赏主体的需要,又不得不强调对其本真性的保留。这就构成了生态文化保护的原真性悖论①刘晓春:《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3-158页。。原真性悖论已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以绕开的症结。列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文化空间,也同样存在原真性悖论难题,并且原真性悖论的出现与从场所到场域的空间转变直接相关。在转变过程中,政府部门、各类媒体、广大游客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介入不同程度地冲击了文化空间内本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生产活动,改变了既有文化生态的原真性。例如,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发展规划和各专项政策本身是从 “他者”的角度出发进行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干预,它脱离了本真性文化发展的轨迹。
无论是文化生态原真性的削弱甚至丧失,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然状态下走向式微乃至消泯都不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初衷。而成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的文化空间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原真性悖论。面对难以回避的原真性悖论,合理的方式是参照戴维·思罗斯比 (David Throsby)的观点①戴维·思罗斯比 《经济学与文化》,王志标、张峥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63页。,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充分考虑代际与代内公平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在保护原真性与人为干预之间寻找平衡。否则将可能导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原真性的丧失、文化事象的碎片化或保护不力等问题的出现。
其他社会主体的介入导致原住民之间以合作共生为主的社会关系平衡被打破。如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的手工艺者之间原本存在的合作关系在场域的环境下出现斗争性因素,当地民众在乡贤或文化能人带动下进行文化生产的模式被打破,文化生产的主导权与话语权转移至政府与学者手中。这从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原住民对本地文化保护积极性的丧失或者文化认同感的削弱。解决这一社会关系弱化危机需要以激发当地民众活力为基础。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体在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当地民众的意见,采取最小干预原则,建立参与与反馈机制,使得原住民有机会参与到规划的制定中。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情况的评价要充分考虑原住民的意见,提升其话语权。此外,在制定规划前需要进行充分调研,遵循谨慎性原则,在制定规划时尽量不改变原住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
结 语
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之前,其所在的空间是当地民众生产生活、寄托身心的场所。民众通过能动的空间参与不仅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事象与实践活动,而且产生了厚重的地方认同感与归属感,该空间也因此打上了原住民 “专属”的烙印。随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建设,外部主体纷纷介入其中,空间的公共性增强,使原本相对单一的空间场所逐渐转变为参与其中的各方基于资本与惯习进行角力的复杂场域。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前后所处文化空间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斗争性的增强,可洞察出其由场所到场域的转变轨迹,即从以合作共生为主调的相对单一的社会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主导的复杂社会关系。同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所处空间的属性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现代语境下的产物,但其保护的对象却是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所在文化空间出现属性的转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保护中的原真性悖论是难以避免的。这种转变既丰富了文化空间内的资本积累,激发了原住民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同时也会导致原住民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削弱甚至破坏。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空间转变带来的积极影响,也要预见其潜在的危机,从而趋利避害,探寻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平衡点。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的原真性保护,通过有效的参与和反馈机制使原住民充分参与其中,并提升其话语权,将是实现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良性发展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