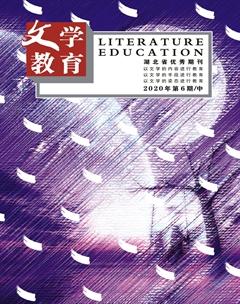《阿拉比》中的宗教瘫痪的出路
王安培
内容摘要:《阿拉比》中小男孩的顿悟不仅是对于现实世界的顿悟,也是意识到当时爱尔兰的天主教会脱离现实,给真实生活盖上一层虚假的掩饰,给爱尔兰人民套上精神的枷锁。乔伊斯利用小男孩的顿悟,试图让爱尔兰人摆脱天主教对人们思想上的束缚,意识民族危机的到来。
关键词:《阿拉比》 顿悟 宗教瘫痪 民族危机
“我深信你要是不让爱尔兰人民在我擦的透亮的镜子中好好审视一下他们自己,那么,你一定会阻碍爱尔兰的文明进程。[1]”乔伊斯的这面镜子,虽然经历十年的不断否定重造变的有些缝隙,但是仍然投射出当时爱尔兰民族宗教瘫痪下的虚伪现实。教会与英国统治者狼狈为奸,共同麻痹和奴役人民,乔伊斯“对教会恨之入骨”。他曾在信中写道:“我在当学生时就曾偷偷地反对过它,拒绝担任神职。如今,我要公开对它口诛笔伐。”[2]乔伊斯利用《阿拉比》中的顿悟让爱尔兰人民意识到民族危机即将到来的生存困境,摆脱宗教的思想束缚,挣脱教会的行为控制,唤醒沉睡在宗教幻影中民众,打破蚕食他们灵魂的宗教枷锁[3],达到彻底顿悟。
一.天主教会
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罗马天主教是爱尔兰的国教,它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宗教上有非常辉煌的历史,曾被称为“圣贤及学者之国”,是个世外桃源的基督教学习之地。但是随着“新教宗主统治”的确立,爱尔兰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政治,经济,甚至连文化传统逐渐泯灭,三千多年历史的母语盖尔语也被英语取代。但实际上,新教的确立并没有让爱尔兰人民的信仰产生剧烈的变化,当时的天主教仍是爱尔兰的主流宗教,控制爱尔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英国为了由内而外征服爱尔兰,一方面以政策打压天主教,有组织,目的性的号召新教徒移民。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新教徒开展了“新开地”运动,肆意掠夺爱尔兰人的土地。另一方面作为主流宗教的天主教,为了延续本教的信仰,没有唤醒爱尔兰人民的面对现实的困境的意识,反而给教民营造出精神牢笼。特别是在“18世纪爱尔兰教会历史被刑法的效力所决定,法条规定宗教信仰的不同决定了人种的区别,从而保证了少数新教群体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优势地位,并且垄断了获得高等教育的优先权。[4]”,英国人制定一系列严厉的法条来限制天主教的发展,例如:惩治法典制定了很多针对天主教徒的措施,千方百计的压制天主教势力的崛起,打击信众的信心,维护新教的优势地位[5]。为了让教民延续其信仰,保持天主教的主流地位,天主教对教义宣扬在爱尔兰人民精神世界中的影响与日俱增。面对如此严峻的宗教镇压,爱尔兰人民把天主教会看成可以帮助他们脱离痛苦的救世主,把天主教看作思想上抵御外来入侵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只要他们继续信仰天主教,爱尔兰人民的身份就能永不消逝,正是由于对天主教盲目的跟从和信任,导致爱尔兰人民意识完全被天主教控制,没有发现天主教实际上只是给教民描绘了虚假的现实。1870年梵蒂冈第一次会议中颁布的教皇无谬误的天主教教义更是进一步加强了教民的思想统治,在爱尔兰人民精神世界中,天主教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安东尼奥·葛兰西说:“一个宗教,为了在其忠诚的教民群体中永久地维持本宗教的声望,总会不厌其烦的重复本教的护教学,挣扎着用某个主张来维持某一层次的知识分子的虔诚,至少维持表面上思想的尊严[6]。”处于两教之争的天主教,不再是之前纯粹爱尔兰文明的摇篮,由于政治矛盾和利益之争,逐渐成为爱尔兰人民精神麻痹。宗教瘫痪的根源。
二.《阿拉比》中的宗教瘫痪与顿悟
在《阿拉比》的开头,有一段关于死亡教士居住地的描写。“房间长期关闭”“散发出一股霉味”“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废纸”“生锈的打气筒”“荒芜的花园”等等,落败的生活环境恰恰暗示了教士代表的天主教的腐朽,然而比肉体摧残更可怕的是天主教对于精神世界的禁锢,这种禁锢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天主教依靠自身的教义对教民进行驯服,另一方面,随着英国入侵的深入,爱尔兰人民对于天主教的信仰日益深重,为了保持主流地位,天主教也更进一步在教民思想上洗脑,或者与爱国主义等思想结合来寻求支撑。首先,在《阿拉比》中,当小男孩进入青春期之后,有了暗恋的姑娘,萌发了肉体的冲动,小男孩整日密切观察姑娘的一举一动,“摇摆的衣服”“柔软的辫子”“白嫩的脖子曲线”“披垂的长发”“栏杆上的手”“衬裙的白色镶边”,从小男孩观察的部位可以看出,虽然肉体的欲望让他有了贪欲,但这种贪欲的想象是点到为止的想象,仅限于目光所能触及的部位,并没持续深入,可以看出在当时,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和道德之上的神学教义对于教民的精神世界还是有一定成效,至少第一步禁欲主义深入他们的潜意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某种不被注意的方式显示出来。另外,小男孩在纠结如何同暗恋的姑娘倾诉自己的爱意时,他把自己的肉体比喻做竖琴,“我的身体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拨弄琴弦的纤指[7]”,渴望和姑娘进行身体接触,但是因为现实中宗教的制约,这种渴望也只能是停留在想象阶段,而且竖琴在爱尔兰是“天使之琴”的象征,代表宁静,和平,博爱和不朽的灵魂,小男孩在平静的生活中,没有过多的烦恼,有的是对青春期对倾慕姑娘的羞涩和迷恋,即使身处嘈杂喧闹的环境,只要一想到心仪的姑娘,就好像捧着圣餐杯,在一群仇敌中安然穿过,小男孩把自己甜蜜的暗恋和宗教的神圣放在同等重要地位,甚至把这个暗恋的姑娘看作圣母玛丽亚的替代。其次,天主教过度宣传自身的教会,首先,《阿拉比》的教士被描述成一个“心肠很好的人”“全部存款捐给了各种慈善机构”“家具赠给来妹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经济的主导权还是在殖民者和宗教组织的手上,本来天主教徒的生活困境就被新教压制,没有与他们同等的权利,但是天主教忽视了其教民的生活水平困难的现实。在劳动力市场,新教徒把持着高收入的专业岗位,而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只能找到收入微薄的入门工作[8]。处于这种生存环境的天主教徒,教会仍然呼吁把錢财捐给教会,不值钱的才留给家人。第二,莫塞尔太太“为了某种虔诚的目的,专爱收集用过的邮票”,虔诚一般形容对宗教的信仰,作者这里用反讽的写法表现出莫塞尔太太对宗教的曲解,而莫塞尔太太在这个年纪居然没有人陪她聊天,要一个小男孩耐着性子听她嚼舌,也可以理解为某种扭曲的宗教文本机制,而小男孩能耐着性子倾听,说明小男孩对这种宗教的扭曲也可以接受[9]。一般来说,集邮有三种目的:益智;怡情;蓄财。既然是“虔诚的集邮”,那么集邮势必与宗教有关联,或许可以联想到莫塞尔太太是把集邮当成保值升值的一笔财富,再把邮票转手卖出在捐赠给天主教传教士来表示对天主教的忠诚。第三,小男孩的暗恋的姑娘--曼根的姐姐,“曼根”这个名字是爱尔兰爱国主义诗人詹姆斯·克莱伦斯·曼根的姓,这个姑娘既是小男孩心中的“圣母玛利亚”,又赋予了其爱国思想的历史意义。从乔伊斯这些微小的细节描写,含沙射影的表现出天主教对于教民的困苦选择性忽视,却希望教民奉献出最忠诚的信仰,并尽可能将所有美好的品质都和天主教互相联系。
也许是小男孩意识到自己违反了天主教的教义,为了缓解自己的罪恶意识,他来到教士死去的房间里忏悔,虽然这种对异性的冲动只是在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生理现象,但是在当时的天主教的神学体系中,“任何违反上帝指令的语言,行为,思想都是罪孽”[1],所以这种对异性的幻想冲动也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因为“罪孽无轻重之分,肉体之罪和精神之罪都是大罪[10]”,小男孩陷入了两难,究竟是臣服于强势的天主教信仰,还是追求他幻想世界的美好,最终小男孩对想象世界中真实的渴望挣脱了长久以来天主教带给他的精神牢笼,“我庆幸自己不能看清一切”,放任自我追逐心中所爱,这是小男孩成长过程中一次重要的思想转折点。之后小男孩克服所有困难,终于在散场之前来到阿拉比,但是“大半个厅堂黑沉沉的”“犹如置身做完礼拜后的教堂”,这个时候把阿拉比比喻为黑暗的教堂,和小男孩当时躁动不安的心情相呼应,宗教已经完全丧失了之前抚慰人心灵的作用,反而显得阴沉和黑暗。《圣经》中记载,耶稣进入上帝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桌子和卖鸽之人的凳子,對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小男孩心中的神圣也在这个阿拉比的市场上化为乌有[11]。在听见摆摊女郎和其他两位的男士的调情之后,小男孩顿悟了,发现阿拉比——这个他以为的美好世界也是肮脏的,就像黑暗的教堂一样,只是宗教给人们建立的虚妄的世界,即使人们挣脱天主教思想上的锁链,揭开这层掩盖布,仍是宗教给人们创造的虚伪现实,在这层假象的外衣下,宗教内部早已腐朽没落,内容已经改变,不再是人们的精神港湾,只是虚伪的自我麻痹罢了。在故事的结局,“大厅上方漆黑一片”,肮脏麻木的现实再次将他们笼罩,小男孩“眼睛里燃烧痛苦和愤怒”,这种痛苦和愤怒是意识到天主教刻意为爱尔兰人民编织的假象世界,意识到宗教已经瘫痪的现实,意识到假象世界背后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压迫入侵,民族危机的迫近,想要唤醒爱尔兰人民对于这一现实的认识,不要在麻痹中苟且度日。
三.结语
乔伊斯认为:“严格地说,都柏林人是我的血肉同胞,但我不像他们那样喜欢谈起我们那‘可爱的脏兮兮的都柏林。都柏林人是我在爱尔兰岛和欧洲大陆遇到的最无可救药,最无用,最反复无常的人。”[12]《阿拉比》中,乔伊斯以小男孩对现实对顿悟折射出对天主教虚伪面目的揭露,利用大众渴望被救赎的心理,企图遮掩自身的缺陷来维护声望和地位。在教民病态的信任下,利用精神世界的权威,追求政治及经济利益,乔伊斯试图用小男孩的顿悟来打破天主家虚假且编织的祥和假象,意识到民族危机的迫近,唤醒每一个爱尔兰人的良知和责任,在瘫痪中脱胎换骨,走出困境,重新获得崭新的生命。
注 释
[1]Scholes, Robert and A.Walton Litz, eds.The Viking Critical Library:James Joyce, Dubliners[M].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9:286.
[2]蔡芳.《阿拉比》与宗教象征[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106-107.
[3]于海,谢永贞.从瘫痪到重生——《都林人》主题评析[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学报.2009(4):111-113.
[4]MacDonagh,Oliver, Mandle, W.F.and Travers, Pauric, Irish Culture and Nationalism:1750-1950.NY:the Mamillan Press:1983.
[5]江振鹏.18-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问题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7:60.
[6]Gramsci, Antonio,Selected Letter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ed&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NY: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
[7][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孙梁,宗博等译,都柏林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1:25.
[8]王鸿义.浅析北爱尔兰冲突中的宗教因素[J].科教导刊,2014(7):152-152.
[9]蒋仁龙.小男孩宗教信仰的虚妄之路[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6):30-34.
[10]Aquinas, Saint Thomas.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uinas. Vol.II.ed.Anton C. Pegis.New York: Random,1945.
[11]蔡芳.《阿拉比》与宗教象征[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106-107.
[12]大卫.诺里斯, 卡尔.富林特,周柳宁译.乔伊斯[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9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