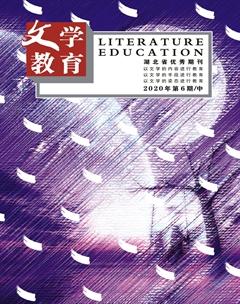解读尤雷克·贝克尔小说《说谎者雅各布》
赵娜
内容摘要:小说《说谎者雅各布》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其作者尤雷克·贝克尔的童年是在隔离区和集中营中度过的,而在成年后遗忘了童年时期的几乎所有记忆。于贝克尔而言,就这一话题的文学创作就是一种重新建构记忆、寻找自身认同感的途径。该文本试图从回忆的空间因素、时间因素以及回忆的媒介几个角度来解读小说《说谎者雅各布》,探寻贝克尔是如何重构记忆的。
关键词:重构记忆 空间 时间 媒介
尤雷克·贝克尔是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说谎者雅各布》发表与1969年,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小說的框架故事是:集中营幸存者,即匿名的第一人陈讲述者“我”,在事情过去20多年后,回忆了其在犹太人隔离区的见闻。小说内故事中,“我”只是个小配角,主要是主人公雅各布的故事:一次偶然的机会雅各布在警察局的收音机上意外听到一则苏联红军进逼隔离区的消息。为了阻止同伴米沙企图偷盗车皮内的马铃薯的愚蠢行为,雅各布告诉了米沙这一消息。为了使其确信消息的可靠性,雅各布撒谎称自己有一台收音机。这消息成功地阻止了米沙的盲目行为。但雅各布有收音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为了满足隔离区同伴们的好奇心,雅各布不断想方设法编造消息,给几近绝望的同胞以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小说有两个结尾:一个是讲述者编造的结尾,雅各布试图逃出隔离区,但被哨兵枪杀了,而几乎同时苏联红军解放了隔离区,解救了其他犹太人;另一个是真实的结尾,最终隔离区的所有犹太人一起被运往集中营。
不同于其他的描写大屠杀的作品,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强调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反而处处强调其中的很多内容是不确定的。可以说《说谎者雅各布》是作者贝克尔虚构的故事,是讲述者“我”记忆结合想象的故事,是主人公雅各布的谎言所构建的故事。
一.重构记忆的需要
《说谎者雅各布》明显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作者贝克尔出生于波兰小城罗兹的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他的早期童年,从2岁到8岁,是在隔离区和集中营度过的。成年后他丧失了此间的几乎所有记忆。贝克尔试图分析自身记忆缺失的原因,他将其总结为四个原因:首先这是一种人的自我保护,遗忘最艰难的经历,使自己免受伤害;其次隔离区和集中营中的生活仅对成人而言令人紧张万分,因为每日都要面对死亡的威胁,对于儿童则是单调乏味。再则那里的日子不能称之为生活,仅能称为生存,因为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存活下去。因而对于儿童而言,这些记忆毫无值得保存的价值。[1]10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语言:贝克尔的父母原本说易第绪语,这是东欧犹太人常用的一种语言。但当时他们生活在波兰,父母坚持让他说波兰语,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但在其和父亲定居德国后又被父亲要求学习德语,波兰语在他熟练掌握德语前就已早早遗忘。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中,语言对于承载与之相关的记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语言的缺失也是贝克尔几乎完全遗忘自身童年记忆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哈布瓦赫的理论,个体通过保存并不断回忆自身各时期的记忆而使认同感长存。[2]82儿时记忆的缺失使得贝克尔的自我认同感不能实现,因而记忆的缺失一直困扰着他。贝克尔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这样写到:缺失了童年的记忆,就好像是你一直拖着一个沉重的箱子走路一样,箱子里的东西你是未知的。而且你年龄越长,箱子于你越沉重。你也会越发缺乏耐心,越发想打开看清里面的内容物。[3]11
贝克尔也尝试从父亲那里了解自己的过去,但其父亲,一如很多经历过大屠杀的犹太人,对于过去的经历一直保持缄默。在父亲去世之后,贝克尔才理解父亲的沉默。父亲在大屠杀中丧失了自己的家园,这里的家园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指人:亲人和朋友。这些人在战争中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1]11二战结束时贝克尔家仅幸存下三人。[1]9所以父亲如同当时千千万万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一样选择了沉默。沉默使得父亲不再因过往的苦难生活而痛苦,沉默使父亲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沉默成了父亲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一种生存策略。贝克尔在父亲那里得不到有用的信息,但他又有唤醒自己儿时记忆的需求,所以他尝试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来重新建构自己缺失的记忆。
二.重构记忆的方法
记忆理论中过去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流逝,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与回忆者有内在联系。回忆的过程本质上不是简单的恢复的过程,是一个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一个建构的过程。要重构已经缺失的个体记忆就必须依赖记忆的集体框架,也就是个体所处群体的记忆。正如哈布瓦赫所言,人是群体动物。记忆是一项集体功能,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有着紧密的联系,个体通过把自身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个体能将回忆唤回到脑海中。[2]71
那么贝克尔要借由哪种集体记忆来唤醒自己的个体记忆呢?小说《说谎者雅各布》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描写隔离区的日常生活的。显然他试图借由犹太人这一特定的集体来重构自己的个体记忆。为了重构失去的记忆贝克尔参阅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1961年还再一次回到波兰的隔离区找寻素材。尽管如此,小说的内容基本都是作者虚构的。贝克尔通过写作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并试图让这个虚构的故事来填补自身记忆的空白。而写作的过程对其而言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是一个个体记忆重新建构的过程。贝克尔说:“我就像个专家一样写有关隔离区的东西。或许在我的内心以为只要我写得够多就能找回记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或许我已经把自己虚构的东西当成了自己的记忆。”[4]19
三.记忆的空间因素
按照记忆理论,记忆需要空间来承载。但贝克尔在创作时却刻意模糊了这些。尽管在创作中作者是以其自身幼年待过的罗兹隔离区为素材模板的,但文中的隔离区没有给出具体的名字。读者仅能知道,这是波兰境内的某个隔离区,文中仅有的几个地名也是虚构的。这样的处理,使得这个隔离区成了所有隔离区的一个具化的符号。隔离区有铁丝网,高墙,塔楼,岗哨,内部生活条件恶劣,有多条规定,禁令。例如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六芒星章,必须强制工作;晚上8点后宵禁;禁止书报,钟表,收音机;禁止豢养动物;禁止有绿色植物等等。隔离区这一特定的空间即是展示德国人暴力的舞台,也是显示犹太人无力的场所,是犹太人进入地狱般的集中营前的中转站。
因为隔离区空间的限制,文中情节主要围绕几个地点:德军的警察局和专属厕所,米沙的房间,琳娜的阁楼,雅各布的房间和地下室,富兰克福特尔家及其地下室,吉施鲍穆家,火车站。警察局和德军的专属厕所是德国人的专属空间,其中警察局是隔离区内的地狱。在雅各布之前从未有犹太人活着从里面出来过。米沙的房间是他和罗莎享受平凡的小幸福生活的场所。琳娜的阁楼是她的庇护所。雅各布的地下室是雅各布为琳娜展示神奇世界的地方。法兰克福特家的地下室是其藏真正收音机和能让他忆起往昔荣光的物品的秘密处所。火车站是书中多位主要人物工作的场所,是他们交流和传播新闻的地点,它也联通了隔离区和外部世界,是将所有犹太人引向死亡的冥道。前面这些构成了在隔离区时的过去的记忆的承载空间。与之相对的,文中出现的被隔离前以及被解放后的空间则是满目绿色。
小说中除了特定的真实空间外,还有雅各布的谎言为大家虚构的理想空间:没有饥饿,没有死亡的恐惧,充满了希望与幸福。这一谎言建构的空间为隔离区的犹太人带来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
四.记忆的时间因素
记忆除了空间的承载还需要时间因素。哈布瓦赫认为:时间真实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有内容,是否提供作为思想素材的时间。[2]16现在的一代人是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置起来而意识到自身的。[2]43过去是由与己身相关的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回忆过去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而是一个在过去的基础上的重新建构的过程。
《说谎者雅各布》以“我”的回忆开篇。“我”出生于1946年,现年46岁,是一名集中营的幸存者。正如贝克尔所说,幸存者总有一种负疚感,会觉得自己是牺牲了他人的生命才存活下来的。[5]71正因为这种内心的负疚感,“我”一方面想忘却那段苦难的记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强烈的要回忆过去的内心需求,要为死者竖起一座纪念碑。在时隔二十几年之后,“我”开始回忆在隔离区的过去。“我”尽管也是亲身在文中的隔离区生活过,但对于要讲述的故事,“我”的记忆是有缺失的,因为故事主要的消息来源是雅各布,且很多事情是有漏洞的。为了弥补一些漏洞,“我”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又重游了故地,甚至某些地方还进行了测量。为了确定吉施鲍穆被轿车带走时的确切情节,“我”甚至专门拜访了当初带走老教授的其中一位德国人。[6]160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大的漏洞,且找不到证人。“我对自己说,事情大概是这样那样的;或者,我对自己说,如果事情是这样那样的,那就最好,那我就这样讲述,就这样做,好像事情真的与此有关。”[6]30“我”的记忆结合实地调查,再加上个人的想像,使得“我”成功完成了故事地讲述。而讲述过去使“我”消除了负疚感,得到了内心的平静。
文中的“我”也是联系过去与现在的关键人物。小说中故事叙述的时间也同空间一样,也没有具体化。文中仅出现诸如“今天”,“然后”,“又是一天”等非具体的时间表述。這也符合隔离区中禁止拥有计时工具的现实情况。隔离区里的时间不涉及确切的可计数的时间,而是被迫劳动,充满饥饿及死亡威胁的日常生活。
对于文中人物而言还有存于意识中的时间,即隔离前的时间和人们听信了雅各布的谎言后开始憧憬的解放后的时间。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将来的展望对于剧中人物而言都是他们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动力。
五.承载记忆的媒介
记忆的承载除了空间和时间因素,通常还需要具体的意象作为回忆的媒介。这种意象像是开启记忆之门的钥匙。在小说中有两个重要意象成了回忆的重要媒介——“树”和“收音机”。
(一)“树”
对叙述者“我”而言,引起他回忆的具体意象当属“树”了。“树”的意象在小说中有多层次的含义。文章开篇即:“我听到大家在说一棵树……”[6]1树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9岁时“我”从苹果树上摔下来,左手骨折。17岁“我”第一次和一个姑娘躺在一颗山毛榉树下。又过了几年,“我”的妻子卡娜在一颗树下被枪杀。另一个“我”之所以偏好“树”的重要原因就是前文提及的第31号禁令:严禁在犹太人居住区种植任何种类的观赏植物和经济植物。这一点也适用于树木。[6]2为何会有如此禁令,答案不难回答。“树”的意象在文学上历史悠久。比如在西方文化重要来源之一的《圣经》中,“树”就代表了希望,智慧以及永恒的生命。[7]46
小说叙述者在第一次提及雅各布的时候,就将雅各布和树作比较:要是人们看到了雅各布,绝对不会想到一棵树……雅各布个子矮得多……他和我们大家一样胆子都很小。[6]3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使得雅各布成了“英雄”,成了希望的创造者,成了拯救者。首先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在《圣经》里的《旧约》中,雅各布是一个欺骗者的形象,他曾欺骗父亲,欺骗其双胞胎哥哥以扫,滥用上帝的名义。这一形象身上有颇多缺点。但在同上帝的摔跤中他没有输给上帝,且一生对上帝顺服。上帝使其子女众多,并让其改名“以色列”,他的后裔便自称为以色列人。《圣经》中的雅各布既是一个撒谎者,也是一个希望的传播者。他在犹太民族处境危难之际撒谎,使人们振作起来。他撒谎的动机是为了给予犹太人希望和生的勇气。[8]29
尽管雅各布的形象不像树一样伟岸,但在读者心中,这就是一个像树一样高大的另类“英雄”的形象。雅各布为了阻止米沙在车站的自杀式行为,跟其透露他听到的新闻。为了使其相信消息的真实性,谎称自己有收音机。这个消息成功阻止了米沙的愚蠢行动。尽管表面上看这是一起偶然事件,但事实上这也是雅各布的必然行为。在被隔离之前,雅各布就类似于一个心灵安慰者。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谁都乐意到他那儿去,为的是把自身的弱点改掉……人们到他那儿去,是因为去过他那儿之后世界会显得美好一点儿,是因为他说些琐事比其他人说“昂起头来”,或者说“一定还会变好”之类的话更能令人信服。[6]194
雅各布的乐于助人还体现在他收留了八岁的小琳娜。她的父母被运往了集中营。没人愿意领养孤儿,只有雅各布。从米沙试图偷土豆的行为我们能看出隔离区里食物短缺。历史事实是,为了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从1941年12月开始,约两万犹太人被以“去罗兹隔离区外工作”的名义运往了库尔姆霍夫死亡营。[9]30贝克尔的母亲也是死于营养不良。[9]35尽管食物如此短缺,雅各布仍然收养了琳娜,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跟她分享食物,有时甚至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食物给琳娜。
但雅各布也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在日复一日的编撰谎言的过程中会犹豫,会迟疑,会想放弃。如在停电事件中,大家伤心于不能每日听到新闻。但雅各布回复科瓦尔斯基却说,希望能停电20年。且在电力恢复之后他又对外声称收音机坏了。这导致科瓦尔斯基给他带来了一位修理工。面对如此局面,雅各布只得继续每天编制谎言,继续为隔离区的犹太人创造生的希望。其后雅各布又一次不堪忍受重负,向科瓦尔斯基吐露了实情。这又直接导致了科瓦尔斯基因生的希望的破灭而上吊自杀身亡。科瓦尔斯基的死又让雅各布深怀内疚,收音机又继续工作了。
尽管小说中雅各布内心的种种纠结显示出他也只是个平凡人。但总体上而言,雅各布仍旧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是一个像树一样高大的形象。
除了雅各布,书中还有几个角色也用到了“树”的象征。比如心脏病专家吉施鲍穆(Kirschbaum),及其胞姐。Kirschbaum本意“樱桃树”。吉施鲍穆是个声望卓著的外科医生,原属精英阶层,他在隔离区中平易近人,为大家诊疗。对琳娜的诊治过程就能感受到其极富爱心。对雅各布的劝告也是真诚用心。在德军强制要求他去医治盖世太保头目时,他决意要像其胞姐那样一生富有尊严。他平静地跟随德军前往,在快到达时平静地拿出两粒药片,骗说是治胃灼痛的药,平静的服下。到达时,吉施鲍穆已经死亡。他以他的生命为代价拒绝为德军服务。事后当大家得知其死讯时,评价其是个大人物,并偷偷为其哀悼十分钟。吉施鲍穆的姐姐谢绝了雅各布对她的建议,没有躲避,最后也被德军带走,离开时仍然如往常那样富有尊严。吉施鲍穆姐弟的形象一如雅各布,也是文中的英雄角色。
赫舍尔·施塔穆(Herschel Stamm)则是另一个另类英雄的形象。Stamm德语原意为“树干”。赫舍尔原本是犹太教堂的仆役,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即使在隔离区内,也保留着自己的鬓角鬈发。为了隐藏鬈发,一年四季他都戴着顶有护耳的黑色皮帽。每天赫舍尔都会虔诚祈祷。雅各布有收音机的消息在隔离区传开后,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欢欣鼓舞,每天渴望能听到好消息;一派则担惊受怕,深怕被德国人发觉而受牵连。赫舍尔就属于后者。他每天的祈祷内容变成了让上帝毁掉雅各布的收音机。在隔离区断电事件发生后,赫舍尔将断电看成了自己的功绩。但就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普通犹太人,在火车站工作的某日,发现了停靠在铁轨上的车皮里装着要被运往集中营的同胞,他不顾生命危险告诉了里面的人俄国人就要打来了的消息。最终赫舍尔被枪杀。这正好发生在雅各布不堪压力想要让自己的收音机消失的时候。文中写道:收音机尚未被火烧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因为鬈发者赫舍尔,他今天上午冒雨趴倒在两根枕木之间时把它修理好了。[6]112
“树”的意象在文中如同一条红线贯穿全文,它联系起了过去和现在。讲述者“我”看到树就开始回忆往昔,这种不断的回忆最后迫使其开始向人们讲述这段过往的黑暗岁月。在真实结局中,人们被装在车厢里运往集中营,透过仅有的小窗,看到沿线久违的绿树。树在这里又联系起了生与死。
(二)“收音机”
文中除了“树”这一意象外,“收音机”是另一个重要意象。贝克尔曾说过,“雅各布和他的收音机的故事”的来源是他的父亲。父亲在罗兹隔离区认识一个真正拥有一台收音机的犹太人,这个人常为隔离区的人带来鼓舞人心的新闻,最后被盖世太保发现并枪杀了。贝尔克的父亲认为那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建议儿子为这位英雄著书立传。但在贝克尔看来,这样的素材及故事在关于二战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見,故而他对该素材做了处理。这位隔离区的英雄并没有真正拥有一台收音机。[4]5而在最后成文的小说中,贝克尔让主人公雅各布拥有了一台虚构的收音机,每天为大家编纂能带来希望的“谎言”。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剧中人物费里克斯·富兰克福特尔却拥有一台真正的收音机。但当他得知雅各布有台收音机,并经常给大家带来新闻的时候,他偷偷地彻底毁坏了自己那台,免得受到牵连。这一真假收音机的对比更加凸显了雅各布的形象。
六.结语
反映二战犹太人遭遇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小说《说谎者雅各布》却能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为数不多的再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最佳作品之一,这要归功于小说独特的叙述角度及它的语言特色。贝克尔没有选择从重的美学角度来直接写法西斯的反人道和暴力恐怖,而是选择轻的美学角度来描写犹太人在隔离区的日常生活。贝克尔深深了解,一个人的牺牲是一个不幸,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只是一个数字。在他的笔下每个隔离区内的犹太人都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贝克尔用轻快,幽默的笔触来记录这些独特人物的日常生活。从这些日常的事件里,揭露出了法西斯的野蛮,残暴与非人道,与此同时也赋予犹太人以人格的尊严,展现出他们的英雄气概。小说的语言轻快幽默。例如在赫舍尔为了传递消息而被哨兵枪杀的一幕中,贝克尔是这样描写那声枪响的:这一声枪响像是个气球,气打得鼓鼓的,突然啪的一声爆裂了。又像是上帝咳嗽了一声。[6]104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作者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创造出一种含泪的微笑的效果,把悲剧变成了轻喜剧,又使这出轻喜剧成了乐观主义的悲剧。
参考文献
[1]Becker, Jurek: Ende des gr?觟?覻en Wahns, Aufs?覿tze, Vortr?覿ge[M].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6.
[2]莫尔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Kiwus, Karin: Wenn ich auf mein bisheriges zurückblicke, dann muss ich leider sagen. Jurek Becker(1937–1997), Dokumente zu Leben und Werk aus dem Jurek-Becker-Archiv. [M]. Berlin: Aka- demie der Künste 2002.
[4]Arnold, Heinz Ludwig(Hg.): Text + Kritik[J].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Band 116: Jurek Becker. München: Edition Text + Kritik 1992.
[5]Matzkowski, Bernd: K?觟nigs Erl?覿- uterungen und Materialien, Jurek Becker, Jakob der Lügner[M]. Hollfeld: C. Bange 2005.
[6]Becker, Jurek: Jakob der Lügner[M].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6.
[7]Kutzmutz, Olaf: Jurek Becker: Jakob der Lügner[M]. //Interpretationen. Roman des 20. Jahrhunderts, Band. 3. Stuttgart: Reclam, 2003.
[8]Wiese, Lothar: Jurek Becker. Jakob der Lügner[M]. München: Oldenbourg 1998.
[9]L. Gilman, Sander: Jurek Becker. Die Biografie. [M] Berlin: List Tb. 2004.
(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