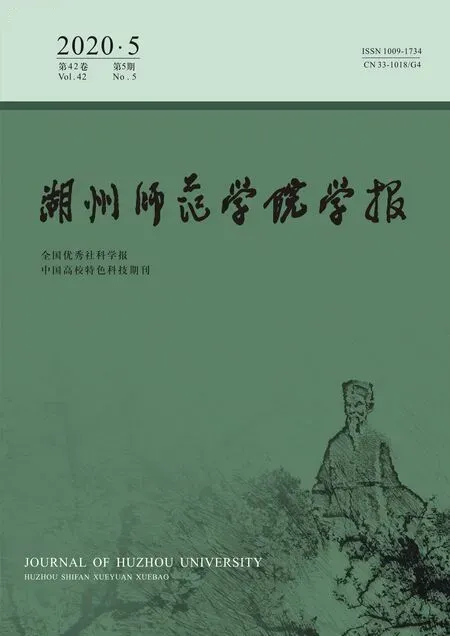日暮乡关何处是:民初清遗民诗歌中的故乡书写*
陈义报
(湖州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浙江 湖州 313000)
传统中国是个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然因宦游、为学、行商等种种原因,士人离乡不可避免,导致中国前现代诗歌中的故乡书写一直绵延不辍,蔚为大观。前现代诗歌中的故乡书写大抵以思乡为主,乡愁灌注其中,其在书写风貌及抒情指向上相沿成习,很少变化。但民国之后,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以及西方现代性思潮的涌入,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故乡书写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现代和现代的鸿沟已然形成。
鸿沟不是一夜形成的,在前现代和现代诗人之间,有这样一群过渡诗人,他们本应归居于桑梓之地,但秉承“民国乃敌国也”的逊清遗民理念,乃成“有乡而不得归者”,苟全于华洋交集、光怪陆离的上海等租界都市;他们的道德指向与审美情感皆停留于传统,但却在中晚年身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等二元对立所生发的撕扯与煎熬。他们就是民初的逊清遗民。关于清遗民与故乡,王国维在《彊村校词图序》中有过很好的论述,他分析了古代至近代士大夫面对故乡的三种方式,一种是“归于乡里”,一种是“乐居游宦之地的山川之美”,然而到了清遗民这里,士大夫们身处乱世,进退失据,乡关无着,城市隔膜,失魂落魄,踌躇愤懑,唯有流聚于北则天津、青岛,南则上海等海滨租界,依托“有朋文字之往复”,于相互构筑的文字精神世界里,聊可托命于万一。
从王国维的分析可以看出,清民鼎革,不仅仅是传统的改朝换代,更是清遗民们安之若素的传统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性的因子已然出现在道德、审美、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清遗民们在前清与民国、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的二元张力中张皇失措、失意彷徨。作为在传统审美中具有情感抚慰和安顿身心功能的故乡,能否在清遗民诗人的笔下焕发出“归去来兮”般的古典田园色彩。本文拟将他们的故乡书写放在民初这一独特历史语境下予以考察,以期描述出清遗民故乡书写中内蕴的心路历程、情感特征及其在中国故乡书写脉络中的位置及意义。
一、现代都市背景与清遗民的故乡书写
故乡到底以什么面目首先闯进思乡者的脑海中,笔者认为恐怕是思乡者对于家乡的风土人情的铭记,这种风土人情不是游览者匆忙的一瞥,而应该是思乡者将自己的成长体验与故乡的风土人情糅合在一起,形成的一幅带有浓厚生命意识的心理图景。民初清遗民大多少时在故乡读书科考,后获取功名后在京城或地方为官,临近暮年,本该和古人一样,告老还乡,栖居桑梓,但辛亥鼎革改变了这一切,故乡成了“归而不得”之所在。正因为人生暮年“归而不得”以及他们与民国内在的紧张关系,故而故乡在他们心目中呈现出从前不曾有过的别样风采。比如王国维,其故乡在嘉兴海宁,辛亥“国变”后随罗振玉避居日本,在日本他以少有的欢快深情笔调写了一组昔日畅游故国的组诗《昔游》,其二写故乡:

王国维辛亥前的诗歌中也曾有故乡的描写,但多悲苦烦闷之音。去国怀乡,故乡以“春融”“秋爽”“微风”“明月”“波暖”的明亮之色和温情的面目抚慰着经历鼎革之变的去国流民,这样的故乡书写也具有了传承古典诗歌故乡书写的情感和美学意味,令人熟悉与舒适。
雅言紫荷花,俗言荷花紫。厥用殖垆坟,不殊豆麻底。名或淆地丁,秋先撒花子。明岁迟归舟,饶侬醉茵徒。[2]948
此诗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沈曾植学者之诗的特色,寥寥数行,就对花草子的别名、特性进行了考证,但对于故乡书写不可能仅仅是考据学意义上的求道问真,而最终落脚处在于“明岁迟归舟,饶侬醉茵徒”。故乡因着这种审美意义上的乡风民俗,从而由地理实体进入精神归宿的层面,惘然中带着甜蜜的的回首与向往。

西成一扫黄云痕,风露气上苏秋根。参差又见新苗出,玉立平畴添稻孙。语家著意护田稚,长养关天半人事。他时捃拾得升斗,邀邻共醉蒸作酒。[3]122


当然,清遗民中有一些诗人由于是官宦世家,从小就基本脱离了农业劳作,比如陈三立、沈瑜庆等。但古代农本思想深厚,所以所有的故乡书写基本都离不开对乡土的描述,即使这些清遗民没有劳作经验,但一旦进入故乡书写模式中,春种秋收之类的想象必然出现。比如沈瑜庆,沈葆桢之子,名门之后,虽对乡村生活没有体验,因为他家“世以笔墨糊口”,他又“守先人遗训,亦未敢以官禄置田宅”,“未尝一日亲农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2]951但也作了近十首田园秋收绝句,诗中虽缺乏具体的劳作描述,但对乡村生活还是感同身受,充满了浓浓的民俗风味。
乍一看,清遗民的故乡书写似乎在审美情感与表达方式上与前现代的故乡书写并无二致,但如果将这些书写放入到清遗民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这些书写呈现出复杂的色调和意味,也就是说,文本虽然风貌相似,但书写者的历史语境与书写心境已然不同,知人论世,故而文本内核的精神世界早已发生巨变。
清遗民在晚清大多有功名,社会地位比较高,然“辛亥以后,通都小邑,桴鼓时鸣,恒不可以居”[4]101,成为“夫有乡而不得归者”,大多流聚上海、青岛等租界,而上海等海滨城市具有乡村完全不同的气质,陈三立写道:
当国变,上海号外裔所庇地,健儿游士群聚耦语,睥睨,指画,造瑞流毒以为渊薮,而四方士大夫雅儒故老亦往往寄命其间。喘息定类,其忧悲愤怨,托诸歌诗,或稍缘以为名,市矜宠。[5]986-987
对此,从日本归国就寄居上海的王国维也有同样的看法:
二地皆湫隘卑湿,又中外互市之所,土薄而俗偷,奸商傀民,鳞萃鸟集,妖言巫风,胥于是乎出,士大夫寄居者,非徒不知尊亲,又加以老侮焉。[4]101
对于清遗民们来说,上海等海滨城市是不友好的,这种不友好不仅是清民鼎革,他们曾经的权势和社会地位随之消失,更是他们由熟悉的四民社会被抛入一个完全异质的物质性存在——带有极强人为性、强制性、陌生性的现代城市,周遭环境与自身境遇的变化便更加触目惊心。[7]9他们自己也哀叹他们“残生只合入山迁,那更移居向还壖”。[6]370况且,这一代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徘徊者,不像后来聚集上海新一代的职业文人,从一“诞生”就是属于城市,也不像后来的学者,不论是执教新式大学,还是栖居报刊出版,与城市的亲合度同样在不断增加。与之相比,清遗民们是由漂游悬浮的“未定项”强行被塞入城市,不得已成为他们自我指称的“海滨流人”,这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冲击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7]9对于乱离时代羁栖租界的感受,遗民们大多戚戚然,典型于陈三立,其在《除夜》诗里坦露心声:
亘古存残夜,孤呻有小楼。灯扶浆担去,埃杂海光流。逃世吾宁及,攀天梦亦休。夷歌暖杯酒,摇入万方愁。[5]326
“夷歌暖杯酒,摇入万方愁”,此愁深入骨髓,无以排解,是治统已去、道统崩溃的特定历史节点上前路茫茫、后退无着的大忧大愁,这恐怕是逊清遗民独特的历史感受。遗民由审美的、传统的、熟稔的“山林”进入物质的、现代的、陌生的“城市”,这恰与前人相异,也与前代遗民不同。前代遗民,比如王夫之、方以智沉迷于“荒山野岭”,傅山、顾炎武一直“蹇足途中”。固然在历史上,文人与文学想象早已与“城市”结缘,但与“现代”都市的相遇,无疑还是头一遭。在前现代中国,对于“学而优则仕”的文人而言,更鲜明的并非“城市”与“乡村”的对峙,而是“在朝”与“在野”、在“庙堂”与在“山林”的分别。“在朝者”进入城市,毋宁说是进入朝堂。对在野者而言,不论是南宋词人流连青楼,还是明末文士齐聚声场,“都市”在某种程度上,仍具有“江湖”的意味。文人游走于瓦肆、酒楼,“小红低唱我吹箫”,眼中心中所及,仍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自然性景观。可以说,对于整个前现代的乡土中国而言,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在近现代中国,现代都市的崛起则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同时伴随着“士农工商”秩序层级的崩解。上海作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大都市,这一点尤为明显。[7]9
在异质性的沪上,故乡所代表的乡村就是代表着审美、传统、道德的一端,引得遗民思之念之,进而采取了“仿故乡”“仿乡居”的话语策略。通过仿写,都市宛若乡村,沪上宛若故乡。沈曾植明明身居沪上,却徜徉于《山居图》中自设的乡村语境中:
昔余初至此邦,尝作《山居图》寓意:以途人为鱼鸟,阛阓为峰崎,广衢为大川,而高囱为窣堵波。[2]453
在遗民们看来,“途人”“阛阓”“广衢”“高囱”都是异质性的存在,而“鱼鸟”“峰崎”“大川”“窣堵波”才是身心皈依之所在,只有这些才能满足他们对于故乡、田园、理想、盛世的期待。
类似的表述还有陈夔龙作《梦蕉亭杂记》,其《自序》开头一派太平时节亲情融洽的乡居时光:“虫声四壁,皓月在天。庸庵居士与儿辈纳凉于梦蕉亭花阴深处。”然而“仿乡居”终究是仿写,花近楼也罢,梦蕉亭也好,终究不是少小耕读的贵州老家,于是伤逝之情顿起:“默数年华,忽忽已六十八甲子矣。后此之岁月如何,天公主之,诚不敢自料……时宣统三年后甲子年七月十三日也。”[8]78无限低徊与感叹之意、衰飒与惆怅之情溢于笔端。于此背景下,他们的故乡书写无论如何都没有了前现代诗歌中的那份纯净与安详,而是充满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的紧张与对立。
一般说来,前现代的乡愁是一种基于时间流逝和空间阻隔的乡恋,多表现为羁旅情思、离别之苦,故而无论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是“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都是一种可以把控的、具有线性特征的乡恋和乡愁。在前现代中,故乡,以其原初性的农业文明形态安抚着诗人的心灵,这是传统的、审美的、浸润于漫长乡土社会中的诗人的典型记忆,这些记忆与前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一起,构建了一个个令人迷恋的、有着田园意象般的故乡书写符号。但时至民初,清遗民即便在思想、情感、审美上想留在前现代的故乡书写中,然而历史语境已然改变。可以说,从他们开始,人与其故乡的古典式的和谐亲密的关系开始一去不复返了,开始从文化史和心灵史上真正领略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内在意蕴,其故乡书写也呈现出复杂的意蕴与斑驳的光谱。
二、遗民身份与清遗民的故乡书写
孝为中华伦理文化之核心。孝之为二,一是对于在世的父母或长辈的敬顺,一是对于过世父母或长辈的悼念与祭祀。而扫墓是后者的一种集中体现方式,在古代士人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文化强调叶落归根,故而父母或长辈去世后一般都安葬在故乡,因此扫墓与故乡就有了天然的联系。扫墓的过程不仅仅是沟通血缘、践行孝文化的过程,更是扫墓者由此体察故乡的时机。因此,扫墓书写可算作故乡书写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类书写中,最为痛彻心扉,情真意切,当属陈三立。陈三立乃江西义宁人(今修水),但因父陈宝箴常年在外为官,故陈三立随父辗转多地。1900年陈宝箴去世,墓地在南昌西山,是为“崝庐”,此地距离义宁不远,其祖母、伯父、先妻罗夫人、胞弟陈三畏均安葬于此,故而此地成为其“烦冤茹苦、呼天泣血之所”。鼎革前,陈三立基本每年清明都到西山扫墓。鼎革后,陈三立由南京避住上海,国内形势一放松,他就马上到南昌西山凭吊亡父。可以说,陈三立的“崝庐”书写就是故乡书写,这种书写中包含着对先父及其他亲人的思念、过往的追忆、鼎革的悲戚以及人世浮沉、时光荏苒的慨叹。对于“忠孝传家世所尊”的陈三立而言,“崝庐”就是其故乡的核心所在。“四海无家对影孤,余生犹幸有江湖”[9]97,一年一度的“崝庐”扫墓,其实就是他与故乡(父亲)的一次亲密邂逅与精神接引。陈三立曾写下许多痛彻心扉的谒墓诗,如《崝庐述哀诗五首》其三:
堵竹十数竿,杂桃李杏梅。牡丹红踟躇,胥父所手载。池莲夏可花,棠梨烂漫开。父在琉璃窗,颏唾自徘徊。有时群松影,倒翠连古槐。二鹤毡毽舞,鸣雄漫惊猜。其一羽化去,瘗之黄土堆。父为书冢碣,为诗吊蒿莱。天乎兆不祥,微鸟生祸胎。怆悢昨日事,万恨谁能裁。[5]16
“父在琉璃窗,颏唾自徘徊”,回忆中温情满怀。陈宝箴1900年“以微疾卒”,享年70,可谓高寿。时年陈三立48岁,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按理说,父高寿离世不应如此悲切,但是父亲的死仍然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和内心痛楚,其诗歌中反复呈现出浓重的“失怙”之情。这种“失怙”蕴含着深厚的家国隐痛,这里的家就是父子亲情以及由此漫延充溢的成长的精神故乡,国其实就是清民鼎革以及由此产生的传统士人精神文化凭依的轰然倒塌。民国后甲寅年(1914),陈三立“世变”后第一次从沪上返西山扫墓,沉郁悲愤之情更为浓烈,写下了《崝庐三首》,其一曰:
久客归敝庐,有如打包僧。空宇存几榻,照壁凄龛灯。凝尘满鼠迹,挂断青丝绳。旧佣挈男去,薪脚堆相仍。舟车载病奚,僵卧侪冻蝇。呻吟万山腹,断续雌鸱膺。量水调散剂,味谁辨淄渑。出入自操作,仰见白月升。墙根风啸竹,疑有鬼物凭。拒户橐驼坐,吾其悟大乘。[5]406-407
陈氏诗歌,不管辛亥前后,皆有萧索荒寒、忧愤郁勃之气,但崝庐之诗更多一种沉郁哀恸之情。诗中尽是“空宇”“凝尘”“鼠迹”“青丝”,可见故乡凄败难堪,亲人阴阳永隔,而这一切皆由“国变”“世变”而起,令陈三立悲痛不已。
平局苦局促,未厌小园小。漂泊返幽栖,弥爱林塘好。开帷省图史,蛛网纷未扫。堆案横鼠迹,不意拾残稿。樱桃子垂檐,红紫杂花绕。海棠百年物,双干惜中槁。独存安石榴,萧然一遗老。春风苏病树,生意盎庭草。坐对散郁陶,幽情语时鸟。[3]114

陈曾寿年纪相对上述遗民较为年轻,辛亥鼎革时,其才四十多岁。陈乃湖北人,鼎革后,1915年其第一次回到故乡扫墓,写了《乙卯四月归里谒祖墓》:
中载重来祖墓山,老僧成塔隶为官。更无煮笋烧茶事,已过花时问牡丹。
惭谒家祠第一回,磬声惊是梦中来。堂堂陈氏非王腊,可鉴涂生怜国哀?[10]71
诗写得沉痛而深情,既抒发了对现实的不满,又饱含着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大部分清遗民都曾有过类似的上冢经验。可以说,这种情感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集体性情感。它包含着深刻的宗亲意识、血缘感情和乡土认同,是中国人理解自身和生命渊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扫墓,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其不仅是血缘深情、乡关之恋,更为显见的是所谓的家国之痛。墓中亡人、故乡残景更容易激发遗民对清民鼎革所引发的四维沦丧、纲纪废弛的痛心与哀叹。故而扫墓诗一面写故乡及亲人,一面顺理成章地引申到“换世”之悲,因此他们的故乡扫墓诗皆充溢着悲切之情。比如沈瑜庆写道:“奔湍十里傍山行,乱石澄沙作镜清。肠断父兄携我处,白头来此听溪声。”“别墓饥驱事可哀,梅亭松柏记重栽。两行家国仓皇泪,新自祟陵捧土来。”[11]152沈曾植诗云:“寒食王周三月春,还家上冢越流人。”“双衔家国终天恨,不转山河坏劫悲。”[2]791对遗民而言,长眠于墓中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大多数与前清政治有很密切的关系,许多人还是政府高官,比如沈瑜庆之父沈葆桢和外祖父林则徐、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沈曾植之高祖沈廷煌和祖父沈维鐈都曾出任要职,他们家族的历史在清朝的历史之中嵌入甚深。因此,祭扫先人庐墓就不可避免地触发了家国之痛和历史兴亡之感。
传统中国,历来是家国同构,因此,对于清遗民来说,故乡,推而广之,其实与故国同义,故国就是扩大版的故乡,而京城不仅是故国最显在的象征,更是许多清遗民年轻时求学问宦之地,因而辛亥后他们对于京城的反复吟咏也就具有了故乡书写的意义。他们基于自己的现实处境与“五代式民国”的历史现实认知,在诗歌中对旧时帝京的“盛世景象”展开想象和书写。在他们的书写中,帝京已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实体,而是一个带有强烈情感倾向的经想象和回忆建构的文化风景,是一种与他们身历之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的“王道乐土”,更是他们心目中道德、情感和审美等几重叠加的精神故乡,于是帝京在他们笔下有着别样的迷人之处:
先帝龙飞之二载,我偕计吏初游燕。一击不中狂呼酒,日日长安市上眠……散衙有时谋一醉,不惜三百青铜钱。天桥酒家尽识我,自惭才调非青莲。……天维地轴几翻覆,眼中沧海成桑田,坐中俱是望京客,一片心常北斗悬。[2]932-933
重黎生昔共登险,据地坐想姚朱歌。后来人事多复多,二李二王盛黄载酒时经过。[2]930-932
自别京师三十载,江湖落魄天无梯。当年计偕二三子,一趁薄醉寻轮蹄。……尔来铜驼鼠荆棘,承平故事过者迷。[2]935
也难怪遗民们对京师如此念念不已。在京师,他们过着士大夫最为理想的风雅生活,诗酒雅集,切磋学问,品评时事。他们在京师各大胜迹,诸如宣南万柳堂、崇效寺、慈仁寺、法源寺、长椿寺、报国寺、松筠庵、陶然亭等流连忘怀。这一青壮年的美好韶光与帝国的中兴之治交融在一起,犹令晚来流寓海滨、故乡无着的遗民们生出今非昔是之感。“谁知少年乐,一去不可复。到今四十霜,历历空在目。”[12]1214-1215在遗民的吟咏里,帝京、故国与故乡边界无存,融为一体,帝京是故国的回忆标的,更是遗民们故乡书写的精神内核,它们在时间上同属于过去,对它们的叙述都属于回忆性的追溯。这种回忆既是生命体验方式,也是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故乡超越了地理学和空间意义上的狭窄范畴,在居住和情感的维度上,加入了个体的实践体验、情感体验和精神体验。对遗民们来说,故国与故乡融为一体但过去和当下泾渭分明,过去令人沉迷,当下令人哀恸。遗民们对故乡帝京的念念不忘,事实上是对“失去”的一种执迷与眷恋,潜流着他们历经世变彷徨于无地的困惑与焦灼。[13]36遗民之遗,本身就是指向过去的,故而遗民们的诗歌,非唯故乡书写,可以说所有书写都是回忆式的,回忆是他们的叙事起点和情感起点。
三、独特意义
清遗民诗人由于历史境遇的不同,已经与前现代诗人们的故乡书写拉开了距离。受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思想的冲击,故乡已然具有了某些不一样的色彩和意义。前现代诗人思乡的终点是叶落归根、回归故乡,而清遗民则不然,思乡之情虽仍强烈,但历史与时代却赋予了他们无法归、不愿归的境遇。前现代诗人诗作中的怀乡仅仅是因为远离家乡和亲人,抒发的是一种离别之苦、思乡之情,是非常个人化的一己之愁绪,而清遗民与之相比,多了“道出于二”(2)语出王国维,他认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见王国维《论政学疏稿》,《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版,212页。罗志田联系近现代史实,对此有翔实论述,见其《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焦虑,开始面对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等二元对立产生的撕扯与冲击,从而以一种更高、更广泛的视角来对故乡和自身进行体察与审视,不管清遗民们自身承认与否,他们的故乡书写相对而言都有了一种现代意味。
但与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相比,清遗民们的故乡书写又仅仅是一种现代萌芽状态。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是一种真正的现代性书写。在他们的书写中,那种带有古典色彩的原初性的美感和价值世界渐行渐远,还乡者欲有所留却无可奈何。一方面,他们以启蒙理性解构或祛魅故乡所具有的伦理与审美的乌托邦形象,显示着现代性洪流对传统世界的冲击和断裂。基于此,现代个体丧失了前现代中所常有的稳定和依托,面向故乡抒发的不再是温暖和单纯的怀恋之情,而更多是面对故乡的哀婉和忧郁,愤懑与失落,即为“怨乡”。另一方面,古典的美,即一种确定性的美又时时吸引着他们,使得他们频频回顾,是为“恋乡”。现代作家常常将“怨乡”和“恋乡”两种情感扭在一起,结果就是他们的故乡书写呈现出一种因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无家可归”,而这是清遗民所不具备的。[14]44
清遗民悬在前现代诗人和现代诗人中间的地带,既回不到前现代的过去,又无法进入现代性的未来。虽然他们仍然用古典的诗歌进行表达,但他们已经身历或感知到即将到来的历史巨变。他们以遗民特有的回忆姿态想在古典美学中寻求慰藉,但他们脚下的现代性图景正急剧展开。他们无法像他们的前辈,如明遗民那样,“不入城”“不入市”,有着完整的儒家道统可以庇护。从他们开始,人与其出生地亲密和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故乡不仅仅是人生那个“最初的时刻”和“第一声的哭处”,更是一个带有强烈情感倾向的经想象和回忆建构的审美渊薮和文化风景。面对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前清与民国,他们踌躇、彷徨,是真正喟叹“日暮乡关何处是”的一代。